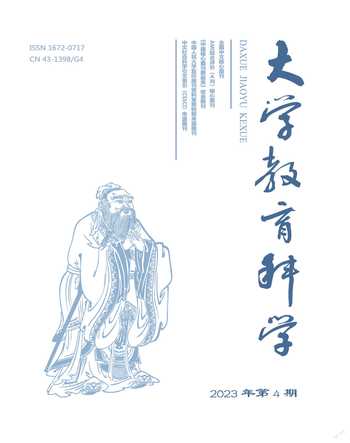施萊爾馬赫的大學觀及其對現代大學的影響
賀國慶 楊嘉晟
摘要: 施萊爾馬赫的大學觀主要體現在他為創辦柏林大學而撰寫的《關于德意志大學的思考:附論將要建立的大學》一文中。在該文中,施萊爾馬赫全面論述了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學的形象:這種大學離不開國家的支持,但也要盡可能謀求獨立于國家;大學教育的目的是通過科學教育喚醒青年理性之最高理念——認知;哲學院是大學中最高級的學院,學生和教師都應該植根于哲學院中;大學師生應享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學術講座和專業研討課是最適合大學的教學方法。在普魯士大學改革的大背景下,施萊爾馬赫積極參與柏林大學建校計劃,并且作為洪堡設立的建校委員會委員,能夠直接在政策制定與執行層面上將部分理論思想真正融入辦學實踐中,對柏林大學內部組織結構、學院架構、授課方式的塑造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不僅保留了德國大學的傳統形式,還為其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令柏林大學的模式與建校思想成為了現代新式大學發展和改革的重要原則與典范。
關鍵詞:施萊爾馬赫;大學觀;現代大學;影響
中圖分類號:G519?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0717(2023)02-0083-08
一、引言
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8-1834)是德國著名的新教神學家、哲學家和古典語言學家,他對普魯士宗教、生活和文化的影響極大,被推崇為“現代神學之父”。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施萊爾馬赫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對大學的論述經洪堡吸收借鑒,融入柏林大學的辦學實踐中,對現代大學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施萊爾馬赫1768年生于普魯士的布雷斯勞,1782年入虔敬派摩拉維亞兄弟會舉辦的學校學習,1785年又入巴比的兄弟會神學院學習。他在1787年升入哈勒大學學習神學之余開始研讀康德的著作,并在古典學者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的指導下,攻讀希臘經典作家的作品。大學畢業后,施萊爾馬赫曾擔任家庭教師,并開始從事傳教活動。法國大革命爆發后,他贊成大革命的意義,譴責專制政治,反對教會和國家的聯系,主張國家不應過問臣民的宗教信仰。1797年,施萊爾馬赫在柏林結識了早期浪漫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弗·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兩人結下了深厚友誼,從此施萊爾馬赫也被視作浪漫主義的神學家。1804年,施萊爾馬赫接受哈勒大學的聘請,任神學院副教授兼大學牧師。在哈勒大學任教時,施萊爾馬赫已開始關注大學改革問題,盡管他自身并不富裕,但常常免收學生的聽課費,并且全身心投入到教學之中。1807年,哈勒大學被并入拿破侖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王國,愛國的施萊爾馬赫回到柏林。
早在1803年,普魯士大臣拜姆(K.F.Beyme)就曾向著名學者征文,討論在柏林創建新型高等教育機構的可能性。耶拿戰敗后,拜姆立即向費希特等人征求創辦新型高等教育機構的建議。施萊爾馬赫聞訊后不請自到,精心撰寫并提交了《關于德意志大學的思考:附論將要建立的大學》一文。洪堡就任普魯士文化和教育廳廳長后,邀請費希特和施萊爾馬赫為洪堡籌建新大學出謀劃策。由于施萊爾馬赫的方案較費希特的方案更為溫和且更為切合實際,因而得到了洪堡更多的青睞,也更多地被納入到柏林大學的辦學實踐之中。
柏林大學開辦時,施萊爾馬赫被聘為神學教授和神學院首任院長,1815~1816年出任柏林校長。
二、施萊爾馬赫的大學觀
(一)論學術組織和國家的關系
施萊爾馬赫將致力于科學教育的學術組織分為三種,即學術性中學、大學和科學院。這三類組織與國家是無法分離的,“隨著它們不斷發展,必然要求更多的資金和不同類別的工具,要求從合作者那里獲得更多的權限,以此能夠通過合法途徑與作為其合作者的其他組織進行來往,而這些無疑只能通過國家獲得;因此人們也要求國家尊重那些為科研目的而聯系在一起的人……要容忍他們,庇護他們。”[1](P4-5)此外,他認為國家還要給其成員一些適當的特權。
國家為什么要容忍、庇護學術組織的成員呢?施萊爾馬赫認為,“國家其實也明白,知識乃至科學是富有教益的、使人獲益匪淺的。無論其疆域有多大,無論其為保全自身獨立的作為是否合乎公義,只有浩繁的知識才能保證國家的存在。”[1](P8)為了促進知識和學術的發展,國家就會支持那些學術組織的發展,“而倘若它們還沒有被創建起來,那么國家便會自己去創建;由于學術組織也有受國家保護與支持的需要,因此它們兩者便會致力于相互理解,達成一致。”[1](P8-9)
施萊爾馬赫所處的時代,德意志諸邦國各自為政。出于利己之心,統治者希望其支持的學術組織僅局限于自己的疆域之內,他們擔心蒸蒸日上的學術組織對國家漠然不顧,甚至對別國機構持有好意,以及對本國臣民的思想產生不利的影響。施萊爾馬赫說:“倘若這些邦國彼此間保持著一種確切的關系,這無疑是明智可取的;但倘若它們想將各邦國的科研機構僅僅是為己所用,這無疑是愚蠢的。”[1](P11)“如果一個德意志邦國想要連同它的科研教育機構一道閉關自守,那么便再也沒有什么事情能夠比這還要怪異,比實現共同利益所要求的更為遙遠了。”[1](P11)“既然學術教育能夠教人謹飭審慎,將狹隘短淺的狂熱與偏見洗濯盡凈,而又不為私心之利所蒙蔽,那么難道除了通過盡可能廣泛地使之發展普及外,還有什么方法能夠最終明確而不帶個人情感地決定這種割據分裂的局面還會持續多久,又將何去何從?”[1](P12)
施萊爾馬赫說,國家從自身的利益出發,認為科研機構必須被領導與管理,因而將它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國家的統治者有清楚的認識,即使“國家必須由有識之士統治”的要求不被接受,但國家與學者們必定會更加團結一致。然而,國家常常也會對學術組織做出錯誤的干預,迫使學術組織一方面力圖使自己擺脫國家的權力與規定,一方面又試圖增強自身對國家的影響。憑借這些方法,他們始終在謀求盡可能獨立于國家。[1](P15)
對國家而言,政府應任由科學自主獨立地發展,任由學者自主管理學術組織的一切內部機構,而國家本身僅保留財政管理、警方監督以及觀察這些學術機構對國家政務直接影響的權利。施萊爾馬赫不無擔心地說:“國家若基于錯誤的擔憂而制定政令,從而助長了致力于傳揚科學的學者之間的那些誤解,那么學術性中學將變得輕浮草率,大學里的主業將被大量無關緊要的瑣事壓得透不過氣來,科學院也將因其工作范圍僅僅局限于那些具有實際用途的事物而不斷遭人鄙夷。久而久之,國家便親手拋卻了科學研究帶給它的最基本的益處,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可能會愈加缺乏那些能夠理解偉大之物、實現偉大事業、以敏銳的眼光發現一切錯誤之根源和內在聯系的科學人才。”
(二)論大學教育的目的
施萊爾馬赫認為,學術性中學是大師名家與學徒齊聚之地,大學則是大師名家與滿師的學徒相聚之地,而科學院則是大師名家云集之地。這三種學術機構既是彼此聯系的機構,也各具不同的意義。
學術性中學以獲得知識為主導,它完全是體育訓練式的,即鍛煉人的力量。學術性中學接受稟性好讀、天資聰穎的少年。施萊爾馬赫說:“判斷某人是否適應接受高等教育的依據有二,其一是某種獨特的才能,即使之能夠立足于某一單獨知識領域的天賦;其二是對一切學問之統一與普遍關聯性的全面理解,是一種系統性的抽象思維。如果某人要成為杰出人才,就必須同時具備這兩種要求。”[1](P24)學術性中學的任務就是對天賦與學術思維施加影響。“一方面,學術性中學必須孜孜不倦地傳授講解全部知識內容的要點概況,使每個沉睡的天賦之人覺得某種事物對他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學術性中學也必須格外強調突出那些很早便體現出整體與關聯性的科學形式,即同時也是所有其他知識的一般輔助工具的事物,并孜孜不倦地對其進行闡釋講解。出于這種原因,學術性中學最主要的課程無疑是文法及數學。我想說,它們是唯一能夠以學術性的方式來傳授的學科。與此同時,學術性中學必須在教學方面訓練所有思維能力,使其彼此界限分明,不同功能也能清楚地被認識到。此外,學術性中學還須致力于增強這種能力,使各種能力都能輕而易舉地掌握某一現存的事物。學術性中學的目標即在于,通過最簡單、也最穩妥的教學活動使上述兩方面結合起來。”[1](P25-26)
科學院是學術大家的集合地。施萊爾馬赫強調科學院的任務是發表作品,“但不是那些篇幅巨大、包羅萬象甚至具有革命性的書籍,而是文集。其中每篇文章應闡明尚未被研究的主題,闡述自己的發現、發表或檢驗新的方法。因為科學院的任務便是通過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來促進已經具有一定規模與基礎的學科的發展,而它每篇作品的分量越重,一致性越強,科學院便會獲得更多的功績。”[1](P29-30)
那么處于學術性中學和科學院之間的大學又是什么呢?施萊爾馬赫指出:“學術性中學只傳授知識本身。籠統說來,學生對知識本質的理解、對學術思維的理解、創造力與自主推論的能力,學術性中學只能試圖初步激發他們的上述幾點能力而不會去培養。而科學院卻要求其成員已具備了上述條件。”[1](P31)大學的基本職責則是孕育與教養。“青年時,人借助知識的基礎及自主學習而為科學受教;成年時,他們則在朝氣蓬勃、精力旺盛的學術生活中自主研究,擴展知識的領域,或將其耕耘得更好;大學如此便在青年與成年之間架起了過渡的橋梁。”[1](P32)施萊爾馬赫說,大學的任務就是“去喚醒那些較為高尚且具備一些種類知識的青年人心中的科學理念,幫助他們在各自格外想要投注心力的知識領域中掌握這種理念。使他們擁有如此之品性,即以科學的眼光看待一切,不是孤立地觀察每個單獨的部分,而是觀察它們之間存在的最為緊密的科學關系,并將其置于一個更寬廣的關系之中,且始終不脫離知識統一與總體的根本;使他們學習能夠在每一種思考中意識到學術的基本準則,借此在自身之中逐漸塑造出自主研究、發明與展示的能力。這一切均是大學的工作”[1](P33)。
施萊爾馬赫進一步解釋了為什么大學學業短于中學學業。他認為,這并非在于“大學生在大學無需包羅萬象地學習各科知識,所以也不必耗費更多時間;而是由于他們可以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學會如何學習,由于他們在大學中所度過的無非只是一個片刻,實際所完成的只有一項任務,即喚醒‘認知這一理念——它是理性的最高狀態,并將其作為人的基本思想準則。”[1](P34)
施萊爾馬赫堅決反對“分別設立大學和高等專門學院,將那些能夠接受最高等之教育的人與那些適合于一個較低層次的人區分開來”的想法,他認為這種想法對于每個積極參與培養青年之事業的人而言都是駭人聽聞的。“人們應當讓那些杰出的人與平庸的人一同在大學中接受為塑造青年自身之學術生涯而安排的重要檢驗,若他們未達到最高之目標,他們中絕大多數人會主動將自己定位于忠實且勤勉的勞動者這一較低的層次上。而學術機構卻極其需要這樣的勞動者,因為那些少數的真正占主導地位的創造之人可能需要許多成員參與工作。為此,大學也須同時承擔高等學校之角色,以便促進那些主動放棄追求科學之最高榮譽、卻仍對其大有幫助的人的繼續發展。……他們雖然不具有這種更為高等的學術思維,卻仍因其受過學術教育與一定知識儲備能夠對國家有所幫助。所以,國家出于這種原因也必須致力于使大學同時扮演著高等專門學院的角色,涵蓋一切對國家服務有用的知識中首先與根本的學術教育相關的事物。”[1](P53-54)
至于有人希望廢除“大學”這一形式,以各專門學院直接對接普通高級中學,施萊爾馬赫認為這將造成極為不幸的后果。“其作用便是對最高等、最自由之教育與一切學術思維的壓制,它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在所有專業中,一種機械重復式的特征與一種可悲的狹隘將變得愈加嚴重。如果那些建議我們將所有大學轉型與拆分為專門學院的人不假思索便采取行動,或者沾染了那種非德意志的墮落思想,那我們無疑便可認為科學事業在倒退,精神思想處于沉睡狀態。就如同那些國家,大學的形式已自我消亡,抑或盡管政府并非加以妨礙,但真正的大學卻沒有誕生,一切皆以學校之形式而存在。”[1](P56-57)
(三)論大學學院
傳統大學由神學院、法學院、醫學院與哲學院組成,施萊爾馬赫說:“根本上的大學,就像學術組織想要創建的那樣,看起來似乎只存在于哲學院中,而其他三所學院相反只是專門學院,它們要么是由國家建立的,要么至少被國家更早更全面地納入其控制之下,因為它們與國家的根本需要有直接聯系。哲學院則相反,正如學術組織對國家而言也只是私有機構而已,哲學院對國家而言起初也只是私人社團罷了,也僅僅因科學的內在所需以及作為其他學院教職人員的輔助而順帶得到發展,因此哲學院在四個學院中的地位是最低的。”[1](P72)
施萊爾馬赫身為神學院教授,卻肯定哲學院在大學的地位和價值。他說:“如果一所大學誕生自學者間自由的聯合,那么現在匯集于哲學院之中的一切將自然而然地占據最高地位,而其他那些國家與教會懇請與哲學院聯合的院系只會占據次要地位。”[1](P76-77)在施萊爾馬赫看來,哲學院是最高級的學院,真正統御著其他學院。因為,無論所屬哪個學院,所有大學成員的基礎都必須植根于哲學院之中,所有人首先都將接受哲學院的檢驗,并被它接受。倘若學生們一開始就被允許進入其他任何一個學院,那么這無疑是有害的。施萊爾馬赫希望人們能夠認識到,“把青年們送入大學就是為了學習。如果他們能夠用一年時間來牢牢掌握基本原則,并獲得對所有真正的科學學科的概貌,那么這些時間就不會白費,他們的思想、熱情與賦能將在此期間得到最為穩定堅實的發展,他們將確實可靠地尋找到正確的職業,并且享受到這種獨立尋獲的巨大優勢”[1](P79-80)。
不僅是學生,所有大學教師的根基也應當扎根于哲學院中。“雖然有的教師并非隸屬于哲學院,但作為特別的教師有責任承擔某一理論分支的內容,并且經常需開設關于純粹學術領域且與自身學院毫無直接關系的講座。只有如此,人們才能夠在外在形式上確保哲學學說與實證科學間具有生命力的連接得以維護下去;如果缺少了這種紐帶,那么那些學說也將在大學中毫無容身之地。那些自覺沒有精力與興致在其他領域內——或是純粹哲學,或是道德倫理、哲學歷史學,抑或語文學——取得屬于自己的卓越建樹的法學或神學教師,確實理應受到嘲諷并被開除出大學。”[1](P80-81)
施萊爾馬赫十分強調各學院的聯合,他認為大學必須普遍追求避免將自身劃分得過于冗繁與明確,避免將每位教師嚴格局限于其自身學院之內,抑或將教師完全局限于該學院中某種特定的專業上。他說:“為什么要阻止一位教師涉足另一學院的領域呢?所有學院都彼此相連,在許多點上多有交集,因而并不缺乏從一所學院涉足其他學院的動因。一位學者若真正利用這種機會,并且不滿足于僅僅為了自己的學業而從他處汲取所需,那么當他決定進行公開演講時,他無疑會在陌生領域獨出機杼、別有見解。學院之間因它們各自的領域而互相嫉妒,這無疑是陳腐可笑的。”[1](P82)“正因如此,一所大學真正的精神在于,在每個學院內也保證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規定講座課先后順序,將整個學科領域明確細分為若干部分,這都是愚蠢的……相反,如果每門分支學科由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在其他學科領域投注更多精力的人重新加工修改,那么這便會注入新的活力。”[1](P83)如此看來,施萊爾馬赫的觀點,與今日大學提倡的學科交叉、學科融合與跨學科研究何其相似。
(四)論大學的學術自由
施萊爾馬赫將大學視為由學者們自由聯合而誕生的私人團體,自由聯合是大學最自然也是最美妙的一方面。他說:“也許存在有這樣的事業,即使為其工作的人僅僅是受外界的強制與驅使,該事業仍會發展。然而科學事業絕非如此,它只能夠借由興致與熱愛而存在,若是缺少了興致與熱愛,即使有最完善的外在準則與章程,它們所能做到的永遠只是金玉其外而已。”[1](P92)
在大學教師的選聘上,施萊爾馬赫主張大學必須扮演重要的角色。當時德意志大學的實際情況是:“政府通常將此職務的任免問題交由一名舉足輕重的官員負責。如果他具備足夠的施政能力,對該事業擁有真正的熱忱,那么他便不會無法將優異之人召集起來;然而,若他的繼任者是錯誤的人選,那么他也會糟糕地推選一系列無足輕重之人,而非出類拔萃之人。”[1](P93-94)同時,施萊爾馬赫也不贊同將選聘的權力完全交給大學。他說:“就如同在耕地上只播撒由它自身所產出的種子,便不會結出累累碩果;或如同在那些只互相來往與通婚的家族中,墨守成規,思想僵化,一所大學若也如此,他將變得愈加片面與干涸。”[1](P96)選擇教師最好的辦法是由國家委任的學監和大學及其學院共同協商決定。他建議:“對于最為嚴格的保留其學術特性的教職,大學自身應按其多數票先后順序大約推選出三名候選人,而后在學監到場的情況下進行選擇。通過建立這種針對不同大學也將有所調整的機制,均衡狀態將得到最好的保障,而絕大多數不良影響也將受到阻遏。”[1](P100)
在施萊爾馬赫看來,大學應當享有充分的學術自由,“關于那確實屬于校務范疇的一切事務,大學必須自由且獨立地形成自己的處置權,并且能夠視環境情況而進行更改;同時,國家不得橫加干涉、發號施令,而應當只要求獲知詳情,并行使監督之責,以便不逾越這領域的界限”。[1](P103)
大學生也應當享有充分的學術自由。施萊爾馬赫認為大學生的自由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與中學相比在大學中享有的自由,這主要涉及他們的思想活動。他們不屈服于任何形式的強制脅迫,不會被推向任何一個地方,也沒有什么東西對他們來說是禁止觸碰的。沒有人命令他們學習這門或那門課程,也沒有人能指責他們對待此事漫不經心,或者完全不去上課。除了他們自愿托付給一位教師的那部分監督權外,他們的所有學業不受任何監管。他們清楚自己離開大學時需要具備什么要求,將面臨何種考試與檢驗。至于想要以什么樣的勤奮與熱情向著此目標前進,如何平均或不平均地分配這種熱情,完全由他們自己決定。大學需要確保他們不會缺乏深入鉆研學習所需要的輔助工具,至于他們是否合理使用,即使被人發現,他們至少無需向任何人解釋。他們或是選擇沉溺于慵懶懈怠與可恥的閑散消遣之中,或是能夠毫無責任地虛擲他們人生中最美妙的時光,而不是選擇值得贊揚的勤奮努力,這全是他們的自由”。[1](P108-109)
為什么要給予大學生這種自由呢?施萊爾馬赫的回答是:“單單學習本身無論如何并非大學的目的,大學的目的是使學生得到認識。人們忘記了,在大學不應靠死記硬背知識來塞滿大腦,也不應僅僅使人的理智變得深邃,而是應當在青年之中激起一種全新的生命,如果可能的話,激起一種更崇高的、真正的學術思維。然而在強迫之下,這是不會成功的,只有在一種思想完全自由的氣氛中才能夠致力于這種努力。”[1](P109-110)
學生自由的另一面是生活方式的自由。施萊爾馬赫說:“嚴格來說,這種自由的本質在于,大學生之間幾乎不用遵循所有那些相習成風的社會準則;那些畢業之后每個人必須遵從的所選行業的習俗規范,大學生們卻可以不受它們的約束,各式各樣的習俗與生活方式都能夠在大學中最為自由地開展。”[1](P117)經過這種持續一段時間離開家庭、脫離國家的境況,他們才變得有能力正確地選擇將來的工作職務與生活方式,建立只與其天性相符的人際關系。“那些需由外界規定道德規范的人們,是沒有能力獲得真正的認識,甚至也沒有能力去理解與接受教育的。”[1](P122)
(五)論大學教學方法
施萊爾馬赫認為,大學課程的要務是進行學術性闡釋,因而學術講座無疑是大學最重要的教學方法之一。他說:“盡管大多數教師將此種類型的課程講得極差,但驚奇的是它竟一直保存了下來,這顯然證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學的特征。”[1](P60)
講座無論在何處都是大學教師最基本的本領。施萊爾馬赫認為,“這種本領之中須結合兩種品德:一是活力與熱忱。大學教師的重現過程不能僅僅是一種游戲,它必須再現真理。每當大學教師以演講的方式考察其自身認識之起源、其現在與曾經的面貌特征,每當他描繪自科學之中心通往相鄰領域的道路時,必然要求大學教師自身也真正地走過這條道路。這對科學事業中每個真正的大家而言都是如此。倘若沒有一個新的推論、新的發現激發起大學教師的活力與興趣,那么他也不可能進行這種重復;大學教師在教學的同時也總是在學習,總是充滿活力地、真正是在創造性地立于聽眾面前。二是嚴肅謹慎與思路清晰。這是為了將那些處于激動興奮中創造出來的事物塑造成易于理解、有促進作用的事物;為了使大學教師與后進之輩共處的意識永遠保持鮮活,就要求他不是在自說自話,而是真正為學生做演講,使學生得以真正理解他的思想與推論,增強學生對知識的記憶,如此學生的心中所形成的將不再是對知識之肅穆壯麗的隱約之感,而就是知識本身。”[1](P63-64)教授們擁有的學識越多自然越好,但若缺少了“講座”這門技藝,絕大多數學識也派不上用場。施萊爾馬赫批評照本宣科的講座,他說:“一位要求照著一本為一勞永逸而寫就的書宣讀與抄寫的教授,不合時宜地使我們想起了那個還沒有印刷術的時代,當時若一位學者同時向許多人口述他的手稿,如此起作用的便是口頭形式的演講而非書本,但即使這樣,也比照本宣讀更有價值。”[1](P65-66)
除了講座,施萊爾馬赫也肯定了專業研討課的價值。由于研討課常常是小規模的,常常是由國家開設及資助的課程,不僅負責這些研討課的教師能夠得到更為優厚的薪酬,參與其中的學生也幾乎毫無例外地享受到明顯的好處。大學正是因為有了研討課才與科學院更接近。在研討課中,學生被指導嘗試自主論述,對于單獨部分進行精細入微的研究與調查。施萊爾馬赫指出:“在這種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的研討課上,學生已然需要進行學術產出,教師則無須做任何直接的講授,而只需引導、支持這種產出的過程,并給予評判。”[1](P88)
施萊爾馬赫極力倡導的講座和研討課19世紀以來一直是德國大學最主要的教學方法,后傳播到世界各國的大學中。
三、施萊爾馬赫對現代大學的影響
施萊爾馬赫畢業于哈勒大學,后又在哈勒大學任教。1807年,施萊爾馬赫移居柏林,他在布道之余積極參與關于建立柏林大學的討論,其大學觀對柏林大學的辦學實踐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1810年開辦的柏林大學是現代大學之母,她是在德意志民族和國家處于最困難的時候開辦的。1806年普魯士在耶拿戰役中被法國打敗,拿破侖關閉了耶拿和哈勒大學。1807年8月,以法學教授施馬爾茨(H. Schmalz)為首的前哈勒大學教師代表團請求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同意在柏林重建大學。國王欣然允諾,不僅將原來發給哈勒大學的經費全部撥給柏林大學,而且準許將原王子宮殿作為新大學的辦學場地,由國王最器重的大臣拜姆負責在柏林建立“一所綜合性教育機構”。拜姆先后向費希特、施馬爾茨和沃爾夫(F. A. Wolf)等人征集辦學建議,神學家施萊爾馬赫雖然不在征求意見的名單里,但他聽說這個計劃后也提交了自己的方案,這就是1808年《關于德意志大學的思考:附論將要建立的大學》一文的由來。施萊爾馬赫的方案后來成為新大學思想的憲章。
1809年新任普魯士教育大臣的洪堡接手了柏林大學的籌建工作,他繼續向費希特、施萊爾馬赫等人征求新大學的辦學意見。1810年6月3日,洪堡在辭職前成立了一個四人委員會,負責起草柏林大學臨時章程。除洪堡外,其他三位委員分別為烏登(W. Uhden)、蘇弗恩(J. H. Suvern)和施萊爾馬赫,前兩人均為普魯士內閣文官。起草委員會曾向法學家薩維尼(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征求意見,最終由施萊爾馬赫歸納成文。施萊爾馬赫起草章程的主要依據即是自己兩年前撰寫的《關于德意志大學的思考:附論將要建立的大學》一文。史家認為:施萊爾馬赫并沒有像激進派費希特那樣提出新的組織形式,而是強調了傳統的大學組織結構,因此柏林大學就成為一所以聘用正教授為基本結構的常規式大學。[2](P19)
該章程草案保留了興起于中世紀的神學、法學、醫學和哲學四個專業,但沒有像很多德國大學那樣將它們分為高低不同的等級;保留了傳統的教師體系,即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但不設世襲頭銜,各級內部也無等級之分,這就遏制了當時某些教授的自我優越感。草案規定,只有正教授才是大學的正式成員,大學由各個學院或研究院組成;每個學院均由一名正教授全權負責,如需資金和物質支持,由該學院正教授直接與內閣溝通而無需通過學校;學術事宜,如學位的授予,則由正教授選舉產生的評議會決定。大學校長通過教授選舉產生,代表學校處理校務,任期兩年,不得連任。該章程草案經委員們逐字逐句商討,但未做任何實質性修改,于1810年9月22日獲得通過,同年10月2日經國王批準后正式開始任命教授、臨時校長及院長[2](P34)。
毫無疑問,制訂柏林大學章程的核心人物是施萊爾馬赫。美國學者法倫(Daniel Fallon)說:“施萊爾馬赫設計的大學組織結構形式被德國所有大學效仿,并沿用至今。這種模式使德國能夠通過政府文教部門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學術活動。”[2](P36)
洪堡被譽為“現代大學之父”,他在任職普魯士教育大臣的僅僅16個月期間,完成了柏林大學的籌建工作。然而,“洪堡創辦大學所依據的精神和道德準則是其他人先期設想的”[3],這些人至少包括康德、席勒、費希特、謝林、施萊爾馬赫等人,其中施萊爾馬赫的影響無疑是首屈一指的,其《關于德意志大學的思考:附論將要建立的大學》成為創辦柏林大學的重要文獻之一。美國學者麥克萊蘭(Charles E.McClelland)指出:“可以肯定的是,費希特和更為激進的新人文主義者對新柏林大學實際發展的影響是非決定性的。如果說有哪位改革者在新柏林大學最初發展的決定性階段占了主導地位,那就是神學家施萊爾馬赫。將施萊爾馬赫關于新大學指導方針的備忘錄與費希特的備忘錄進行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前者比后者更通融、務實,更尊重德國大學的某些古老傳統。”[4]
與費希特較為激進的方案相比,施萊爾馬赫的方案是偏保守的。費希特提交的方案用“學府”(Anstalt)替代了“大學”一詞,但施萊爾馬赫拒絕另起爐灶創建一個全新類型的機構。美國學者霍夫施泰特爾(Michael J.Hofstetter)說:“施萊爾馬赫并不想改變大學,只是想改善大學。他希望保留舊的形式,但注入新的活力。他渴望讓年輕人的頭腦更加出色,使大學成為科學的中心。但作為一個事業有成的哈勒人,他并不想將一切推倒重來。”[5](P101)施萊爾馬赫堅信,無論如何,新機構的名稱仍是“大學”,大學的精華必須保留,但傳統大學的糟粕必須去除,如高級學院的支配地位應該結束,哲學院應該占支配地位。地方主義的壁壘,即各個小邦僅僅為了本邦的狹隘利益而利用大學,將讓位于邦與邦之間的真正的學術競爭和對卓越的追求[5](P99-100)。在費希特的方案里,大學是國家的機構,大學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之間沒有沖突,大學將成為國家的道德指南。而施萊爾馬赫則認為國家是大學的天敵,因為國家有狹隘的、實際的利益,這與知識的無限性是相矛盾的。他承認大學的運行需要國家投入資金,但他對此感到不安。最重要的是,他害怕國家干預大學事務,認為這會對學者之間思想自由交流造成威脅[5](P100-101)。施萊爾馬赫也不贊成費希特將大學與科學院相融合的建議,主張大學應保持自己的傳統。最后,施萊爾馬赫和費希特對大學生的生活也產生了迥然不同的看法。“費希特設想了一種斯巴達式的環境,學生們統一制服和膳食,這將發展道德以及學生的精神生活。沒有兄弟會,沒有酗酒,沒有嫖娼和惡作劇。相比之下,施萊爾馬赫認為學生不應該被如此控制,而應該更多地聽任他們自行決定。”[5](P101)
當然,除了分歧,施萊爾馬赫和費希特的方案也有很多相同之處。客觀公允地說,兩人的方案均對柏林大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例如,兩人都主張學術自由,一致認為國家需要發展學術來培養有知識的國民。學術自由則可以保障學者們(也包括學生)在學術交流活動中促進知識的發展[6](P21-22)。又如,兩人都認為,哲學的任務就是突破專業的界限建立學術思想來確保一切研究領域和專業都擁有共同的思想基礎。“每位學者首先必須是學習過哲學的學生,所有人在第一學年都必須先學習并且只學習哲學。”[6](P22)德國學者勒爾斯(Hermann R?hrs)評論說:“費希特和施萊爾馬赫的上述思想被洪堡所采用。即使今天看來,這種思想仍然對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6](P22)
19世紀初,德國大學的聲譽跌入谷底,其鄰國法國的大學已經被完全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專門學院,以至于普魯士的學者和改革派在提出要在柏林建立新型高等教育機構時都紛紛回避“大學”一詞。主管高等教育工作的司法大臣馬索夫(J. V. Massow)干脆主張關閉大學,以專門學院取而代之[2](P8)。費希特用“柏林高等教育機構”一詞替代大學。洪堡也曾一度舉棋不定,他在其備忘錄中提到要建立“柏林高等學術機構”。惟有施萊爾馬赫對大學充滿信心,他把科學元素納入傳統大學,使古老的大學舊貌換新顏。1809年,洪堡向國王遞交了《建立柏林大學的申請》。洪堡寫道:“我相信在陛下看來,‘大學這個名字不需要任何理由。這只能表明科學沒有被排除在外,教學機構也將賦予學術盛名。”[7](P35)洪堡向國王保證,“一切過時和有害的東西”都將被排除在外,但是,試圖建立一個不叫大學的高等教育機構是不可行的,因為在教學中理論與實踐是不能輕易分離的[7](P35)。很明顯,洪堡的申請附和了施萊爾馬赫有關大學的核心觀點。
在施萊爾馬赫的時代,大學遇到了自創辦以來的最大危機。在意大利,古老的大學早已褪去中世紀的光環;在法國,以巴黎大學為代表的傳統大學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專門學院;在英國,牛津、劍橋因循守舊,不再享有昔日的聲望。到18世紀后半葉,德國大學岌岌可危,一度面臨法國大學同樣的命運。正是施萊爾馬赫和洪堡等人的堅持和不懈努力,德國大學的傳統形式最終得以保留,并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以柏林大學為代表的現代大學的崛起,成為大學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從此,廢除大學的呼聲銷聲匿跡。
參考文獻
[1] Schleiermacher F D.Gelegentliche über Universit?ten in deutschem Sinn,Nebst einem Anhang über eine neu zu errichtende[M].Berlin:Realschulbuchhandlung,1808.
[2] Fallan D.The German University[M].Boulder: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80.
[3] [德]彼得·貝格拉.威廉·馮·洪堡傳[M].袁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76.
[4] Mcclell C E.State,Society,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1700-1914[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120.
[5] Hofstetter M J.The Romantic Idea of a University,England and Germany,1770-1850[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1.
[6] R?hrs H.The Classical German Concept of the University and its Influ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M].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1995.
[7] Garcia K.Reexamining Academic Freedom in Religiously Affiliated Universitie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6.
Schleiermachers University View and its Influence on Modern Universities
HE Guo-qing? YANG Jia-sheng
Abstract: Schleiermacher's idea of university is mainly embodied in his essay Thoughts on German-style Universities: On the University to be Established writte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He discussed comprehensively the image of his ideal university: it cannot work without the support of state, while it should seek independence from the stat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purpose of university is to rouse the cognition of young people, which is of the supreme importance in reason, with science education. The College of Philosophy is the most advanced one in university, in which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be rooted i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be provided academic freedom properly. Academic lecture and seminar are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s for university. During the University Reform in Prussia, Schleiermacher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found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and served as a member of the founding committee set up by Humboldt. By directly integrating certain theoretical ideas into the practice of the university at the level of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olitics, he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shaping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aculty architecture, and teaching methods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He not only preserved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German universities but also injected new elements and vitality into it, making the model of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important principles and exemplar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moder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Schleiermacher; view of university; modern universities; influence
(責任編輯? 陳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