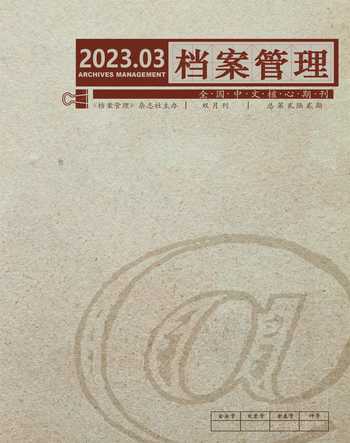族群檔案的身份認(rèn)同價(jià)值及其啟示
周林興 周晴
關(guān)鍵詞:檔案;身份認(rèn)同;河南;戲劇;族群;價(jià)值;品牌;開(kāi)發(fā)利用
0 引言
信息化時(shí)代,網(wǎng)絡(luò)世界的豐富與脆弱、真實(shí)與虛幻、個(gè)體角色的多重性與人際關(guān)系的不確定性導(dǎo)致和誘發(fā)人們對(duì)精神歸屬的追求與迷失。[1]人們迫切尋求精神上的共鳴與歸屬,不斷思考“我是誰(shuí)”“我從哪里來(lái)”“要到哪里去”的問(wèn)題,期望通過(guò)各種文化活動(dòng)與自身反思不斷確認(rèn)自身在社會(huì)中的身份感與歸屬感。
自2011 年特里·庫(kù)克提出“證據(jù)、記憶、認(rèn)同和社會(huì)”的“檔案四個(gè)范式”以來(lái),檔案管理的模式便逐漸從“國(guó)家模式”向“社會(huì)模式”轉(zhuǎn)變。[2]檔案學(xué)界越來(lái)越關(guān)注“檔案”“記憶”“認(rèn)同”三個(gè)非傳統(tǒng)范式的研究。其中,認(rèn)同這一檔案范式關(guān)注的是作為社會(huì)資源型的檔案從支撐學(xué)術(shù)精英的文化遺產(chǎn)轉(zhuǎn)變?yōu)榉?wù)于認(rèn)同和正義的社會(huì)資源,[3]認(rèn)為檔案可以通過(guò)發(fā)揮其證據(jù)價(jià)值和記憶屬性構(gòu)建社會(huì)記憶,借由集體記憶這一紐帶,促進(jìn)身份認(rèn)同的建構(gòu)與強(qiáng)化。因此,在檔案機(jī)構(gòu)與工作者服務(wù)職能轉(zhuǎn)向的今天,積極開(kāi)展族群檔案資源建設(shè),開(kāi)發(fā)其中的記憶價(jià)值,構(gòu)建族群的身份認(rèn)同乃至樹(shù)立整個(gè)民族、國(guó)家的文化認(rèn)同是實(shí)現(xiàn)檔案當(dāng)代價(jià)值的應(yīng)有之義。
本文以《只有河南·戲劇幻城》(簡(jiǎn)稱《只有河南》)作為分析對(duì)象,肯定族群檔案具有建構(gòu)民族身份認(rèn)同的價(jià)值,并通過(guò)分析戲劇幻城利用族群檔案發(fā)揮身份認(rèn)同價(jià)值的這一成功案例,為族群檔案的開(kāi)發(fā)利用提供借鑒與參考。
1 族群檔案的身份認(rèn)同價(jià)值闡釋
“在普通公民看來(lái),檔案不僅涉及政府的職責(zé)和保護(hù)公民的個(gè)人利益,而且更多地還要為他們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體記憶。”[4]它不僅可以為身份認(rèn)同的歷史主義分析提供追蹤性、連續(xù)性素材,更可以為身份認(rèn)同的結(jié)構(gòu)分析提供多視角、多層次的素材。[5]當(dāng)然,檔案本身并不會(huì)產(chǎn)生身份認(rèn)同,它的實(shí)現(xiàn)需要通過(guò)一個(gè)中介——集體記憶,[6]即通過(guò)構(gòu)建、重建、強(qiáng)化集體記憶來(lái)實(shí)現(xiàn)其在身份認(rèn)同上的價(jià)值。[7]族群檔案能夠幫助族群成員確認(rèn)、確證、接受與承認(rèn)自己的集體記憶,與族群身份認(rèn)同形成一種天然的關(guān)聯(lián)。
1.1 族群檔案是維系族群根源的紐帶。在人類社會(huì)演變的歷史進(jìn)程中,人們的組織形式與居住地在不斷更迭,在不同的歷史場(chǎng)場(chǎng)景下,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以血緣、信仰和共同歷史為基礎(chǔ),人們形成了各自的族群,這些族群擁有不同的組織形式、身份認(rèn)同與情感追求。族群認(rèn)同是需要與模仿的某種結(jié)合。所以,族群認(rèn)同是成員有意識(shí)構(gòu)建起來(lái)的,或者說(shuō)是共享利益意識(shí)的結(jié)果,[8]族群成員根據(jù)自身的需要,通過(guò)文字符號(hào)不斷記錄、修正與遺忘自身歷史,形成維護(hù)自身認(rèn)同的檔案記錄。[9]這些用文字符號(hào)固定下來(lái)的并在漫長(zhǎng)歷史長(zhǎng)河中動(dòng)態(tài)擴(kuò)充的經(jīng)驗(yàn)及認(rèn)知集合,形成了族群檔案。它是維系族群根源和延續(xù)認(rèn)同的基礎(chǔ),更是串聯(lián)族群歷史血脈的紐帶,還是凝聚族群“我群”意識(shí)的超越時(shí)空而存在的信物。族群檔案記錄了一個(gè)族群自誕生以來(lái)的歷史活動(dòng),代表了族群成員的共同經(jīng)驗(yàn)與文化特質(zhì),具有邏輯和時(shí)間上的根源感,能夠?yàn)樽迦撼蓡T提供歸屬感、托付感。更重要的是,嵌于族群檔案中的“根源感”,使族群成員可以通過(guò)保存、追溯、強(qiáng)化或重溫族群檔案來(lái)催生尋根意識(shí),實(shí)現(xiàn)身份認(rèn)同。[10]族群就是在不斷建檔修史中強(qiáng)化自身的身份認(rèn)同,將共同的族群意識(shí)傳遞給后代,保持著族群的本真特質(zhì),維系族群的根源感。
1.2 族群檔案是構(gòu)建共同記憶的土壤。集體記憶在族群回溯性的身份認(rèn)同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集體記憶是檔案發(fā)揮身份認(rèn)同價(jià)值的中介,作為一種與認(rèn)同相互作用的重要參與變量,[11 ]成為族群保有共同體意識(shí)的黏合劑。族群檔案自誕生以來(lái)就存在記憶屬性,一方面,檔案延續(xù)了族群記憶。在一個(gè)族群中,個(gè)體的生命是有限的,僅僅憑借個(gè)體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重新再現(xiàn)他以前再現(xiàn)的東西的,除非他訴諸所有群體的思想。[12]群體可以通過(guò)檔案這一記憶傳播載體進(jìn)行人與人、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的記憶傳遞。[13]并且,族群檔案記錄共同記憶的過(guò)程,同樣也是族群區(qū)分自我與他者的過(guò)程,更是對(duì)族群意義和價(jià)值范疇內(nèi)容上的理想狀態(tài)的構(gòu)想、憧憬與追求。另一方面,檔案所承載的族群記憶能夠向族群的個(gè)體傳遞。[14]因?yàn)橛洃洸粌H是過(guò)去留在人們心中的圖像,它還會(huì)轉(zhuǎn)化為活的文化基因,滲透和融化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傳統(tǒng)中,永遠(yuǎn)伴隨人類社會(huì)的延續(xù)。[15]對(duì)于族群而言,檔案充當(dāng)了佐證與建構(gòu)族群身份認(rèn)同的記錄載體和有效媒介,使得族群在代際傳遞中保存、重溫和強(qiáng)化共同記憶,最后被個(gè)體所內(nèi)化,實(shí)現(xiàn)身份認(rèn)同的維護(hù)與延續(xù)。
1.3 族群檔案是延續(xù)情感歸屬的媒介。族群是一個(gè)“想象的共同體”,[16]它不是許多客觀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集合,而是通過(guò)族群成員內(nèi)心對(duì)于族群的情感歸屬而形成的。[17]情感是最深遠(yuǎn)、最穩(wěn)定、最持久的認(rèn)同,在族群認(rèn)同的理論研究中,影響力最大的兩種理論中的根基論認(rèn)為族群認(rèn)同主要來(lái)源于根基性的情感聯(lián)系,[18]這種原生性的情感羈絆幫助族群成員整合分歧、凝聚共識(shí),能夠穿越時(shí)空而存在。情感上的認(rèn)同是根深蒂固的、下意識(shí)的,它在族群成員之間形成一種強(qiáng)大的聚合力,即使族群成員經(jīng)歷了地理位置上的遷移,這種主觀心理上的情感歸屬仍然能夠強(qiáng)有力地維系“我群”認(rèn)同。例如歷史上,猶太民族雖然歷經(jīng)了兩千多年的流浪史,經(jīng)受了數(shù)次滅族事件,但他們的民族特性仍然得以保存,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一直堅(jiān)定自己精神層面的信仰和情感歸屬。
族群檔案作為一種文化符號(hào)和記憶載體,不僅是在傳達(dá)一種群體共同的認(rèn)知,也在共享和傳播一種群體的價(jià)值觀和情感取向,[19]它是喚醒族群成員情感歸屬的有效工具,是族群成員的“情感倉(cāng)庫(kù)”。承載著族群成員的情感表達(dá)與寄托,是族群情感活動(dòng)的重要媒介和源泉。[20]當(dāng)一個(gè)族群回溯自己的過(guò)去時(shí),檔案蘊(yùn)含的精神力量給予了成員情感上的歸屬與依附,幫助族群更好地理解自身過(guò)去與現(xiàn)在的連續(xù)性,向內(nèi)增強(qiáng)成員的情感聯(lián)系,完成身份認(rèn)同的灌輸。
2 《只有河南》的檔案敘事對(duì)身份認(rèn)同的多層次構(gòu)建
《只有河南》是由建業(yè)集團(tuán)推出的以黃河流域文明為根基創(chuàng)作的文化作品,是中國(guó)目前規(guī)模最大、劇目最多以及演出時(shí)間總計(jì)最長(zhǎng)的戲劇聚落群。《只有河南》采用戲劇形式,整合河南族群檔案資源,將河南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每一層記憶寫(xiě)成劇本,并通過(guò)搭建沉浸式展演空間再現(xiàn)歷史場(chǎng)景,借助科技和多媒體集成敘事,讓觀眾通過(guò)視覺(jué)直觀、立體地感受到河南的乃至中華民族的文化力量,開(kāi)展一場(chǎng)尋根溯源之旅。
2.1 檔案敘事內(nèi)容觸發(fā)族群身份認(rèn)同。族群檔案中記載了一個(gè)族群的共同遭遇,其中包括輝煌記憶與創(chuàng)傷記憶。族群認(rèn)同的建構(gòu)離不開(kāi)崇高感的獲得,崇高感是人們基于對(duì)崇高對(duì)象的敬仰、贊嘆而生發(fā)的情感體驗(yàn)。[21]輝煌記憶能夠使得族群成員獲得自豪感,進(jìn)一步激發(fā)對(duì)族群的認(rèn)同與維護(hù);而創(chuàng)傷記憶可能會(huì)對(duì)族群造成情感挫傷,但是作為族群的共同記憶,它是不可回避的部分,群體及其成員曾經(jīng)遭受的苦難也是群體繼續(xù)存在和發(fā)展的支柱。[22]通過(guò)謹(jǐn)慎敘事與引導(dǎo),同樣也可以給予成員情感驅(qū)動(dòng)力,在輝煌與苦難中,族群通過(guò)共享情感與記憶緊緊凝聚在一起。戲劇是一種表現(xiàn)藝術(shù),它能夠通過(guò)故事和演繹激發(fā)不同的情感意象,并通過(guò)意象的性質(zhì)和它們之間的矛盾關(guān)系演繹出意義。[23]《只有河南》通過(guò)戲劇形式,提取河南族群檔案中蘊(yùn)含的族源記憶,在檔案和觀眾之間建立起情感的通道,喚醒河南人乃至中華民族的身份認(rèn)同,實(shí)質(zhì)上是利用檔案提供文化產(chǎn)品與服務(wù),滿足公眾文化情感需求的行為。每一個(gè)檔案都是一個(gè)故事的信念,積極采取各種手段發(fā)現(xiàn)和選取檔案能夠引起民眾共鳴、連接民眾情感并能夠增進(jìn)河南人對(duì)自己歷史的回溯和族群認(rèn)同感。[24]在檔案故事的選擇中,《只有河南》通過(guò)各種歷史人物、朝代更迭展現(xiàn)了河南乃至中國(guó)文明的輝煌歷史,引發(fā)觀眾情感的共鳴與民族自豪感,鼓舞了觀眾的民族自豪感。同時(shí),對(duì)于創(chuàng)傷記憶的演繹,《只有河南》也著墨頗多。磨難記憶是群體關(guān)系的催化劑。[25] 三大劇場(chǎng)中的兩場(chǎng)——火車站劇場(chǎng)和李家村劇場(chǎng)都講述了河南大饑荒的故事。這種集體磨難能夠引發(fā)觀眾的共鳴,加強(qiáng)族群的情感聯(lián)系。
2.2 檔案敘事手段增強(qiáng)族群身份認(rèn)同。隨著技術(shù)的發(fā)展,人與信息交互的界面從紙質(zhì)的檔案轉(zhuǎn)變?yōu)楸话母兄h(huán)境。[26]通過(guò)知覺(jué)沉浸進(jìn)行檔案敘事,開(kāi)展多感官的檔案展覽活動(dòng)成為更具效率的檔案信息傳播方式。[27]沉浸式的檔案記憶展演能夠增強(qiáng)人們與族群記憶的互動(dòng),借助具體的媒介手段,族群成員能參與情感儀式的再現(xiàn),并進(jìn)行傳播擴(kuò)散。[28]不僅能在感官上獲得更好的藝術(shù)體驗(yàn),還能激發(fā)族群成員的身份認(rèn)同。從檔案故事展演空間形態(tài)上說(shuō),《只有河南》的觀演關(guān)系被消解和模糊,舞臺(tái)是分散的、立體的、變幻的,觀眾是行走的、體驗(yàn)的、接觸的。這種呈現(xiàn)方式一方面改變了演員與觀眾的物理距離;另一方面,從心理情感層面上說(shuō),觀演距離分隔使觀眾與演員相異的職能暗示得到強(qiáng)化。[29]他們彼此觀望,互為鏡像,在看與被看中,以彼此為“他者”,區(qū)分與內(nèi)化身份認(rèn)同。沉浸式的舞臺(tái)設(shè)計(jì)增強(qiáng)了觀眾對(duì)檔案記憶的參與感,在劇場(chǎng)中,借助戲劇與想象,實(shí)現(xiàn)了族群記憶的回溯與身份認(rèn)同的建構(gòu)。除了舞臺(tái)形式的消解,數(shù)字科技的參與更加強(qiáng)了表演效果的呈現(xiàn)。《只有河南》在視覺(jué)的呈現(xiàn)上創(chuàng)新運(yùn)用了“變質(zhì)”的藝術(shù)手法,通過(guò)對(duì)“黃土坡”“李家村”“清明上河圖”等中原景觀、文化符號(hào)等介質(zhì)進(jìn)行“視覺(jué)質(zhì)變”,讓它們呈現(xiàn)出當(dāng)下的新媒體藝術(shù)語(yǔ)言特性。科技的參與創(chuàng)造了立體觀感的戲劇效果,增強(qiáng)了觀眾的沉浸式體驗(yàn)與視覺(jué)觀感,[30]喚醒了觀眾的情感認(rèn)同,增強(qiáng)對(duì)檔案記憶的深度理解與互動(dòng)。
2.3 檔案敘事場(chǎng)景表征族群身份認(rèn)同。當(dāng)代建筑營(yíng)造具有敘事感的空間是其重要的設(shè)計(jì)傾向之一,作為一種敘事語(yǔ)言與敘事符號(hào),建筑能夠承載記憶、傳遞情感,具有意義傳達(dá)的敘事特質(zhì)。[31]劇場(chǎng)是具有較強(qiáng)敘事性的文化場(chǎng)所,能夠起到宣傳教化的作用,《只有河南》在劇場(chǎng)設(shè)計(jì)中充分考慮了族群檔案的特色元素與時(shí)空關(guān)系,通過(guò)場(chǎng)景再現(xiàn)、設(shè)置空間道具、融入自然景觀和虛擬影像等空間情景構(gòu)建形式,[32]增強(qiáng)檔案記憶敘事的效果,引發(fā)族群成員的情感共鳴與文化認(rèn)同。《只有河南》將建筑特色和戲劇內(nèi)核相融合,打破了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時(shí)空界限。[33]劇場(chǎng)設(shè)計(jì)從“棋盤”與“盲盒”之中創(chuàng)意取材,打造了328米長(zhǎng)的巨型城郭,21個(gè)劇場(chǎng),設(shè)計(jì)了56個(gè)不重樣的方格空間,根據(jù)戲劇故事再現(xiàn)對(duì)應(yīng)的場(chǎng)景,如“坤臺(tái)”“第七機(jī)車車輛廠禮堂”“天子駕六遺址坑”等等。為族群記憶的再現(xiàn)提供了沉浸式的布景,使得觀眾有身臨其境之感,從而引發(fā)情感共鳴。并且,圍繞“河南”這一族群檔案主題,戲劇幻城在建筑設(shè)計(jì)時(shí)充分考慮了時(shí)間與空間的協(xié)調(diào)。“一磚一瓦一片瓷皆為史詩(shī),一枝一葉一抔土都是故事”,從四四方方的麥田地到若干非遺主題館,再到21個(gè)劇場(chǎng),表現(xiàn)了河南記憶的歷時(shí)性與延續(xù)性。過(guò)去與未來(lái)、他人與我者在這里碰撞,為檔案記憶展演營(yíng)造了良好的氛圍。再加上,建筑的設(shè)計(jì)結(jié)合了地域特色,在抵達(dá)戲劇幻城的路上,設(shè)置了百畝麥田,再走近,是360米長(zhǎng)的夯土墻,這些建筑意象都是族群地域性的紐帶,通過(guò)黃土、麥田等文化符號(hào),傳遞和表達(dá)了河南的地域性關(guān)聯(lián)和精神內(nèi)核。通過(guò)設(shè)置這些建筑意象,為觀眾營(yíng)造一個(gè)確認(rèn)身份的空間介質(zhì)。最后,戲劇幻城利用科技造景,利用聲、光、電,帶領(lǐng)觀眾穿越時(shí)空。在夯土墻上實(shí)現(xiàn)《清明上河圖》《千里江山圖》的動(dòng)態(tài)投影等,拓展了敘事空間,呼喚觀眾的民族情感,建構(gòu)身份認(rèn)同。
3 族群檔案身份認(rèn)同價(jià)值開(kāi)發(fā)利用的啟示
族群檔案是構(gòu)建身份認(rèn)同的重要資源,《只有河南》利用族群檔案資源,通過(guò)敘事再現(xiàn)族群記憶,喚醒族群成員情感聯(lián)系,實(shí)現(xiàn)超越時(shí)空的檔案與現(xiàn)實(shí)、族群與個(gè)體的鏈接,為族群檔案身份認(rèn)同價(jià)值的開(kāi)發(fā)利用提供了新思路。
3.1 開(kāi)放合作,挖掘族群檔案身份認(rèn)同價(jià)值。(1)重視族群檔案資源的多元主體。當(dāng)前一個(gè)重要趨勢(shì)便是檔案資源范圍向公眾擴(kuò)展,使得不同群體的身份認(rèn)同獲得檔案的支持,尤其是非官方組織、少數(shù)民族或種族、社會(huì)特殊人群、邊緣群體的身份認(rèn)同問(wèn)題,應(yīng)得到關(guān)注。美國(guó)檔案學(xué)者帕特里克·奎因(Patrick Quinn)早在1977年就提出檔案工作者要主動(dòng)參與到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中去,將利用檔案為少數(shù)群體權(quán)益而斗爭(zhēng)作為檔案工作的一種目標(biāo)。[34]面對(duì)檔案工作社會(huì)化的趨勢(shì),檔案工作者應(yīng)積極走向社會(huì),重視多元主體的身份認(rèn)同需求,了解群體的發(fā)展歷程和個(gè)體的社會(huì)經(jīng)歷,甚至可吸納群體成員來(lái)共同開(kāi)發(fā)本群體的檔案,幫助群體在檔案的編纂與開(kāi)發(fā)利用活動(dòng)中了解自身、傳播自身。[35](2)鼓勵(lì)族群檔案資源的立體開(kāi)發(fā)。鼓勵(lì)多視角、多群體、多維度重新定義檔案內(nèi)涵及檔案工作各項(xiàng)內(nèi)容,有利于引導(dǎo)檔案館聯(lián)合社會(huì)機(jī)構(gòu)、公眾共同開(kāi)發(fā)檔案的身份認(rèn)同價(jià)值。[36]在檔案服務(wù)社會(huì)化的時(shí)代背景下,檔案資源的開(kāi)發(fā)需要多元主體的協(xié)同,各界技術(shù)人才的創(chuàng)意碰撞,以及社會(huì)資本等的資助,有利于規(guī)避檔案部門本身人員較少、開(kāi)發(fā)力量薄弱等問(wèn)題。[37]加強(qiáng)檔案部門與社會(huì)外部力量的互動(dòng),也能夠更好地發(fā)掘檔案中隱藏的民族認(rèn)同、政治認(rèn)同、文化認(rèn)同以及時(shí)代認(rèn)同價(jià)值,增強(qiáng)身份認(rèn)同的建構(gòu)與強(qiáng)化。
3.2 善用敘事,增強(qiáng)族群檔案的情感聯(lián)系。敘事能夠?qū)Ψ?hào)進(jìn)行重組,使得刻寫(xiě)于檔案中的歷史記憶被人們感知,[38]運(yùn)用語(yǔ)言和敘事,族群檔案記憶能夠在社會(huì)層面實(shí)現(xiàn)重生。[39]敘事的情節(jié)與場(chǎng)景能夠幫助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群體特征,傳達(dá)族群情感與認(rèn)同,為族群檔案資源的開(kāi)發(fā)利用提供新的思路。
(1)敘事內(nèi)容:深度挖掘族群檔案資源。“要想教人理解自己,就要排除那些抽象術(shù)語(yǔ)。要想叫人聽(tīng)你的,就要賦予歷史激動(dòng)人心的興趣,使歷史永遠(yuǎn)興趣盎然。”[40]挖掘族群檔案資源開(kāi)展敘事,首先要會(huì)講故事。
檔案機(jī)構(gòu)在敘事內(nèi)容的構(gòu)造上要關(guān)注文本本身,在敘事內(nèi)容的主題選擇上,深度挖掘檔案資源,選取多樣化的主題,既要把握總體故事的完整性,也要深入細(xì)節(jié)的描述。既要選取輝煌部分發(fā)揮激勵(lì)作用,也要正視創(chuàng)傷部分,促進(jìn)反思與情感凝聚。建構(gòu)起多角度、立體化的敘事結(jié)構(gòu),構(gòu)建全面的故事世界。[41]在敘事內(nèi)容的文本詮釋上,要注重對(duì)檔案材料的考證與串聯(lián),關(guān)注文本的可讀性和邏輯性,加強(qiáng)對(duì)故事情節(jié)的刻畫(huà)。同時(shí),充分考慮現(xiàn)實(shí)的公眾情感需求,從而創(chuàng)造出超越個(gè)體記憶的,有別于他者的整體記憶,使敘述中的故事和人物更顯魅力,讓公眾真切感知檔案中的歷史情感、民族情懷,樹(shù)立身份認(rèn)同感與價(jià)值觀,[42]凝聚主體與身份之間的情感共鳴。
(2)敘事手段:技術(shù)賦能族群檔案敘事。基于身份認(rèn)同的族群檔案開(kāi)發(fā)可以依靠可視化敘事手段,挖掘檔案資源中的故事,拉近用戶與檔案信息的時(shí)空距離,構(gòu)筑完整的敘事情境,力求用戶可感知敘事要素真實(shí)細(xì)致,加強(qiáng)刻畫(huà)故事人物形象、社會(huì)關(guān)系、心理變化、地理環(huán)境、人文環(huán)境細(xì)節(jié),令用戶擁有沉浸式體驗(yàn)。[43]可以使用聲光電等多種技術(shù),延伸觀眾的感官,增強(qiáng)觀眾對(duì)檔案內(nèi)容的認(rèn)可,產(chǎn)生情感認(rèn)同,觸動(dòng)身份認(rèn)同共鳴。另外,基于身份認(rèn)同的族群檔案開(kāi)發(fā)可以采用新媒體手段將檔案記憶盡善盡美地呈現(xiàn)出來(lái)。檔案館應(yīng)借助時(shí)代力量,充分運(yùn)用新媒體手段,采用“文字(敘述)+音頻(情感傳達(dá))+圖片、視頻(視聽(tīng)呈現(xiàn))”的模式,渲染情感,表現(xiàn)檔案作品的價(jià)值。還可以通過(guò)多媒體聯(lián)動(dòng)促進(jìn)檔案文化的傳播,將敘事應(yīng)用在檔案主題展覽、檔案文化講座、檔案宣傳視頻、檔案內(nèi)容推送等檔案文化傳播途徑中,增強(qiáng)檔案文化產(chǎn)品宣傳,以強(qiáng)化社會(huì)公眾體驗(yàn)。[44]也要兼顧不同媒介特性,選擇恰當(dāng)?shù)谋磉_(dá)方式,如電影的視聽(tīng)環(huán)繞感、游戲的互動(dòng)參與感、表演的藝術(shù)立體感、VR的虛擬交互感等。大力推動(dòng)數(shù)字檔案資源可視化敘事與網(wǎng)絡(luò)電視媒體平臺(tái)的合作。
(3)敘事場(chǎng)景:場(chǎng)所優(yōu)化族群檔案敘事。一個(gè)連續(xù)且完整的敘事空間,可以更好地促成展示內(nèi)容與參觀者之間的對(duì)話。[45]敘事場(chǎng)景的設(shè)計(jì)關(guān)乎檔案展演主題和內(nèi)容的表達(dá)與傳遞,是觀眾感受記憶與情感的場(chǎng)所,是作用于觀眾心理,引發(fā)思考與想象的器皿。敘事場(chǎng)景的搭建可以從族群檔案中獲取靈感和精華,增強(qiáng)與族群成員的聯(lián)系,通過(guò)再現(xiàn)檔案中對(duì)真實(shí)歷史場(chǎng)景的描述,給觀眾帶來(lái)身臨其境的感受,增強(qiáng)檔案記憶展演的效果。此外,可以將檔案敘事場(chǎng)所繼續(xù)擴(kuò)大至學(xué)校、社區(qū)、公園、劇院等,選擇恰當(dāng)?shù)谋磉_(dá)方式,如電影、游戲、藝術(shù)表演等形式,為公眾提供更廣泛的檔案文化公共服務(wù)。
3.3 文旅融合,打造族群檔案資源品牌。(1)把握契合點(diǎn),提高自身影響力。旅行是記憶過(guò)程的延伸,旅游業(yè)特別是遺產(chǎn)旅游有助于游客參與創(chuàng)造集體記憶,重現(xiàn)集體記憶,激發(fā)認(rèn)同感。族群檔案資源承載了族群成員的集體記憶和獨(dú)特的地域性文化符號(hào),其蘊(yùn)含的身份認(rèn)同價(jià)值與文化屬性,與旅游產(chǎn)業(yè)十分契合。在旅游中融入族群檔案可以建立目的地和用戶的關(guān)系,打破“我者與他者”割裂的界限,提高旅游的獲得感和滿意度。[46]人們基于對(duì)集體記憶和情感共鳴的尋找,對(duì)有文化特色的旅游產(chǎn)品表達(dá)出偏愛(ài),良好的經(jīng)濟(jì)效益與市場(chǎng)反應(yīng)又能夠促進(jìn)檔案資源的開(kāi)發(fā)與利用,從而形成良性閉環(huán),二者相互契合。族群檔案與旅游業(yè)的合作與普及,能夠?yàn)闄n案公共服務(wù)提供新的場(chǎng)所。重視身份認(rèn)同價(jià)值的檔案開(kāi)發(fā)利用可以順應(yīng)文旅融合的時(shí)代趨勢(shì),選取有特色的社群檔案資源進(jìn)行開(kāi)發(fā),打造族群檔案資源品牌,提高自身的文化影響力與輻射力。(2)注重社會(huì)需求,增強(qiáng)品牌吸引力。打造特色檔案資源品牌,首先,檔案機(jī)構(gòu)與工作人員應(yīng)面向社會(huì),立足自身資源優(yōu)勢(shì),關(guān)注個(gè)人與集體的文化需求以及身份認(rèn)同迷失問(wèn)題,照顧社會(huì)公眾尤其是少數(shù)群體的需求情節(jié)。其次,要注重族群檔案資源的開(kāi)發(fā)深度與文化內(nèi)涵,充分發(fā)揮其身份認(rèn)同價(jià)值,滿足社會(huì)公眾日益增長(zhǎng)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斷推出思想性、學(xué)術(shù)性、知識(shí)性、時(shí)代性相統(tǒng)一的檔案文化產(chǎn)品。最后,要善于創(chuàng)新檔案資源開(kāi)發(fā)模式,通過(guò)跨界合作、政府+資本等方式,打造高質(zhì)量的,能夠經(jīng)受市場(chǎng)考驗(yàn)的文旅品牌,從而提高檔案的社會(huì)地位與文化影響力,吸引更多的人了解檔案,走近檔案。
總之,當(dāng)下檔案資源的整合方向應(yīng)緊跟時(shí)代步伐,在新的社會(huì)背景下強(qiáng)調(diào)族群檔案的身份認(rèn)同價(jià)值。作為與檔案記憶相承接的研究課題,身份認(rèn)同賦予族群檔案資源開(kāi)發(fā)新的時(shí)代使命,同時(shí)也為檔案機(jī)構(gòu)與檔案工作者提高社會(huì)知名度和影響力帶來(lái)了新的契機(jī)。
4 結(jié)語(yǔ)
檔案通過(guò)傳承和建構(gòu)記憶,使得社會(huì)群體找到認(rèn)同并由此獲得力量。本文通過(guò)分析《只有河南·戲劇幻城》戲劇幻城中對(duì)檔案身份認(rèn)同價(jià)值的開(kāi)發(fā)與利用,認(rèn)為其成功經(jīng)驗(yàn)在于其認(rèn)識(shí)到了河南乃至華夏的身份認(rèn)同需求,并從檔案故事的敘事內(nèi)容、敘事場(chǎng)景、敘事手段等方面構(gòu)建集體記憶,喚醒和強(qiáng)化公眾的身份認(rèn)同。檔案資源見(jiàn)證歷史、承載記憶、凝聚著民族認(rèn)同。檔案工作者責(zé)任意識(shí)的覺(jué)醒,利用族群檔案幫助社會(huì)個(gè)人或群體建構(gòu)身份認(rèn)同,是檔案資源開(kāi)發(fā)利用的邏輯必然。未來(lái),檔案機(jī)構(gòu)及工作者應(yīng)轉(zhuǎn)變檔案資源開(kāi)發(fā)思維,確認(rèn)文化認(rèn)同的價(jià)值取向,依靠多元參與、善用敘事手段和文旅融合模式對(duì)集體記憶進(jìn)行構(gòu)建,從而激發(fā)群體認(rèn)同,傳承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