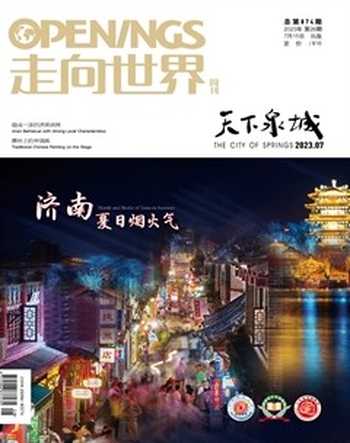“唐宋三大家”濟南情緣深幾許
張智輝
“唐宋八大家”在中國文學史上是道絢麗的彩虹,始于韓、柳,接力于歐和“三蘇”的古文運動,蓬蓬勃勃,為詩文發展蕩起強勁風潮,具有里程碑意義。這其中,蘇軾、蘇轍和曾鞏三位,因從政、尋親訪友等經歷與濟南結下不解之緣。
穿越千載,回望這些搖筆散珠的文章大家,同樣具有撒豆成兵的政治才干,有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濟世情懷,還有著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故事。
二臨齊州——千年文豪留佳話
場景:雪花飛舞,春寒料峭。公元1077年初春,濟南老城墻門口,3位風神瀟灑的少年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著。
“嗒嗒”馬蹄聲由遠而近,一位滿面征塵不失風度的中年男人翻身下馬,高個少年眼前一亮,邊跑邊喊:“伯父——我們可把您盼來了!”3位少年拱手彎腰,行拜見禮,中年男人疼愛地將他們摟在懷里,用略帶沙啞的聲音,一一猜著他們的名字:遲兒——適兒——遠兒,眼眸噙滿喜悅的淚滴。忽然,中年男人問:子由何在?高個少年稟報伯父,父親兩個月前進京述職。中年男人先是一怔,繼而,一聲嘆息,悵然若失。
這一幕發生在北宋神宗熙寧年間的齊州(濟南),風塵仆仆的中年男人就是千年文豪蘇軾,在雪中迎接他的就是其胞弟蘇轍的三個兒子蘇遲、蘇適、蘇遠。此行,是蘇軾從密州(諸城)趕往徐州赴任的途中,順道看望弟弟一家人。對蘇軾首次濟南之行,不僅史料詳實可查,蘇軾在詩文中也數次憶及那一幕幕溫暖而感人的片段。

風起于青萍之末。北宋時期,濟南就以山水之美名滿天下。蘇轍于1073年“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自請而來,任齊州掌書記。
《濟南通史 宋金元卷》記載:“到神宗熙寧時,蘇轍出任齊州掌書記,蘇軾則知密州,并兩次經過濟南。”
“四海一子由”,蘇轍的到來,牽動了遠在杭州任通判的蘇軾。任期一滿,蘇軾奏請神宗“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蘇轍《超然臺賦序》。東州就是京東路,統領密州、齊州等八州;他甘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蘇軾《超然臺記》;他在《密州謝上表》中坦言:“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宦游無定,羈旅南北,親情是撫慰心靈的良藥。
天遂人愿,蘇軾于1074年底來到與濟南數百里之隔的密州任職。事有湊巧,當時密州蝗災嚴重,“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齊州(濟南)正是“大旱幾歲,赤地千里”。 一心“致君堯舜上”的蘇氏兄弟全身心投入了賑災救濟工作,遲遲未能會面。
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如影隨形。在詩人的筆下,則是幸福的憂傷。“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自杭州赴密州途中,蘇軾馬上賦詩,以陸機、陸云自比;“休對故人思故國”,密州“超然臺”(蘇轍命名)上蘇軾暏物思人;寫于密州的“兼懷子由” ——“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成為中秋祝福的千古絕唱。
“平野水云溶漾,小樓風日晴和。濟南何在暮云多。歸去奈愁何?”極目遠眺,原野平闊,水天一色,波光粼粼,那樓頭風和日麗。西望齊州,盡是離愁,“暮云多”讓詩人淚朦朧眼朦朧。“歸去”則指此前二人相約“夜雨何時聽蕭瑟……慎勿苦愛高官職”。1076年九月,蘇軾寫下《畫堂春 寄子由》。
如果說蘇轍來濟是山水為媒,那么,蘇軾來濟更多的是親情召喚。“不思量,自難忘”“天公為下曼陀雨”“每逢暮雨倍思卿”。詩人對親人的思念,雖經千年,仍直抵人心魅力不減。
馬蹄嗒嗒,雪地泥濘,蘇軾姍姍來遲。
有人推測,這是蘇軾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信息不暢,路遇大雪,旅途受阻,在濰州(今濰坊)度過了除夕,初一雪剛停便立刻上路,結果再遇大雪,只能在泥濘中艱難跋涉。
雖沒能見到心念已久的弟弟,蘇軾的心情應是愉悅的。征途漫漫,人馬疲憊,他遠遠望見了迎接他的蘇家孩子們,蘇遲、蘇適、蘇遠三個侄兒恭立雪中,翹首企盼,等候伯父的到來。兩家人終于相聚了,杯盞交錯,共敘家常,其樂融融,這足以重溫蘇家久違的暖意。
“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雪里。我時移守古河東,酒肉淋漓渾舍喜。”《將至筠先寄遲適遠三猶子》。多年后,他回憶當年赴濟場景,字里行間盡是滿滿的喜悅和感動。
蘇軾首次濟南之行,有遺憾也有驚喜。蘇軾與蘇轍兄弟,兩位“大咖”失之交臂,文壇少了一次 “雙星會”,濟南少了一場文化盛事。
瑕不掩瑜,幸好時任齊州知州的李常(字公擇,北宋著名詩人黃庭堅的舅父),是蘇軾故友。兩人志趣相投,“相好手足侔”。 三年前曾有過一次激動熱烈的相會。老友久別重逢,喜不自勝,他們話往昔歲月,吐心中塊壘,歡飲達旦,詩酬唱和。
“敝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宦游到處身如寄,農事何時手自親。剩作新詩與君和,莫因風雨廢鳴晨。”他描述抵達濟南時的窘態,裹著破氈,騎著瘦馬,忍不住想起了在北海渴飲雪、饑吞氈的蘇武前輩。他以李白自喻,慨嘆宦海沉浮,與老友互訴衷腸。
“夜擁笙歌霅水濱,回頭樂事總成塵。今年送汝作太守,到處逢君是主人。聚散細思都是夢,身名漸覺兩非親。相從繼燭何須問,蝙蝠飛時日正晨。”往事不堪回首,聚散皆是夢。《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
透過這珍貴的詩文,可以略略感受946年前濟南那個空氣里都彌漫著詩意的春天。名滿天下的蘇軾,所到之處皆詩意。
在此期間,蘇軾曾與李常策馬暢游龍山,欣然寫下《答李公擇》:“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斷腸聲。”
雪后初霽,春光正好,摯友相伴,策馬揚鞭,來到濟南城東龍山鎮,心情豁然開朗。 “馬足輕”應脫胎于王維“雪盡馬蹄輕”, 與“雪初晴”相照應,即景即事,借物寫人。后兩句溫馨中有戲謔,以“請客對主”的巧妙技法,道出與老友的惜別離,情趣盎然。
此行,蘇軾還在李常、晏幾道等人的陪同下游覽了檻泉,觀賞了檻泉旁的梅花,并“寫枯木一枝于檻泉亭之壁”(見《濟南金石志》卷四),劉詔曾將其模勒于石。對這“枯木一枝”解讀眾說紛紜。有“題字說”:題寫四字。還有“畫畫說”:畫枯木一枝。還有的推測已流失。
原記載在《禹城縣志》中,后收入乾隆《歷城縣志》的說法是:“趵突泉“枯木一枝”石刻”:北宋,趵突泉時稱“檻泉”,位于寺丞劉詔家庭院內。熙寧十年蘇軾游檻泉亭墻壁上寫下“枯木一枝”四字,后來劉詔讓人刻石。此石刻后來輾轉到了禹城文廟中,因前來求字或摩拓的人太多,當地官吏怕得罪人,索性把刻石扔進井中,碎為數塊。再后來,有人撈出碎石比著筆跡制成木版,可字跡卻失去神韻。
這“檻泉”即今之趵突泉,幾易其名。宋代曾鞏出任齊州知州時,為趵突泉取名“檻泉”。“檻泉”典出《詩經》“觱沸檻泉,維其深矣。”但濟南百姓卻因“檻泉”之稱太雅,直接棄之不用。金代元好問在《濟南行記》中記載道:“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濟南百姓仍叫它“爆流泉”,后稱趵突泉。
“更憶檻泉亭,插花云髻重。蕭然臥灊麓,愁聽春禽哢。”對這次客居濟南期間的檻泉之游,蘇軾印象極深,《蘇軾集卷十一》《次韻李公擇梅花》。并追憶與李常詩文往來之趣“忽見早梅花,不飲但孤諷。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疼。”
更為難得的是,濟南一行不僅深植在詩人記憶中,漸漸成了心中的牽掛。“每思檻泉之游,宛在目前。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蘇軾集卷八十》《與幾道宣義》,詢問濟南有無水患?
蘇子之與濟南,何曾是初見,夢里心中,已是多少歲歲年年。
當年二月初一這天,蘇軾行經位于王舍人莊的張掞(字文裕)故宅,并手書“讀書堂”三字,鼓勵張世后人承繼家風,讀書傳世。不久后,當地人即據蘇軾手書刻石為碑。
元好問《濟南行記》云:“繡江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后來,該碑不知何故被埋入地下。明萬歷初年,村民在修房挖宅基的時候復將其挖出,后被運往歷城縣學文廟,作為鎮廟之寶立于縣庠橋門外,以激勵后世學子讀書精進。
這位張掞非等閑之輩。齊州歷城人,進士出身,是北宋時期重臣。乾隆《歷城縣志》推測,或許是元好問誤將“范純仁”(范仲淹次子,元豐四年(1081年)知齊州)寫成了“范純粹”,因在范純仁《宣忠公集》能找到《張掞侍郎讀書堂》詩:“三紀仁皇侍從臣,當時文學動簪紳。高明已入儒林傳,舊室長存歷水濱。峴首空留王粲宅,香山猶識白公真。他年遺跡應無廢,不墜詩書世有人。”

據考,詩中“歷水”就在濟南市東,“歷水出歷祠(在舜井旁,北宋后改名為舜祠)下,泉源競發,與濼水同入鵲山湖。”《水經· 濟水注》《寰宇記》。
細讀范詩,可以看出張掞其人很得皇帝倚重,且文名很盛,并在當時就已經被寫入傳記評說;而且張掞在泉城濟南歷水邊上有一所名宅,這所宅院也非常有名,可以和“峴首詩人王粲宅”以及洛陽香山白居易的白園相媲美;詩人想象著多年以后張家宅院會依然存在,張家后人將世世代代保持著詩書繼世的家風傳統。
張掞外,他還有一個哥哥叫張揆,“性剛狷,闊于世務”,官至右諫議大夫,獲進龍圖閣直學士,曾任皇帝侍讀。“一門雙學士”,兄弟二人因為道德文章受世人所重。1073年,蘇轍任齊州掌書記,次年,張掞過世,蘇轍作《張文裕侍郎挽詞》詩悼念他;1077年,蘇軾來到齊州,親往吊唁張掞,作詩《張文裕挽詞》“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空推德業馀。每見便聞曹植句,至今傳寶魏華書。濟南名士新凋喪,劍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以其深切之情表達了對其才學品行的景仰和朝廷痛失良材的惋惜。
蘇軾首次來濟,盤桓一月有余,再來已是十年之后。
蘇軾一生仕途蹭蹬,宦海沉浮,行跡如風,有人說不是被貶或流放,就是在被貶或流放的路上。
這不,登州一任就如“走馬燈”。元豐八年(1085)六月,蘇軾奉旨知登州(治所在今蓬萊市)軍州事,再次踏上了齊魯大地,并于十月十五日抵達登州任所。誰知朝廷政局多變,改革派與保守派幾易其手,受其影響,任命朝令夕改。僅在五天之后,蘇軾又接到了要他進京擔任禮部員外郎的任命。
于是,他只好于當年11月初匆匆地離開了登州,趕赴汴京(即今河南開封)。冥冥之中,似有前緣,在赴京途中,蘇軾第二次來到了濟南。
上次,親友相聚、檻泉留墨、策馬龍山,對“好客濟南”頗有好感,因“嗨”得很,盤桓達一月有余。這次仍為過客,行色匆匆,但有備而來,不顧旅途疲憊,馬不停蹄,城西拜佛,城東訪友,興致勃勃。
有緣處遇有緣人。家風熏染,蘇軾早年喜佛、青年游禪、中年近禪、老年逃禪。他與佛印“互損”的故事傳播甚廣。傳說他上朝時服裝不同尋常,皇帝暗中打聽,方知他內穿僧衣。他的詩意境達觀,外儒內禪。
正是這位有緣人,1085年12月路經長清縣時,吸引了眾多“蘇粉”追捧。長清縣真相院(位于長清老城區西北隅)住持法泰是其中一位,他誠邀蘇軾到真相寺一敘。法泰熱情有加,加之蘇軾本有佛緣,真相院喜氣臨門。當蘇軾得知法泰所建十三層磚塔(名全陽塔,今已不存)未有葬物,便想將蘇轍所藏的釋迦舍利捐獻出來,為已過世的父母祈求“冥福”。法泰聽后當然是求之不得,只是當時蘇軾急急趕赴京師上任,并未留一物。
這位法泰是個行動派,說干就干。第二年就赴京師找蘇軾拜請法舍利,并請蘇軾撰寫塔銘。出于對佛的虔誠和對父母的敬重,他一改往日的隨意灑脫,鄭重其事地寫下了《齊州長清縣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敘)》,然后又贈法泰“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眾人,以具棺槨”。宋元祐二年(1087),法泰又將東坡書跡刻勒于石。
此事在《塔銘》中來龍去脈記載詳實。“八年,移守文登,召為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真相院,僧法泰方為磚塔,十有三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于此耶。”蘇軾表達了捐贈舍利子的初衷和愿望。
有感于父母的恩典,他寫道“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舍所愛作佛串,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這位千年才有的大才子,也是一位大孝子。
該刻石于1965年在全陽塔地宮中出土,現被長清區博物館珍藏。從保存的碑刻看,書刻精湛,用筆豐腴跌宕,結體天真爛漫,字字神完氣足,如珠似璣,堪為蘇軾書中逸品。
法泰去世后,真相院的繼任住持文海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也據東坡書跡刻石一塊,這塊刻石現亦存于長清區博物館。只是由于歷代摩拓過多,其形神俱遜于法泰刻石。因有復刻,故市場所見拓片有兩種。
好客長清喜獲至寶,“舍利子”本是無價,蘇軾墨跡在當時已是一字難求,這篇楷書《塔銘》更是珍品難得。
蘇軾此行的另一站,是龍山鎮(今屬章丘)看望時任龍山監鎮的宋寶國。這位“小宋”頗受王安石器重,當時,宋寶國把王安石所書的一卷《華嚴經解》給蘇軾看,并請蘇軾為之作跋。蘇軾因此作了《跋王氏華嚴經解》一文《蘇軾集補遺》。
蘇軾記述龍山論佛:“濟南龍山鎮監稅宋保國出其所集王荊公《華嚴解》。余曰:“《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曰:“公謂我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曰:“予于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這佛語與菩薩語撲朔迷離,難辨真偽。
腦洞大開的蘇子,設譬取喻,現身說法,“非獨子不能,荊公亦不能也。予昔在岐下,聞汧陽豬肉至美,使人往致之。使者醉,豬夜逸,買他豬以償,吾不知也。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言外之意,諷荊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嘴不饒人的蘇仙意猶未盡,直接“吐槽”。“今荊公之豬未敗耳。屠者買肉,倡者唱歌,或因以悟。子若一念清凈,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大意,現在王荊公所認為的這些佛語就像那頭作為替代品的豬一樣,只是事情還沒有敗露罷了!至于說佛語深妙、菩薩語比不上,難道不是像夢話一樣嗎?宋寶國點頭稱是。
真不知這段話,荊公聽后作何感想。推理,這觀點應很快傳到王安石的耳朵里,因在當時通訊極不發達的情況下,蘇軾無論身在何處,他的詩文片言總能像插了翅膀飛到京城,可見蘇子“當紅”名重當朝。
蘇軾既是文壇巨擘,又是一代宗師。“蘇門后四學士”之一李格非為濟南市章丘人。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蘇軾在京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時李格非在京任太學錄之職,經常持詩文習作請教蘇軾。
《宋史》和《濟南通史 宋金元卷》記載: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蘇軾”。雙方建立了密切的師生之誼,元豐六年(1083年),蘇軾被貶謫到黃州時,李格非前往拜訪。紹圣元年(1094年),蘇軾被貶惠州,生活困窘,李格非特意致函慰問。足見師生情義深厚。
李格非詩文均好,尤以文為佳。論文尚“氣”,尚“誠”,還尚“橫”,皆承東坡衣缽。李格非言:自漢后千年,唯韓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即蘇軾)《筼筜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張邦基《墨莊漫錄》)。對蘇文欽佩之情溢于文中。
文脈綿綿不斷。“渾涵光芒,雄視百代”的蘇風鑄就了格非“橫”文,格非以其家學淵源滋養了“一代詞宗”李清照,細品其詞,豈只于“婉約”,那“生當作人杰”骨子里就是“大江東去”的豪邁。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蘇子兩次濟南行,其碑刻、詩文等成為濟南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蘇軾一生如雷似風,少年及第,名動朝野,烏臺詩案,大難不死,宦海游歷“黃州惠州儋州”。 何止于此,還有“齊州密州徐州”。
為什么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個蘇東坡,人性之美成就了詩神。誠如林語堂先生所言,蘇東坡“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鴿子的溫厚敦柔”。
覓“轍”跡——蘇書記不薄吾州
占盡物華的濟南,英才輩出,名士薈萃。大舜、鄒衍,神醫扁鵲,梟雄曹操,賢相房玄齡,義士秦瓊,詩人李白、杜甫、“二安”,燦若群星。
繼曾鞏離開濟南數月后,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秋,濟南有幸迎來了另一位文壇大家蘇轍,任“齊州掌書記。”三年任期,情系濟南的“蘇書記”,上憂其君,下憂其民,踏遍青山,情注筆端,留下了數以百計的詩文。籍此,盡可回望千年前濟南風物和人文景觀。
“書記”古指文體,后演變為文字之士,至唐大抵相當于秘書長,至宋各州設“掌書記”一職,府衙屬官,掌管箋奏公文。自蘇轍始,掌書記的地位逐漸提高。
“蘇書記”原本慕名而來,他在《舜泉詩并敘》中坦陳心跡,“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東方之人多稱之。”贊濟南為泉水之鄉、魚米之鄉,直勝江南。“東方”指齊魯之地。
“歷山巖巖,虞舜宅焉。”這“舜泉”位于舜祠下 ,在宋代與舜祠一起成為濟南的重要名勝。
“灌濯播灑,蒲蓮魚鱉,其利滋大。”“連宵暑雨源初接,發地春雷夜有聲。”舜泉復噴讓詩人欣喜若狂激動不已。“有洌斯泉,下民是祗。泉流無疆,有永我思。源發于山,施于北河。播于中逵,匯為澄波。有鱉與魚,有菱與荷。”他以細膩筆觸詠贊這造福蒼生的泉水。與詩圣“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愛民情懷一脈相承。
眾泉之首趵突泉(古為檻泉)千年之前的景色,借助蘇轍《檻泉亭》得以還原。“連山帶郭走平川,伏澗潛流發涌泉。洶洶秋聲明月夜,蓬蓬曉氣欲晴天。”連山帶郭,洶洶蓬蓬,泉水、秋聲、月色構成一幅絕妙的園林畫。“誰家鵝鴨橫波去,日暮牛羊飲道邊。滓穢未能妨潔凈,孤亭每到一依然。”生動而俏麗,盡顯田野風光。孤亭煢煢獨立,結尾一嘆,也是一種藝術“缺陷美”。
“蘇書記”齊州任上風物入胸懷,才思滾滾來。在《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并敘〉》中,稱李公“愛其山川泉石之勝,怡然有久留之意。此邦之人,安公之惠,亦欲公之久于此也。”贊山水形勝和濟南人的熱情好客。結尾處“安邊本余事,清賞信良圖。應念茲園好,流泉海內無。”情景兼容,堪為經典,寫出了濟南獨一無二冠蓋天下的美。
此詩為蘇轍在熙寧七年(1074)二月齊州任上所作。題目中的“西湖”為大明湖的曾用名。大明湖在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中稱“歷水陂”,唐時又稱蓮子湖。北宋文學家曾鞏稱“西湖”“北湖”。金代文學家元好問在《濟南行記》中始稱“大明湖”。
波光瀲滟大明湖,生動有趣的勞動場景,詩人陶醉其中,詩興大發。春風送暖、柳色嫩黃。詩人徜徉在大明湖畔,興致勃勃地看農人踏藕:“春湖柳色黃,宿藕凍猶僵。翻沼龍蛇動,撐船牙角長。清泉浴泥滓,粲齒碎冰霜。莫使新梢盡,炎風翠蓋涼。”
夏日炎炎,明湖泛舟。詩人饒有興趣地觀看漁人捕魚:“西湖不放長竿入,群魚空作淘河食。漁人攘臂下前汀,蕩漾清波浮兩腋。藕梢菱蔓不容網,箔作長圍徒手得。逡巡小舟十斛重,踴躍長魚一夫力。柳條穿頰洗黃金,會縷堆盤雪花積。燒薤香橙巧相與,白飯青蔬甘莫逆。食罷相攜堤上步,將散重煎葉家白。人生此事最便身,金印垂腰定何益。”
秋風習習,湖上“野炊”。詩人與友人煮食采自湖中的芡實:“芡葉初生縐如谷,南風吹開輪脫轂。紫苞青刺攢猬毛,水面放花波底熟。森然赤手初莫近,誰料明珠藏滿腹。剖開膏液尚模糊,大盎磨聲風雨速。清泉活火曾未久,滿堂坐客分升掬。紛然咀噍惟恐遲,勢若群雛方脫粟。東都每憶會靈沼,南國陂塘種尤足。東游塵土未應嫌,此物秋來日嘗食。”
“西湖”處處留“轍跡”。其《北渚亭》詩:“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攜上古城。”北渚亭就是大明湖東北的北水門,也是濟南老城的古城墻,而百花汀即大明湖南門外的百花洲歷史文化街區。“云放連山瞻岳麓,雪消平野看春耕。臨風舉酒千鐘盡,步月吹茄十里聲。猶恨雨中人不到,風云飄蕩恐神驚。”依稀可望“西湖”外大片田野,登高望遠,群山起伏連綿,把酒臨風,思緒萬千,好一派田園風光、西湖美景。這般氣象,不知詩人可否賞到“西湖”中的“佛山倒影”。
“濟南風物在西湖,湖上逢公初下車。”“西湖”——已成為詩人托物寄懷遣興的意象。
因烏鵲翻飛、扁鵲煉丹和古戰場等故事聲名鵲起的鵲山,是古文人雅士的“網紅打卡”地,“蘇書記”自有游興。“筑臺臨水巧安排,萬象軒昂發瘞埋。南嶺崩騰來不盡,北山斷續意尤佳。”在《鵲山亭》詩中,詩人見景生情,寓情于景,“平時戰伐皆荒草,永日登臨慰病懷。更欲留詩題素壁,坐中誰與少陵偕。”稽古勾沉,發微抉隱,感慨萬端。
濟南南部山區更是“蘇書記”心中的期待。“自我來濟南,經年未嘗出。不知西城外,有路通石壁。初行澗谷淺,漸遠峰巒積。翠屏互舒卷,耕耨隨欹側。云木散山阿,逆旅時百室。茲人謂川路,此意屬行客。”這首《初入南山》,是蘇轍在南部山區,循群山中崎嶇道路,直抵泰山北麓。“久游自多念,忽誤向所歷。嘉陵萬壑底,棧道百回屈。崖巘遞崢嶸,征夫時出沒。行李雖云艱,幽邃亦已劇。坐緣斗升米,被此塵土厄。”層巒嶂迭,幽谷深澗,詩人疑似走在故鄉蜀道的峰壑之中,不禁發出“何年道褒斜,長嘯理輕策”的浩嘆,“褒斜”為漢中入蜀之路。
中國四大名剎之一——靈巖寺,聲名遠播,早有佛緣的蘇轍過靈巖寺專門寫有《題靈巖寺記》“青山何重重,行盡土囊底。巖高日氣薄,秀色如清洗。”寫靈巖勝景。“居僧三百人,飲食安四體。一念但清涼,四方皆兄弟。何言庇華屋,食苦當如薺。”述僧眾寮房。碑刻尚存,清晰可見,落款為“題靈巖寺 眉陽蘇轍”。其石刻半米見方,結字扁平、筆畫舒展,書風頗似“蘇體”,許是書丹者用心而為。“眉陽”即四川眉山,其兄也常以“眉陽蘇軾”自稱。

春去春又回。詩人的足跡從靈巖寺到“四禪寺”(遺址在長清區張夏鎮),“山蹊容車箱,深入遂有得。古寺依巖根,連峰轉相揖。樵蘇草木盡,佛事亦蕭瑟。居僧麋鹿人,對客但羞澀。”在這首《四禪寺》詩中,他描寫了當時寺院已是佛事蕭瑟,僧侶竟羞于見人。遂又敘述了義凈法師不遠萬里取經、親手譯經、刻碑、傳法等情景。最后感嘆“粲然共一理,眩晃莫能識。末法漸衰微,徒使真人泣。”
“轍”行未遠,回響仍在。現“四禪寺”遺址(含大殿、刻石)為濟南市文物保護單位。“四禪寺”附近有一個車箱峪村,源于“山蹊容車箱”。“轍”與“車”就這樣巧合在一條崎嶇的山路上,流傳至今。
“蘇書記”任職期間,濟南城市建設兩件大事賴其之功完好傳承至今。一是建濼源石橋,記載在《齊州濼源石橋記》中。他以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介紹了建橋的主要過程,起因是“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于城下,橋不能支,輒敗。”方法是“取石于山,取鐵于府,取力于兵。”效果是“三跌(橋墩)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為虐。”還給我們總結出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于民,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利益與百姓共享,費用量化分配,法令寬大,故事易成。二是修閔子騫紀念祠,記載在《齊州閔子祠記》中。建祠背景是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將有舉焉而不克……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缺?”有墓無廟,祭祀不便,鄉賢們對閔子騫不能配享寺廟很遺憾。落成后“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洟,淚也,觀禮人涕淚交加。為這兩件事專門作記,也體現了“蘇書記”關心民本民生的施政意旨。
蘇轍因慕濟南甘泉流水而來,孰料趕上齊州“大旱幾歲,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上任伊始,就助知州賑災安民,馬不停蹄。
“肝膽皆冰雪”。任上,蘇轍和曾鞏一樣,以其冠蓋于世的才華“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抒寫對濟南山山水水的熱愛。
翻閱“蘇書記”這些珍貴的詩文,我們可以多維度了解當時濟南生態和人文環境。“岱陰皆平田,濟南附山麓。山窮水泉見,發越遍溪谷。分流繞涂巷,暖氣烝草木。下田滿粳稻,秋成比禾菽。池塘浸余潤,菱芡亦云足。”《寄濟南守李公擇》。可見彼時:河湖環繞,池塘浸潤,水稻種植極為普遍,菱芡等水產蔬菜十分豐富。
再如,宋元時期黃河多次決口,每次都波及濟南。如熙寧十年(1077)秋七月,“河決于澶淵,東流入巨野,北溢于濟南。”對農業生產和生態環境帶來嚴重影響“河之所行,利害相伴: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為之破稅,此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言簡意賅,兼論利害。
清代大詩人王士禛在讀了蘇轍詩作之后,感嘆:“其于吾州亦不薄矣!”
“不薄”濟南,還表現為“蘇書記”是“社牛”型官員。盡管“三年政令如牛毛”“宦游少娛樂,纏縛苦文案”,但這位“秘書長”與三任知州配合默契,成為彼此惦念的好友。“相對各忘歸,西來自嫌速”。與當地文士頗多交友。熙寧七年(1074),作《送張正彥法曹》,稱“憶見君兄弟,相攜謁侍郎”,由此可知蘇轍曾拜謁張掞。與歷城人徐遁有交往,曾有《題徐正權秀才城西亭》詩。徐遁做《祭閔子文》,受到蘇轍贊賞。
濟南堪稱蘇門福地。熙寧七年(1074)蘇轍的幼子蘇遠在濟南出生。因適逢寅虎,虎年得虎子,蘇轍為其取乳名“虎兒”。正在赴密州知州任途中的蘇軾聽說此事后,立即作《虎兒》“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于菟。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蘇轍以《和子瞻喜虎兒生》相和:“生男如狼猶恐尪,寅年生虎慰爺娘。汝家家世事文史,門戶豈有空剛強。”有趣的是,這位有世上“最暖二胎”之稱的小弟詩尾不忘幽他一默,“我今老病思退藏,生子安得尚激昂。不見伯父擅文章,逡巡議論前無當。”“老病”實為自嘲,時年蘇轍36歲,充其量中年得子,狂贊其兄,既有“吾兄筆鋒雄,詩俊不可和”之敬,也有省人之意,提醒嘴不饒人的哥哥謹言慎行。
北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十月,蘇轍離開濟南赴京(開封),等候吏部銓敘。
如其兄,蘇轍一生宦海沉浮,羈旅匆匆,宦局濟南三載成了他的“溫馨之旅”,“我生本西南,為學慕齊魯。從事東諸侯,結綬濟南府。”“遠游既為東魯,遷居又愛南山。”也是他的“開心一刻”,“舜井溢流陌上,歷山近在城頭。”“野步西湖綠縟,晴登北渚煙綿。蒲蓮自可供腹,魚蟹何嘗要錢。”“飲酒方橋夜月,釣魚畫舫秋風。冉冉荷香不斷,悠悠水面無窮。”“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烝。勝處何須吳越,隨方亦有游朋。”在他與表兄弟文與可的詩文酬唱中,大“秀”濟南時光,盡是滿滿的幸福和喜悅。
比照看,蘇軾的光芒讓蘇轍生活在影子里,其實,在很多方面,“兄弟不必不如兄”,在政治成就方面,蘇轍官至副宰相,接近權力中樞;在學術方面,著有《欒城集》等九十六卷;在人格魅力方面,以其“謹重自持”不同與其兄“明敏尤可愛”,就是反對他的人,如蔡京也稱贊蘇轍“沉毅自重,令人敬佩”。“扶軾瞻遠,顧轍思由”,果如其父所言。
憶“南豐”——深夜“溜”走的知州
場景:“大人——您不能走啊!”烏泱泱的人群簇擁著一位老態盡顯身著官服的人,人群中呼喚的聲音此起彼伏,幾位近前的老者情難自已,聲音里帶著哭腔。
“鄉親們——圣命難違呀!”大人滿含深情地向自發前來“送行”的鄉親們鞠躬施禮。
依依不舍間,城門被緊緊關閉,吊橋被高高吊起,天色不早,大人無奈回府。入夜,街衢漸靜,大人匆忙離濟而去。
“及代去,州人絕橋閉門遮留之,至夜乘間乃得去”《歷乘》。952年前,在濟南就有這樣一位離任時夜間“溜”走的“父母官”。此人曾鞏,字子固,北宋時期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雅號南豐先生。北宋熙寧四年(1071)六月任齊州(今山東濟南)知州,兩年任職期間,因廣行善政、政績卓著,深受百姓愛戴。
沒有哪一座城市能像濟南將湖、山、泉、林揉為一體,自成一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一向被認為是濟南“城即園林”的經典描述,這一格局定型于宋元,奠基于曾鞏主政期間。
馴龍有術,“北水門”變成“幸福門”。齊州城地勢南高北低,南面為山,北面有河,城中泉眼星羅棋布,匯聚成渠縱橫交錯。“水龍王”稍不如意便大發脾氣,“若歲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則常取荊葦為蔽,納土于門,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堅完,又勞且費。”每逢雨季,泉水猛增向北匯聚,而北面水系又會向城內泛濫,因此城北門(大明湖北岸,宋以前稱歷水陂)附近常常陷于水困。曾大人勘察地形水勢,因地制宜,綜合施治,“龍頭工程”放在城北舊水門改建上,他“以庫錢買石,僦民為工”,從府庫撥出專款,雇傭民工,用石頭壘砌了兩岸,中間置以石楗,安上了兩大扇木門,并“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這種木石結構可以視水位漲落開啟閘門,歷史性的突破在于既可由北往南自主排水,又可防止外水回灌,如此一來,大明湖就成了可以調節水位的天然水庫,城北平原不僅免受水患,還能就地取水灌溉,“北水門”成了造福南北的“幸福門”,“ 水龍王”低頭伏法,齊州城北再無水患之憂。
“內外之水,禁障宜通,皆得其節,人無后虞,勞費以熄。”懷著欣喜之情,他寫下《齊州北水門記》。
老濟南原有四個城門。古代,由于濟南的東、西和南、北門都不在一條軸線上,北門為水門,所以有“四門不對,北門不開”的說法。而今,唯有北門尚存,這就是大明湖東北隅的匯波門。這北水門就是當年曾鞏所建。
曾堤縈水,“百花洲”直勝“桃花源”。當年,大明湖南門牌坊以南有一大片雜草叢生的水塘,叫“百花洲”, 曾鞏在州內建造了“百花臺”,在臺周圍廣植花木,本是“美人胚子”,一番巧梳妝,更是風景絕佳。曾鞏詩贊“煙波與客同樽酒,風月全家上采舟。莫問臺前花遠近,試看何以武陵游。”在詩人眼中,百花洲分明是武陵桃花源仙境了。
同時,曾鞏還利用疏浚大明湖時挖掘出的泥沙,修筑了一條貫通南北岸的長堤——百花堤,將湖水隔為東、西兩部分。這段路徑,人們親切地稱為“曾堤”。
拂堤煙柳醉春煙。踏青時節,大人從百花洲棄船登百花堤,登臨北渚亭,寫下《百花堤》“如玉水中沙,誰為北湖路。久翳荒草根,未承青霞步。我為發其枉,銹營極幽趣。發直而砥平,驊騮可馳騖。周以百花林,繁香泫清露。間以綠楊陰,芳風轉朝暮……”從詩里可知,這一帶曾荒草萋萋,整治后“筆直平坦,可馳駿馬,兩邊植樹花,間以綠柳,清露芳風,怡情興”。可騎馬賞景,不亦樂乎。
杭州“蘇堤”晚于“曾堤”17年建成,言蘇軾是在濟南看到了百花堤受到啟發,應不是噱頭。
2009年,大明湖新區擴建,將小東湖擴進大明湖,湖內近岸廣植荷蓮,與湖畔垂柳相映生輝。為紀念曾鞏,擴建中將南豐橋與南豐祠之間的一段路命名為“曾堤”,堤上楊柳垂蔭,百花飄香,堤兩側湖水縈岸,波濤陣陣。這一新建景觀,稱之為“曾堤縈水”, 天下第一泉風景區明湖新八景之一。
有亭翼然,湖光山色收眼底。熙寧五年(1072),來濟后的次年,曾大人在北城墻上修建了北渚亭。該亭十分壯觀,飛梁和重檐好似籠罩在太空中一般,如人間仙境,置身其中湖光山色一覽無余。
后任掌書記的蘇轍贊嘆“云放連山瞻岳麓,雪消平野看春耕” 。二十多年后,晁補之出知齊州,登上北渚亭舊址,只見“群峰屹然,列于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
此亭元代中葉后廢圮蕪沒,遺跡無存。清初詩壇領袖王士禛在《香祖筆記》中云:“據蘇穎濱《北渚亭》詩,當在北城之上無疑。”
七橋風月,眾星拱衛詩意濃。曾大人又沿湖及泉渠間砌石筑橋,修建了鵲華、百花、芙蓉、水西、湖西、北池、濼源七座各具風格的石橋,將湖水泉溪勾連在一起,這一逶迤綺麗、水波蕩漾的詩意景觀,被稱為“七橋風月”。臨橋眺望,湖水迂回曲折,迤邐伸展。朝煙暮靄之際,湖上煙霧繚繞,七橋如虹似月,出沒其間,恍若人間仙境。
“將家須向習池游,難放西湖(即大明湖)十頃秋。從此七橋風與月,夢魂長到木蘭舟。”“誰對七橋今夜月,有情千里不相忘。”曾鞏離濟后,對此景深情依舊。大明湖擴建后,由秋柳橋代替濼源橋,其余全部恢復重建,再現“七橋風月”景觀。
絕妙的是,大人還在大明湖東岸、南岸,修建了仁風廳、靜化堂、芙蓉堂、名士軒、凝香齋、水香亭、采香亭、環波亭、芍藥亭等數處亭閣水榭,使之點綴于湖光山色之中,與七座石橋構成了眾星拱月的美妙景觀。讓這方“紫荷香里聽泉聲”的人間樂土擁有了更多詩情畫意。
曾大人雖一介儒生,但頗具文韜武略。且不畏強暴,嫉惡如仇。掃黑治亂,自有錦囊。
“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資雄里中。周氏子高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污人婦女,服器擬乘輿。”齊州曲堤有戶周姓人家,是當地名門望族,周家子弟周高依仗家勢在鄉中為非作歹,成為一害。曾大人上任不久,果斷將周高拿下“取置于法”,而周氏家族自知理虧竟也未敢再生枝節。
“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橫行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者。”歷城和章丘有個令百姓膽寒的“霸王社”,橫行鄉閭多年,盜竊財物、劫車奪囚、無惡不作。曾大人先以雷霆之勢抓捕流放了其中的31人,又組織村民結成保伍,聯合巡查剩余盜寇,凡有盜賊出現就擊鼓傳遞消息,相互聲援形成合圍。如此一來,盜寇每次行動都會有人被捕。
“有葛友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其中有個叫葛友的,不堪追捕之苦,主動向官府自首。曾鞏又施妙計:他為葛友安排了幾名“隨從”,令其鮮衣怒馬鄉中巡游,這一示范效應立竿見影,其余盜匪見狀也紛紛自首,“霸王社” 迅速瓦解。
“為生民立命”。這曾大人心憂天下,關注民生。熙寧六年(1073年)春,河北山東集役疏浚黃河,齊州當出役兩萬人,每戶有二至三個男丁出夫役,這嚴重削弱生產力。曾鞏適時改變政策,出臺“九丁出一夫”新令,留下勞力,讓出役的人安心,有效地解決了役征和勞動力的矛盾。

懲治惡霸,抑制豪強,在其治下,齊州“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跡,州部肅清,無枹鼓之警,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百姓徭役負擔減輕,齊州出現了“市粟易求倉廩實,邑猶無警里閭安”的和諧景象。
“繼往圣之絕學”。曾大人作為地方主官,興學重教,振興齊州《尚書》之學。同時作為文章鉅公,以其嚴謹的治學精神勘正典籍錯訛,使文脈道統傳承有序。
為歷山“落戶”。經考辨否定了此前盛行的“舜耕歷山”之“歷山”為河東歷山(位于今山西境內)之說,并說:“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
為“第一泉”命名。第一次將“趵突泉”之稱用文字記載下來。此前稱“溫泉”或“瀑流泉”,民間俗稱“噗嘟泉”,曾鞏依“噗嘟泉”之稱寫為“趵突泉”,文雅頓現,沿用至今。
為泉源正名。曾鞏到濟南時,有關泉水之源的流行說法,是濟南位于濟水之南,泉水“為伏流于地下的濟水所發而成”。大人數次到南部山區考察,反復試驗,最后終于摸清了泉水的來路,在其《齊州二堂記》中寫道:“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趵突泉的泉水來自南部山區。對其他名泉大人親自做了試驗:“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現代技術手段驗證了曾鞏的判斷。
源于對濟南山川風物的熱愛,齊州任職年,亦是這位文壇大家的創作豐收年。曾鞏《元豐類稿》收錄有關齊州任上的文有10余篇、詩達70余首。
“行到市橋人語密,馬頭依約對朝霞。”“市井蕭條煙火微,兩衙散雪夜深時。”籍此,可以看到950多年前老濟南的早市和夜景,可以窺測當時商業繁榮程度。
“一派遙從玉水分,暗來都灑歷山塵。滋榮冬茹溫常早,潤澤春茶味更真。已覺路傍行似鑒,最憐沙際涌如輪。曾成齊魯封疆會,況托娥英詫世人。”曾鞏詠泉詩最著名的當屬這首《趵突泉》。
“南狩一時成往事,重華千古似當年。更應此水無休歇,余澤人間世世傳” 曾大人贊大舜居功至偉,深情寫下《舜泉》。
“左符千里走東方,喜有西湖六月涼。”這“左符”即是大人上任時手持的符契,不遠千里而來,炎炎夏日幸有西湖(大明湖)可以納涼。
齊州任上,大人嘔心瀝血, “自強柔弱,頗殫竭蹙之勞。”“漾舟明湖上,清鏡照衰顔。”大明湖水為鏡,映照著他因操勞過早衰老的容顏。
念念不忘,終有回響,這回響來自百姓心底。早在明初正統年間(1447年前后),人們就在千佛山半山腰上修建了曾公廟,廟中祀曾公像。后來,人們又在大明湖修建了“南豐祠”,開設了“曾鞏展覽館”。峨冠博帶,儒雅瀟灑,凝視著南豐雕像,緬懷、景仰之情在心中升騰。
這世上,有一種光亮,遠隔千里,卻給人以方向。這世上,有一種力量,遠隔千年,卻給人以堅強。愛不夠的蘇軾,道不盡的蘇轍,寫不盡的南豐。今天,在百花洲,在大明湖畔,濟南之南、經緯之間,仍可尋覓到他們的足跡,感受到他們卓越非凡的才思和悲天憫人的情懷。
這正是:古城千年,造化自然。倚山抱泉,物華獨占。人杰地靈,千祥云集。近悅遠來,明星璨璨。一代文豪,睿藻仙才。二臨齊州,弄墨揮翰。策馬龍山,談佛說禪。轍跡猶深,辭章絢爛。決橋閉門,美名永傳。“一代醇儒”,滿腹錦繡。園林擘畫,“江漢星斗”。祥瑞濟南,文脈綿綿!
In poetry, the greatest glory of the period, all the verse forms of the past were freely adopted and refined, and new forms were crystallized. “Eight Great Prose Master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refers to a grouping of prose writer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ree of them - Su Shi, Su Zhe and Zeng Gong - had built connections with Jinan when they had a local government role or visited family and friends here.
The masters were renowned for their prose writing, mostly in the essay form. Almost all of the masters are also accomplished in other aspects of Chines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their time. This place is filled with fascinating stories with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