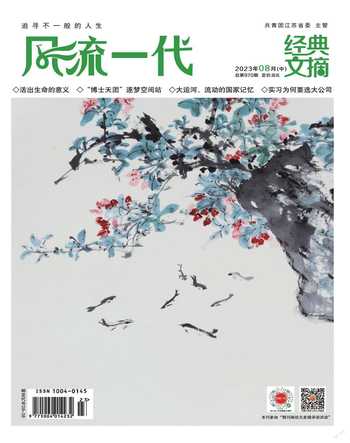伏爾泰的洞見與微笑
任昕
伏爾泰是近代以來法國思想文化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學、哲學、政治學、歷史、法律等多方面開啟和奠定了近代以來法國文化思想體系。在法國,人們尊稱他為“法蘭西思想之王”。
波瀾起伏的人生
伏爾泰,原名弗朗索瓦·瑪麗·阿魯埃,伏爾泰是其筆名。1694年11月21日,他出生于巴黎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其父是一名法律公證人,后任審計院司務,母親是來自普瓦圖省的貴族后裔。
伏爾泰年少時曾在耶穌會學校就讀,中學畢業后,父親把他送到法科學校,希望他將來能成為一名法官。但是年少的伏爾泰已開始顯露出思想獨立的特質和極具鋒芒的個性,他不想從事法律工作,而想成為一名詩人。他經常即興作詩諷刺時弊,初露文學才華。
1711年至1713年間,伏爾泰一直在法科學校學習法律,畢業后在法國駐荷蘭大使館擔任秘書。1715年,他因寫詩諷刺當時的攝政王奧爾良公爵被流放到蘇里。1717年,他因寫諷刺詩影射宮廷,被投入巴士底獄關押了11個月。
在獄中,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戲劇作品《俄狄浦斯王》。在這部劇本中,他首次用“伏爾泰”這個筆名,這是他的法國南部家鄉一座城堡的名字。1718年,《俄狄浦斯王》在巴黎上演,引起轟動,伏爾泰也因此被譽為“法蘭西最優秀詩人”,這年他24歲。當同齡人還在讀書和享受青春時,伏爾泰已經開始了他人生輝煌的軌跡,并終身保持著這種旺盛的創作力。
1726年,伏爾泰與貴族德·羅昂發生爭執,再次被投入巴士底獄關押了一年。出獄后,伏爾泰被驅逐出境,流亡英國期間是伏爾泰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階段。他在英國待了三年,這期間,他詳細考察了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政體、英國社會風尚習俗、文學藝術,接受了英國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牛頓的物理學最新成果和其他科學成果。他對比了英法兩國政體,深感法國封建專制政體的弊端,形成了他反對法國封建專制統治、向往開明君主制、崇尚自然法、希望以理性建立公平美好社會的政治學主張和哲學觀點。在此基礎上,他完成了他的一部重要的政治學和哲學著作——《哲學通信》。
因得到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默許,伏爾泰回到法國。他筆耕不輟,先后寫出悲劇《布魯特》《扎伊爾》以及歷史著作《查理十二史》等。1734年《哲學通信》發表,因書中宣揚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就和立憲政體,抨擊法國封建專制主義,引起路易十五不滿,書籍被查封,巴黎法院下達逮捕令,伏爾泰逃至一個莊園,在那里隱居了15年。
1746年,伏爾泰被推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這段時間是伏爾泰的多產時期,隱居生活使他的才能得以源源不斷流出。他寫下許多史詩、戲劇、哲學、歷史、科學著作,如戲劇《凱撒之死》《穆罕默德》《放蕩的兒子》《海羅普》,哲理小說《查第格》,哲學和科學著作《形而上學》《牛頓哲學原理》等,這些著作為伏爾泰贏得了巨大聲譽。
1750年,伏爾泰應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請,赴柏林擔任宮廷文學侍從一職。1753年,伏爾泰撰文諷刺一個叫莫佩爾的科學家,由于此人深得國王賞識,伏爾泰與國王關系破裂,離開了普魯士。這一時期他最主要的作品是《路易十四時代》。
伏爾泰在位于法國和瑞士邊境上一個叫凡爾納的地方置辦了一處房產,定居下來。此后,他開始全身心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啟蒙運動中。他撰文并印發小冊子,痛斥天主教會在宗教外衣之下的種種惡行和對新教徒的殘酷迫害,同時熱情洋溢地支持和參與青年一代的啟蒙運動,為百科全書派撰寫哲學詞條,他的《哲學辭典》一書就是他所撰寫的哲學條目的匯集。與此同時,他仍然勤奮創作戲劇,并完成了歷史著作《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羅斯》《議會史》,創作了他的文學名篇《老實人》《天真漢》等哲理小說。伏爾泰以其持續不斷的斗爭和大量作品引領著一代風氣,推動啟蒙運動的發展,他本人也被人們尊稱為“凡爾納教長”。
1778年2月10日,84歲高齡的伏爾泰回到了闊別29年的巴黎,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但不久便病倒了。當地天主教神職人員得知他抱病的消息后,別有用心地潛至他的病榻前,試圖說服他懺悔,卻被趕走。同年5月30日,伏爾泰那顆永遠洋溢著熱情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臨終前,他以伏爾泰式的戲謔叮囑其身后事,要人們把棺材的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這樣,如果上帝讓他上天堂,他便從教堂這邊上天堂;如果上帝讓他下地獄,他便可以從棺材的另一邊悄悄溜走。直到臨終,他都不忘對自己詼諧一把,同時也順便捎上他一生抨擊和與之抗爭的宗教和神職人員。11年后,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
思想的力量
1878年5月30日,維克多·雨果在紀念伏爾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講中這樣說道:“他接受戰斗。他的武器是什么?這武器輕如和風,猛如雷電——一支筆。”是的,一支筆所傳達的是人的思想和心聲,它是思想的利器,是頭腦的代言,是心靈的迸發。伏爾泰是法蘭西民族思想上的英雄,他所面對的敵人是龐大的封建王權、貴族和神權勢力,他的思想和作品就是他的利劍。
伏爾泰還是當時歐洲少數能夠超越西方文化自身界限,將目光投向東方,并從東方文化中尋求人類智慧之光的智者。盡管并沒有游歷過中國,但伏爾泰通過閱讀一些翻譯書籍和記述,對代表著東方文明的中華文化懷有濃厚的興趣和好感,他看到了一個與西方迥異的文明并從中發現了道德的力量。伏爾泰對孔子給予了高度敬意和評價,在《關于〈百科全書〉的問題》一書中,在“論中國”的詞條中,伏爾泰這樣寫道:“我認真讀過他的全部著作,并做了摘要;我在這些書里只找到最純潔的道德。”他認為中國人已經“完善了道德科學”,提倡應按照中國模式建立經濟和政治制度。在《風俗論》中,他駁斥了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禮儀的極大誤解。他對比了東西方文明,認為東方文明的品性要好于西方。
當時在西方鉆研東方文化的人中,伏爾泰是引領者,他投入了極大的熱忱并盡可能以一種不帶文明偏見和優越感的視角注視著這種異質文化。伏爾泰還引進和改編了中國的戲劇故事《趙氏孤兒》,寫出劇本《中國孤兒》。伏爾泰在法國思想界的地位以及他對孔子的尊崇,在傳播中華文明、推動啟蒙運動中的貢獻,也使得他被人稱為“歐洲的孔子”。
仁者的胸懷
雨果在提到伏爾泰的微笑時說:“微笑,就是伏爾泰。”的確,見過伏爾泰畫像或雕像的人都會對伏爾泰的微笑印象深刻。
伏爾泰的微笑似乎是嘲諷的,那種嘲諷又是詼諧的,是機敏、睿智、通透和天性中自帶的喜劇感。伏爾泰是一位喜歡以嘲諷的方式表達深刻洞見的富有幽默感的思想者,他常常嬉笑怒罵,善于舉重若輕,直指本質。而在這一切當中,他的微笑又包含著對世間疾苦的深切體會和悲憫。因此,若仔細看去,便會看到他笑中的淚,他譏誚背后的辛酸。他反對黑暗和不公,同時對眾生疾苦心懷悲憫,他的嬉笑怒罵中懷有強烈的正義之情和博愛之心。
伏爾泰晚年定居在法國和瑞士邊境的凡爾納莊園,當時正值天主教與新教之爭時期。伏爾泰本人曾收留過大批宗教受害者,而卡拉案件則是當時一件影響很大的事件。當地一個頗受人尊敬的新教胡格諾派商人卡拉被法官無辜判罪,法庭惡意粗暴地判處卡拉極刑。伏爾泰聞訊后,收集調查證據,對整個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斷。他撰寫了揭露這起冤案的小冊子并廣泛分發,還親自寫了上訴書,最終使這起冤案得到昭雪。
伏爾泰的思想在當時承擔起了“培育良知”的責任,貫穿了整個啟蒙運動的發展,開啟了歐洲近代文化思想之先。
(上善若水摘自2023年5月25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