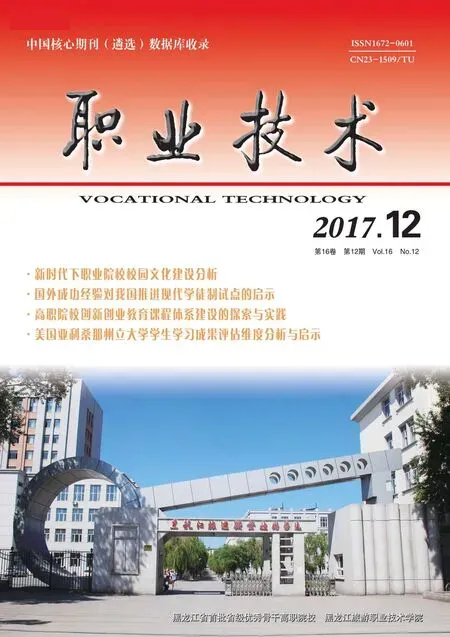信息經濟學視角下會展業發展的研究
周恩超(黑龍江旅游職業技術學院,哈爾濱 150086)
0 引言
會展作為一種集體性的商業或非商業活動,近些年來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越發突出,主要是在于生產、傳播和分配信息等幾個方面的重要作用。展覽會從其最開始舉辦到不斷演變的過程中,自始至終使得“信息市場”以一種“隱性”形式與展品的物質市場并存,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會展就是一種信息市場,一直發揮著信息交流和傳播的功能,頗有“無心插柳柳成蔭”之意。在本質上會展也是一種流通的媒介和營銷的工具,通過改良信息的傳導方式和渠道,從而減少交易的成本。因為會展自身的特點,諸如集聚性、直觀明了性、便當直捷性和交流互動性等,使得與其它的營銷工具相比,會展的競爭優勢就在于較低的交易成本。
1 信息市場
通過舉辦各種形式的會議和論壇、展覽、展銷,會展帶來直接或間接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逐漸形成一種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這就是所謂的會展經濟。大型會議、展覽活動等會帶來源源不斷的人流、物流,從而帶動商流、資金流、信息流的運轉,也直接推動舉辦地的酒店、商貿、運輸業和旅游業等的發展,一個較成熟的會展帶來的效應就是新的商機不斷,投資大量流入,進而聯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并形成以會展活動為核心的經濟群體。如果將會展看作一個小型的市場,那么在信息經濟學上,會展是一個信息市場,參展商品散發傳遞著多層次全方位各領域的豐富市場信息,參觀者身處各種市場信息之中,可以篩選獲取需要的信息,并且所有的信息都可以與會展中的其他信息進行交換,信息交換反映出商品市場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各種經濟關系。
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商品相關的信息得以實現交換,會展中的信息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樣,也是可以用來交換的,用于滿足某種需求的商品( 或服務) ,同時擁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展覽會上,參展商品的信息涉及宏觀與微觀,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多種信息,這些信息在展會上通過商品的交換得以向參展者傳遞并實現交換,從而實現參展者的各種工作、生活或學習的需求。會展中的信息也有多重用途,不僅可以滿足生產經營者的決策、產品、競爭等需求,而且可以滿足日常生活中的日用品、旅游、健身、娛樂等需求,這些信息的聯合效應在眾多會展中引起巨大作用,信息進一步的傳遞擴散,可以在整個社會產生不可估量的使用價值。
2 會展經濟
通常關于會展的概念可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從狹義角度來看,會展主要指的是展覽會和會議,而廣義上的會展包括各種類型的博覽會、展銷活動、交易會、展銷活動、各種類型會議和文化節日慶典活動等,是會議、展覽會、節事活動和各類產業或行業相關展覽的統稱。對于會展的概念學術界至今尚無定論,本文側重第二種觀點。而在本質上,會展是一種營銷的工具和流通的媒介,它也是一種臨時市場,通過改善傳遞市場信息的方式,達到減少交易成本的目的。與其它的營銷工具相較而言,會展的競爭優勢是較低的交易成本,這是由其自身具有的集中性、直觀性、便捷性和互動性等特點決定的。舉辦一次會展的成本費用遠遠低于一般性的人員推銷、公關和廣告等普通、單一分散的營銷手段的成本費用。根據英聯邦展覽企業聯合會的調查,通過一般的渠道找到一個大客戶,大概需要花費219 英鎊,而通過會展方式,卻能降低成本至35 英鎊。
2.1 形成的動因
從交易成本理論來分析會展形成的動因可知,會展是由傳統流通市場演變而來的,市場交易形式的改變始終伴隨著為了減少交易成本費用而作出的改變調整等行為。隨著市場的發展,商品種類呈現復雜化,更多的人已經不能接受一對一或者一對少的個體社交模式中的時間成本,更樂于接受規模化社交和使用各種聚會活動來制造市場交易氛圍,以及軟化簡單的人際交易關系,增加人們在群體交流中交叉的交易效應。這個時候交易所需的信息也達到一定的數量規模并且形式雜亂,而量變在一定的條件下就會產生質變,導致傳統的流通市場開始向會展模式轉變,并且會展繼續發展逐漸適應滿足新的市場需求。就是由于這樣的原因,會展是部分市場主體參與創造出來的一個成本相比現實市場交易成本更低的臨時市場。
2.2 交易成本
會展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交易工具。在會展中,會展商、參展商(代表賣方)和參展者以及與會者(潛在的購買力)有面對面的交流機會,此過程省卻了廠商的時間成本,具體表現在尋找合作者、訂立契約、議價談判等中間交易過程中。同時也降低了廠商與企業的交易費用,相對降低了消費者尋找新產品(品牌、效用、質量等)的機會成本,因而是一種低成本的交易行為。
3 結語
在現實生活中,會展起到生產、傳播和分配信息的作用。會展作為一種信息市場,以一種無形的方式與展品的商品市場并存,起到交流和傳播信息的作用。作為信息交流媒介,會展可以減少市場中供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性,促進供求雙方充分交流產品信息,聯接信息供給方和信息需求方等重要的要素,從而促進經濟循環運行,優化合理配置各類相關的市場資源。會展業發展至今,在越來越多的國際主題會展的帶領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會展的信息市場功能顯得更加重要。
[1]烏家培,謝康,肖靜華.信息經濟學[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楊勇.現代會展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3]奧利弗·威廉姆森. 交易成本經濟學———經典名篇選讀[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