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滾樂現場的表征與價值研究
周楊 章崇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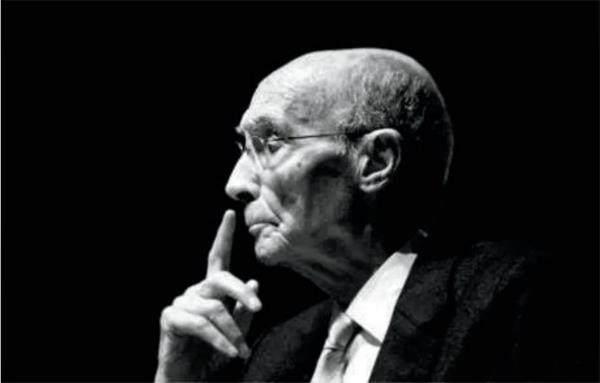
一、巴赫金狂歡化理論概述
(一)狂歡化的由來
狂歡節源自于盛大的狂歡節慶典活動。類似狂歡節的節日可以回溯到古希臘-羅馬甚至更早的歷史時期。在古希臘時期,人們崇敬酒神并舉行祭拜儀式:奧林匹克神系中,狄俄尼索斯掌管豐收,凡逢收獲季節,人們在歌舞中向酒神獻上祭品,并祈禱來年的豐收。祭獻活動過后,人們佩戴上面具,穿著奇裝異服到街上肆意狂歡。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狂歡節慶祝活動還包括但不限于不同地區、國家和時期的被特定命名的慶祝活動,如復活節、愚人節抑或圣誕節等,甚至是可能暗含某些狂歡性質的日常活動,如市集中的一些行為和某些現場的音樂表演。巴赫金把類似狂歡節的慶祝活動的整體稱為“狂歡節風格”,這顯然具有其象征性的意義。
(二)狂歡化的基本內容及歷史演化
巴赫金指出:“狂歡節已經發展出一整套感官形式的語匯,每一種都擁有獨特的象征意義,從復雜的大大小小的群眾集會到個體或個別的的狂歡行為,這種語言表達了狂歡世界的統一愿景[1]。顯然,這種獨特的語言并不適合精確地翻譯成書面語,甚至是抽象的概念。然而,它可以通過藝術形象的語言進行某種程度的解釋,即轉變為文學語言。正是這種狂歡式抽象到文學中的現象,我們稱之為狂歡化。簡而言之,將狂歡節的感性而具體的行為轉化成文學表述的語言,就是狂歡化。
巴赫金將有關狂歡化的一切問題放到歐洲歷史及歐洲文學發展史及歐洲歷史的流程進行研究:他不但精細酌量了文藝復興時期以及中世紀時期的文學狂歡化現象,而且通過文學狂歡程度較高的特定作家的作品對上述以及其他時期的狂歡現象進行了細致的總結和梳理,簡明扼要地說明狂歡是如何有機地嵌入他們的作品中的,并對狂歡化的歷史演進進行了概述[2]。毫無疑問,狂歡節起源于狂歡節本身,17世紀下半葉以前,人們直接參與到狂歡節活動中,并將其具象化。在古希臘-羅馬時期,狂歡節體裁的文學作品都與狂歡節直接相關,某些體裁甚至直接為狂歡節慶典活動服務;從中世紀開始,許多用各種白話文和拉丁文寫成的比擬狂歡體文學,都不同程度地與狂歡節慶典活動有關;至文藝復興時期,狂歡化的趨勢蔓延到正統文學的所有體裁,整個文學實現了非常深入和完整的狂歡化。然而,17世紀下半葉以后,狂歡節不再是狂歡化的直接來源,狂歡體文學的影響逐漸取締了其地位。對于近代大多數的作家來說,狂歡化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傳統意義更為重大,非文學性的直接感官刺激——真正的狂歡節現場意識較為模糊。然而,狂歡節的種種特征隨著時間的糅合已被不斷吸收到多種文學中,與它們的自身特點融合,同時作為這些體裁的組成元素而存在[3]。狂歡化作為一種由狂歡式的直觀行為所純化出的精神文化現象,同時也可看作一種特有的文藝思維方式和世界觀,它不是一個封閉的自足體,而是一種不息變動的開放性體系,諸多固有觀念在這里被破壞,死亡與新生交替變更,解構與重構合二而一。
狂歡化的內核,是以一個被狂歡節精神所浸染的世界感受、烏托邦化的理想、平等對話的精神和開放性等特點為基礎。狂歡化的氛圍使社會等級暫時取消,原有的權威、屈從以及社會地位暫時消失,人們以一種無拘無束的狀態存在,一個烏托邦式、自由平等的“狂歡式的”世界被暫時建構起來:狂歡精神使一切被等級觀念所限制的東西都重新煥發出活力。
二、搖滾樂現場狂歡化的來源——搖滾樂中的暴力美學
搖滾樂現場之所以能與巴赫金狂歡化理論的諸多特質相聯系,甚至與它的來源——狂歡節極為相似。搖滾樂的世俗根源——布魯斯,最初,它是在南北戰爭后的南方黑人社區中出現的一種歌唱風格。一般來說,它被認為是由田間工作的勞動號子和勞動歌曲演變而來。[4]它也代表了被壓迫者錐心刺骨的凄聲;同時,黑人的宗教與白人不同,他們并不是通過靜坐參禪來接近上帝,而是通過肢體的運動與宣泄性的吶喊,在在迷狂中達到忘我[5]。拋開歷史起源問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音樂與生俱來的“基因”與其內在“性格”,它是由 "聲學暴力 "這種力量作為驅動的,以及這種文本特質與思想感情的完美連接。
(一)蘊含沖擊力的表演形式
在表演形式上,搖滾樂構建出了一個高能的力場,演出時普遍使用先進的技術成倍地放大聲音的強度,利用噪音和基于聲音的音樂元素來增強音樂的懸念和緊張度,結合高密度且極富動力性的節奏加之舞美對表演進行詮釋,與此同時,現代技術與數字媒介的應用以及與音樂本體的有機結合,不僅在聽覺上滿足了參與者,也不乏現場帶給人的視覺震撼[6]。“本性與直率”永遠是搖滾樂的標簽,手舞足蹈的身體敘事以制造自維空間的癲狂,電聲的運用制造了類似噪音的樂音,音響的強震感往往是長時間強力度的進行,進而讓在場的樂手和樂迷共同置于狂歡性的躁動中。
(二)極富動力的節奏節拍
值得另外一提的是搖滾樂的節奏節拍,搖滾樂中較為固定的節拍律動主要是由鼓與節奏吉他完成。同時,低音鼓與貝斯的緊密結合加強了音樂律動感,特別是在金屬等快速的作品中尤其突出。旋律節奏多以小切分、大切分、附點、弱起等不規則的節奏型構成[7],這些共同構成強有力的推動力,從而音樂充滿現代生活的動感,進一步打破了藝術與生活的界限,使藝術變得更為平易近人,足以讓共樂者同瘋狂。
三、巴赫金狂歡化理論在搖滾樂現場的映射
巴赫金的狂歡節化理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狂歡節本身。雖然這個特定的儀式已經在漫漫的時間長河中消解,進入非封建社會的人們也不再生活在教會的壓迫之下,但“狂歡節”依舊作為一種象征性的意義被保留下來。雖然巴赫金的研究視域集中在小說體裁,但其狂歡化理論的意義是無比深遠的,遠遠超出了小說這一文學體裁,甚至超越了文學的畛域,其諸多特點與搖滾樂現場的多種特質異曲同工。
(一)狂歡式的感受——現場宣泄的狂歡化
搖滾樂最令人矚目的感性特點之一是其“重擊如鞭、狂熱和宣泄”的聲音,這種音響形式聯結了情感與思想。諸如,重金屬重擊如鞭、狂飆式的吉他演奏風格已經成為搖滾文化族群的一種“音響圖騰”,引無數搖滾樂迷頂禮膜拜。這在像Van Halen這樣的樂隊表演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美國康涅狄格州的音樂會上,當昏暗的燈光突然打在樂隊主唱身上時,現場所有的樂迷將淤積著的期待、渴望與沖動洋溢著傾瀉而出,瞬間歡呼聲和掌聲響徹云霄。電吉他伴隨著主唱的一聲狂呼而咆哮,如同數萬把利劍劃過天空,在巨大的掌聲中掠過舞臺,咆哮著沖開臺下巨大的歡呼聲。臺下的樂迷沒有時間思考,燃燒的樂場就綻放開來,樂隊編織了一張音質的火網,開始了瘋狂而激情的焚燒。此時,會場上所有的生命都被淹沒在聲場肆意的噪音中,仿佛空氣都如烈火一般熾熱。為之四顧,沸騰在人山人海的狂熱氛圍直逼舞臺,無數的燈光懸掛在高空,把整個舞臺裝點得燦爛恢宏,這些燈光也像有生命似的,伴隨著熱情洋溢的音樂與現場的人們一起縱情燃燒[8]。
對于正在努力應對高壓力生活方式的當代人來說,似乎缺乏情感表達的渠道,搖滾樂現場的出現很大程度上為現代人群提供了一個可以“極盡本性之所能”的平臺。人們置于這種狂歡化的現場,暫時性地從過往的經驗、社會地位、階級差距中抽離,并拋棄乏味的的情緒塵垢,舞臺上洋溢著狂熱的歌聲與有沖擊力的燈光和聲音的融合,散發著一種壓制性的激情,進入一種不日常的、甚至與平日的嚴肅壓抑完全相悖的混亂狂歡狀態,并在高度興奮中以緊密的參與度和樂手一起完成肆意狂歡的氛圍,并在這個“狂歡力場”中補充能量。這種暫時性的”狂歡節“儀式,作為狂歡文化的當代版本,大量地保留了狂歡的價值和意義[9]。
(二)階級和地位的暫時消解——現場無差別的平等參與
就搖滾樂的起源而言,其最初即為超越民族和種族文化差異的多元化聚合體,也是黑人和白人文明相互作用的文化雜合子,這意味著它從誕生開始,就具備著兼收并蓄的能力,并在時間的沖刷打磨下愈發寬容。冷戰時期的美國受冷戰思維及持續存在的民族主義問題的影響,極度排斥外來民族的文化(抵抗社會主義國家文化的現象最為顯著),但美國反正統文化的先鋒們掙脫主流政治文化的枷鎖,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種族歧視,嬉皮士們以他們倡導的“博愛”態度,積極從他民族文化中尋找充滿生命力的音樂元素來武裝自己。對于當時冷戰的音樂反抗產物——迷幻搖滾來說,對東方音樂的吸收(如斯塔爾琴的引入)則是這一理念最直觀的例證[10]。
搖滾樂所倡導的“平等”在演出現場同樣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搖滾樂的演出現場,其實并不存在單純的“受眾”,聽眾往往高度參與音樂的生產過程:場下觀眾的高度參與性以及歌迷的瘋狂行為均遠遠超過其他古典或流行音樂演唱會。樂迷來到現場也并不是持有一種追星的態度,而是想要享受音樂,他們與樂隊地位平等,都已成為這個狂歡現場的組成成分。青年搖滾樂迷在參與現場的過程中,通過個體間的互動與協作,構建了一種無差別的樂迷身份認同,Pogo、Mosh、死墻、金屬禮、跳水、甩頭等動作都是獨屬搖滾樂現場的傳播方式[11]。其次,搖滾愛好者有機會參與現場表演,與樂隊成員互動,甚至以“表演者 "的角色,準備在舞臺上搶占聚光燈。
搖滾樂,一個從一開始就被賦予反叛精神的音樂流派,卻在其演出現場中培養了最具凝聚力的團結氛圍。在這些儀式性的體驗中,粉絲們忽略了他們的個人區別,摒棄了任何身份或等級的界限,融合成一個無差別的集體,原有的權威、屈從以及社會地位暫時消失,人們以一種無拘無束的狀態存在,表演者與觀眾共同創造出了涌動著熱情與生命力的搖滾現場,而搖滾樂迷參與合唱與現場互動,此外,它在樂迷身上培養了一種強有力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感,一個烏托邦式、自由平等的“狂歡式的”世界被暫時建構起來,使一切被等級世界觀禁錮的事物得以重生[12]。
(三)廣泛的對話精神:持續性的現場信息交互與情感傳播
一些較受歡迎的Live House場次中,蜂擁的人群使個體之間的距離縮短,樂迷們幾乎已經到了“貼臉”交流的狀態,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更為密切的同時,樂迷與樂手的距離也極為接近,在這種近似零距離的信息交流場中,樂手用身體符號和聲音表現詮釋音樂氛圍,樂器的音色與音量幾乎直觀地沖撞到樂迷面前,同時樂迷將自己潛意識的反應不加思索地拋回,由此形成一個閉合的、情感交互的回路。但觀其本質,還需要回溯到搖滾樂產生的源頭——非洲黑人音樂。非洲藝術學者羅伯特發現,西非部落中,進行鼓樂演奏時的“傾倒程序”:舞者彎腰并靠近鼓者,有時候會彎腰碰到主要鼓者面前的地面”,研究表明,在非洲文化中這通常代表著舞者對鼓者敲出撼人樂句進行交流與回應的信號。“呼叫與回應”作為非洲音樂在演奏時不可或缺的環節,帶有溝通和交流的意味[13]。在搖滾樂的完成過程中,樂手與樂手間,觀眾與觀眾間也存在這種潛在的互動交流聯系,而這樣的聯系尤其體現在Live House這一特殊空間里。在現場音樂場所的脈動氛圍中,一種類電力的刺激被表現出來,將現場的能量強化到令人振奮的高度。這種能量極大地增強了與會者的熱情。這些音樂場所的連續性,如Live House,促進了一種持續的互動,使搖滾愛好者體驗到一種強大的情感交流。正是通過這種參與和介入,搖滾樂迷真正遇到了參與的樂趣,并培養了深刻的歸屬感,以及情感共鳴的加深。
搖滾樂現場演出不僅體現為表演者在舞臺上對于歌曲的演繹,或者為樂迷帶來現場音響的沖擊,筆者在親身體驗與欣賞搖滾現場視頻之后,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搖滾力場下表演者與參與者所建構出的狂歡化的群體氛圍。縱然搖滾現場強烈的節奏、無限放大的音量與表演者縱意的行為營造了肆意狂歡的音視環境,而觀眾對表演者的齊聲喝彩、觀眾之間親密無間的協助互動更不斷推動著這種集體性的狂熱。搖滾樂現場充滿激情、放蕩不羈的表演與接受,共樂者動態接受、集體參與及毀滅地位與階級的過程,這也正是古希臘時期狂歡節所創造出的“第二世界”,也是巴赫金論述的“狂歡節”中平等自由的烏托邦理想。
注釋:
[1]夏忠憲:《巴赫金狂歡化詩學理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5期,第74-82頁。
[2]張麗:《巴赫金表述詩學的狂歡模式》,《貴州社會科學》2021年第12期,第54-60頁。
[3]蔣理,武閩:《巴赫金狂歡化理論的哲學內涵:兩重性相互轉化》,《貴州社會科學》2021年第4期,第22-29頁。
[4]姚松圻:《搖滾樂演化史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音樂生活》2022年第6期,第27-31頁。
[5]付菠益:《宣泄的儀式》,《中國藝術研究院》2008年,第110頁。
[6]張笑梅:《中國戶外流行音樂節的文化特征解讀》,《音樂傳播》2014年第2期,第53-58頁。
[7]孫慧慧:《20世紀80年代中國搖滾樂研究》,《山東師范大學》2014年,第68頁。
[8]周華生:《搖滾音樂敘事及終結》,《人民音樂》2009年第5期,第82-85頁。
[9]周華生:《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搖滾(樂)的存在及其聲音感覺的邏輯》,《上海音樂學院》2009年,第160頁。
[10]任少仁:《迷幻搖滾:音樂語言與社會意義》,《上海音樂學院》2010年,第49頁。
[11]唐波:《搖滾樂表演作為演示類敘述的特征》,《北方文學》2019年第21期,第122-123頁。
[12]姜在輝:《傳播儀式觀視角下的中國搖滾樂研究》,《蘭州大學》2022年,第71頁。
[13]劉芳芳:《跨文化視域下的披頭士樂隊研究》,《溫州大學》2021年,第78頁。
周 楊 南京藝術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
章崇彬 南京藝術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 李欣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