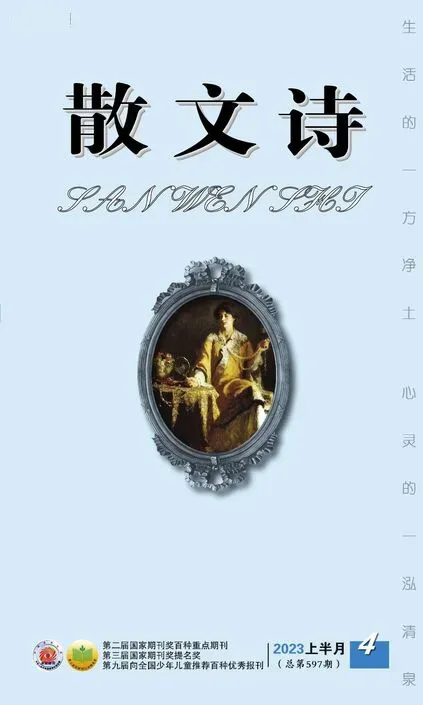但少閑人
◎焱 引
卷 簾
絲綢建起的房子里, 卷簾是最堅實的防盜鎖。向微風(fēng)貢獻一些雕紋華飾, 歸家的黃雀就不再沉溺于追求月亮。
每一次搖動, 都是對幾株伏于墻角的草苗的陪伴。而更多的時候, 一只誤入的蝴蝶借著垂簾, 靜靜地窺視著我。我因此注意到了窗臺一角的面包屑, 也因此習(xí)得以某種傾斜度, 改變我過分耿直的眼神。
曾經(jīng), 那被懸束于高閣的簾角裝飾也這樣凝視我。它們褶皺出一張沉默的臉。可我長期低頭寫字, 未必懂得欣賞穿上紗裙的藍天。
有許多掛扣生銹了。我必須去懲罰吊鐘于此的失聲。窗邊的桂花樹也是不能幸免的, 花蕾仍然缺乏坎坷, 沒能挽留蒸干水分的花香。
唯有那對經(jīng)常從窗戶外頭朝我微笑的老夫婦應(yīng)當(dāng)被贊揚——那位靠輪椅行走的老爺爺, 卷簾擦過他眼角的時候, 總有一雙手開始流露溫柔。
于是, 我決心練習(xí)抬頭。不僅為了把簾拉成某種值得審美的角度, 更渴望將恰到好處的陽光分享給這個小書房。
獨 居
字不見了。我從來舍不得忘記的。但確實不在那個地方了。
所幸月亮還舍不得把燈關(guān)上。掛掉忙線的電話, 才聽見門被輕輕叩響。恰好二更時分, 不多不少。就像心跳的節(jié)奏, 不緩不急。
我們都知道什么叫做無用功。
假如, 春天可以和秋天重疊在一起呢? 當(dāng)飛鳥躺在花海里吮吸山捻子, 害相思病的愛侶互相為對方準備驚喜。或許, 我也不至于失眠。
鄰里昨日撿回來的野貓估計是睡了。我記得他們家的魚缸擺得很高, 那一尾魚兒總睥睨地看著我, 優(yōu)雅地用鳳尾掃掉我的想象。
樓下的小孩肯定又闖禍了。最后一聲哐當(dāng)過后, 風(fēng)停了。
都怪我過分平庸的廚藝, 以及演技。既不敢邀約那個躲在角落里的少年, 也無能逗他開心。逗哏不適合我, 捧哏也是。我斗膽能學(xué)習(xí)一下如何寫劇本。
不必去照鏡子。那上面全是塵。
重 讀
重讀一本書, 不僅是重新命名某個顛沛流離的人物, 更是對某種記憶的刪繁就簡。倒敘, 推翻, 斷裂, 新生。豐滿更多的經(jīng)驗, 飄蕩更自由的隨想情思, 順便與一個毫不奔疲的靈魂靜坐。
甚至不必發(fā)言。不必與所謂的作者對話, 不必為進一步表達而陳述。
傾聽即可。
聽作者, 聽主角(假如有), 聽自己。聽其言語。盡管這依然無從幫你領(lǐng)悟某種崇高的旨意或達地知根的本質(zhì), 但你依舊能夠抓起一支墨香的筆, 慢慢研磨它的耐心。
某日, 我又試圖從古希臘劇院的出口默看起風(fēng)沙的路。雙目雖沒陷入光的誘惑, 卻依然感到刺痛, 宛如某個彷徨多年的王子,一直不能尋到區(qū)分深邃與激情的法則。但彼此依然需要踏上征途。
所有因自己曲折的意義, 所有因自己注釋的方向, 都在穹宇的赤黃染色瓶翻倒瞬間, 遮蓋住自身赤裸的細節(jié)。為此, 我不再尋找更多詮釋重復(fù)的借口。在某段靜謐中, 我只能讀出那么一兩個字, 不糾結(jié), 也并非荒謬, 我的影子在書內(nèi)書外反復(fù)出逃。
可是, 就算我不去追趕它, 它也會逐漸在徘徊中自我覺醒:偽設(shè)糊涂, 并且不對他者罔置一詞。
書本漸漸凸起皺痕, 可我早忘了重構(gòu)一盞幽冷的晚燈。切勿來質(zhì)詢我, 為何出演著昨日的戲, 筆尖卻繪著明日的詩。
觀影:謝幕
我在那束光線的折返中, 抓住了不一樣的形式。有過那么短暫的一瞬, 電影按下了定格鍵, 某一句臺詞跳出命運。過程十分簡單, 只不過是利用鏡片的傷痕, 順便用繩子綁緊了突兀醉倒的閃光燈。
每一位觀眾都習(xí)得評論的主體性, 證據(jù)是前一位布置命題的評論家失聯(lián)。錯誤是允許被寬宥的, 或許我也應(yīng)該習(xí)慣于, 在暫停后繼續(xù)播放之時, 幫某只迷途的小貓合上雙眼。我是早就了解的, 生銹的機械韌帶, 褪色的銀幕斑痕, 只是, 還有一些疑問,在于爆米花融化的時候, 它們選擇了怎樣的姿態(tài)?
所有的眉蹙或微笑都是編織的, 正如所有的粗糙手藝都將被后來者反復(fù)革新。但我依然把握住了某一瞬自然的停頓。
——實心的句點。頑固而不肯讓步。
終于, 幸存一道迷途的射線, 封堵住了臺詞最后的字眼:謝。
“謹對以上工作人員表示鳴謝”。
替來者留下命題的時候, 劇情內(nèi)容早已從我的記憶細胞中分解。推開門, 一道道光開始了它們的交互工作, 過程中, 只留下一些不起波瀾的輕塵。
對于某一部電影, 我無從得知那些以往或?qū)⒅恋娘L(fēng)骨。我唯能做的, 僅僅只是念著自己的名謂, 并且孑然行走于落日余暉。
木 舟
在這近乎干涸的湖, 劃槳成為一種懸念。
游蕩久了后, 朽木早已分不清楚, 名曰“航行”的尺度。身旁, 有黑天鵝飛走, 有翎羽揉進淤泥, 還有一個用作坐標的凸物。但并沒有一個人, 選擇蕩舟。
因為翅膀與雨云都是奢侈的, 木頭的遲鈍便取得了占有一艘舟的合法性。如今, 這片命懸一線的浮葉, 看著這些愚鈍的孩子,與殘疾的湖面對飲, 與棱角的沉鐵比硬, 還肆意地將蠢動的塵屑,一層層剝離。
它所能夠嘗試的, 只剩下浮蕩, 而意義僅僅是維持一副被沾濕的軀干。
畢竟, 這木舟曾如此匱乏重量, 甚至在一尾魚撞入骨頭的時候, 遺落一根穿透咽喉的長釘。
直到一輪月亮, 鱔一般將其捆綁。
于是, 瘋狂踉蹌。在吹拂的風(fēng)和樹叢間沉默的頭顱面前, 它只能借助嘶啞, 來幻想艱難扭轉(zhuǎn)朝向——可這幾乎瀕臨癱瘓。最后, 獨剩下一根龍骨, 支撐著一直不見彎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