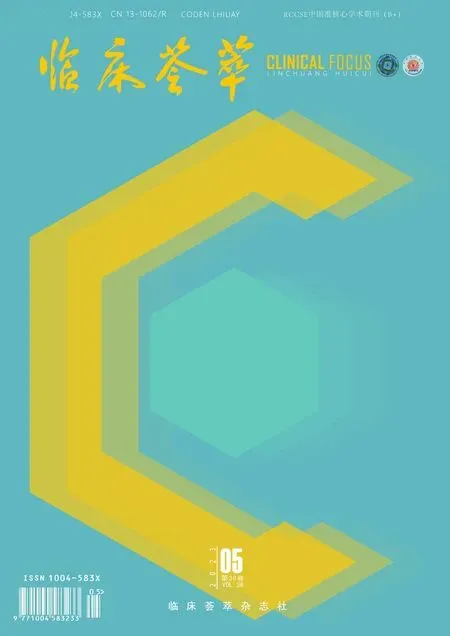肝門部膽管癌的非手術治療進展
陸知非,王高卿,高 過
(寧波大學附屬李惠利醫院 肝膽胰外科,浙江 寧波 315046)
肝門部膽管癌(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HCCA)是一種常見但侵襲性極強的惡性腫瘤,患者預后較差,長期生存率低。1965年, Klatkin[1]首先詳細描述了HCCA獨特的臨床和病理特征,故又稱為Klatkin腫瘤。這種腫瘤起源于肝外膽管上皮細胞,占所有膽管癌的60%~70%[1-2]。HCCA位置隱蔽,早期診斷難度大,且具有高侵襲性,常侵犯肝臟、血管及周圍淋巴組織,導致患者生存率低,患者在初診時往往已經失去最佳手術機會,因此HCCA非手術治療手段對改善患者預后有著重要意義。本文就關于近年來HCCA非手術治療及其進展做一綜述。
1 膽道支架植入術
膽道支架植入術是一種通過可跨越惡性梗阻并允許內部引流的支架,引流功能最佳肝葉的治療方法。其方法包括經皮穿刺膽道支架植入術、經內鏡膽道支架植入術、超聲內鏡引導下膽管內引流術等,在植入方式的選擇上,目前學界仍存在一定的爭議。但無論何種膽道支架植入術都可以在保留原消化道結構的同時,解除膽汁淤積、改善肝功能、提高消化能力、維持腸道正常菌群等,對于改善伴有膽道梗阻的HCCA患者的生存質量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在支架材料的選擇上,有研究顯示塑料支架擁有更高的介入成功率,金屬支架則擁有更長的通暢時間,但是支架的選擇可能不會影響預后[3-4]。然而膽道支架植入術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如對腫瘤本身無治療作用、易脫落等。
2 化療
對于無法進行手術切除的HCCA患者,化療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臨床上多采用單用吉西他濱或吉西他濱聯合順鉑(GC方案)、吉西他濱聯合奧沙利鉑(GEMOX方案)、吉西他濱聯合替吉奧(GS方案)等。英國有研究證實,相比于單用吉西他濱,吉西他濱聯合順鉑組的治療效果更好,總生存期更長[5-6]。同時近年也有研究顯示GC方案在治療膽道惡性腫瘤的隨機試驗沒有表現出明顯益處,且此方案對患者基本狀況有著較高的要求,體力較差患者難以耐受[5, 7]。然而,2019年日本的一項3期臨床研究中顯示:與應用GC方案的患者相比,應用吉西他濱聯合順鉑、替吉奧(GCS方案)的患者,腫瘤縮小更多更快且預后更好[8]。同時,因全身化療方案受到細胞毒性和耐藥性的限制,臨床上也出現了支架聯合膽管內灌注化療等局部化療方案,此類方案延緩了膽道再堵塞的時間,延長了患者的生存時間[9]。有研究顯示,術后輔助化療也可改善術后患者的生存率[10]。近期一項3期臨床研究(SWOG 1815)中顯示,接受白蛋白紫杉醇聯合GC方案患者的客觀應答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31%)高于接受GC方案患者的ORR(22%),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提示晚期膽管癌可能因GC方案中添加白蛋白紫杉醇而獲益。然而化療也可能引發一系列的不良反應,如膽道炎癥、肝臟纖維化等[11]。總體而言,全身化療方案受細胞毒性和耐藥性等因素的限制,有關化療在HCCA患者中的應用仍需要更多的探索。
3 放療
關于傳統的放療治療晚期HCCA,無論是單獨使用還是與其他方式聯合使用的數據都較少見。并且由于HCCA特殊的解剖位置、較高的異質性等特點,傳統的外放療治療在HCCA的臨床應用上受到了嚴重的限制[12]。因而一種聯合了膽道支架植入術和持續低劑量近距內放療的治療方法----支架聯合125I粒子植入術應運而生。周傳國等[13]對38例惡性肝門區膽管梗阻進行對照試驗,分為接受支架聯合125I粒子植入術和單純支架植入兩組,其中支架聯合125I粒子植入術組生存時間[(201.83±27.50)d 遠長于單純支架植入組(142.25±15.46)d],且支架聯合125I粒子植入術組膽道支架通暢時間[(192.94±28.58)d也長于單純支架植入組(121.40±15.39)d]。符譽等[14]的試驗也得出了相同的結果,表明這種新型的治療方案安全有效,可以有效地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目前,徐州中心醫院一項關于支架聯合125I粒子植入治療HCCA的研究(NCT04779788)正在進行中。此外,2020年報道1例HCCA患者應用新型125I雙鏈膽道引流管治療后梗阻性病變消失,且10個月內未見復發[15]。2021年9月有研究顯示,9例應用新型125I雙鏈膽道引流管治療的膽管癌合并梗阻性黃疸患者隨訪期內僅1例死亡,且患者術后2個月谷丙轉氨酶、谷草轉氨酶、總膽紅素、直接膽紅素、CA19-9、腫瘤最大徑均較前明顯下降[16]。支架聯合125I粒子植入術具有創傷小、療效好、可重復性高等眾多優點,在未來有良好的應用前景;新型125I雙鏈膽道引流管可實現膽汁引流與近距離放療雙重作用,有望在HCCA的臨床治療中發揮重要作用[17]。但值得注意的是125I粒子治療可能引起造血功能下降等損害,目前仍需大量病例的進一步評估和長期的臨床隨訪研究。
4 靶向治療
近年來,隨著精準醫療的提出,腫瘤靶向治療飛速發展,靶向藥物也逐漸運用到無法切除的HCCA治療中。靶向治療是作用于細胞分子水平上的治療,且不參與DNA復制,相較于傳統化療有著較小的細胞毒性。一種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抑制劑——佩米替尼已于2020年4月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加速批準,用于攜帶FGFR2基因融合或其他重排的HCCA患者。有研究顯示,佩米替尼對于該類FGFR2基因突變的患者治療效果理想,擁有35.5%的ORR和6.9個月的中位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18]。近年來也有發現異檸檬酸脫氫酶1(isocitric acid dehydrogenase 1,IDH1)變異可發生于部分HCCA患者中。針對IDH1靶點的藥物艾伏尼布表現良好,一項納入了187例患有IDH1突變的膽管細胞癌患者的隨機雙盲試驗發現,艾伏尼布治療組中位生存期(10.3個月)高于安慰劑組中位生存期(7.5個月),且耐受性良好[19]。于2021年6月美國FDA加速批準的英菲格拉替尼同樣表現良好,2期臨床試驗顯示108例FGFR2融合或重排膽管癌患者經英菲格拉替尼治療后客觀有效率達23.1%[20]。然而,靶向治療也存在大量的問題,如決定耐藥性的多克隆突變的出現、腫瘤較高的異質性等,仍需不斷的探索。
5 免疫治療
免疫治療是一種通過干預免疫系統,從而抑制和消滅腫瘤細胞的治療方法。目前,免疫治療是臨床上各類腫瘤治療的熱點,而關于HCCA的免疫治療還處于起步階段。有學者在研究中發現,大多數膽管癌患者都存在PD-L1的表達[21]。也有研究表明,帕博利珠單抗單藥在經過大量預處理的PD-L1陽性晚期膽道癌患者中表現出了適度的抗腫瘤活性且抗耐受性良好[22]。另一項在日本進行的關于納武單抗的臨床1期試驗中顯示,納武單抗單藥治療組30例患者中1例有客觀效果,中位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為5.2個月,中位PFS為1.4個月;納武單抗聯合化療組30例患者中11例有客觀效果,中位OS為15.4個月,中位PFS為4.2個月,且患者耐受良好[23]。這可能提示免疫治療聯合化療可能可以提高對HCCA的治療效率。靶向聯合免疫治療也有不錯的表現,一項2期臨床試驗顯示,38例不可切除的膽管癌患者在接受侖伐替尼聯合PD-1抑制劑治療后,中位OS為17.7個月,客觀緩解率達42.1%,并且其中有13例獲得手術切除的機會,并行手術切除[24]。2022年9月,美國FDA宣布批準度伐利尤單抗聯合GC一線治療進展期膽管癌,2期臨床試驗顯示進展期膽管癌經度伐利尤單抗聯合GC治療后,客觀有效率達72%(34/47),結果令人振奮[25]。近日一項大樣本量的研究顯示,帕博利珠單抗聯合GC組的中位OS(12.7個月)明顯長于安慰劑聯合GC組(10.9個月)[26]。并且目前仍有多項有關免疫治療HCCA的臨床研究正在進行,如PD-1抗體聯合GEMOX 作為HCCA的術后輔助治療(NCT05430698)、度伐利尤單抗與曲美木單抗(Tremelimumab)聯合或不聯合卡培他濱(Capecitabine)輔助治療膽管癌(NCT05239169)、測試新型抗癌藥物Peposertib與阿維魯單抗(Avelumab)聯合放療治療進展期/轉移性實體瘤和肝膽惡性腫瘤(NCT04068194)、特瑞普利單抗(Toripalimab)聯合侖伐替尼作為晚期膽道癌的二線治療(NCT04211168)等,結果令人期待。關于免疫治療或免疫治療聯合其他治療的組合治療HCCA的價值仍需要更多探索及臨床數據加以支持。
6 光動力療法(photodynamic therapy, PDT)
PDT是一種近年來開展的針對不可切除HCCA的治療方法。PDT的基礎為腫瘤細胞攝取光敏劑分子,再給予特定波長的光激發,使光敏劑分子與氧發生反應,在腫瘤細胞中產生自由基、單態氧等細胞毒性物質,從而誘導腫瘤細胞死亡[27-28]。有研究表示,PDT能夠較好地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同時可以使患者獲得更佳的生活質量[29]。PDT也可聯合膽道支架植入術治療HCCA。Witzigmann等[30]研究顯示,184例HCCA患者中68例行PDT治療聯合膽道支架植入的患者中位OS(12個月)明顯高于56例僅行膽道支架植入術的患者,這提示膽道支架植入可以明顯改善PDT的治療效果。一項納入了6項研究的薈萃分析中顯示,行PDT治療聯合膽道支架植入的患者1年生存率(56%)明顯高于單純支架植入的患者1年生存率(25%),且兩組在膽管炎發生率和其他不良反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明PDT治療可在不增加不良事件的情況下提高HCCA患者的生存率[31]。但是PDT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如需要避免陽光直射,治療價格與其他方法相比較昂貴,技術相對復雜等,因此目前PDT在臨床的廣泛應用尚有一定的難度[31-33]。
7 膽道射頻消融術(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與納米刀消融
膽道RFA通過內鏡或經皮途徑將射頻消融導管置于膽道狹窄處,施加高頻交流電,在癌細胞中產生離子攪動,使細胞內外的水蒸發,導致癌細胞凝固性壞死,從而實現局部腫瘤的控制,令阻塞的膽道實現再通[34]。RFA一般與膽道支架植入術聯合治療,以減小腫瘤組織脫落而引起的繼發梗阻、感染的可能[35]。有研究發現,與單純植入膽道支架的患者相比,RFA聯合膽道支架植入術的患者擁有更長的生存時間,且膽道暢通時間也更長[36]。目前荷蘭一項關于RFA治療HCCA引起的惡性膽道梗阻的臨床試驗(NCT05546372)也正在進行中。然而由于肝門周圍膽管的管壁比肝外膽管更薄,膽管與血管的解剖關系也更復雜,因此RFA引起并發癥的風險可能很大[33]。
納米刀消融是一種治療不能切除惡性腫瘤的新型消融技術,利用不可逆電穿孔技術,在細胞膜上形成不可逆的納米級通道,破壞其組織的動態平衡,從而誘導腫瘤細胞的凋亡[37]。有多項研究表明,應用納米刀消融技術治療不可切除HCCA安全有效,且可有效延長患者生存期、明顯提高患者生活質量[38-40]。目前,臨床上對HCCA開展的納米刀消融較少,有關其確切療效及安全性還需要大量的臨床數據支持。
8 小結
HCCA是一種罕見的高侵襲性膽道惡性腫瘤,發生在膽道匯合處或周邊組織,起病較為隱匿。非手術治療對于失去最佳手術時機的進展期HCCA患者具有重要意義。目前HCCA的化療價值尚有一定的爭議。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精準醫療的展開,免疫治療、靶向治療均有重大突破,為HCCA患者帶來了曙光。125I粒子植入術、射頻消融、PDT等治療方法有望成為HCCA治療新的突破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