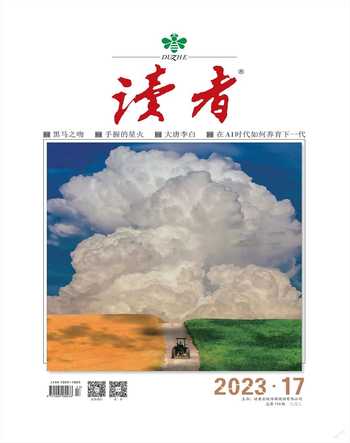1分鐘經濟學知識
何青綾

什么是種子輪融資
舉個例子,假如我想開一家飯店,奈何手頭沒有錢,于是我每天和你一起扛著扁擔在大街上賣早飯。結果我爸媽看不下去了,給咱倆打款500元,讓咱倆買輛小推車,這就叫種子輪。
有了小推車,咱們開始研究怎么做煎餅馃子。終于在不斷地拍腦門兒之后,咱倆新創了香蕉餡兒的煎餅和榴梿口味的豆漿。這時候,一些口味奇特的客人(天使投資人)開始陸續給我們塞幾萬元、十幾萬元,說要合伙做生意。因此,我們不但可以租個鋪子,還能通過他們認識更多口味奇特的大老板(風投機構),這個過程就叫天使輪。
有了錢,我們開始招人、做渠道,何氏煎餅進入規模化生產、流水線作業階段。因為我們的產品口味獨特,越來越多的大老板想給我們投資,分煎餅鋪子的股份。于是,我們只能按照A、B、C、D輪的順序按批次收錢。
我們收的錢越來越多,煎餅鋪子的股東就越來越多。大家都希望自己手上的股份更值錢,于是,煎餅鋪子被炒作得十分玄乎,它的估值也就越來越高。最后,我們兩個賣煎餅的成了“精神偶像”,身家十幾億元。有的股東怕我們跑路,就逼著我們上市“割韭菜”。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公司上市以后,股東們會在第一時間套現走人。畢竟這么高的估值里有多少水分,是所有人都不敢想象的。
什么是基本面(此處僅指股票行業)
我們通常把做投資的人分成兩種類型。
一類就像金庸小說里的“氣宗”,他們喜歡透過現象看本質。他們認為,一只股票的好壞和市場環境、公司的經營狀況直接相關。而那些紅紅綠綠的K線圖,全是莊家騙人的玩意兒。
于是,這些“氣宗”前輩會不斷地搜集、分析行業政策和公司的財報,以此來判定一家公司長線上的漲跌。這種偏財務分析的做法,就叫基本面。
還有一類,他們就像金庸小說里的“劍宗”。他們更喜歡研究K線的奧秘,并按幾十年被“割韭菜”的經驗,給各種特殊的K線取名字,比如“烏云蓋頂,逃命要緊”“雨后彩虹,必有三浪”。
甚至有人把這些口訣整理后研發出一套電腦程序。現在外面很多掛著“人工智能”旗號的分析軟件,大概率是套這種口訣的。其實技術分析是證券行業所有從業者入門的必學內容,后期的基本面分析也必須建立在對技術理論熟稔的基礎之上,再和對手方在量價方面進行博弈。
我們只有真正摸清了一家公司的深水區后,才能按照它的“套路”和各種突發事件帶來的影響微調手上的產品。
什么是凈值型產品
凈值型產品就是告訴你,你得對所買產品自負盈虧。哪怕它是從銀行這種大機構里放出來的,也可能會讓你虧到連本都收不回來。
過去很多人喜歡買一些大機構發行的“某某一號”固收產品,倒不是因為它們讓你賺得多,而是因為它們讓你賺得穩。畢竟這類產品的介紹里往往會帶上“保本保息”的字樣,這就等于明擺著告訴你:投我10萬元,明年你一定可以拿到11萬元。
但是,這些機構在投資方面并不專業,所以他們在拿到大戶的錢以后,可能轉手就交給外面的投行去打理,自己則從中抽頭。而外面的投行,野路子實在太多了,虧損是常有的事。甚至有很多小公司,年初開,年尾就倒閉了。這就苦了那些發行保本保收益的大機構,他們只能自掏腰包給顧客發錢。演變到后期,他們只能拆東邊大戶的資金,去補西邊大戶到期的收益。這種玩法,就叫作資金池。
后來有些資金池的窟窿越來越大,甚至讓大機構都瀕臨破產。監管層一看,這風險也太大了。自古以來,也沒有哪門子生意是穩賺不賠的。所以新規出臺,保本保息和預期收益慢慢成為歷史,自負盈虧的凈值型產品未來會越來越多。
什么是對沖交易
舉個例子,夏天到了,可樂肯定賣得比冬天要好。于是,我用30元進了一箱可樂,順手再以30元的價格預售了一箱果汁。
一個月后,假如飲料市場漲價:果汁的價格漲了30%,那我就等于賠了9元;可樂的價格上漲50%,那我就賺了15元。這樣,我就能賺取中間差6元。
但如果受大環境影響,飲料價格下跌:果汁的價格跌了30%,現價變成了21元,但我已經收了30元的果汁定金,所以相當于賺了9元;可樂的價格跌了10%,現價變成了27元,而之前我已經以30元的售價采購過了,所以相當于賠了3元。這樣,我依然能賺取中間差6元。
這種通過犧牲一定的可能利潤來換取抵御部分風險的玩法,就叫作對沖。
(晨 云摘自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分鐘經濟學知識》一書,黎 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