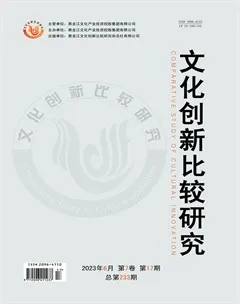動態系統理論下非英語專業大學生英語書面語能力動態發展研究
張燕
(青島理工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山東青島 266520)
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高校大學生作為新生代的高知群體,其濃厚的家國情懷、豐富的知識儲備和勇于探索的創新精神表明了大學生在中華文化對外傳播中可以發揮生力軍作用。
然而,當前非英語專業大學生在英語書面語方面普遍存在詞匯使用有限、詞塊類型欠缺、簡單句式過多等缺陷。鑒于此,本研究以動態系統理論(Dynamic System Theory)為分析框架,探討在外刊選讀的二語寫作教學模式下引入非英語專業大學生英語書面語中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的動態發展路徑,探究兩者的關聯性,進而在實證基礎上探討在當前國情下如何有效地提升大學生英語寫作能力,增強其文化傳播的語言技能,以期豐富和發展國內動態系統理論視角下二語學習者二語書面語能力的研究成果。
1 動態系統理論及其研究現狀
1.1 動態系統理論內涵
動態系統理論概念起源于牛頓運動定律,原用于描述系統的復雜、動態變化過程,后被廣泛應用于數學、物理學、生物學、化學、經濟學等多個領域。20世紀90 年代,美國語言學家Diana Larsen-Freemen將動態系統理論引入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為二語習得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Larsen -Freeman[1]認為指出動態系統理論具有動態、復雜、非線性、混沌、不可預測、初始狀態敏感、開放、自組織、反饋敏感和自適應的特點,這些特點之間相互作用又相互統一;而人類語言習得過程因具有復雜的動態性特征,也被視為動態復雜的系統,因此動態系統理論可應用于二語習得研究領域。之后,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以動態理論為指導,從不同角度出發探討外語教學和二語習得研究問題。Nick C.Ellis[2]更是指出動態系統理論的應用是21 世紀“二語習得研究新時期到來的標志”。
1.2 動態系統理論下國內二語寫作研究現狀
國內對動態系統理論下的二語寫作研究主要聚焦在對學習者英語書面語產出詞匯的動態發展研究、學習者英語書面語語言流利度的動態研究、對學習者英語書面語詞匯復雜度的動態研究,以及對學習者英語書面語句法復雜度的動態研究等。鄭詠滟[3]以16 名大一學生一學年期間寫作的128 篇作文為語料,通過歷時研究,基于移動極值圖法、再抽樣法、蒙特卡羅模擬、移動相關系數圖等動態系統理論特有的分析方法,較為全面地揭示了學習者英語書面語產出詞匯的動態發展過程。陳艷君[4]以二語寫作流利度為觀測點,采用變點分析器跟蹤研究了大一新生二語寫作流利度的動態發展過程,發現學習者的寫作流利度發展呈現出差異性變化。王宇、王雨[5]從動態系統理論視角出發,以英語專業三年級一個班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微變化研究法,對英語專業三年級學生的二語產出性詞匯復雜性和多樣性的變化及其交互關系模式進行了一學期的跟蹤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深入探究了學生詞匯動態發展與學習者所處的發展階段、學習信念、詞匯輸入及作文話題的相關性。朱慧敏[6]采用移動極值圖、動態建模等,跟蹤研究了2 名英語專業學生4 個學期的議論文,考察了他們文本語料中句法復雜性3 個指標的發展軌跡并擬合動態增長模型。黃婷、鄭詠滟[7]通過對比分析雙外語學習者和單外語學習者在一學年內第一外語(英語)書面語句法復雜度的動態發展過程,發現兩組學習者在外語書面語句法復雜度上的發展水平總體相當,但雙外語學習者在從屬結構使用上的變異度更高。王海華等[8]在實證基礎上對119 名非英語專業大學生完成的三種體裁作文的語言復雜性和準確性的特征,以及兩者間的互動關系進行研究。
由此可見,國內動態系統理論視角下二語寫作研究已從純理論研究逐漸發展為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研究,研究對象日益寬泛。然而,當前國內在該方面的研究仍處于初級階段,存在幾點不足:一是依托動態系統理論來深入分析語言子系統內發展路徑以及各子系統間的關系的實證研究相對匱乏,研究廣度和深度還需進一步拓寬和加深,研究方法亟待完善;二是研究對象多為大一和大二學生,研究成果覆蓋面受限。因此,本研究以動態系統理論為分析框架,探討引入外刊選讀的二語寫作教學模式下非英語專業大學生英語書面語詞匯復雜性和句法復雜性的動態發展路徑,進而豐富和發展國內動態系統理論視域下二語書面語發展研究數據,以期在實證基礎上建構適合我國國情、具有本土化人才培養特色的二語寫作教學模式。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動態系統理論”為指導,對引入外刊選讀的二語寫作培養模式下10 名非英語專業大三學生的英語書面語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的發展軌跡進行動態考察,進而探討該寫作模式對學習者二語寫作能力提升的實效性和可行性。研究主要解決三個問題:
(1) 引入外刊選讀的二語寫作教學模式下學習者英語寫作書面語的語言準確性的動態發展軌跡是怎樣的?
(2) 引入外刊選讀的二語寫作教學模式下學習者英語寫作書面語的句法復雜性的動態發展軌跡是怎樣的?
(3) 學習者英語書面語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是否存在相關性?
2.2 研究對象和研究語料
本研究的受試者為某10 名非英語專業大三學生,研究語料為該10 名受試者一學期內分5 次完成的共計50 篇英語習作。這10 名受試者在教學實驗前參加了大學英語四級考試。經獨立樣本t 檢驗分析,10 名受試者的考試成績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表明了該10 名學生的英語水平相近。為方便分析統計,本研究用S1-S10 指代選取的10 名學生,用W1-W5 指代每個學生提交的5 篇作文。
2.3 研究過程和測量工具
研究過程如下: 在為期15 周的教學實驗中,授課教師除向10 名受試者教授寫作策略外,還從《經濟學家》《時代周刊》《自然》《麥肯錫季刊》 等期刊中選取合適的文章作為學生外刊選讀材料,引導學生掌握英語寫作中常用的高階詞匯和復合句型,從而側面提升學生二語寫作水平。與此同時,10 名受試者每隔三周依托智能寫作平臺完成一次英語習作,均在統一的測試地點和時間內限時完成寫作任務。選取的作文體裁和難度與考研英語寫作難度相近。學期末,本研究共收集50 篇習作語料。
此外,本研究對10 名學生英語書面語能力的考察主要依據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語言準確性的衡量指標是作文中無錯誤的T 單位數與T 單位總數的比率(EFT/T)。Polio&Shea[9]指出EFT/T 是判斷語言準確性的一個可靠指標。句法復雜性則是指“語言產出中出現的形式范圍以及這些形式的復雜程度”。Lourdes Ortega[10]認為句法復雜性的主要依據之一是從屬句比率(DC/T)。T 單位指“包含有一個主句,以及附加和嵌入的所有從句和非從句結構的不可分割的最小單位”。從屬句比率(DC/T)是指每篇作文中的從屬句總數(dependent clauses)與T 單位的比率[11]。一般該比值越大,其句法結構越復雜。
本研究主要采用兩種測量工具: 一是采用變點分析器(Changing point Analyzer),將收集到的每個學生5 次作文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的動態數值輸入CAP,對變化可能發生的置信區間和至信水平進行分析,從而對于變化是否發生、何時發生,以及有多大可能性發生這三方面作出判斷; 二是利用SPSS 軟件的皮爾遜相關分析對作文樣本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的關聯性進行考察,以此進一步探討語言準確性(EFT/T)與從屬比(DC/T)之間是否存在顯著關聯。
2.4 數據收集與分析
將收集的50 篇作文樣本進行標注并進行統計分析,計算出每個樣本的T(T 單位分數)、EFT(無錯誤的T 單位數)、DC(從屬分句總數)等。經過數據分析,統計出各作文樣本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的各項指標,結果如下(見表1)。

表1 10 名受試者5 次作文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EFT/T&DC/T)
可以看出,10 名受試學生的語言準確性(EFT/T)呈現一定的波動,學習者英語書面語的語言準確性存在個體內和個體間差異。就個體內差異而言,學生語言準確性存在一定的波動,但都在一定區間內。就個體間差異而言,對于較為熟悉的議論文體裁,部分學生完成習作時顯示出豐富的詞匯量,語言準確性較高。而在應用文寫作方面,一些學生則在使用詞匯時出錯較多,顯示出對該體裁熟悉度不夠,接受的專項訓練較少。此外,大多學生在完成期中考試前和期末考試前布置的兩次習作時,其寫作語言準確性較高,可能的原因:一是學生正處于備考階段,詞匯量較為豐富,因此在寫作時詞匯出錯率會有所降低;二是學生在這兩個階段輸入了較多的外刊文本,詞匯量有所豐富。Ellis 等[12]曾指出二語習得的語言構式習得是受各類輸入因素如語言輸入的頻率、突顯度、原型性等因素的制約。蔡金亭和王敏[13]也深入探討了此類觀點。在本研究中,語言準確性指標(EFT/T)側面印證了這一點,即語言系統中某個構式出現的頻率越高,就越有助于學習者加強固化該構式,也就越能推動該學習者熟練地應用該語言構式。所以,受試學生學習議論文體裁越多,就越容易提高議論文寫作的語言準確度。
此外,還可看出10 名受試學生作文的句法復雜性在DC/T 這一個指標層面上呈現一定的波動。整體來看,第3 次和第5 次習作的句法復雜性稍高于其他3 次,第1 次和第4 次習作的句法復雜性則稍低點。原因可能是第1 次習作還未展開較多的寫作培訓和外刊選讀,受試學生的知識儲備量并無太大差別,所以在英語寫作能力上沒有顯著變化。到第3次和第5 次寫作時,學生已掌握了一定的寫作技巧,閱讀了較多的外刊,且這兩次恰好為期中考試和期末考試前夕,學生進行了集中備考,所以在完成習作時能運用復合句式來提高寫作句法復雜性。第4次習作句法復雜性有所弱化可能是由于期中考試結束,學生產生了一定的倦怠感。
與此同時,本研究還對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進行了皮爾遜相關分析(見表2)。

表2 10 名受試者5 次作文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的皮爾遜雙尾相關性
通過分析發現,在本研究中,受試學生作文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兩個指標呈顯著的負相關性,表明了句法復雜性和語言準確性存在競爭關系,即學習者產出的句法復雜性越高,其語言準確性就越低。學習者使用的從屬成分越多,句式越復雜,就越會在詞匯使用上出錯。這一研究結果也印證了Skehan[14]的權衡假說,即學習者在習得語言時,受個體注意力資源有限的影響,會導致一個子系統發展與其他子系統發展產生相互競爭的關系,使得語言子系統之間發展不平衡,形成此消彼長的語言特點。
3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動態系統理論為分析框架,借助CPA軟件對10 名理工科大三學生10 次英語作文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進行了跟蹤研究。經過分析可看出:第一,學習者英語書面語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都在一定范圍內出現波動,兩個指標的發展過程呈現出階段性和非線性的發展軌跡,但都未發生突變現象,原因可能為大三學生的英語書面語能力已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第二,學習者英語作文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與其受訓時長的增加呈正相關,即寫作培訓和外刊選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擴充其詞匯和句法的知識儲備,側面提高其習作能力。學習者的受訓時間越長,其英語書面語能力就越能得到提高;第三,學習者二語語言的各子系統內以及各子系統間存在復雜的互動關系。就本研究而言,學習者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受輸入材料的信息量、作文體裁、學習動機,以及寫作話題的熟悉度等因素的影響。學習者受哪種寫作體裁的專項訓練越多,就會在該體裁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上能力越強。此外,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也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具有此消彼長的語言特點。
因此,在今后的二語寫作教學中,教師應將學生的英語書面語能力發展的非線性、動態性和變異性等特征納入考慮范圍,針對不同學生的個性化差異特征,因地制宜地指定不同的寫作策略培養方案。同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應根據寫作需求適時地引入不同的外刊材料,增加學生的信息輸入量,側面提高其詞匯和句法使用能力,從而多維度地提高學生的語言使用能力,增強其文化傳播的雙語能力。
4 結束語
本研究以動態系統理論為指導,通過為期15 周的教學實驗探討了在引入外刊選讀的二語寫作教學模式下,非英語專業大學生英語書面語的語言準確性和句法復雜性的動態發展軌跡。本研究雖豐富和發展了國內二語寫作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不足,如選取樣本量較少,寫作任務次數還待增加等。未來研究應進一步擴大取樣的范圍,測量指標應更為細化,在此基礎上得出更具代表性的結論,從而為如何有效地提升我國高校大學生英語書面語能力、增強其中華文化國際傳播能力提供可供參考的數據,以拓寬外語教學和二語習得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