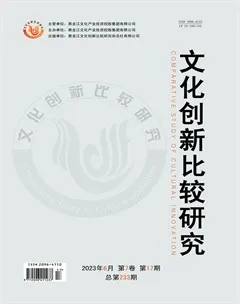從“Turkey”到“Türkiye”
——土耳其英語國名的改變考析
施思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廣東廣州 510545)
近年來英語翻譯及語用的新話題,其探討散亂于網絡、報紙與時政雜志評論中。對修改物品英語名稱甚至國家英語名稱現象的討論熱烈,角度各不相同,有從政治影響力和國家歷史的視角進行辨析的,有從文化傳承和身份認同角度來探討的,也有從個人情感等微觀視角來闡發的。立場不同,得出的結論自然不同。2022 年6 月1 日,應土耳其的要求,聯合國將土耳其的英語國名從“Turkey”改成“Türkiye”。2021 年12 月,土耳其開始在國內和國際場合上使用“Türkiye”作為其英語國名,成為英語語言現象級“頂流”。土耳其不惜力氣改國名,再次證明了英語語用這個舊話題的新意義就是符合本國文化的用詞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土耳其改名具有分析價值,再加上現在聯合國發展成熟,信息分享簡便,相信未來還會有更多來自土耳其的“Türkiye” 走入大家的視野,帶來更多代表不同地域文化的用語。
1 土耳其開展更名行動的原因
1.1 “Turkey”語義的負面影響
土耳其的英語國名為“Turkey”。在劍橋字典中“turkey”的一個解釋為“a stupid or silly person”,即“愚蠢的人”[1]。現實使用場景中,“turkey”的含義在一些場合和場景中引申為“嚴重失敗的東西”或“愚蠢的人”,一直被土耳其人視為“有失體統”。一直以來,“Turkey(土耳其)”與“火雞(turkey)”的無端聯想亦是有損土耳其的國家形象。事實上,自從1923 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起,其國名的土耳其語就一直寫作“Türkiye”,意即“突厥人的國家”,在其他語言的翻譯中,也都沒有問題,如在中文中,土耳其一詞并無歧義,唯獨在英語含義中出現了和火雞同名的現象。一個強大的國家有滑稽的名字,更名勢在必行。對土耳其這個國家來說,正名是邁向強國的一個關鍵。
英語是當今世界最流行的語言,在土耳其英語國名加入土耳其文字符的嘗試,顯然來自該國的創新。起名字屬于國家權力,怎么叫確實應該尊重本國的意愿。土耳其官方媒體土耳其廣播電視臺(TRT)在對改名進行解釋時表示,如果在谷歌引擎中輸入“Turkey”一詞,結果往往是代表土耳其形象的圖片和其他一系列圖片混在一起,土耳其認為這明顯有損該國國家形象。事實上,一個國家更改英語國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不僅僅是聯合國批準與否,還將涉及由各國政府到全世界全方位的改變,其中包括民間使用習慣的改變。為此,土耳其推出了一系列大張旗鼓的造勢宣傳活動,不惜成本。盡管很多國家的英語名稱也有其他含義,例如中國的英語國名“China”首字母小寫時為“china”,意為“瓷器”。另外一個例子是小寫的 “japan”,其與表示 “日本”的“Japan”意思大有不同,這點和“Turkey”情形極為相似。“japan”的名詞意思是“漆器;日本亮漆”,它的動詞意思是“往……上涂漆”。對此,中國與日本并不在意,因為這些詞匯的含義在國家形象方面與國家文化相輔相成,形成良性的影響,因此不會興師動眾更改自己的英文國名。但是對于土耳其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情懷的大國和在國際舞臺上有政治抱負的總統埃爾多安來說更改土耳其英語國名可謂勢在必行。
1.2 國家品牌推廣需求
國名雅俗程度和積極程度能夠影響對民族特征、國家吸引力和可信度的評價。一般生僻程度較低、越高雅或者越積極的國名,所獲得的評價越好,也能產生光環效應,能提高國家吸引力。在翻譯者的視野中,國家或者地名翻譯用詞的更改現象由來已久,如漢城改為首爾,這種更貼切的詞語就被韓國人認同,全世界接受。英國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塞利姆·科魯說:“與火雞的聯系確實讓埃爾多安的政府感到惱火。鑒于政府對國家形象的敏感性以及對民族主義言論的喜愛,這并不奇怪。”土耳其英語國名的變更是土耳其的一次品牌重塑,土耳其政府此舉意在緩解以英語為主的外交格局。這并非土耳其第一次試圖更名,20 世紀80 年代中期,時任總理的圖爾古特·厄扎爾曾做過類似的努力,但從未獲得成功。
“Türkiye”概念的提出與討論,離不開與現實緊密相連的時代背景:國家經濟實力增強讓土耳其人自信心增強,與外界交往日益頻繁導致摩擦頻率相應提高,還有土耳其人在接觸其他社會后對自我身份有了重新思考及再認識。這些都是導致土耳其國民民族主義高漲的原因。一直以地區大國的定位自居的土耳其,此舉背后的政治動機,更多的是一種重塑國家品牌的策略,以提高該國的國際地位。土耳其本身橫跨歐亞大陸,在土耳其看來,西方將“火雞”與“土耳其”強行聯系在一起,就是西方人對土耳其人的種族歧視。“Türkiye”作為土耳其的英語國際名稱,有助于進一步提升土耳其的品牌和聲譽。因此,土耳其改名成為世界矚目的現象,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再次揭示了翻譯更改的國家社會文化背景與語言技術背景特點。“Türkiye”的提出能讓不同國家和語言的人改變以往英語國名造成的刻板印象,實現埃爾多安所說的“以最佳方式代表土耳其民族的文化、文明和價值觀”。
1.3 政治強人的出現
可以說,沒有政治強人的出現,就不會有土耳其大國抱負的出現,也就不會有英文譯名更改的產生。作為土耳其政治強人,埃爾多安早就要求徹底改掉這個糟糕的名字,不再忍受這種變相的羞辱,而替代“Turkey”的“Türkiye”在土耳其語中意為“突厥國”,完美地把該國的民族和歷史結合起來,以期重塑祖上榮光,以及以英語為主的外交格局,為埃爾多安建立一個更強大、更傳統的土耳其提供正當理由。“Türkiye”概念的重新提出,代表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一個愿望,希望“以最佳方式代表土耳其民族的文化、文明和價值觀”。2021 年12 月4 日,他頒布了總統令更改國名,要求將土耳其的官方英語名稱從“Turkey”更改為“Türkiye”。土耳其總統府通訊局局長阿爾頓表示,更改英語國名是土耳其政府為加強國家品牌推廣采取的重要步驟,土耳其政府將會在職能范圍內,在所有的活動和文書往來中強化“Türkiye”的標識。
土耳其現任總統埃爾多安不遺余力地推動土耳其改名有一個重要原因。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土耳其語:RecepTayyip Erdoan;英語:RecepTayyip Erdogan,1954 年2 月26 日-)在2014 年出任土耳其總統,并于2018 年成功連任,是土耳其共和國第12任總統。埃爾多安在任期間,土耳其人均收入翻了三倍,他因此謀求成為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也因試圖恢復奧斯曼帝國,被《經濟學家》稱為“新時代的蘇丹”。埃爾多安說:“如果把我們看作一個二流國家那就大錯特錯了,土耳其曾經強大過,我們要找回自己的位置。”[2]
2 “Turkey”與“Türkiye”的英文語義構成分析
尤金·奈達說過,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于國名的情況尤為突出。土耳其的英語國名翻譯中蘊藏的文化內涵往往被土耳其本土外的人忽略,而只用一對一的對等翻譯來處理。國名在不同語種中的翻譯因歷史文化背景差異造成的問題或者尷尬,有時要過幾百年才能顯現,土耳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此,必須對深藏其中的文化加以深入了解,才能避免出錯。這點在人名翻譯中尤為突出,例如:2022 年英國女王逝世,王儲查爾斯繼位為“查爾斯三世” 國王 (Charles III)。查爾斯英文名字“Charles” 音譯為“查理” 或“查爾斯”,長期以來“Charles”存在兩種中譯法是正常現象。查爾斯國王在登基前的譯名普遍為“查爾斯王儲”,在繼位后以“查爾斯三世”為稱號順理成章。但是,英國歷史上曾出現兩任查理國王——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而新國王延續的查理三世譯名算是理所當然。然而,據《倫敦時報》報道,查爾斯曾考慮在繼位后選用喬治七世,以紀念他的祖父,避免使用在王室圈子里被認為招來厄運的“查理”。兩種譯名都可接受,而查爾斯的考量背后是英國歷史的特別意識形態的牽動,這是英國作為個別社會語境來選擇合適譯名的典型。
2.1 “Turkey”的英文語義構成分析
“Turkey”產生的首因效應在于國際社會習慣用英語單詞“Turkey”稱呼土耳其。這個已經使用了100年的英文名稱,與首字母小寫的“turkey”(火雞)相同,并且帶有某些貶義意味。這種令人困擾甚至尷尬的聯系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前,歐洲殖民者踏上北美時看到當地野生火雞,他們錯誤地認為它與珍珠雞相似,珍珠雞原產于東非,通過奧斯曼帝國傳入歐洲。這種野生火雞很快成為殖民者餐桌的美味。自此,火雞與殖民者節日的聯系就存在了。只要提到土耳其,國際社會率先想到的就是“火雞”,甚至有人直接將其稱為“土雞”;也有人將其與“殖民”聯系起來。這讓土耳其國民十分不滿并感到難以接受,其中無論哪種形象,其本質上都只是西方意識形態謀劃下的“他者”,一種服務于文化帝國主義霸權的參照物與陪襯。
2.2 “Türkiye”的英文語義構成分析

土耳其的前國名 “Turkey” 來源就是突厥的音譯,因為都是突厥系民族,土庫曼斯坦名字前也有“Turk”的前綴。“Türkiye”意為“土耳其人的家園”,詞根“Türk”有“突厥人”之意,符合很多土耳其人自認為是突厥后代的身份認同。“Türkiye”兼有介紹國家主體民族的風俗禮節、精神文化等因素的功能,讓土耳其特點更好地展示給外部國家。與此同時,土耳其是一個具有極強歷史情懷的國家,歷史上奧斯曼帝國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在16 至17 世紀,在蘇萊曼一世統治時期達到鼎盛,帝國統治的區域地跨歐洲、亞洲和非洲。在埃爾多安看來,改變“火雞”與“土耳其”的聯系,是該國振興的前提條件,“國名一改火雞變鳳凰”,是改變土耳其的“哈士奇”形象、大展宏圖、恢復土耳其祖上榮光并提升民族自信心的重要籌碼。
3 土耳其更名的特征
由于“Türkiye”具有獨特的語用價值,因此能夠在土耳其取得共識,其中反映了該國人民感情傾向的變化。通過對含有歷史文化和民族理想語義的“Türkiye”例子的分析可以發現土耳其人民在情感發生了巨大改變。該詞變成國家的英語名稱,展現了英語詞匯包容性特點。“Türkiye”專有新名詞被聯合國接受,將逐漸深入人心,雖然當下它作為一種新身份出現在英語世界眼前。
3.1 明顯的突發性
土耳其更名行為是由于主體的國家或總統實際行動,出于重大國家定位的考量——不希望土耳其被“對號入座”,成了當務之急,更名同步引發土耳其民眾對國家、民族前途、利益的思考。更名后的主要障礙是國際社會接受改名可能耗時頗久,普及率也難以保證,推廣起來還是存在頗多障礙。單個國家是構成世界的主體,如今國與國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關系。在當今變化和演變中,國家的代表要素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國家的名字有可能隨之發生變化,從某種程度上看也反映了土耳其國民的心態:對國家的文化自信提升的迫切希望。
3.2 一定的自發性
更改國名是某個主權國家的一種自發行為,具有自發性。如土耳其更名“Türkiye”的行為完全處于一種自覺狀態,并且可以隨時隨地不受任何事件和空間限制——只要主權國家擁有主觀愿望即可,土耳其認為這是找回自己應有地位的一種方式。每個國家在聯合國都可以表達自己國家的意愿,世界上還有一些國家曾改變了自己的名字,有的是為了擺脫殖民遺產,有的是為了重塑形象:荷蘭Netherlands原來是Holland; 馬其頓因為和希臘的政治紛爭,Macedonia 因而改名為北馬其頓North Macedonia;伊朗Iran 于1935 年由波斯Persia 演變而來;現在的泰國Thailand 曾經是暹羅Siam;津巴布韋Zimbabwe改名之前是羅得西亞Rhodesia,顯而易見是西方殖民時期的遺產。
3.3 諸多的政治考量與理性思考相結合
雖然土耳其英語國名的變更給外界造成的印象是帶有若干政治野心的大國夢想,但“Türkiye”的使用對本國人民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是對國家利益、民族復興的強國之路的反思,彰顯著該國的理想的光輝。因為每個國家的正式國名只有一個,當土耳其宣布改名時,其他國家選擇尊重其更名意愿。同樣的如緬甸,1989 年,為了擺脫原來的殖民色彩而改名。“Burma”是緬甸的英文舊稱,后改為“Myanmar”,現已經是聯合國和全球絕大多數國家使用標準用詞。緬甸政府認為,“Burma”為英國殖民者命名,帶有鮮明殖民主義色彩,加上不符合當地人發音習慣,所以決定改名。時任緬甸外交部長吳溫納貌倫在會見仍然使用“Burma”的美國官員時就指出,“也許你認為這是小事,但‘Myanmar’這個詞關乎一個國家的尊嚴”,“正確使用國名顯示一種相互平等和尊重”。但是,當今世界,“Burma”仍常見于西方官方場合和新聞報道中[4]。
“年度流行詞語是一幅展現社會動態變化的歷史畫卷,以其獨特的角度表達人們的價值觀、文化觀,也反射出社會和時代的變化特征,而且還反映出社會的文化形態。”[5]對“Türkiye”的熱烈討論也說明“Turkey”和“Türkiye”在英語世界可能長期并存使用。以上幾個特點,正意味著國家更名后,“Türkiye”一詞作為英語外來詞,在造詞結構和文字意義上和習慣詞“Turkey”有很大的區別,為英語詞匯帶來了外來詞匯的一種新奇性。同時,由于國際社會習慣還處于動態發展中,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接受由“Turkey”到“Türkiye”的轉變[6-10]。
4 結束語
英語是目前世界的共通語言,有較強的話語權。各國語言與英語相比較,在文化身份表現方面要顯示作用,應該還有一段距離。“Türkiye”是更名,更是正名。維護本國傳統和歷史的文化積淀,才能提升自我的文化自信。“Turkey”一詞缺乏土耳其文化內涵,與本國語言本意相去甚遠,這使得“Turkey”英語國名的土耳其文化內涵空洞化,造成文化歧義的后果。強化土耳其文化,以塑造國家形象和提升國人文化自信,是刻不容緩的一項任務。表面來看,土耳其更名是“Turkey”這個詞的詞義不好,實際上,新的國名“Türkiye”更貼近土耳其歷史上的文化根源,避免了不同語言的歧義和意義不雅。土耳其的更名做法更有著深刻的社會意義,從國家主權意識的增強、民族獨立精神的覺醒、歷史傳統的傳承和文化自信與文化多樣性的追求等方面得以充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