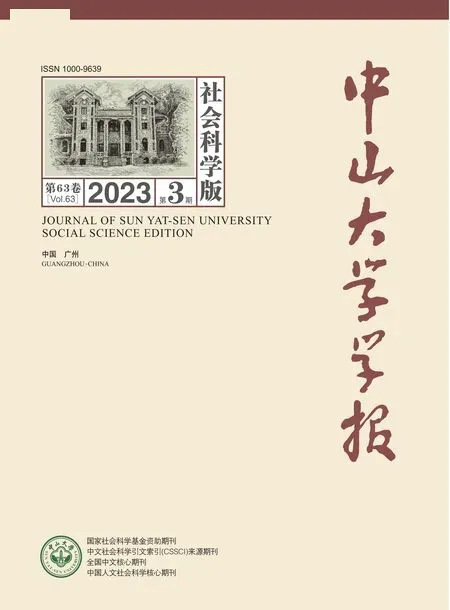天經·地義·人情:具體普遍性的結構 *
陳 赟
普遍性及其與特殊性的關系,對于人類思想具有根本性的意義,中國步入近代以來,它就是一個中心性的課題,馮友蘭曾以共相與殊相、一般與特殊的關系表述這一課題,并認為這是哲學的最基本問題①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3頁。。同時,普遍性本身又恰恰是飽受爭議的課題,在對普遍性的理解上,人們很難達成共識。從譜系學的思路看②按照伯納德·威廉斯的概括,“一個譜系是這樣一種敘述:通過描述一個文化現象在過去發生、或根本可能已經發生、或可以想象已經發生的一種方式,來試圖說明那個文化現象”。[英]伯納德·威廉斯著,徐向東譯:《真理與真誠:譜系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26頁。,奠基于超越性的絕對普遍性以及與之相關的均質普遍性,在今日已經深陷困境,它無法深層地支持多元共生的主題;為超克普遍與特殊的對峙,我們擬借助于儒家傳統中的天經、地義、人情的思想來闡明“具體普遍性”的可能性,以此為共生與多元提供新的普遍性基礎。
一、超越性的絕對普遍性:根基、困境和終結
今人對普遍性的理解,深受古希臘邏各斯傳統與猶太—基督宗教兩大傳統的影響。前者為普遍性提供了立足于概念及其形式化運作的思想工具,這使得在智性意識中可用剝離質料的方式來構建形式的普遍性;后者提供了這樣一種進路,即“因為絕對,所以普遍”。在前者,質料是特殊的,甚至是雜亂的,對質料的形式化處理是普遍化的關鍵環節;在后者,普遍性由純粹超越性或絕對性來界定,而絕對性就其內涵而言免除了任何限制,本質上就是純粹創造性和絕對自由的化身①陳赟:《歷史意義的焦慮:“普遍歷史”的回應及其病理》,《學術月刊》2022年第1期。。在前者,普遍性通過人的智性意識(noetic consciousness)被給出;而在后者,靈性意識(pneumatic consciousness)才是絕對普遍性顯現的恰當方式。
絕對普遍性的構建可以有兩種進路:一種是嵌入式(embedding)路徑,一種是脫嵌式(disembedding)路徑。嵌入式路徑是將絕對者作為根據,層層嵌入個人、社會、宇宙、歷史之中;絕對者無所不在,內在于一切之中,但又不能化為任何事物及其整體,因為絕對者并不能被理解為宇宙內事物,而是宇宙及其內部所有事物的最終根據。對于個人而言,他與絕對者之間的關系是以具體社會、宇宙秩序或歷史過程為中介的,這種層層嵌入的秩序構造模型,提升并擴展了人的生存論視野。而脫嵌式進路恰恰相反,將絕對者從與個人、社會、宇宙的給定捆綁和關聯中層層突破,它的極端形態則是在脫離宇宙及其秩序的層次上被構想,于是它作為絕對的創造與自由而被體驗,這就是在保羅傳統中發生的情況。就西方的歷史過程而言,以脫嵌式構造的絕對普遍性具有根本性的影響。
脫嵌式絕對普遍性成立的社會學條件是宇宙論帝國秩序的壓迫。向異族擴張的王國將自己的政治秩序鑲嵌到宇宙論秩序中,通過神化統治者及其統治以達成正當性,政治秩序被視為宇宙論秩序的縮微形式。對帝國征服的抵抗就必然關聯著對宇宙論秩序的抵抗,猶太民族之所以率先突破宇宙秩序而構想更高的普遍性,正因猶太民族在抵抗宇宙論帝國的漫長經歷中,深感必須在宇宙論秩序之外為生存重新確立根據。與《但以理書》對人類帝國無常更替的意義加以否定相關聯,保羅傳統對宇宙秩序及其意義予以根本性否定:宇宙不是意義的缺席或匱乏,而是根本就沒有意義。奧古斯丁之所以被視為一位“打破宇宙者”(cosmoclaste),就是因為他不但以為宇宙的節律在絕對者面前黯然失色,而且強調:一個人若了解世界的終極創造者,就不必了解被創造世界的結構②[法]萊米·布拉格著,梁卿、夏金彪譯:《世界的智慧:西方思想中人類宇宙觀的演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7頁。。一旦生存的意義被唯一地系屬于同絕對者的聯系,而絕對者又只能在靈性意識中顯現,那么,身體、萬物、政治社會的世間乃至星辰宇宙,都變得無足輕重③奧古斯丁說:“我們神游物表,凌駕日月星辰麗天耀地的蒼穹,冉冉上升,懷著更熱烈的情緒,向往‘常在本體’……一再升騰,達于靈境”,“在那里生命融合于古往今來萬有之源,無過去、無現在、無未來的真慧。真慧既是永恒,則其本體自無所始,自無所終,而是常在;若有過去未來,便不名永恒。”奧古斯丁所追求的靈性上升,不僅是對宇宙的脫離,而且還是對此身、此生、此世的脫離,“在一人身上,血肉的蠢擾,地、水、氣、天的形象都歸寂靜,并自己的心靈也默爾而息”,“此生已毫無留戀之處。我不知道還有何事可為,為何再留在此世”。[古羅馬]奧古斯丁著,周士良譯:《懺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77—178頁。。以脫嵌式方式建構絕對普遍性,必然導致因極端凸顯純粹精神性而貶抑宇宙、社會與身體性。
在抵抗性的社會學條件下,當人與絕對者的關聯成了最高也是最緊要的唯一事情時,人與絕對者的縱向關聯就會被視為生存論的奠基性視域,而人與社會、宇宙、歷史的關聯則會被貶抑為橫向性的水平層次,而且是現象性層次。既然世界與人生的意義都是由絕對普遍性賦予的,因而它“假定人擁有一種關于絕對的知識,而且因此恰恰是關于最重要之物的充足知識”④Friedrich Nietzsche,The Will to Power, trans.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ongdale,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8,p.10.;如果沒有這種絕對的知識,就無法確立道德的無條件性⑤Hans Küng, Does God Exist? An Answer for Today, trans. by Edward Quinn,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80, pp.578-579.。普遍性作為終極根據,它壟斷了意義,宇宙內事物及其意義都由絕對者賦予。從宇宙內事物的視角而言,不同事物之間都因與絕對者具有相同的距離而獲得了彼此的平等性;相對于同絕對者的距離,宇宙內不同存在者之間的等級與距離都可以忽略不計,因而,超越普遍性傾向于敉平事物之間的差異性、異質性、多樣性。縱向層次的絕對普遍性,在橫向層次反而要求一種均質的普遍性。
如果作為被造物的天地萬物,如同諾威奇的朱利安(Julian de Norwich)所說的那樣,只是絕對者手中的一小塊石頭,那么天地萬物就因其與絕對者的同等距離而言,它們彼此之間再沒有什么本質性的差異。在保羅與馬克安傳統中,人與人的一切差異都被抹去之后,只剩下與絕對性的關系,被發明的正是普遍同質的均質化個體。盡管人在血氣、才情、稟賦、地位、角色、家庭、國籍、民族、語言、歷史等方面存在著種種不同,但這些已經被排除在人的自我界定之外。因而所有的個人,不管他在世間有何種差異,在絕對者面前都是平等的均質化普遍個體;等級性社會與層級性宇宙不再有決定性的意義,“徹底消除天地萬物中各個部分的差別,產生的結果就是世界的內容被置于同一水平。世界的每個地方都與上帝保持相等的距離”①[法]萊米·布拉格著,梁卿、夏金彪譯:《世界的智慧:西方思想中人類宇宙觀的演化》,第215,225、226,235,236頁。。天地萬物的均質化與人類自身的同質化,都不再支持宇宙整體的等級性,人憑借其精神性,就能服務于絕對者,這決定了人的高度,他是從更高處來到宇宙之內的,這導致了在中世紀曾出現的如下觀點:“大的人”降生在“小的世界”里——這與內嵌式絕對普遍性所支持的“大寫之人是縮微之小宇宙”的觀點完全相反。
絕對普遍性基于超越性的視野,為抵抗世間性的一切形式的等級制度、不平等體制、人與人之間的不合理壓迫形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性能量,它為現代普遍個體的構造提供了強大支撐;但同時,由于它敉平宇宙內事物間的差異化與多樣性,因而成為一種均質的普遍性。伴隨絕對普遍性而來的還有對宇宙的秩序本性與美善品質的褫奪以及對自然性的解構。由于絕對普遍性只在內在的靈性意識中顯現,而宇宙與社會同樣是其“受造物”。相對于靈性意識而言,宇宙與社會只不過是絕對者的“粗心大意的作品”,“罪人的居所,混亂必然存在于此”,是“垃圾場”;甚至連整個地球都是“一座巨大的廢墟”,“真正的廢墟”②[法]萊米·布拉格著,梁卿、夏金彪譯:《世界的智慧:西方思想中人類宇宙觀的演化》,第215,225、226,235,236頁。。由此,世界萬物失去了倫理性,不再與美善相關;而去宇宙化的自我理解受到靈性意識的“內在之光”的指引,以與作為絕對者的上帝的關系來界定自己,人便成為脫離宇宙的孤獨者,在世界上漂泊的異鄉人。與此同時,人們所獲得的是一個去倫理化的純粹廣延性的物理宇宙,后者對人及其生存意義漠不關心。近代自然科學進一步解構了作為居所與秩序的宇宙,世界不再是有機整體,不再是由原初渾沌(chaos)敞開的入口來介入的秩序,無限開放的浩瀚宇宙(universe)與人性并無聯系,它自身并無道德與精神的內涵。祛魅后的世界顯現出其價值中性的冷漠虛無和無動于衷,倫理學已經不再需要世界,世界只是人類活動的陌生的、漠然的背景,它在人成為人的過程中注定并無實質意義。
由于絕對者籠罩了宇宙及其一切,這使得天地萬物再無“自然”可言,不再是自己如此,而是被造物。這就造成了一種景觀:自然界的事物并不“自然”(自己如此),相反它是“被動”的,因而能以同質化方式塞進“自然界”的集合空間,“天體萬物的概念把天跟被創造的其他事物放在同一水平。‘上帝平等地存在于一切事物,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物質,存在于天和地。天不再處于受到青睞的位置’”③[法]萊米·布拉格著,梁卿、夏金彪譯:《世界的智慧:西方思想中人類宇宙觀的演化》,第215,225、226,235,236頁。。這為對天的理解從本體論與宇宙論視域讓位于物理學的進路提供了前提:既然一切神圣性與奧秘性從天地萬物中被抽空,剩余的只是物質;而在物質這一點上天地萬物包括人的肉身都并無區分,這就允諾了那種普遍同質可以為思維所穿透的世界圖像。當奧卡姆強調宇宙中“物質是以完全相同的比率存在”④[法]萊米·布拉格著,梁卿、夏金彪譯:《世界的智慧:西方思想中人類宇宙觀的演化》,第215,225、226,235,236頁。時,我們看到了一個被絕對性抽空之后只剩下物質的均質化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因其靈性距離絕對者更近,而居于中心位置,他站得比天還高、比地還廣。絕對者與人以外的天地萬有之間的差異已經無足輕重,對于唯一與絕對者保持聯系的人而言,它們既是同質的,也是空洞的。在這樣的宇宙圖景中,人的尊嚴被大大突出,“大的人”凌駕于諸天宇宙之上,而真正被視為生活在絕對者的近處。這一均質化的宇宙圖景同時也導致了人自身的無法彌合的鴻溝,人的肉體與物質性的宇宙一樣,微不足道,同質而空洞,人的自我界定只能聚焦于與絕對者為鄰的精神性。
不難看到,脫嵌式的絕對普遍性,既吸納了宇宙自身的“自然”與意義,又吞噬了萬物固有的多樣與差異,一個普遍、均質、空洞又被剝奪了自然本性的世界,與吸納性、吞噬性的絕對者共在;反過來,一個被抽空了意義與本性的普遍同質化的世界才更需要絕對者,來作為意義虛無的世界與自我的意義本原。在抵抗的社會學條件下,脫嵌式的絕對普遍性無疑提供了精神自由與解放的思想能量。然而,當它進入內在世界與帝國秩序的和解時,就會面臨超越性與世間性的張力,甚至成為帝國的宗教。只有絕對超越性與世間性保持永恒的張力性結構而不是彼此互滲結合時,地上國家與精神原鄉才不至于兩敗俱傷。一旦絕對者進入政治社會與共同生活世界并與之結合,就會形成反向性的后果:一方面導致“利維坦”裝置的神圣化,另一方面則導致絕對普遍性的探尋者通過世間性的盈利心與功業心以求確證的信念。兩方面合流的結果則是“世俗化時代”或“虛無主義時代”①[英]彼得·沃森著,高禮杰譯:《虛無時代:上帝死后我們如何生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 年,第1—34頁。此外,唐納德·克羅斯比區分了政治虛無主義、道德虛無主義、認識論虛無主義、宇宙論虛無主義和生存論虛無主義。[美]唐納德·A. 克羅斯比著,張紅軍譯:《荒誕的幽靈:現代虛無主義的根源與批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2—46頁。的到來。
當人被縮減為世間存在者時,不論是宇宙或歷史整體還是脫嵌式的普遍性都失去了在人那里顯現自身的可能性。自尼采與現象學以來,觀看宇宙萬物的視角主義原理被廣泛接受②阿瑟·丹圖曾指出,個人不可能享有使得歷史整體的觀看得以成立的認識支點。這一點也適合“上帝之眼”,人不可能具有那樣一種無視角性的視域。[美]阿瑟·丹圖著,周建漳譯:《敘述與認識》,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年,第11—18頁。羅斯指出,“一種沒有明顯的視角局限性的意識,根本就不是意識”,“所有的視角和秩序,包括上帝,都是選擇性的和條件性的,都是排除性的和限制性的”。Stephen David Ross,Perspective in Whitehead’s Metaphysics,Albany,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3.p.251、272.,作為有限者的人不再被認為擁有觀看絕對者以及大寫歷史或宇宙整體的“全知敘述者”(omniscient narrator)視角,這一視角本身往往與“上帝之眼”“絕對者的視野”“無限者的視野”“從永恒的觀點看”等等關聯起來,作為一種全方位的視角,它本質上是一種“無視角的視角”,是透視主義或視角主義觀看原理的例外。歷史地看,“無視角的視角”之所以可能,本質上也是基于特定的歷史文化脈絡,尤其是啟蒙運動過程中出現的“絕對時間”——本質上它是“數學時間”,即自身沒有任何內容,而只是單純的量度,因而是形式的、客觀的、均質的③1687 年,牛頓以“均勻的,不依賴任何外界事物”來界定“絕對時間”,他區分了絕對的、真實的數學時間和相對的、表面的共同歷法時間。參見Donald J.Wilcox,The Measure of Time Past:Pre-Newtonian Chronologies and the Rhetoric of Relative Tim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22。。這種時間與幾何空間的組構,就很容易產生一種“單一透視技術”(technique of single-point perspective),從而獲得一種客觀的、中立的“絕對世界”。但這樣的“無視角的視角”就像測量地形地勢的地圖,卻不是被測量的地形地勢本身;或者說是編織不同地區歷史的經緯線,卻不是不同地區歷史的實質內容。作為一種將世界不同地方的歷史文化納入同一個系統的方式,它通過時間的同質化以贏獲世界的同步化(synchronization),把具有橫向多元性的民族、文明、文化納入同一個縱向的線性歷史進程,作為同一個世界歷史的不同階段或環節而定位不同的文明。這是一種借助“同一世界假說”(One World Hypothesis)④Elizabeth Deeds Eemarth,“Beyond History”,in Alun Munslow ed. ,Authoring the Past:Writing and Rethinking History,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3,p.72.以達到對不同民族、文明與國家的重新編織,進而通過普遍同質化世界的建構,以達到對普遍同質世界的代表者之外那些“不得其所”的“棄人”“棄物”的分層與支配。
但絕對世界與單一透視技術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可以不斷向前追溯的“深層時間”概念的提出,動搖了源自基督教的神圣時間框架,物理學上相對論則突破了“絕對時間”,現象學的視角主義顛覆了單一透視。絕對、神圣的一元線性時間,現在被視為“外在于人的時間。它推動人們,強迫人們,把他們個人的時間涂抹上同樣的色彩。它的確是這個世界上專橫的時間”①[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著,劉北成、周立紅譯:《歷史學和社會科學:長時段》,《論歷史》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62頁。,是借助未來而達成的對當下人們的強力介入與催促。德國學者萊因哈特·科澤勒克提出了“不同時代的同時代性”(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闡發了一種類似于“地質褶皺”的多元時間層次:“‘時間層次’,恰如它們的地質原型一樣,指的是不同持續時間和不同起源的各種時間等級,它們仍舊存在,且同時有效。甚至不同時代的同時代性這一最豐富的歷史現象,也被包含在這個概念中。同時發生的每一事件,從異質性的環境中產生的每一事物,所有這些既是共時的又是歷時的。”②[德]科澤勒克:《時間層次》,轉引自[德]黑爾格·約德海姆著,張濤譯:《導論:多重時間與共時化的工作》,《史學月刊》2020年第11期。如果說,任何一種“大寫的歷史”(如絕對主義、超越性)的歷史普遍性以獨立于任何具體事件的“絕對時間”觀念為基礎,這一絕對時間將歷史時間、自然時間(包括編年時間、技術時間和宇宙時間)整合在一起,那么,這一現代的時間體制已經瓦解。
多重時間意味著多樣化的、異質性的、混在性的時間經驗,其實1799年赫爾德在其《元批判》中就刻畫了這種多元時間:“每個可變的事物都有其固有的時間標準;即使沒有其他東西存在,時間標準仍舊存在;世界上沒有兩個事物具有相同的時間標準。我的脈搏、我的步伐,或我飛逝的思緒,都不是其他事物的時間標準;河流的流動、樹木的生長,其時間標準不適用于所有河流、樹木,以及植物。大象的生命周期和最短命動物的生命周期是截然不同的,而所有行星上的時間標準有多么不同?換言之,(一個人可以認真而勇敢地說出來)宇宙中任何時候都有無數個不同的時間。”③轉引自[德]黑爾格·約德海姆著,張濤譯:《導論:多重時間與共時化的工作》,《史學月刊》2020年第11期。多元時間的概念關聯著具體的時間,杰瑞米·瑞夫金在其《時間的戰爭》中指出:“每一種文化都有它自己獨特的時間指紋。認識一個民族,其實就是去認識它如何使用時間。”④[美]羅伯特·列文著,范東升、許俊農等譯:《時間地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1頁。厄爾瑪斯提出了“節奏時間”(Rhythmic Time)的觀念,每個事物都有自己的運作節奏或生存節奏,不同存在者的節奏交織疊構成復雜的時間之網,沒有絕對的中心,也無固定的邊界,而是相互交織、多元多線、異質混雜、千差萬別,具有不確定性、彌散性、開放性、聯結性、相對性等特點。昆蟲的鳴叫、歌曲的韻律、腦電波圖、均勻的呼吸、脈搏的跳動等,所有這些事物的節奏,都體現了節奏的時間⑤Elizabeth Deeds Ermarth,Sequel to History: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al Time,New Jersey:Princetion University Press,1992.p.45. 關于厄爾瑪斯節奏時間的研究,參見鄧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學理論與歷史書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98—119頁。。節奏性的時間其實是具體的時間,它不是在抽象化、智性化的思考中顯現,而是可以感受性地顯現。借助這種無所不在的節奏,人們仍然可以感知到宇宙整體的韻律。正如山崎正和所云:“人的身體本身伴隨著節奏,并非能由意識來控制,但心跳、呼吸等節奏卻能由人的意識作用放大或縮小。仰望天空,日有起落,月有盈缺;細觀天象,也會感受到宇宙的脈動、星系的節律。節奏的感受性,超越了人類地域和歷史的分隔,與所謂文明發展的程度無關,為一切人所共有。毋寧說沒有文字的史前文明,其韻律感受性可能會高于文明人。”⑥[日]山崎正和著,方明生、方祖鴻譯:《節奏之哲學筆記》,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頁。節奏連接了文明與自然,溝通了意識與無意識,超越了進化論與人類中心主義的視野,甚至在人類生命的內部,即諸種官能之間的運作,通過節奏時間而形成生命整體的體驗①山崎正和指出,“人感受到的如一瞬間戰栗般的生命的節奏,是超越了感覺和知性,直接向身體整體襲來的一種現象”;不僅如此,節奏時間的體驗克服了柏格森等所指出的現代人對時間空間化的智性化對待模式,因為“節奏是一個流動的節奏”,“節奏是反復運動的流,可以看作是反復中斷的流動”,正如路德維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在其《節奏的本質》(Vorn Wesen des Rhythmus)中所指出的,節奏的流動并非均質的連續;節奏不是單純反復運動的流,而是多種往返運動的流,表現為“往”“復”兩種不同的運動組合起來的流動。[日]山崎正和著,方明生、方祖鴻譯:《節奏之哲學筆記》,第1—11頁。,故而它克服了智性化與抽象化的現代對感受性與體驗性的敵視。更為重要的是,節奏時間恢復了地方性、多元性、差異性、非同質化的視野,這些都具有了本體論的意義。
節奏時間的發現,使得線性的、一元性的、單一性的、目的論的時間經驗黯然失色,絕對時間喪失了立足之處,它只是近代歐洲的一個發明,是1400 年至1900 年歐洲中心主義社會形成過程中的創建②Elizabeth Deeds Ermarth,“What If Time is a Dimension of Events,Not an Envelope for Them?”Time & Society,Vol.19,No.1(2010),p.134.,這個創建為西方文明對非西方社會的支配提供了正當性基礎。正如人類學領域以線性時間的異時論取代各民族的共時性,這樣的時間經驗“已經成為占據空間的一種工具,成為一種封號,向其擁有者授權,為了歷史去‘拯救’世界上廣闊的領域”,實質上卻是以自身意識形態化方式支撐了一種帝國征服與殖民理論,它實質上是非時間性的,是“建基于完全的時間空間化的概念”,它的理論和方法本質上是“分類學的而非起源與過程的”③[德]約翰尼斯·費邊著,馬健雄、林珠云譯:《時間與他者:人類學如何制作其對象》,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81頁。。一旦大寫歷史及其超越的、絕對的普遍性所立足的“絕對時間”瓦解,那么,大寫的歷史也就不再被視為可能。歷史經驗與書寫現在被認為本質上具有不完全性,“在任何情況下,歷史學家稱為一個事件的,都不是直接地和完整地被掌握的;它總是不完整的和側面的”;既然“歷史是殘缺不全的知識”,那么,當我們試圖重構一種完整的歷史時,“我們從這一邊得到的,總是會從另一邊失去”④[法]保羅·韋納著,韓一宇譯:《人如何書寫歷史》,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5—6、20、23,39—40頁。。由歷史經驗的不完全性,再到歷史事件沒有“絕對的尺寸”,保羅·韋納得出,“只存在‘……的歷史’”,“大寫的歷史的觀念是一個無法接近的極限,或者更多是一個超驗的觀念;人不可能書寫這個歷史”⑤[法]保羅·韋納著,韓一宇譯:《人如何書寫歷史》,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5—6、20、23,39—40頁。,這種歷史最多可以期待承擔“一種啟發性原則”。既然大寫的歷史不存在,那么歷史本身的目的論架構,或終結目的、終極根據、終極意義等表述,都失去了有效性與基礎。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后現代時間體制與后現代多重性的時間經驗和歷史經驗,由絕對者及其各種變形的或關聯的概念系列所鼓勵的單一性、均質化、絕對普遍性、超越性的歷史經驗走向終結。
在基督教神學的視野中,人類的世界與歷史將“迅速走向終結”,“所有的時代以及年歲都將毀滅”,在朝向基督的第二次降臨所標識的“永世”或“天國”的視野中,一切世間的歷史與年代,民族與文化及其差異性、多樣化變得無足輕重,它們最終不過同質化地被引向“最后的世代年表和世界末日的日程”⑥[美]阿摩斯·馮肯斯坦著,毛竹譯:《神學與科學的想象:從中世紀到17世紀》,北京:三聯書店,2019年,第323—327頁。。人類歷史說到底不過被視為從基督第一次降臨到第二次降臨之間的均質化歷史,“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詩篇》90:4),換言之,人類歷史不過是通向神圣歷史(非時間性永在)的插曲或瞬間。然而,伴隨著“上帝之死”與絕對時間之終結,這個神圣歷史已經不再可能;本來被作為瞬間或插曲的人類歷史,回到了多樣性、異質性、混雜性、相對性的狀態,而終極根據、目的論、透明性等概念或思維方式都不再能穿透它的內部,它們必須被重新理解。歷史感或歷史意識更是不必再與歷史過程的終極目標、歷史整體的意義、線性終點等相關聯。
二、“天經”與“地義”的交互滲透:普遍性的具體充實
以絕對性、目的論、終極性等術語刻畫的“大寫歷史”總是將自己措置為超驗性存在,即不能“認識”而只能“思想”的存在。一旦將其作為“認識”的對象,它就會被引向神秘主義的悖論:一方面它在認識能力的彼岸,因而是超驗的,另一方面它又總是被誤置為宇宙內的最高存在者(最高生存者)。嚴格意義上的絕對者只是普遍性的擔保,作為思想的構造,往往被視為“天上的存在”,因而它所關聯著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并非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遍性,而是基于概念及其運作而由人的思想加以構造的思維中的普遍性。由于它只能生存于思想空間,或沒有消耗、摩擦與阻力的“幾何空間”,或由信念、信仰所構筑的純粹“彼岸”空間,因而它并不是具體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沒有力量。盡管它是思維的抽象,是人類高度智性化的產物,然而,只要它被發明建構出來,被運用于地上的人們的歷史經驗中,找到它的擔綱主體,那么它就具有改造地上世界與人類生存方式的能量,近五百年來的世界歷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現代科學與技術正以同樣的高度智性化與抽象化形式,在人類生存格局中占據著顯要位置,它建基于思維與概念普遍性的越來越技術化的操作及其成果,極大地影響了我們的生存世界。因而尋求普遍性的歷史過程并不會終結,關鍵是要消解與它關聯著的支配性秩序。如果我們進入一個萬物各有自身節奏的世界,那么普遍性又將如何安立自身?
回到中國思想的經驗,“沒有超越者的超越性”本質上是終極無為的天道的突出品質。郭象以“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①郭慶藩:《莊子集釋》卷1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112頁。,闡發中國古典思想中的“天道”。這意味著,天之生物與物之自生自成,乃是同一個過程。孔穎達解“天地之大德曰生”云:“天地之盛德,常生萬物而不有生,是其大德也。”②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9,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第619 頁。按,李道平所引孔疏與通行本《周易正義》文辭稍異,參見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49—350頁。生而不有生,不生而物自生,即將生之所有歸于萬物,天之生物實即萬物之自生,生生本身就同時具有無為的本性。孔穎達解《易》之“復”卦云:“天地養萬物,以靜為心,不為而物自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動,此天地之心也。”③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3,第132頁。即便是對天的主宰性仍然堅持的朱熹也強調萬物的自生與自然:“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妝點得如此!”④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45,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85頁。這一點可與《論衡·自然》的如下觀點相發明:“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⑤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卷18,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776頁。天道之生生同時又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五十一章)⑥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37頁。,它并不給萬有提供生存的最終根據,而是將根據交付給了萬有自身。“物各自生”⑦郭象云:“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郭慶藩:《莊子集釋》卷1下,第50頁。,此即天道。《孟子·萬章上》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⑧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9,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08頁。天命并不能被理解為宇宙內的生存者,也不能被理解為保羅傳統中的創造性與自由性本身,而是各有自身生存節奏,體現為多元、差異、異質的萬有及其交互作用的整體的“復合組構”;“天”就在它所命的萬有之整體及其秩序中,“天下”之外沒有“天”自我顯現的場域。在這個意義上,天道并非絕對性的,天下萬有各具生存節奏,并不能被同質化,天道展開為各有自身生存節奏的萬有的秩序本身。它既不是作為開端,也不是作為終點,而是展現為無始無終的萬有交互作用構成的網狀秩序整體。
基于天道的普遍性被稱為“天經”,但“天經”絕不可能被理解為思維基于概念運作而構建的抽象化、形式化、智性化的普遍性,而是在天下發現由人與萬物共同遵循的道理。前者是我們用以理解世界的思維形式,后者則是內在于事物中的運作節律。世界本來不可穿透,即便是世界符合于我們的思維形式,但這種符合本身也是不可理解的,世界的可理解性并非思維的建構。“一陰一陽之謂道”①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7,第315頁。,這是《易傳》對天經——天道的概括,天地間的萬有的生存節奏都源自陰陽二氣交互運作。當《荀子·王制》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②王先謙:《荀子集解》卷5,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64頁。時,氣化運作的節律是水火、草木、禽獸、人共同遵循的。當我們這樣理解“天經”時,它類似于下述意義的“自然法”:“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給一切動物的法律。因為這種法律不是人類所特有,而是一切動物都具有的,不問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動物。”③[古羅馬]查士丁尼著,張企泰譯:《法學總論——法學階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6頁。自然法是各民族與一切動物、植物甚至無機物都共同遵守的,相當于宇宙論的氣化或力學原理。
當然,由于古代中國思想對“天”的理解包含著“渾天”的向度,這一向度并不能還原為天文學意義上的天觀,而是哲學性的:天包地外,又在地中,在天地間一切萬有之中,一物之在便有一物之天,萬有各有其天,這個意義上的人性或物性就是在人在物之天。這種意義上的“天”是落在地中、人物中的“天”:落在地中而有不同地域的風土、人情、習俗、文化、傳統之差異,即地方性之不同;落在人物中便有人性與物性的不同——這兩者已經把我們引向“地義”與“人情”的問題。“天”之所以不是超驗和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體的、可以為經驗性感受所切入的普遍性,便是因為“天”總要下落到地中、人物中以“命”的方式顯現自身,盡管這種下落到具體性中的“天”并非“天”的全部。“天經”與“地義”“人情”三者交織疊構,只是從人類理解的角度,才可以將其區分開來。“天經”即天之常道,它有自己的描述性語言,即可以用陰陽、四時、五行等加以刻畫的萬有節律。“天經”意味著最大化的普遍性,它體現了天空、大地與人類社會共通的節奏和律則,它所體現的普遍性仍然可以稱之為universality,只不過必須明白,universality并非基于概念與思維、人的或神的邏各斯,而是基于萬有的生存節奏和運作律則。
亞里士多德區分月上的世界與月下的世界④根據亞里士多德,月下世界是指地球和月球之間的區域(包括地球本身),四種基本元素(土、水、氣和火)構造了自然的、可感知的物體,物體運動以合乎自然或反自然的直線方式進行,有始點也有終點,因而不能無限不朽。月上世界,即月亮以外的區域,包括月亮、太陽、行星和恒星,物體由第五種元素“以太”構成,“以太”有進行完美的圓周運動的天然趨勢,無始無終,無限且不朽。因而,月上世界更加純凈美善,是神居之所,而月下世界則是人物所居之地。[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徐開來譯:《論天》,苗力田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第2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年,第265—351頁。,張載與王夫之區分經星以上的宇宙與經星以下的宇宙⑤陳赟:《氣化論脈絡下的身體與世界——以船山〈張子正蒙注〉為中心》,林月惠主編:《中國哲學的當代議題:以氣論與身體為中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9年,第161—215頁。,月下的世界、經星以下的世界,是天地交合萬物在其中化生的世界,也是人與萬物居于其中的世界。在基督教神學中,作為絕對者的上帝之創世,被伊本·以斯拉(Abraham ibn Ezra,1093—1167)限定在月下世界,創世的敘述是按照適合人的語言講述的,月下世界是為著人的緣故而被創造,至于月上世界,則《創世記》完全保持沉默⑥[美]阿摩斯·馮肯斯坦著,毛竹譯:《神學與科學的想象:從中世紀到17世紀》,第284—289頁。。嚴格意義上的“天經”是展現在經星以上世界與以下世界的貫通性原理。但是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天經”只是月上世界的天上真理,而不是月下世界的地上真理,二者具有根本的非同質性,永恒不朽的神圣世界獨立并高居于時間中衰變的地上世界而存在。但是在古典中國思想中,對于“經星以上”的世界保持了沉默,我們所能理解者乃是它與我們的關系。然而,這個意義上的“天經”并不是歷史事物在其中運作的場域。“天經”包含著兩個層次:從不下落到世界歷史中的“天經”(地外之天),以及下落到世界歷史中的天經(地中之天),正如在奧古斯丁那里,上帝之言有并不落入具體語言、并不落入感性世界而只是作為其自身的上帝話語(Verbum Gottes),與進入感性顯現的、以外在形式出現的上帝話語(Divine Word)之分①落入地中之天,也就進入了世界歷史中,此與地外之天不同。奧古斯丁區分了在某個特定時間進入歷史世界的圣言(Divine Word)和與上帝同在的圣言(Verbum)。這個區分涉及上帝自身以及上帝在人所居住的世界中的顯現。與此相關的是,本源的言說和思想是內在的,即一種心靈的語言,并不具有感性的或物質的形式,而只是純粹的理智和普遍的形式,它還沒有采用一種特殊的或歷史的語言形式,因而也并非耳朵所能聽到,然而它存在于每一種語言之中,并且先于一切可以“翻譯”(übersetzt)它的符號。這種沒有進入世界歷史的上帝及本源言說,頗為類似于我們這里所謂的狹義的“天經”,它是上帝的智慧或自我認識。一旦靈魂或內在的話語采取一種具體的語言的感性形式,以一種為肉體所能辨別的形式表達出來,也就不再是如其所是的“天經”。對上帝自身而言,上帝的智慧及其在世界歷史中的顯現是同一的,但對人而言,這種同一從來沒有發生。關于奧古斯丁的上述區分,參見[加]讓·格朗丹著,何衛平譯:《哲學解釋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59—61頁。。純粹的“天經”無所謂歷史,一旦進入歷史,也就進入經星以下的世界——作為人與物的居所的“天地之間”。古典時期的人們相信:從不下落到地中的“天經”是絕對的,超越于大地萬物,不能從宇宙及其內部的事物來理解其自足性、自明性,正像不以自然語言表達的邏各斯(內在邏各斯)才是真言,一旦落入自然語言中成為“外在邏各斯”,其自足性、自明性與絕對性就會打上折扣;但在人類歷史展開的過程中,這一信念漸漸被視為形而上學的迷夢,天經具有與地義不可分割的特征,脫離了地義的天經,我們或許了解其存在,卻無以理解其與我們的關系和對我們的意義②必須進一步理解,上帝的內在言說不能入世,其入世必然采用適應于人所能理解的自然語言。《創世記》的語言創世說其實展現了一種古老而普遍的思想,譬如在蘇美爾人的觀念中,“無稱謂者”無法存在于世;“賦之以名”“呼喚其名”,即是令其見之于世的方式。[美]塞·諾·克雷默著,魏慶征譯:《世界古代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80頁。。
對于經星以下的世界,或“天地之間”的世界,僅僅依靠“天經”的陰陽運化節律就無法充分理解,行動也難以獲得正當性。從氣化論視角來看,由于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質的介入,源自天道的陰陽原理與來自地道的五行節律交織疊構,由此而有多樣化與異質性的萬物。更重要的是,天地之間的人物運作規則,不僅必須遵循“天經”,而且還有“地義”。如果說“天經”意味著天道作為尺度具有無所不在的普遍性,那么“地義”則意味著地方性的向度,不同地方的風土、習俗、傳統、語言、音聲、衣服等呈現出根植于地理環境的差異性。群居的人類也生活在不同地域,而有民性的風土差異。“地義”的“義”不同于“天經”的“經”,“經”意味著更大程度的普遍性,而“義”則是適宜性原理。
適宜性原理根植于“地道”的特征。《周易·坤卦·文言傳》以“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③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1,第36頁。來表述地德——坤——的品格,此與《大戴禮記·曾子天圓》《淮南子·天文訓》《呂氏春秋·季春紀·圜道》所謂“天道曰圓,地道曰方”④見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卷5,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98 頁;何寧:《淮南子集釋》卷3,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69頁。《呂氏春秋》作“天道圜,地道方”,見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卷3,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78頁。,形成義理上的連接。由于大地上萬有各不相同,每個事物都處在與其他事物的交互作用的網絡之中,每個事物所在的網絡都有自己的親疏遠近的層級性,因而每個事物的具體生存環境各不相同,而且這種生存環境如氛圍一樣隨時隨地不斷變化,因而個人在沒有固定規則、變化無常的環境中與環境及他者的最大化協調,或者一件事的具體做法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與多種因素之間達到最大化的適合度,就是適宜性。“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體,故不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執己之見,無傷于和。”⑤劉寶楠:《論語正義》卷16,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45頁。地道何以是方的,而不是圓的?天道展開為陰陽交互運作,這個運作并非出自某種深層意志和目的,而是陰陽不測,具有神妙萬物而又無始無終的特點,甚至在經星以上的天,無法以其作用于物的關系來理解,以至于張載將其刻畫為“清虛一大”四種品質①程頤曰:“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個清虛一大。”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2上,《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4頁。;只有在其生物時才能顯現其乾健不已的陽剛品質,但除了這種乾健品質是穩定的以外,天之生物、殺物皆對人而言處在“不測”畛域;人所能把握的也只是天之作用于人與萬物的層次,所理解的天不過是天與人的關系,至于天之自身,乃至在物之天,都非人所能確知。
但地道就不同了,“地道曰方”,它是“方內”的原理,與地方性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每一地的地方性總是可以在“方物”的過程被感知,這是因為“方”之為“道”具有一定的規則,可以為智性所理解,此與天道之“圓而神”“神無方而易無體”不同。天道之常經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乃是由于它不是人的參與所構造的,對人而言是被給予的,當然天作為最終的給予者,本質上是沒有給予者的給予。故而,在天經那里,具體的人無所用力,畢竟天不是工夫的對象。但是,每個人都是地道的參與者,地道的規范之所以是“義”,因為它適應了此地的地方性。但是適應于此地的未必適應于其他地方,畢竟各地的地方性并不相同,這也就使得適宜性原理本身在普遍性上有了限制。事實上,“地義”原則可以視為對“天經”的限制。純粹的“天經”意味著最高最大的普遍性,因為它不落在地方性上,不受地方性限制。但這樣的天經并不存在于“天地之間”,而是存在于“天地之外”的廣袤宇宙;或者它可以存在于我們的思維宇宙,卻無法存在于天地之間的氣化空間。純粹的普遍性沒有受到地方性的阻力,因而它不會因消耗、磨損而降低其普遍性,就如同幾何學的圓和方那樣,它們并不存在于天地之間,不是如同草木花鳥人那樣的具體生存者,因而是純粹的、普遍性的;但天地之間作為生物居處的世界,由于有著交互作用,有著摩擦、阻力和消耗,因而總是無法化約為思維空間或幾何空間,也因此無法達到完全的普遍性,它所要求的其實也并非普遍性,而是適宜性。適宜性原則雖然也為基督教西方所憧憬,但只要地道沒有從天道中分化獨立出來,它作為獨立于“天經”的原理就無法成立。當伊本·以斯拉強調《創世記》僅僅適用于月下的世界,其所記載的上帝的言語只是上帝對人說的并且僅僅適合于人,是人能聽懂的話時,他已經不自覺地采用了適宜性原則(principle of accommodation[adequtio])來理解被視為“上帝的話”(the Bible)的經書。事實上,正如馮肯斯坦所說,在相當長的時段,適宜性原理都被作為釋經學的原則用以調和啟示與理性的關系②[美]阿摩斯·馮肯斯坦著,毛竹譯:《神學與科學的想象:從中世紀到17世紀》,第290頁。。然而,適宜性原則的本質及其形上學基礎一直沒有獲得課題化的處理。
要理解作為適宜性原理的“地義”,不妨將其解析為如下三項要素:一是“在地性”的氛圍與環境,一個在地性的環境是由當地的人文風土與自然風土組成,由此形成了該地的地理氣候、山川風物、語言歷史、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等;二是每一個在此地生活的個人;三是在同一個地方生活的他人以及其它種類的存在者,如動物、植物等。三個要素的結合就形成一個地方性的復合組構,也是一個地方不同于另一個地方的根本所在。日本哲人和辻哲郎接續海德格爾將人理解為“在世者”(being-in-the-world)的思想勞作③[德]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中文修訂第二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79—93頁。對其深入系統的研究,參見[美]休伯特·德雷福斯著,朱松峰譯:《在世:評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第一篇》,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49—72頁。,提出存在論結構上的風土性問題,它與時間—歷史維度同樣重要。在和辻哲郎看來,“不與空間相結合的時間還并非真正的時間,海德格爾之所以停留于此,是因為他所說的Dasein(此在)最終僅限于個人。他把人類存在僅當作個人存在來理解”;然而,“只有當精神成為能夠將自我客體化的主體時,也就是具有主體性的肉體時,才能創造出自我發展的歷史。這種被稱為主體性的肉體正是一種風土,人的有限、無限的雙重性最為顯著地反映在人的歷史和風土結構上”④[日]和辻哲郎著,陳力衛譯:《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13—14頁。。其實,海德格爾未嘗沒有意識到地方性的問題,他曾指出:“‘地方’將人放置在了一種特定的方式當中,既揭示了人自身存在的外部關系,又揭示出他自己所擁有的自由和現實的深度。”①Martin Heidegger,“An ontological consideration of place”,inThe Question of Being,NewYork:Twayne Publishesers,1958,p.19.然而,和辻哲郎的深刻之處在于認識到時間與空間的相即不離就是歷史和風土密切相連的根本支柱,風土是一個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綜合而形成的地方性,人的存在論結構不僅有時間軸,還有風土性。人作為主體的超越性,不能僅僅由時間與個體意識來說明,而必須納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個體意識中的時間是以群體的歷史性為基礎并從中分化出來的。風土嵌入到主體的身體存在中,在風土中發現自我,構成身體的自覺;身體展開的背景視域是共同體的思維方式、語言表達方式、生產方式和房屋建造式樣等歷史文化傳統。具有主體性的人將自己客體化到風土中,從而主體與風土之間具有共構的特征,這使得風土的類型同時也是人類自我認識的類型,其實也就是不同文化與文明的類型。風土或地方性的概念,揭示了人的生存結構在世界性之外,還有地方性。人的居家方式不僅僅是會通于當前活動中的世界視域,即作為在世者而存在,他還同時寓居于世界的某一個地方。與世界性共生的地方性,而不是脫離地方性的世界性,才是人的真正家園。
人的家園體驗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段義孚所謂“戀地情結”(topophilia)②[美]段義孚著,志丞、劉蘇譯:《戀地情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世界性總是在地方性中顯現為世界性,即不同地方的連接會通;沒有被不同地方所充實的世界,只是抽象的世界。地方性的經驗,不僅給出了世界的具體性與多樣性,同時在長期貶抑特殊性的文化地脈中也給出了特殊性的位置。如果沒有立足于地方性的文明與文化傳統,那么世界性本身就變成脫離地面而缺乏生活世界支撐的彼岸化的“天經”;反過來,世界觀之所以并非單一義的、同質化的,正是因為所有的世界觀都是來自某個地方與某個歷史時段的世界觀。當然,地方性并不是與世界性相對峙的范疇,而是作為世界經驗的基本維度而存在。風土或地方性不同于自然地理學意義上的區域(region),也不同于某個特定“地點”(location),它意味著某種世界經驗的方式以及相應的生活方式,它與人的存在的深度與命運深層相關。詢問某人來自某地,其歷史、文化、風土、自然景觀、民性等都在當地的涵攝之中。你的品格、性情、口音、口味等等,都帶有那個地方的印跡,當你在該地生活時,渾然不知,你已經與那個地方融為一體,它銘刻在你的無意識與身體里,當你走出該地來到另一個地方時,原來那個地方與你的深層關系才會顯現出來。地方性構成個人感知體驗世界與自己的結構性要素,它把同一個空間中的人們結合到了一起,組建了個人及其所屬群體共同的生活世界。
時間與歷史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穩定地方性情結的某種資源。“人類的地方經驗里更為深層次的意義則體現在人們對他們的地方進行保護,避免受到外來力量的破壞;或體現在對特定地方的思戀與懷舊中。作為人,就意味著你始終是生存于各種重要地方所組成的世界里,也就是說,作為人而言,就意味著你擁有并知曉屬于你的地方。”③[加]愛德華·雷爾夫著,劉蘇、相欣奕譯:《地方與無地方》,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頁。地方性經驗也是將某個地方的所有存在者聯系、會通為整體的體驗,人在這個整體中為自己定位;如果喪失了地方體驗,那么將無法回答我們來自何處以及我們是誰的深層自我理解問題。“天經”如果不與“地義”結合,就無法獲得其具體性,而駐留于抽象的普遍性。落實在歷史理解上,就會將歷史構想為一種既脫離人性又脫離地道的不可阻擋的普遍化總體進程,這個客觀化進程會均質、勻速且以同樣的方式降落到人類生活的大地上的不同地方。其結果則導致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1872—1956)所表達的下述悲觀狀況:“地球的實質(Erdessenz)在19 世紀80 年代已經離開了地球。”④[德]雅斯貝爾斯著,李夏菲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年,第186頁。在這種情況下,就不難理解,和辻哲郎在“風土”這一意象性表述中揭示的東西,正是作為生存結構的地方性維度,這種維度在古典中國思想中是以“地道”的概念加以闡述的。
事實上,和辻哲郎《風土》中最早的一篇文章《藝術的風土性》最初就以“因‘地’而異的藝術特殊性”為名發表于1928年12月“巖波講座”《世界思潮》上。“地道”不僅僅是大地或自然意義上的風土,更是大地上具有區域類型性的人文與自然的整體存在方式。一切政治社會禮法的創制根基固然要考慮不違背作為自然法意義上的“天經”,但更重要的卻是本于“地義”的適宜性原理。“地義”的“義”,周人作“誼”,意為“人所宜也”,“云誼者,人所宜,則許(慎)謂誼為仁義字。今俗分別為恩誼字,乃野說也。《中庸》云:‘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是古訓也”①段玉裁云:“鄭司農注《周禮·肆師》:‘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是謂義為古文威儀字,誼為古文仁義字。”“‘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按,此則誼義古今字。周時作誼,漢時作義,皆今之仁義字也。其威儀字,則周時作義,漢時作儀。”許慎撰,段玉裁注,許維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1099、168頁。。《禮記·樂記》所說的“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②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090頁。,深刻表達了禮法制度的“地義”根基。禮法制度固然不是自然界本有之物,而是人的社會創造,但任何禮法創造都必須以當地人們生活中長期形成的習俗、傳統與生活方式為背景和基礎,而不是基于思維的演繹發明一套完美或理想的制度來強加于人。制度禮法的創制雖然經由人的頭腦,但一旦獲得地道的支撐,那么它就是從大地中生產出來的;它并非完全的人造物,而是始終具有某些被給予的因素與維度,因而創制的新作品本身也有與地方性的禮俗傳統與文化背景相協調的問題,這樣它才是活的、流動著的。
對于人而言,“天經”“地義”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天時”與“地利”。《孝經·三才章》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③《左傳·隱公十一年》君子謂“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昭公二十五年》鄭子大叔述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禮教之設,其源遠哉!見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第126、1447頁。關于“天經”,鄭玄的解釋是,“春夏秋冬,物有死生,天之經也”;與此相應,“則天之明”意味著“視天四時,無失其早晚也”;鄭注《孝經·庶人章》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皮錫瑞指出:“春生,夏長,物所以生;秋收,冬藏,物所以死。物有死生,承四時而言也。”至于“地義”,鄭玄的解釋是:“山川高下,水泉流通,地之義也”;“因地之利”即“因地高下所宜何等”;這與鄭注《孝經·庶人章》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一致,而所謂的“水泉流通”指的是“畎、遂、溝、洫、澮之水行于兩山大川之間者也”④皮錫瑞:《孝經鄭注疏》,吳仰湘編:《皮錫瑞全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56—58頁。。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理解“天經”,即是將天經作為宇宙論意義上的萬物之生存節律的根據。萬物各有其生存的法則與節奏,這是被給予的,是自然性,在這里并無形而上學和神學層面上的“作者”。所有的事物都必然遵循自然的法則,而這些法則本身卻不是事物自身創建的,而是自然的被給予者。而且這些法則本身是無一例外的,但對于不同的存在者而言,又是各不相同的,是它們自身現實存在的自然節律。這些節律表現為一種在無常的陰陽氣化過程中事物自身存在的自然的穩定性,它可以作為認識的對象被從現象層面加以描述,可以知其然而無法知其所以然,這種生存節律關聯著存在整體,但無論是對事物而言,還是對觀察它的人而言,始終是奧秘,超越了人的智性所及的范圍,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法則它是自然的“天經”。“天經”是一切存在的基礎,哪怕是歷史、文化、精神等具有無法被天經所涵蓋的內容,也只能以“天經”為基礎。
在這個意義上,“天經”意味著最大化的普遍性原理,但它需要天地萬物充實,由此展開為萬物各自不同的生長節律在其中并行不悖地運作而共顯出來的時間秩序。其中,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就是這種時間秩序的最直觀例示,人之晝出夜伏就是這種時間秩序在人那里的展現。各種不同的生存節律都是漫長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并沒有給予者,然而萬有的各自不同質的節律彼此各是其是而又并行不悖,構成復調交響的天籟。故而萬物之遵循天經,與遵循自己自然的生存節奏是一致的。人之法天,在某種意義上正是與天時同步協調、相和共鳴。
至于“地義”,則首先與自然風土密切相關,人居住在天地山川之間,各因其地方風土、植被、地理、氣象等的特殊性為基礎,而敞開其天經,因而具有最大化普遍性的“天經”。就其顯現而言,則有與之相應的根源于“地義”的視角性,不同的人們生活在不同的“地方”,這種“地方”既是敞開天經、敞開天地萬物與自我理解的特定視角,也是遮蔽這種敞開性與自我理解的洞穴。正是“地道”的原理,展現了世界整體顯現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不圓滿性,這種不完全與不圓滿,意味著對于生存在天地之間的所有存在者而言,地道構成了存在的情境性條件。而且,這種生存的脈絡性條件,也處在無常的變化過程之中,因而與此條件相應的只有適宜性原理——義。“義”既是穩定性的作為“應當”的規則,也是與條件相適應而必須的隨時隨地的靈活性調整。一種行動的合理性與某種政治社會秩序的正當性,在其結構上都必須既循“天經”,又合“地義”。如果沒有地義只有天經,則禮法的根基是無法落到地上的“普遍主義”,根基本身并不是從政治社會的土壤中生長出來,而是外在于“地義”的“天經”,它表現為遠離世間與大地的純粹理念世界或幾何空間。以此為根基的秩序和禮法,如同以幾何學意義上的方形、圓形要求粗糙的地面上的方形、圓形;甚至,幾何學意義上的方圓被作為原型,而粗糙地面上的方圓則被視為模擬物來對待。胡塞爾曾將西方文明危機診斷為理性主義危機:“歐洲危機的根源在于一種誤入歧途的理性主義。”①[德]胡塞爾著,王炳文譯:《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392頁。理性主義如果僅僅基于概念及其邏輯推演,而不面向作為經驗或意識現象的實事本身,就會導致一種與“地義”始終保持不可協調張力的“天經”。
“地義”關聯著的地方性相對于世界性是具體的,相對于“天經”似乎是特殊的;但若從其他視角如個人視角,或內在于某一地方的更小共同體的視角來看,則可能是普遍性的。譬如對雅典而言的城邦共同意見,對于雅典的單個成員或部分成員而言可能是普遍性的,但對斯巴達而言,則可能是特殊的。在地球作為一個封閉世界的情況下,只要基于全球化的禮法秩序沒有最終建立,那么,所有的禮法就都是地方性的,它們不可能僅僅遵循“天經”原理,而拋卻“地義”原理;同樣,基于民族—國家立場的愛國主義相對于世界主義,其根基就是“地義”原理,即便它合乎“天經”,卻不等同于“天經”。若一項原則就某一政治與文明的共同體內部而言是“天經”,但若從共同體外部的視角來看則可能只是“地義”。
“天經”與“地義”有某種程度的重疊關系,即根據哲學意義的渾天說,天不僅在地外,同時也在地中,單就后者而言,有所謂地中之天;據此,在特定地方發現或創建的具體地義規范,一旦在更多地方都被推廣并被視為是適宜的,那么這個意義上的“地義”同時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天經”。當然,就其不重疊的部分而言,“天經”與“地義”是相對的,這種意義上的“天經”遵循的就是純粹普遍性的原則,無所謂“地義”的適宜性問題。一旦討論與適宜性相連的“天經”,則所謂的“天經”乃是與“地義”重疊的“天經”。當“地義”與“天經”相合時,它同樣意味著普遍性。但這種普遍性與純粹的出于“天經”的普遍性有所不同。譬如,當我們將“禮”視為天經地義的時候,這不僅意味著具體的禮的制作與規范根基于某地長期傳承的自然習俗、傳統與生活方式等,而且意味著其適宜性并不僅僅局限于原來的地方,而是在更多地方皆可變通調整、加以推行并被接受,這就是“地義”本身的普遍性。
在西方的文明論脈絡中,與“天經”相應的普遍性是universality,與“地義”相應的普遍性是ecumenicity。具有基督宗教背景的政治哲學家沃格林曾對二者進行區分:ecumenicity“指的是,代表著秩序之神性來源的共同體的趨勢,它傾向于使自身與天下(the ecumene,本指‘人居領地’)重合,從而表達其主張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指的是,對于作為秩序來源、超越于世界之上的神的經驗,由他帶來的秩序對所有人具有普遍的約束力”②[美]埃里克·沃格林著,葉穎譯:《秩序與歷史》第4卷《天下時代》,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年,第208頁。。如果將沃格林所說的“神”替換為“天”,則中國讀者更容易理解。universality 即天無私覆、天道不仁意義上的普遍性,它對于所有的存在者而言都構成規范,并不存在適宜性與否的問題,它來自天道的體驗,以天則、天理、自然法等方式出現,甚至對人與其他存在者都具有約束力。但ecumenicity 則是大地性的,由于連接同一個地方的不同人,或連接不同的地方而使自己超越了特殊性,而具有了另一種普遍性。對所有基督教徒而言的普遍性,乃是ecumenicity 而不是universality,畢竟即便是整個基督教團體也只是地上的一個大的共同體,而不是所有存在者;同樣,在Chinese ecumene(中國的天下)可以發現的普遍性也只是ecumenicity 而不是universality。即便在未來某一天地球人都說英語,在嚴格意義上也不能說英語作為語言具有universality,它所具有的也只能是地球上的最大化適用性,因而只能說它具有ecumenicity。這樣,地球上出現的追求大一統秩序的世界性帝國,只能是ecumenic empire。就此而言,ecumenicity 關聯著共同體的趨勢,它本質上意味著與共同體相關的公共性,但公共性與純粹的“天經”意義上的“普遍性”相比,仍有很大不同,對于一個共同體為公共福祉與共同利益,對于另一個共同體可能是較大范圍內的自私或災害。有鑒于對天經與地義的如上分辨,一方面,用天經提升地義,使之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天經本身也要落到地義之中,才能找到其實施者或擔綱者。由天經與地義的相合而帶來的普遍性,就不再抽象,而是可以通過人類活動而展現在地上的具體普遍性。
三、人情:具體普遍性的人性維度及歸宿
人的存在及其秩序雖然不能不以“天經”和“地義”為前提或原則,但又無法化約或還原為二者,在某種意義上,人的存在同時也是對天經和地義的打斷,對一切被給予要素的打斷,并通過這種打斷而將自身置于天地的界限與連接處,即在天道、地道的分化與交互作用中敞開人道獨有的畛域,這一畛域將人的存在揭示為無法以描述的方式刻畫、無法以知性方式加以認識的“非對象性”存在,它拒絕一切現成性,而是向著可能性敞開,人的意識、志向與好惡等都參與人的規范之生成。因而對于具體的人類社會而言,一切秩序在與“天經”“地義”合拍的同時,還必須另有心性論或人性論的基礎——對于秩序的調節與創建而言,民心、民情、民意則是“天經”“地義”之外不可或缺的另一尺度。“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于人間,合乎人心而已”①此為《慎子》佚文,見許富宏校注:《慎子集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02頁。,相對于天經、地義,人情對人的秩序而言更為根本。《荀子·大略》云:“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于《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②王先謙:《荀子集解》卷19,第490頁。合乎天經與地義而不合人情,則秩序同樣不可能獲得正當性。普遍性固然本于天經、地義,但最終要歸于人情,人情的核心是人心之同然。《禮記·問喪》:“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船山說:“此節總結一篇,而言禮之既定,有如天降地設然者。然天經地義皆即人情而顯,盡人情之實,則亦無非天則矣。”③王夫之:《禮記章句》,《船山全書》第4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1410頁。人情之實,即在人之具體的天經。鄭玄謂:“尋繹天經地義,究竟人情也。”④皮錫瑞:《孝經鄭注疏》,吳仰湘編:《皮錫瑞全集》第3冊,第140—141頁。人情與天經、地義一樣,同為秩序的根據,并且,天經與地義唯有在與人情的協調中,才能進一步具體化。反過來,人情又是在一定條件下發生的,而天經與地義則是人情展開的條件。
人情是人心之大者,它本身不可測度,但在政治生活領域,民情往往表現為共同體成員的共同好惡,以及行事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意見或共同性情取向,即《淮南子·主術訓》所謂“眾適”:“法生于義,義生于眾適,眾適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⑤何寧:《淮南子集釋》卷9,第662頁。一個時代一個地方的集體心智與取向,構成此時此地社會的制度基礎。但人情與地義的不同在于,人情是可以用勸說、誘導的方式加以轉化的。民情或民行是匿名性的,創制的精英圣賢之所以成為他們,是因為他們能夠把握匿名的共同意見,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引導、調節。當然,對于人而言,天道與地道都是通過作用于人情而被人界定。因而,在天經、地義與人情三個尺度上,立足人心所安者,而向天經與地義開放,人對天經和地義的體驗本身也都是人情構成的要素,人情本身所生發的對天地的態度,轉而又回轉到人與人、人與自己的關系中,成為影響人與人、人與己關系的要素而存在。如此一來,人是在人情中,尤其是在共同體的共同意見與集體態度的基礎上接收對天道和地道的理解,這就是將人與天地關系納入由人所創造的文化領域,而文化領域則是隨著時間、情境與問題的變化而不斷調整人與天地的關系,因而文化的世界就同時是歷史的世界,通過歷史,作為文化成員的個人遭遇不同的文化對天人、天地、人地、人人、人己關系的處理和應對方式,從而為更加寬裕地調整在當前與未來時代的生存節奏做出了文化與歷史的積累。立足于“人情”而溝通“天經”“地義”,則使得普遍性的理解更加具體、豐富。
如果說,脫離“地義”與“人情”的“天經”乃是純粹而絕對的普遍性,那么在這種純粹或絕對的普遍性中,就無法給出歷史性的位置。只要從這種絕對或純粹的普遍性來看“地義”和“人情”,則后兩者就會被視為“特殊性”。的確,人們通常將“地義”與“人情”視為特殊性、主觀性,并進而作為“相對性”以與“天經”的絕對性相對立,但這種觀點往往導向對普遍性的抽象理解。“人情”的統一性雖然表現為共同主觀性,即它展開為主體與主體之間,通過交互性的承認、認可與主體間的共情機制而獲得本質上的統一性;相對而言,“地義”則將人與地方性的風土、習俗、禮法、傳統、語言、歷史、文化、民族、國家、文明等關聯在一起,它更多地從人與共同體的關聯上敞開了人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與歷史性不可分割。通過天經與地義、人情協調而敞開的是具體而有生機的歷史普遍性。雅斯貝爾斯指出:“當人們著眼于普遍性(das Universale)時,就會在本質的東西中發現一致,而將特殊之處作為局部的東西加以理解,這些特殊之處附著于地點和時間。但是,這種普遍性恰恰無法構成人類真正的統一。正相反。如果人們凝視顯露出來的真理之深處,便會在特殊性(das Besondere)中找到歷史的偉大之處,而普遍性中的一般性,非歷史的不變性,這就好像是事實性和真實性的分水嶺一樣”;“凡是人們以為找到了某種絕對普遍性的地方,總是同時存在著不同;一些人具備的東西,總有另一些人不具備;絕對普遍性永遠有一種抽象特點,一種單調性。一種在普遍性尺度下完全特殊的事物可能恰恰實現了真正的歷史性。人類的統一只能在與這種歷史特殊性相互關聯時彼此奠定基礎,而這種特殊性不是本質上的不同,而是積極意義上的原始內涵;并非某種一般性的實例,而是人類同一的、廣博的歷史性的一個個環節。”①[德]雅斯貝爾斯著,李夏菲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44、345頁。雅斯貝爾斯對歷史普遍性的思考,超越的是那種將普遍性與特殊性相對立的思維,同時也是那種將普遍性下降為一般性而把特殊性視為一般性之實例的對象性思考方式,后者針對的只是對象化的自然客體,而不是歷史。古典中國思想從天經、地義與人情的統一性視角切入歷史普遍性的構思,則比雅斯貝爾斯對歷史普遍性的構思更為具體。總而言之,“天經”“地義”與“人情”三者共同支撐、相互滲透,構建了一種頗具活力、又接地氣、合人情的具體普遍性。
如果說“天經”既可以指一種不通過宇宙及其內部的政治社會的秩序而表現的純粹普遍性,又可指在宇宙內部所顯現的秩序,這一秩序又與“地義”“人情”有交織疊構的關系的話,那么,“地義”則指向了自然與人文兩者會合而構成的內在于世界的地方性或風土性。正是由于“地義”原則,人類被劃分為不同的地理環境(氣候、水土、地理、植被、膚色、種族等)與文化環境(服飾、建筑、語言、歷史、風俗、傳統等)所構成的共同體、民族、國家、文化、文明,而這些自然和人文結合的風土性最終與不同地方的不同民性——《禮記·王制》以“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②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12,第399頁。表達這一點——的塑造關聯在一起。如果說“天經”(包括地中之天)、“地義”更多地是作為人居住其中的生活世界的被拋性要素與結構而被接受,那么,“人情”作為共同主觀性、作為主體之間的共同認可,它含有主動構成的向度,即人可以作為主體直接參與其構成的向度。如此一來,“天經”“地義”與“人情”的動態平衡,就支撐起一種具體的普遍性,或者說構成具體普遍性的三重向度。
從“天經”到“地義”再到“人情”,意味著普遍性的“下行性”的層層落實;從人情到地義再到天經,則意味著普遍性的“上行性”的自我調節,即“天經”構成“地義”的調節形式,“天經”與“地義”都可作為“人情”的調節形式。與此上行性、下行性過程同時展開的是三個向度的交織疊構,即每一因素就其自身而言都是不完全性的,而不得不向著其他因素開放自身。天經的下行并非對其普遍性的否定,而是進一步的充實,否則就會淪落為德羅伊森所謂的太監式的客觀性;人情的上行則是通過地義和天經化解人情內部的張力性結構。如果說斯賓諾莎等西方哲人提供了“在永恒的方式下(sub specie aeterni/aeternitatis)”觀看世界與人的視角,此一視角的本質是基于“天經”,那么,儒家傳統提供了一種基于“時”的視域,“時”意味著“天經”“地義”“人情”三者之會,它拒絕任何教條,而是向一切情境開放,在這種開放中面對無常世界探尋生存的常道。所謂“圣之時者”,展現的正是基于三者之會的最高人格。這種基于“時”的視域,基于三者之會的視角,展現了中國思想對于歷史普遍性的理解——它指向具體普遍性,既是開放著的普遍性,又是生動性、多樣化的普遍性。不能與“地義”與“人情”諧調的“天經”,只會將普遍性降格為單一性(uniformity)或同一性(identity),從而與多樣化與差異性相對立①嚴格意義上的近代自然科學知識,是純粹基于數學與邏輯推演的“天經”原理而建立的知識體系,其核心就是祛除一切地義性與人情性的主觀化態度,而達到純粹的客觀性,這種知識達到的是現象層面的因果性秩序,它研究的是最個別的現象,尋求現象之間的最普遍性聯系,而且具有無限發展的特征。但它僅適用于對象性的事實世界,能夠給出現象化事實之間的因果性關聯,卻無法提供進一步的解釋,即何以會有這些因果性關聯,更無法提供這種因果性關聯自身的意義。一言以蔽之,它是中性意義上的認識人與世界的方式,卻無法成為生活的要素,對于生存的真理及其意義的深淵,科學始終保持沉默。因而科學的普遍性僅僅是基于“天經”的普遍性,而不是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普遍性。關于地方性知識,參見[美]克利福德·吉爾茲著,王海龍、張家瑄譯:《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222—296頁。現代科學是以描述和說明的方式面對世界的經驗,它可以處理自然事物及其過程,或者歷史中的非歷史因素,卻無法企及歷史事物及其過程。[德]雅斯貝爾斯著,李夏菲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第322—329頁。;與此相應,“天經”就會作為一個來自世界之上的純粹超驗性的普遍性力量而對世間存在者提出強硬但又外在的要求,這種超越的普遍性落實到政治社會,則會形成一種權力分層機制,其世間代表者就將合理地擁有獨占性的支配眾生的天賦法權。“地義”作為適宜性原理,它將普遍性引向大地,引向具體的政治社會的地層,要求普遍性具有從地層深處自然生長出來的品質,正是在“地義”中我們遭逢歷史性的居所,因為一切歷史事物都在“地義”深層生長,沒有地方性的歷史事物不可能被回憶、被書寫、被激活,只有當歷史事件的一次性特征與歷史事件經過歷史記憶與歷史經驗而被激活的特征結合在一起時,歷史性事物才得以顯現,而“地義”則是歷史性事物向我們顯現的“地平線”②在對地方性的探討中,愛德華·雷爾夫指出:“人就是地方,地方也是人,盡管在概念上兩者是可以區分的,但在經驗的層面上,它們兩者很難區分。所以,地方是公共性的。地方因著人們共有的經驗被建造和被認知,地方內部也存在著共同的符號與意義。”[加]愛德華·雷爾夫著,劉蘇、相欣奕譯:《地方與無地方》,第55頁。。
具體普遍性的人情原則,賦予普遍性以生命力,歷史普遍性是通過人們的歷史經驗激活已經成為過去的事物,使之作為我們現在的“過去意識”的構成物而再生,由此而成為歷史事物。在這個意義上,與歷史事物相關的具體普遍性自身攜帶著來自人性深處、來自靈魂深處的震撼,這就是它能夠激喚我們的好惡喜怒,引發來自生命深處的深情共鳴并最終感動我們的深刻根源。換言之,歷史畛域的具體普遍性具有人性的根基,而“天經”與“地義”正是由于接通了這種人性根基,因而富有生命力,而不是僵死、冷漠、無情的抽象普遍性。天經、地義與人情的動態平衡所構筑的具體普遍性,并非否定“天經”所代表的最高普遍性:如果從純粹的天經(地外之天、人外之天)自身來看,地中之天、地義與人情都意味著某種意義上的特殊性;但如果從人的生存論視角來看,“地義”(在地之天)與“人情”(在人之天),就是最大最高的“天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