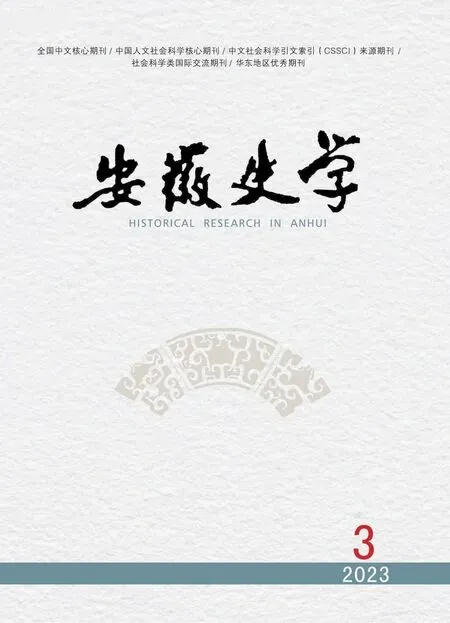思想啟蒙的兩種取向之爭
——192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生育節制討論的歷史闡釋
魏萬磊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2488)
中國人生育控制觀念古已有之,但1922年美國女權主義者桑格夫人(Margaret Higgins Sanger)來華宣傳“科學節育法”卻意義非凡。她先后在北京、上海、廣州和香港等地做了多次有關節育的演講,“象這樣大規模有意識、有目的地并從近代科學的意義上全面闡述節育的理論和方法,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1)梁景和:《五四時期“生育節制”思潮述略》,《史學月刊》1996年第3期,第49—50頁。此后各種節育理論大量涌入中國,討論逐漸深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節育運動逐步興起,1937年以后,隨著全民族抗日戰爭的開始,“救亡”徹底壓倒“啟蒙”,節育運動淡出歷史舞臺。對20世紀20年代還作為思想啟蒙的優生節育討論進行研究,可以有效揭示思想啟蒙的內在困境。
民國時期的“生育節制”擁有諸多名稱,如“節育”“制育”“產兒制限”“生育制裁”等,按照現代人口學奠基者之一陳達的定義——“生育節制是用理智來管束生育的一種方法”(2)陳達:《我們應該提倡生育節制嗎?》,《清華周刊》1931年第35卷第7期,第473頁。,著眼點在于子女數目的控制,與獨身和絕育有明確不同。(3)陳長蘅:《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第319頁。20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開始對民國時期的生育節制展開研究。(4)代表作如王奇生:《近代中國節育運動述略》,《人口研究》1990年第5期。王奇生把民國時期的節育運動劃分為兩個階段——桑格夫人來華的1922年之后的整個二十年代為發端和宣傳的階段,三十年代之后則為從宣傳走向實踐的階段,此后的民國節育運動研究多沿用這一分期方法。大多數研究者從人口與節育、性道德與節育、婦女與節育、優生與節育等四個方面展開討論。(5)如一些學位論文,包樹芳:《民國時期節育思潮初探》,揚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周麗妲:《生育觀念在近代以來的嬗變——以節制生育運動為基點展開論述》,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李春霞:《論近代中國生育節制思想》,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馮思奇:《民國時期生育節制思想及實踐研究》,安徽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俞蓮實:《民國時期城市生育節制運動的研究——以北京、上海、南京為重點》,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等。本文試圖通過文本分析揭示這場思想啟蒙運動在個體取向和國族取向上的差異,進而探討思想啟蒙內在的邏輯困境。
一、生育節制討論的興起
優生節育問題的提出與近代中國城市新市民群體的興起和生活方式的變遷密切相關。傳統生育觀念與小農經濟相聯,之所以提倡“多子多福”,主要因為較多的男性勞動力對農業生產有益。在生活方式的現代轉型中,建立在工商業基礎上的城市興起,新的城市居民與小農社會變得疏遠,他們有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會關系和新的價值觀,因此便有了對自身和后代的新期盼。
在新興的“準市民群體”中,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是他們中的重要成員。在教育方面,他們至少都接受過小學或者中學的教育,優秀者還接受過大學的教育(6)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1—582頁。,在工作方面,他們因受教育水平較高而獲得一份體面的非體力工作,依靠工資來維持生活;在工作之余,他們重視娛樂和享受,吹簫、唱歌、彈琴、看電影、游公園、逛百貨公司等;(7)朱邦興等合編:《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頁。在住宅方面,他們住在新型的城市住宅里,這些城市住宅面積小而緊湊,但設施配備則完全依照現代住宅的標準,適于小家庭或單身的生活;(8)江文君:《近代上海職員生活史》,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321頁。在家庭方面,他們厭惡傳統的家長制的大家庭,提倡核心家庭,向往婚姻的幸福和美滿,以及小家庭的美好生活。(9)江文君:《近代上海職員生活史》,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321頁。社會新階層的出現引起了觀念的深刻轉變,生育節制逐步成為可討論的話題。這一階層不愿拿出足夠多的精力和財力來養育孩子,居住空間的逼仄也需要考慮家庭成員數量;崇尚自我的新價值觀更不愿受“傳宗接代”思想的束縛。對于這些新的城市居民來說,新生活方式和觀念的轉變,使得生育節制在他們看來越來越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種必要了。(10)如在《生活》上刊登的一封讀者來信,就表達了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住宅、工作的壓力下對于節育的需求。參見隱:《受經濟壓迫而想到節育的一位青年》,《生活》1926年第2卷第7期,第54頁。
馬爾薩斯主義和新馬爾薩斯主義是生育節制討論興起的理論基礎。1880年,京師同文館畢業生汪鳳藻翻譯《富國策》,簡要介紹了馬爾薩斯主義,之后又有維新派嚴復和梁啟超等人在著作中對馬爾薩斯主義的介紹。(11)參見[英]托馬斯·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66頁。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2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93頁。時人之所以關注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多半受進化論的影響。到了二十年代,新馬爾薩斯主義傳入中國。新馬爾薩斯主義提出通過科學的、人為的避妊即生育節制來限制人口數量,彌補了馬爾薩斯主義“不近人情”地限制人口措施的缺點,由此得到了學者們廣泛關注。這些學者發現了生育節制對于解決人口問題之外的其他領域同樣頗有價值,這成為生育節制討論的歷史背景。
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場討論中的情緒可以用“羨憎交織”來概括。面對已然“現代化”的西方,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正視人口和人種的問題。桑格夫人同情地將黃種人無節制的生育作為其野蠻落后的根源,她在演講中說道:“在中國,我們目睹了人口過剩這一民族悲劇的最后一幕。這是一個匍匐在塵埃中的偉大帝國。中國,這個擁有藝術、哲學的神秘源泉和世界上最深邃的智慧的國家,已經被黃種人的不良生育和惡性繁殖打垮。”(12)Margaret Sanger, “Birth control in China and Japan”,speech delivered on October 30,1922 in Carnegie Hall,New York.https://documents.alexanderstreet.com/d/1003811409.一些知識分子在參與節育討論的過程中,不自覺地成了西方節育論者塑造的這種“東方”印象的參與者。即使是抵制節育論者也無形中將孱弱的黃種人與先進且優秀的白種人作對標。動物學家陳兼善就指出,白種人與其他有色人種抗爭,“獲得優勢,立于支配者之地位”,因此有色人種更不能夠“拾人牙慧講什么產兒限制,以至于人口衰減,那末有色人種,真是為白人底奴隸了。”(13)陳兼善:《優生學和幾個性的問題》,《民鐸》1924年第5卷第4期,第9頁。周建人更是將民族衰退的重要原因歸結為在與強大民族接觸時無法適應被強大民族所改變的環境,“近來許多不開化的民族,和白種接觸以后,白人雖不撲滅他們,他們自己也會衰頹。這是真的,你如將不進化的民族的土地改做紐約、倫敦般的都會,土人反不能存活其間了。”(14)周建人:《讀中國之優生問題》,《東方雜志》1925年第22卷第8期,第16—17頁。同時,面對西方話語成為討論的主流話語,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憎惡的,試圖守衛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有人列出了反節育的幾類衛道士立場:上天有好生之德;人少何以衛國家;節育有違人倫,以此抵制新思潮。(15)曉風:《生育節制問題》,《民國日報·婦女評論》1922年第39期,第1頁。兩種情緒恰恰是“后發強制性國家”卷入現代化進程后的普遍情緒。
生育節制討論既討論了節育對個人(尤其是婦女)解放的效用,也討論了節育對社會發展、民族存亡、國家興衰的重大影響。論戰雙方圍繞生育觀、婚戀觀與性觀念、女性地位與權利等話題展開討論。
二、個體層面的生育節制討論
“五四”時期“科學”成為主流話語,知識分子呼吁轉變生育觀念,正是借助“科學”之名。無論是革除不人道、不健康的舊生育觀念,抑或是對傳統觀念的再闡發,科學話語始終貫穿在節育與生育觀念的討論中,新生育觀之“新”即在它是“科學的”生育。
鑒于女性承受著來自社會觀念與家族生活兩方面的壓力,這是主張生育節制的出發點,所以新生育觀與舊生育觀針鋒相對。舊生育觀包括三方面,即重視傳宗接代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強調添丁增口的“多子多福”和含有性別歧視意味的“重男輕女”。(16)鄭永福、呂美頤:《中國婦女通史(民國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471頁。新生育觀明確地批評這種傳統生育觀對于婦女健康和幼兒成長的傷害,節育論者同時也批判中國古代控制子女數量的辦法——棄嬰、溺嬰、墮胎等。桑格夫人的科學節育法——在妻子危險期以外同房的節欲法、對男子生殖器官的生育能力進行干預的斷種法和在同房過程中用特定器具或藥物阻礙受孕的機械法,這些方法受到中國節育論者的推崇,被認為是更人道、更科學、更安全的節育方法,而傳統節育方法都是野蠻、反科學的。(17)周建人:《產兒制限概說》,《東方雜志》1922年第19卷第7號,第14—15頁。
也有人重新從傳統生育觀中尋找積極遺產,以此作為新生育觀的基礎,雖然與節育論者觀念不同,但也對傳統節育觀進行修正,優生學家潘光旦便是典型。在人類演化的過程中,除了被稱為“天擇”即殘酷的自然選擇之外,潘光旦更重視和推崇的是“化擇”即文化或社會選擇。他認為西學東漸以前,中國傳統中已經有一些“化擇”的因素,它們有明顯的優生效果,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把傳宗接代放在個人幸福之前,雖然不利于個人權利的伸張,但對宗族延續和幼兒養育具有保障作用,而傳宗接代的重要性是西方優生學者近來才認識到的。(18)潘光旦:《中國之優生問題》,《東方雜志》1924年第21卷第22號,第17—20頁。
婚戀觀和性觀念是節育討論的突破口。婚姻目的被認為是值得審視的問題。傳統的婚戀觀被概括為“婚姻的本質是生育”,節育論者支持婚后節育,認定生育只是“婚姻下可能有的現象和質料,決不是婚姻的要素”(19)陳德徵:《婚姻和生育》,《婦女雜志》1922年第8卷第6號,第86頁。,傳宗接代不是夫妻的義務。潘光旦則反對這種“本質論”的節育觀,他用“權利”與“義務”的關系打比方,認為從性行為到生育的過程中,因與果本是緊密關聯的,但人既然是趨樂避苦的,節育方法的引入便會使人們輕而易舉地把性的娛樂與繁衍后代的責任相分離,造成不良影響。所以節育論者可能只是借助女性權利的由頭伸張其他方面的權利,“主張生育限制最力者大都為女權運動中之激烈分子,往往假借‘母性之自由獲得’之大名義,而推廣其一般的女權。”(20)潘光旦:《生育限制與優生學》,《婦女雜志》1925年第11卷第10號,第1561頁。夏丏尊則針鋒相對地認為婚姻不應該單純為生育服務,主張將性與生育分離,因為婚姻和生育都無法真正確立起男女間性道德的“自覺”。(21)丏尊:《生殖的節制:歡迎桑格夫人來華》,《民國日報·婦女評論》1922年第38期,第1頁。這種道德自覺與傳統的“貞操”觀迥然不同,它不再依靠“法律名譽等消極的外來制裁”,而是“必須積極的從根本上入手,如實施青年男女的性教育,提倡戀愛的神圣,尊重女子的人格”,此外還要一改性道德完全由婦女單方面遵守的舊觀念,提倡由男女雙方共同負起義務。(22)瑟廬:《產兒制限與中國》,《婦女雜志》1922年第8卷第6號,第12、13頁。以往敏感的話題在“科學話語”加持下得以光明正大地討論,很多人聽完桑格夫人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后,直觀的感受是,“‘性’的事情,原來還是值得用科學方法去討論的啊”。(23)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310頁。以張競生為代表的本土性學學者主張科學認知“性”的問題,對中國人的性體驗進行了一次科學大調查,編寫了《性史》。無論是對婚戀要義的探討,還是對性這一敏感問題的大膽辯護,主流論者在圍繞節育展開討論時,都有意用科學認識性問題,盡量避免用盲目的價值判斷直接封堵討論這些話題的可能,使更多人對于婚姻、愛情和性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放。這些討論滲透出鮮明的啟蒙色彩,如兩性平等、個人自由與責任相聯系的觀念等。這從側面說明,五四啟蒙的新文化、新思想已逐漸融進學者的思維方式和話語體系中,成為他們論域的內在組成部分。
生育節制討論所涉及的最重要的對象是女性群體,女性權利是節育討論的重中之重。在節育討論的語境下,“生育”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生理過程,它被看作圍繞這個生理過程所展開的種種活動,包括受孕、生產、養育等,婦女承擔從生到養的沉重負擔,甚至面臨生命危險。一些人把生育看作“人類的天職”(24)羅齊南:《中山先生論人口問題之討論》,《現代評論》1926年第3卷第72期,第20頁。,以此反對節育對以往自然生育秩序的顛覆。節育論者則大多從女性關懷出發,圍繞婦女的生理感受、社會追求展開討論。無論是以實際經驗為證,還是用嚴謹的醫學原理支撐,支持減輕女子繁重生育負擔的論者都表現出對女性艱辛生育感受的理解。(25)本來在這方面最有發言權的論者是女性,但實際上出現了“女性聲音的缺失”,詳見馬姝:《“桑格熱”之后》,《讀書》2022年第9期,第131頁。從已有史料來看,事實大體如此,除了劉王立明等少數新女性知識分子發論,節育討論主要由男性知識分子掌控。生育關乎女性的健康和幸福,但過于頻繁的生育卻往往給她們帶來苦惱和危險,《婦女雜志》1931年初發表的一篇來信很能代表當時女性的感受,一位名叫黃秀芬的女士發出了“生育的機器要做到幾時為止”的質問。(26)黃秀芬:《生育的機器要做到幾時為止呢》,《婦女雜志》1931年第17卷第1號,第221頁。由于傳統生育觀念的束縛和不具備科學有效的避孕措施,女性往往無法真正掌握生育主動權。節育論者對此十分同情,指出生育自主對女性身體大有裨益,相比于宗法社會中接二連三而中間幾乎無喘息時間的生育重負,節育可以減少頻繁生育對母體的傷害;而且男子也應該認識到,女性的身體也同樣是血肉之軀,不能貪圖性享受,無視“婦女在這樣接連不休的生育下要忍受多少的苦痛”。(27)金仲華:《節制生育與婦人生理的解放》,《婦女雜志》1931年第17卷第9號,第6頁。在強調平等、理解與關懷的基礎上,節育論者要求實現女性對生育自主權的掌控,經常就婦女解放發表見解的陳望道提出,女子求幸福、爭解放的基礎之一就是“母性自決”,即“對于讓幾個人來做自己底兒女的事,女性也必然可以自己底意志決定”。(28)陳望道:《母性自決》,《陳望道全集》第5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頁。
民國時期逐漸壯大的新女性群體希望突破“閨閣女子”的舊身份,通過受教育改變自我,爭取男女平權。然而,生育的過程以及生育后的撫養責任很重,而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仍然占據主流,這些都使年輕婦女事業敗給了家庭事務。節育論者認為,如果婦女無休止地承擔生育和養育的繁重工作,就會阻礙新女性自身發展,也阻礙社會進步。有人認為“婦女的被束縛,是無教育,經濟依賴男子及不能替社會服務等應有的結果”,但節育論者則認為這是顛倒因果,事實上是教育不足、經濟不獨立導致了婦女的社會地位低下,而社會沒有給婦女獲得教育、經濟獨立的機會,因為這些機會都被年輕時早婚、早育、頻育的壓力排擠流失。(29)瑟廬:《產兒制限與中國》,《婦女雜志》1922年第8卷第6號,第12、13頁。生育節制成為提升婦女社會地位的必要前提,只有在減輕生育負擔的基礎上,婦女才可能擺脫“生殖機器”的束縛,盡情發揮自己的天賦才能,實現從照顧家庭到奉獻社會的人生意義的量級躍升。(30)西瀅:《閑話》,《現代評論》1926年第3卷第74期,第7頁。
可是,生育節制需要經受的最有力辯難,并非來自對“生育”本身的不同觀點。在討論生育節制的價值時,這場思想啟蒙不由自主地面臨從個體轉向集體的難題,在社會、國家、民族這一層面上討論生育節制比性啟蒙、女性權利等問題占有更大的分量,并且幾乎覆蓋了所有反節育論者的論說。
三、國族取向上的生育節制討論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每個家庭的狀況與變化都是社會整體發展狀況的微縮圖景。隨著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民國時期社會經濟的新發展也反映到城市小家庭的新變化中。在知識分子生育節制的討論中,生育越來越被看作是不僅關系到一家一戶幸福或煩惱的事務,更是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的健康發展息息相關的大事。
由于社會缺乏健全的生育保障措施(31)直到20世紀40年代初,國民黨官方才擬定了一系列獎勵生育的具體方案,詳見俞蓮實:《民國時期城市生育節制運動的研究——以北京、上海、南京為重點》,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311—318頁。,即使對城市家庭來說,頻繁生養幼兒所帶來的經濟壓力也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周建人認為,頻繁生育會造成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即頻繁生育——母親難以離家謀生,用于孩子的開銷漸增——經濟壓力增加,父母對收入需求急迫——母親與較大的兒童為生活所迫做工,工人增加導致工資下降——孩子失去求學以增長能力的機會。(32)周建人:《產兒制限概說》,《東方雜志》1922年第19卷第7號,第12—13頁。因此節育才是解決社會貧困問題的良方。在節育論者看來,一個家庭內子女過多存在拖垮家庭財富的風險,一個社會中人口過剩也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一些人口學家在進行社會調查和數據分析后,認識到中國面臨著“人滿之患”,而判定人滿為患的依據便是“生活程度”的高低和“生活競爭”的劇烈程度。(33)陳達:《我們應該提倡生育節制嗎?》,《清華周刊》1931年第35卷第7期,第473、471—472頁。他們信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基本原理,認為在“人口超過物質所能供給的限度”(34)丏尊:《生殖的節制:歡迎桑格夫人來華》,《民國日報·婦女評論》1922年第38期,第1頁。情況下,不對人口預先進行人為干預,各種天災或人禍就會用更殘酷的方式“抑制”人口,人滿為患的危害會越積越重,形成人口增加——食物供應緊張——天災人禍限制人口——人口又增加的惡性循環。(35)陳達:《我們應該提倡生育節制嗎?》,《清華周刊》1931年第35卷第7期,第473、471—472頁。大力倡導生育節制的人口學家陳長衡做出警告:無節制生育無異于民族的“自殺”。維持“適中的人口密度”,即不斷調整國家人口,以使其達到適中的程度,為此,需要使大眾認識到人口適中的重要性,使每個人負起維持適當生育量的責任。(36)陳長蘅:《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第90頁。
隨著生育問題越來越多地被置于公領域探討,論戰雙方將其上升到關系國家存亡與民族復興的高度來審視,主要討論集中在人口“數量”與“質量”之爭上。新馬爾薩斯主義是節育論的理論基礎,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和節育論者大多從人口過剩、婦女受壓迫和人口素質低劣的不良影響等方面立論。反節育論者主要圍繞馬爾薩斯主義和新馬爾薩斯主義展開批判。譬如臨終前的孫中山就對“蠱惑人心”的馬爾薩斯主義和新馬爾薩斯主義進行了嚴厲批判,他認為馬爾薩斯主義所謂人口多于資源的觀點,實際上為列強們在世界上大肆侵略擴張提供了依據。現如今的中國之所以還沒有被吞并,正是因為列強人少而中國人多。一旦推行節育政策,中國人口減少,更難抵抗外來侵略。孫中山對生產力的進步充滿信心,相信隨著生產力的進步中國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37)孫中山的人口思想存在憂慮“人滿之患”與擔心人口增長過慢前后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前者主要是在1924年以前闡發的,1924年,孫中山人口思想突然轉向鼓勵生育。具體參見胡繩武、戴鞍鋼:《試論孫中山的人口思想》,《學術研究》1996年第10期。很多人支持這一說法,認為鼓勵生育才能保障民族的生存安全,民數及其增長率絕不可落后,否則終會丟掉中國龐大人口這一為數不多的優勢,淪落到滅國亡種的境地。在本民族的外部威脅日益加劇的情況下,“外國人口一天天的增添,中國人口一天天的減削,推知百千年之后,會被天演公例淘汰無余的危險”。(38)羅齊南:《中山先生論人口問題之討論》,《現代評論》1926年第3卷第72期,第20頁。由于當時中國官方沒有做過整體系統的、值得信服的人口統計工作,因而學者在討論人口增長快慢問題時,往往只能依據實際感受、局部的田野調查和國外學者不見得可靠的數據,這就為展開廣泛討論提供了可能。有論者更進一步指出,節育這種西來學說背后可能隱藏著不良動機,中國貧弱的真正根源,是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和壓榨,節育思想幫帝國主義掩飾了這個禍根,“而反到歸罪于中國女人太會養小孩子”,中國堅決不可以推行節育,因為“在中國生活程度低,人民智識文化低,醫藥衛生毫不講求,就是少養幾個孩子,死亡率未必能減低,壽命未必能延長,結果人口定然會大大的減少,正是給人家以殖民可能的機會。”(39)張履鸞:《江寧縣四百八十一家人口調查的研究》,中國社會學社編:《中國人口問題》,世界書局1932年版,第342頁。相反,人口增殖不僅可抵御外侮,還利于國家發展。1927年,中國近代著名鄉村教育家楊效春就抓住了馬爾薩斯主義致命的五大缺點,對“中國人口問題”做了有高度傾向性的總結,他認為一國人口的多寡與國勢強弱、經濟貧富、文化高下、國防力量和個人幸福都有密切關系,這五方面的進步都需要大量的人口作為后盾,他以此批判生育節制主張,節育甚至被他斥責為“民族自殺之策”。(40)楊效春:《對于時論“中國人口問題”的總答辯》,《東方雜志》1927年第24卷第22號,第14、17—18頁。楊文指出,第一,人口增加并不必然比食物增加快,生產力和科技進步將大大加快糧食生產增速;第二,資源分配的矛盾不在資源與人口的比例,而是資源分配不公的結果,是國際和國內的雙重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分配才導致了民族衰弱、平民貧困;第三,馬爾薩斯對天災人禍抑制人口的解釋過于單一;第四,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假設了生產力的緩慢發展,然而發展生產力和促進財富增長的辦法還很多;第五,人口與資源之間并非簡單的對立關系,“人口增加即勞力加多亦可使生產增加,且人多則生存競爭激烈,可使人類事業益超發達”。
節育論者否定自己是為了節育而節育,他們更看重的是人口“質量”的提升,擁有一群高素質的國民才更是民族發展的福祉,為此寧可削減新生人口的數量,以追求少而精的人口結構。不同的是,他們選擇了一條與人口增量論者大異其趣的路徑。一方面,他們認為那種把人口數量看作國家強大標志的觀念已經不符合時代的新要求,在當前國際舞臺上,一個民族的強弱“不在乎數量的多寡,而在乎質地的優良”。(41)瑟廬:《產兒制限與中國》,《婦女雜志》1922年第8卷第6號,第12頁。量的優勢無法保障國家安全,否則無法解釋人口數量龐大的中國屢受人口數量遠少于中國的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欺凌。另一方面,人口增量論著眼民族發展的全局性因素,希望盡快加添人口總量,以達到抗衡強敵的效用。但這恰為節育論者所反對,他們拒絕從“上帝視角”考慮國家的人口問題,而是著眼于個體發展的實際,認為給予個體更充分的發展機會是提升國民貢獻國家能力的前提。如與撫養五、六個孩子相比,只撫養兩個孩子的家庭利于為孩子提供更充裕的生活條件,每個孩子能夠分得更多父母的照料,獲得更充分的教育,“這樣,如果只有子女二人,他們就成了二個健全有用的國民,要是有了五六個,他們對于國家的貢獻反而低落了。”(42)西瀅:《閑話》,《現代評論》1926年第3卷第74期,第7頁。
雖然節育論者和增量論者存在路徑上的分歧,但節育論者無意通過支持節育來否定增量論者的民族救亡愿望。恰恰相反,節育論者試圖在人口增量與提質之間達成某種妥協,以證明數量與“質量”并不矛盾,進而說明優化生育與民族發展正相關。因為少生與優生不僅不會危及種族繁衍的總體局面,還會減少導致人口增長乏力的因素,如災禍對人口的抑制、生育中發生的意外等。他們相信多數女子具有與生俱來的強烈母性,人類具有繁衍后代的本能要求。所以即使實行了節育,也“絕不致種族會自殺的”。(43)周建人:《產兒制限概說》,《東方雜志》1922年第19卷第7號,第17頁。可見節育論者力圖實現的是國民在量與質兩方面的優化,只不過更傾向于把提“質”放在優先地位。
四、兩種取向展示的啟蒙窘境
縱觀20世紀20年代的生育節制討論,可以發現一些顯著的特點。一方面,作為個體取向的生育節制,雖然在節育的理論、方法以及圍繞節育的婚姻、家庭、性、權利等問題,立論雙方的觀點和態度千差萬別,從極端反對、懷疑否定,到部分認同、極力宣傳皆大有人在,但對于那些節育論者而言,他們多側重于從思想解放、個人發展出發,逐步上升到社會改良、民族壯大。他們要求先破除傳統植根于人們頭腦中的舊觀念,如多子多福、無后為大、民庶則國必強等舊價值觀。他們強調個人發展是國家強大的前提,希望通過生育節制將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故而傾向于強調個人“權利”。而反節育論者則傾向于從國家和民族安全的角度出發,把民族生存作為高于一切的立場,個人的解放不能觸動民族、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傾向于“欲享權利必先盡義務”(44)宋國賓:《節育問題之我見》,《醫藥學》1927年第4卷第6期,第26頁。,強調種族繁衍的優先性。個體取向上的生育節制討論,正是兩種不同側重點最典型的例證。
論戰雙方在差異中蘊含著共性,這種共性在個人解放方面并不顯著,而當生育問題與更為宏大的國家和民族前途問題聯系起來時,觀點相左的論者竟自覺不自覺地使用了趨同的話語,即加強對國民生育行為的指導,以合理的生育方針來挽救國家危機,謀求民族復興。圍繞國族層面展開的節育討論包含了內部發展與外部威脅兩種視角。對于民族的內部發展,他們共同擔心的問題是“民族自殺”,只不過節育論者從馬爾薩斯主義出發,擔心“人滿為患”的后果,即無節制的生育造成天災人禍對人口的殘酷抑制;反節育論者則重新拾起古老的民庶則國強觀念,重視“民數”或“民量”,并以新的方式闡釋龐大的人口基數對于現代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的價值。至于民族外部威脅,他們都把列強侵略勢力視為中國生存的嚴重威脅,如何保證本民族能在強敵侵略與國際競爭中生存下來、強大起來,是他們思考生育與人口問題的共同著眼點。節育論者重視“民質”,強調現代國際競爭的新形勢,認為僅僅鼓勵“民數”增加不能改變中國孱弱的現狀。盡管如此,他們也在努力尋找消解“民質”與“民數”間矛盾的辦法,力圖實現中國人口質與量的全面發展。這又從側面印證出,雙方論者在其思想內核中并不存在顯著分歧,民族救亡成了他們闡發節育觀的共同旨歸,在這一點上,“救亡”壓倒了“啟蒙”。
理論走向實踐的第一個誤區,便是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相悖。一些人對節育實踐抱著盲目的樂觀,邵力子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生育節制釋疑》中,他認為生育節制的理論更重要,實踐則是其次。只要經過理論上的研究發現確有節育的需要,決不怕沒有適應這個需要的方法。(45)邵力子:《生育節制釋疑》,《民國日報·婦女評論》1922年第39期,第3頁。邵顯然將節育實踐想得太過簡單。在當時中國的社會環境下,節育的群眾基礎還十分薄弱,甚至有人懷疑節育方法的有效性:“今日所見產兒制限方法不下十余種,其中殆無十分有效而且無害者。即使有比較的確實方法,無絕對可靠者。”(46)劉以祥:《答“再講產兒制限與性道德”》,《晨報副刊》1925年5月7日。這些對于節育實踐的反思,確實反映了當時社會條件下推行節育的困難。任何一種新思潮的傳入,都必須考慮其本土適應性的問題。在節育討論之初,一些歡欣鼓舞的支持者把節育奉為救世的唯一良方。鼓吹節育可以解決一系列因人口過剩引發的社會問題,絲毫沒有考慮到人與人、群體與群體、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差異,以及節育在婦女解放事業中可以發揮作用的限度。這就造成了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的嚴重背離,所以事后來看,“這種科學的知識有賴于正常醫者的研究介紹。然而我國醫者并未注意到這方面,而無知的秘密墮胎卻乘著機會發展的很厲害了。”(47)金仲華:《節制生育與婦人生理的解放》,《婦女雜志》1931年第17卷第9號,第10頁。
理論必須“掌握群眾”才能變成“物質力量”,開展節育啟蒙的社會主體都是社會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民眾則是作為被啟蒙的“社會客體”出現,節育理論在“掌握群眾”的過程中陷入了兩難。正如進入實踐階段,一些有識之士才認識到,理論上,知識分子是有知識、有智慧、有才學的人,是社會中的“優質”人口,“實在是我們健全種族起見要保存繁殖的”,只有知識分子在人口中的占比不會銳減,人種的“質量”才能有所保障。但現實卻是,基本上只有少數知識分子在采取生育節制,而其他社會群體卻未接觸過或不愿節育,那些“一般不負責任的糊涂蟲”,卻在“拼命的作大量的生育工作”。(48)柯象峰:《中國人口問題與生育節制》,《政問周刊》1936年第11期,第9頁。長此以往則社會中的“優質”人口將會越減越少,而社會中的“非優質人口”卻繼續多產,人種的素質就將每況愈下,形成所謂的“反優生”現象。事實上,此前潘光旦就闡釋了這種現象,如果單純相信“天擇律”,強調人與人天生就有智愚賢不肖之分,先天條件遠比后天環境塑造重要,那么那“優質”的人就應該多生,而新馬爾薩斯主義與桑格夫人的生育節制論忽視了固有文化形成的路徑依賴,體弱多病者反而更加需要延續煙火,這樣就會導致“反選擇”現象的出現。(49)潘光旦:《中國之優生問題》,《東方雜志》1924年第21卷第22號,第17—18頁。
精英主導與大眾運動的悖論是另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中國的節育思想受到西方節育思想啟迪,后者萌芽于中產婦女爭取權利的運動中,其本身就帶有精英色彩。節育討論本身就是社會精英推動的啟蒙運動,而為數不多的親身宣傳推廣者和履踐隊伍也主要由精英組成。因此,節育論爭中充滿了精英聲音、精英視角和精英偏見是容易理解的。如果將階級分析的視角引入節育的討論,探究節育的階級屬性和適用范圍,便容易理解將其轉變為大眾運動的窘境。進入30年代,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已成一些知識分子的新理論武器,有人就指出,是生產關系決定了貧窮、失業、戰爭和盜竊等罪惡,而不是人口過剩。提倡生育節制無疑是為資本主義制度遮掩矛盾,生育節制只是資本主義制度茍延殘喘的辦法,卻是工人階級的“悲慘呼號”。節育唯一從根本上站得住腳的理由就是其對優生的功效,但這種優生是“防止不健全的人的生育”,而絕不是那種鼓勵上層生育而要求下層節育的“優生”。“如果節育運動是完全站在真正的人類優生學基礎上而被提倡,那么他不應該根據甚么人口過剩和貧苦的人因為經濟困難而應節育等等理由,更不應該根據知識高低和現有社會地位高下來決定人類之種的優劣,并以此為節育的標準。”(50)陳碧云:《現代婦女節育運動的解剖》,《東方雜志》1933年第30卷第15號,第5—6頁。周建人也明確將節育定位為“一種小資產階級的需求”。而小資產階級之所以推崇節育,是因為“小資產階級想維持他的階級地位,不能不叫兒女受相當的教育,而他的經濟狀況,又限制他給子女受教育的能力”。與此相比,在上的富人不需憂慮養育子女的負擔,而在下的無產階級則忙于生計,無暇關注節育,更沒有經濟能力負擔節育措施。周建人破除了節育的“泛階級”神話,他不僅把握住節育的受眾群體,也鮮明地指出了在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推行節育的局限性。對于備受壓迫的婦女群體來說,節育以減少生養孩子的負擔當然是可取的,“不應當把這題目過于夸張,以為只要用生育節制的方法就可以解決各種重要的社會問題了,就在婦女方面,也決不是只要普遍的實行避孕就能得到解放的”,僅有生育上的解放遠不能實現婦女完全的解放,“在婦女解放上也只占一個極小的部分”。(51)克士(周建人):《關于生育節制》,《東方雜志》1935年第32卷第5號,第92頁。這樣一來,以少數人的意見指導一個在民眾主觀意識上損害自身利益的啟蒙運動,自然會在大多數民眾的漠然無視中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