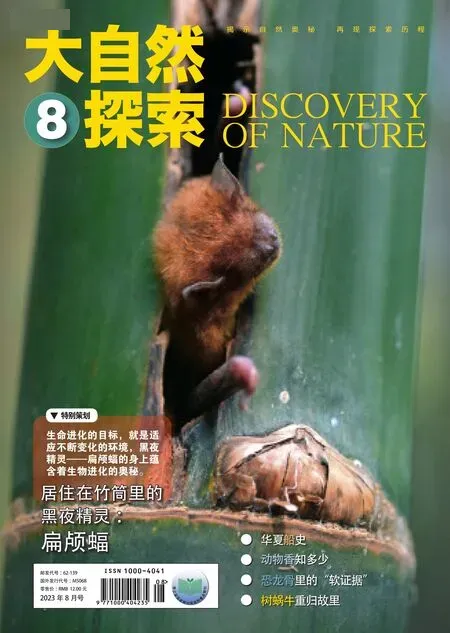懸泉置
撰文 徐寧

懸泉置遺址出土文物
懸泉置是座驛站
1987 年8 月15 日,時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的何雙全接到敦煌市博物館榮恩奇館長的邀請電話,約他一同去一個新發現的遺址考察。第二天,在榮恩奇的帶領下,何雙全徒步四小時,來到那片遺址,并進行了簡單勘察,沒有太多發現,這不免讓他有些失落。三天后,榮恩奇再次邀請何雙全前往那個遺址勘察,但這次竟收獲頗豐。在發現了絲綢碎片、銅箭頭和鐵器殘片等重要文物后,何雙全才意識到這個遺址不簡單。
在后續勘察過程中,何雙全發現了一枚帶有文字的簡牘,并判斷其為漢簡。在何雙全的印象里,甘肅出土的漢簡雖然數量眾多,但都是出土于長城遺址沿線。而這次發現漢簡的遺址距離長城遺址較遠,這里為何會有漢簡?
1990 年11 月11 日,考古人員開始對這片遺址進行系統性發掘。經過兩年間的三次大規模發掘,一座長寬各50 米的漢代郵驛重見天日。

從簡牘過渡到紙張
迄今發現年代最久遠的簡牘源自戰國時代,秦漢和三國時期見證了簡牘的普及。西漢出現的澆紙法和東漢蔡倫改進的抄紙法讓紙張的使用范圍越來越廣。西晉時期簡紙并存,到了東晉,紙張已經完全取代了簡牘。


懸泉是懸泉置的重要水源
“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后漢書·西域傳》
根據簡牘記載,這座郵驛名為“懸泉置”,位于敦煌市和安西縣(今瓜州縣)之間的中心點上。漢代時,懸泉置屬敦煌效谷縣制內,驛站主官稱為“置嗇夫”。驛站整體建筑為一座四方小城堡,大門朝東,院墻高聳。懸泉置背靠祁連山脈的火焰山,東側山谷中有泉眼(即懸泉),西南角設瞭望角樓,內部區域分為辦公區、住宿區、馬廄、垃圾堆等。
經過三次系統性發掘,懸泉置遺址共出土漢簡2 萬余枚,其他重要文物若干。
西漢“特快專遞”
漢承秦制,西漢的郵驛系統也沿用了秦朝制度。漢代的公文是靠置、騎置和亭三者組合構成的郵驛通道進行傳遞的。其中,置是在交通要道上每隔三十里就必須建一座的大型郵驛,特點是占地大、物料齊、公職人員多、配備馬匹和車輛充足。

漢代彩繪磚,上繪人物為傳遞公文的驛使

懸泉置遺址全景
漢宣帝時期,漢朝老將趙充國曾經就平定西羌一事向漢宣帝請示。趙老將軍的這封奏疏從他所守的金城(今蘭州)發出抵達漢宣帝所在的長安(今西安),經漢宣帝批復后返到趙將軍之手,行進的總路程近4300漢里(1 漢里約合415 米),全程卻只用了7天,這還包括朝廷議論奏疏所花的時間——要知道在當時,朝廷派遣官員到距離蘭州不遠的敦煌,走完單程平均都要40 多天。距今兩千多年前的西漢郵驛系統為何能如此快速地傳遞奏疏?
將軍向皇帝呈上的奏疏屬于最緊急的郵件,信使必須飛馬傳遞,一匹馬跑不了太遠,因此信使必須在沿途的郵驛換馬,以接力傳遞。漢朝遍及全國的高效郵驛系統保證了地方(尤其是邊塞)和朝廷的信息互通。根據在懸泉置發現的簡牘,懸泉置平時有公人三四十人,馬四十匹,車輛十乘至十五乘。
懸泉置遺址漢簡中數量最多的是官府文書和皇帝詔書,但大部分殘缺,其次是各種簿籍,例如人事方面的《吏名籍》《功勞案》,以及財務方面的《入租簿》《錢出入簿》《谷出入簿》……這些簡牘為學者研究當時的敦煌和社會制度提供了重要參考。接下來,讓我們看看其中一些簡牘記載的內容。
招待精絕國王一行人
“送精絕王諸國客凡四百七十人。”
懸泉置不但發揮傳信的作用,還兼具接待的功能。現藏于甘肅簡牘博物館的一枚懸泉置木簡(簡雖多用竹,但西域地區很難種植竹子,所以當地簡多用松、胡楊或紅柳制成),其中可以辨析的簡文表明,懸泉置曾接待了精絕國王和其他各國人員470 人。
精絕國為西域三十六國之一。據《漢書·西域傳》記載:“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也有學者認為三十六只是虛指,并非實際數量。據另一份簡牘記載,懸泉置曾接待于闐王一行人,總人數多達1600 人,酒杯就用壞了300 多個。從懸泉置漢簡中,歷史學家們發現了樓蘭、且末、于闐、精絕、大宛等30 多個西域國家和漢王朝來往的記錄。
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 年),朝廷在烏壘城(今輪臺縣境內,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緣)設立西域都護府,其作用是管理西域諸國。西域都護府的建立結束了西域地區四分五裂的狀態,極大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并維持了絲綢之路的長久安定。

張騫出使西域圖(莫高窟第323 窟)

河西走廊風貌

“有急事”簡
賜給鄯善王的宮女
“出粟一斗六升,以食鄯善王、王賜妻使者犬蘇者等二人,人再食,食四升,西。”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俊民認為,該簡屬于“出入簿類文書”,據簡牘記載的內容可知,懸泉置接待的是鄯善王和王賜妻所派的兩名使者,他們從東向西經過懸泉置,從漢地回到自己的國家。在懸泉置停留期間,第一頓飯共吃了一斗六升(西漢一升約合200 毫升,十升為一斗)粟(非黏性的小米),第二頓每人吃了四升粟。
鄯善即樓蘭,當時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小國。面對漢朝和匈奴這兩股強大勢力,樓蘭時常首鼠兩端。《漢書·西域傳》記載:“……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這段內容是說,新樓蘭王將國名改為“鄯善”,漢朝賜宮女為其夫人。如此看來,《鄯善王王賜妻使者簡》中的王賜妻很可能就是這名漢朝宮女,而鄯善王應該就是尉屠耆。
喂養馬匹馬虎不得
“□□馬日匹二斗粟、一斗叔。傳馬、使馬、都廄馬日匹叔一斗半斗。”
雖然這段簡牘內容缺少了前兩個字,但總體意思是完整的。該簡屬于律文類,明確規定了各種馬匹每日的飼料類型和數量,其中“叔”通“菽”,指各種豆類。蘇州大學歷史系教授臧知非認為,按照西漢制度,一般的馬匹用料量是每天粟2 斗、菽1 斗,但傳馬、使馬、都廄馬這類官驛用馬的喂料標準比普通馬每日還多出半斗菽,也就是要額外多喂1000 毫升豆子。
對于郵驛系統,馬匹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懸泉置漢簡不但詳細記載了馬的顏色、性別、標記、身高、名號等信息,還專門對不同用途的馬分別制定了飼料供給標準,當時人們對馬匹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從戰國趙武靈王號召全國“胡服騎射”起,古代帝王就特別重視國家的馬匹資源,馬更是被列為六畜之首。《后漢書·馬援傳》載:“馬者,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濟遠近之難。”可見,在冷兵器時代,馬的數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
并非人人都能吃雞
“十月盡十二月丁卯,所置自買雞三隻,直錢二百卅,率隻八十,唯廷給……”
“出雞一隻,以食長史君,一食,東。”
“最凡雞九十枚……”
現藏于甘肅簡牘博物館的19 枚木簡內容相關且字體相同,因而被認定為屬于同一個簡冊。中間的簡文雖有遺漏,但主要內容是完整的。其中一木簡記錄了漢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26 年)懸泉置為招待過往官員所用雞的出入情況。從木簡內容看,前來懸泉置的使者和官員所食的雞皆由效谷縣廷供給。這些簡牘所在簿籍被稱為《食雞簿》,也稱《元康四年雞出入簿》。
研究人員發現,該簿籍中關于雞的量詞有兩種:“隻”和“枚”。有學者認為,“隻”(只)實為“雙”(雙),也就是兩只,“一枚”則代表“一只”;也有學者認為,”一隻”即“一只雞”,“一枚”即“半只雞”。無論哪種說法正確,一隻都對應兩枚。從簡牘記載的內容看,并非所有人都有資格吃雞,在當時,雞只有一定品級以上的官員才有資格享用。

懸泉置簡

懸泉置麻紙碎片
漢武帝派衛青和霍去病北擊匈奴,大獲全勝,致使匈奴主力退守大漠以北,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無法與漢朝對抗。從此,西域諸國與匈奴的聯系減弱,和漢朝的聯系逐漸增強,漢朝和西域的商貿往來也趨于頻繁。
河西走廊是漢朝向西交流的要道,也是漢朝和西域諸國建立外交的重要通道。西域的范圍從陽關以西到蔥嶺(帕米爾高原)以東,昆侖山以北到巴爾喀什湖以南,面積有200 多萬平方千米。
不過,河西走廊路途實在難走,沿途又缺少補給之所。因此,出于為鄰邦提供交通便利的目的,漢朝在河西走廊上設置了許多驛站。漢朝時期,從敦煌到長安的沿途上,除了懸泉置,至少還有淵泉、冥安、廣至、魚離、遮要、敦煌六置,這些郵驛為往來西域諸國和漢朝的公務人員提供歇腳處,提供食物并發揮傳送詔書、公文、戰報等文書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