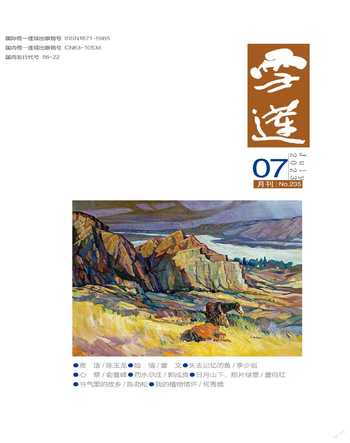日月山下,那片綠意
從我第一次走進湟源峽看到滿山坡的青海云杉、白樺、紅樺和山楊,到2023年4月8日去湟源縣參加“日月山下”歷史文化采風活動,登上高高的石堡城,眺望日月山,走進哈拉庫圖古城,間隔快50年了。50年來許多次從西寧穿越湟源峽,望著山坡上的那片由青海云杉、樺樹和楊樹組成的天然森林,翻過日月山,走向長江、黃河和瀾滄江源頭更大的天然森林,走向柴達木盆地宗務隆山里的祁連圓柏林和梭梭林,多少年來留在心靈深處印象最深的還是日月山下的那片綠色森林和森林掩映下的黃土高原,黃土和森林演繹的悠遠而深邃的歷史文化。
走進湟源的土地,就走近了日月山。日月山不僅有文成公主日月寶鏡的神奇故事,還有非常重要的氣候、地理、生物和文化的標志。不論在史料上,還是文學字眼上,湟源位于中國季風區(qū)與非季風區(qū)的分界線上,地處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疊合區(qū),是青海省內外區(qū)域的天然分界線,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分界線,也是藏文化與漢文化的結合部。而最鮮明的大概要數(shù)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過度區(qū),也就是說黃土高原到湟源,就走到了盡頭。一把黃土在這里沉淀了厚重的歷史文化。面對山坡上那些四季常綠的青海云杉和春天發(fā)芽秋日落葉的樺樹和楊樹,無不使人感覺到湟源還是森林文化與草原文化的分界線。山之西,沃野蒼茫,廣袤無垠的偌大草原宛若碩大無朋的綠色絨毯,從山下一直鋪向遙遠的天際,一群群潔白如云的羊兒蠕蠕而動,仿佛在綠色錦緞上綴滿了顆顆乳白晶亮的珍珠瑪瑙。山之東,山顛覆蓋著終年不化的積雪,似頭戴銀盔的高原衛(wèi)士,山坡上布滿了青海云杉、白樺、紅樺、楊樹、杜鵑、山生柳、金露梅、繡線菊和忍冬等森林灌叢。天然森林與歷史文化的融合,使湟源的歷史顯得更加滄桑而厚重。
湟源——黃土高原的終點
中國的黃土高原是古老的土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黃土高原。在中國北方東起太行山,西北至甘肅省武威市烏鞘嶺,西南至青海的日月山,南連秦嶺,北抵長城的廣袤區(qū)域,成為世界最大的黃土堆積區(qū),面積達64萬平方公里,那厚厚的黃土足有100多米。湟源縣就坐落在黃土高原的最西段。展現(xiàn)在人們眼前的黃土高原的最西段,依然是干旱和荒涼。
昔日的黃土高原并非像今天這樣干旱、荒涼,滿目滄桑。大約在4.6萬年前,黃土高原上從東到西廣泛分布著茂密的森林和迷人的草原。華山松、云杉、圓柏、冷杉、鐵杉、櫟、銀杏等樹種在溫暖濕潤的黃土高原環(huán)境中生長,黃土地上的天然森林遮天蔽日,百鳥鳴翔,群獸游走,充滿著無窮的生機與活力。黃土高原處處是“山上清泉山下溪,窗前竹樹盡扶疏”的美景。據史料記載,在很長一個時期,黃土高原的森林把黃土遮蓋得嚴嚴實實,林木蔽日,林鳥紛飛。秦漢南北朝時黃土高原的森林覆蓋率還有42%,唐末時期減少到33%,明清時期銳減到13%,而解放初期僅存 6%。
后來發(fā)生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使青藏高原因印度板塊的擠壓作用隆升起來。隆升起來的喜馬拉雅山阻擋了印度洋暖濕氣團的向北移動,久而久之,中國的西北部地區(qū)越來越干旱、寒冷。湟水谷地在受喜馬拉雅山影響的同時,北部的祁連山山體抬升和西部的日月山隆起,使湟水流域的氣候更加干旱寒冷,漸漸形成了大面積的干旱草原景觀,在長期的干旱環(huán)境中,森林一天天消失,草原一天天退化,黃土一天天顯露,加之人類不斷向河湟谷地遷移,環(huán)境壓力不斷增大,黃土顯露加劇。
與青海東部的幾個縣相比較,湟源縣是面積較小而峽谷較多的縣,整個縣域被祁連山支脈的大通山、日月山、華石山所環(huán)抱,構成西石峽、巴燕峽、藥水峽“三峽”。受日月山西部青藏高原的庇護,湟水兩岸黃土高坡上的森林較東北部的森林保持得久。隨著高原的不斷隆升,氣候的逐漸干旱,那些喜歡濕潤氣候的樹種華山松、銀杏和遼東櫟等逐漸離開故土東移到中原,而青海云杉、祁連圓柏、樺樹和楊樹們適應干旱寒冷的氣候而遺留在高山峽谷。翻開有關史料,可以看到在距今5000年的民和縣馬家窯文化期的出土墓葬中已用木棺,特別在樂都縣柳灣的齊家文化期1700余座古墓葬群中,不僅大量使用木棺,而且有獨木做的棺材,足以說明當時湟水流域有高大、繁茂的森林。
更值得一提的是,湟源縣大華鄉(xiāng)中莊出土的卡約文化莫布拉遺址,發(fā)現(xiàn)居住房屋4座,房屋結構基本上用直徑10~15厘米的木樁間隔約40~50厘米等距排列楔入地下, 木樁間又用金露梅(河湟谷地的人統(tǒng)稱為鞭麻的灌木)編制成墻體,說明湟水谷地兩岸有豐富的喬木林和灌木林為主的森林資源。
湟水谷地兩岸山坡上茂密的森林為何變成童山禿嶺?這是人類活動與自然變故共同導致的結果!自秦漢以來黃土高原經歷了三次濫伐濫墾高潮,第一次是秦漢時期的大規(guī)模“屯墾”和“移民實邊”開墾。這次大“屯墾”使黃土高原的森林遭到大規(guī)模破壞。第二次是明王朝推行的大規(guī)模“屯墾”,使黃土高原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到空前浩劫。在大力推行“屯田”制中,竟強行規(guī)定每位邊防戰(zhàn)士毀林開荒任務。第三次大墾荒是清代,清代曾推行獎勵墾荒制度,使黃土高原大面積的森林草原被開墾為農田,大面積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加劇。
遠離內地的青海黃土高原的森林也未能幸免這三次大的浩劫。漢武帝時,霍去病向西進軍,湟水流域歸入了漢朝的版圖,大批內地漢族人口不斷遷入,農業(yè)得到空前發(fā)展,對森林的利用和破壞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一直延續(xù)到清朝末年。在湟水流域,漢宣帝時,后將軍趙充國在平定羌人的反抗之后,上書屯田,在湟水流域采伐木材大小6萬余株。趙充國在西寧很短的時間內就能采伐大量的木材并積材于湟水邊上,說明湟水河兩岸有大面積的森林。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李靖和吐谷渾作戰(zhàn)時,吐谷渾采取堅壁清野戰(zhàn)略,焚燒了青海東部廣大地區(qū)的森林灌叢。李素在《西平賦》中描述西寧一帶“木則柳生株萬,松埏丈千。”到了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楊應琚編寫《西寧府新志》時,湟水流域已出現(xiàn)大范圍荒山。修建西寧小峽口河歷橋時不得不“取巨木于遠山”,附近已無森林了。森林線退卻到湟水河主流湟源峽和支流北川河等各支流支溝的上段。
二十世紀初,湟水河流域的森林又經歷了一個大消亡的階段。湟水流域小片林的范圍進一步縮小,湟源一帶原來是“在縣西八十里……連延至日月山,蒼翠可愛”,1919年時還是“林木層層排列如梭……前后引三十余里皆在陰翳之中”。
清宣統(tǒng)二年(1909年)編著的《丹噶爾廳志》記載:“湟源縣響河爾、阿哈吊等處有白楊、樺樹林,拉嘛托亥有柏林。每年伐用數(shù)千株,除修廟宇所用巨材外,民用建筑皆用本地山木。”從現(xiàn)有林木殘跡推斷,這里很早就有豐富的天然森林,城郊鄉(xiāng)的炭窯、和平鄉(xiāng)的曲布炭也是由于當時林木繁多,從事燒炭而得名的。如今僅在湟源峽有小片的青海云杉、白樺、紅樺和山楊等喬木林和金露梅、山生柳、小檗等組成的灌木林。也許是陡峭的山體和湍急的河流保全了這片山林。
湟水谷地的黃土地是一片充滿苦難的土地,從日月山開始,黃土高坡上失去森林和草原植被保護的山體每年有十幾萬噸的泥土要隨雨水東流至黃河,大小黃土山頭每年都要瘦一圈。湟水河北岸許多陽坡上的黃土已經流失殆盡,變成了瘦骨嶙峋的紅土山。
面對一座座童山禿嶺,一代代湟源人盼望著綠色,盼望著湛藍的天空和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飛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在黨和政府的組織和號召下,一代代湟源人用勤勞的雙手把日月山下那片綠色在黃土高坡上一點點地擴大,分布于東峽峽谷的天然森林一直延續(xù)到日月山。川道里一片片、一叢叢人工栽植的青楊、新疆楊、青海云杉和祁連圓柏似一枝枝朝天的綠燭,翠柳葳蕤,綠云密布,田野村舍掩映在綠蔭中。淙淙流淌的湟水河、藥水河波光粼粼,蜿蜒穿行于谷道中。青山綠水在這里成就了一座天造地設的田園詩章。一只只小松鼠在樹枝上盡情地嬉戲,馬麝、馬鹿在林間自由穿行,蜜蜂、蝴蝶在萬花叢中奔忙。
隨著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不斷改善,森林環(huán)境的逐步形成,很多年不見蹤影的大型野生動物開始出現(xiàn)在湟源大地上。2017年11月8日,湟源縣果米灘水電站3名工作人員,在水電站監(jiān)控內發(fā)現(xiàn)水電站的前池內有一只沒見過的大型野生動物在水池中掙扎,可能是池邊飲水不小心掉入池內。工作人員立即撥打110報警電話,并向湟源縣野生動物管理部門報告,同時趕往現(xiàn)場查看。3名工作人員趕到水池邊時看到這只野生動物的頭在水池中時隱時現(xiàn),水池四面光滑,野生動物拼命掙扎也跳不出水池,有隨時淹死的危險,3人合力將其從水池內救起。湟源縣森林公安局和縣野生動物管護站工作人員聞迅趕到現(xiàn)場后,發(fā)現(xiàn)以前在湟源境內尚未見過此種野生動物,就聯(lián)系省野生動物管理部門和青藏高原野生動物救護中心。專業(yè)人員趕到現(xiàn)場后,經鑒定確定為中華鬣羚。中華鬣羚也叫蘇門羚,屬牛科,是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體長可達140至190厘米。外形似羊,兩耳狹長似驢,角像鹿不是鹿、蹄像牛不是牛、頭像羊不是羊、尾像驢不是驢,人們據此將其稱為“四不像”。中華鬣羚平常棲息于針闊混交林、針葉林或多巖石的雜灌林。可能是茂密的森林吸引著中華鬣羚來湟源安家落戶。救護人員檢查中華鬣羚無病無傷后,在大黑溝天然林區(qū)進行了放生,中華鬣羚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中。
2022年7月1日,有關部門在開展野生動物多樣性調查研究時,紅外相機影像資料發(fā)現(xiàn),在日月藏族鄉(xiāng)海拔4096米處發(fā)現(xiàn)了青海旗艦物種、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雪豹的活動影像。這是在湟源縣境內首次拍攝到雪豹影像,為青海省生物多樣性提升和豐富雪豹在青藏高原的分布區(qū)提供了依據。紅外相機在同一區(qū)域內還拍攝到馬麝、荒漠貓、石貂和藏雪雞等多種珍稀野生動物。其中,馬麝為瀕危等級物種,荒漠貓為易危等級物種,二者都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石貂和藏雪雞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東峽里的那片天然森林
湟源縣東峽里的那片森林是我最早看到的長在山坡上的松樹和樺樹。話還得從49年前說起。1974年7月的一天,臨近小學畢業(yè),我乘坐叔父開的拉煤的汽車到離村8公里外的公社照相館去照畢業(yè)證書上用的照片。那時故鄉(xiāng)所屬的平安只是一個公社,屬湟中縣管轄。公社只有一條街道,只有一個照相館。那天照相館恰巧不營業(yè),叔父知道我第一次離家這么遠,一個人怕走丟回不了家,就說干脆跟我去湟源送煤吧。就這樣我又坐上了叔父的煤車。這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門,走出山村。汽車在寬闊的柏油馬路上奔馳,經過小峽來到西寧城,我張著嘴驚奇地看著眼前一座座高樓大廈。
離開西寧,又是村莊和田野,汽車向前行使,一個個土黃色的村莊和一片片金黃色的麥田交叉著向后退去,汽車進入一個兩山緊緊相連,把河水和公路擠在一起的峽谷。叔父說:“快看那山上的森林!”我急忙向車窗外張望,峽谷兩岸的山坡上布滿了密密麻麻的樹。第一次看見這么多樹長在山坡上,那些樹也與故鄉(xiāng)田野里單一的青楊樹完全不一樣,有的是翠綠色高大偉岸的松樹,有的是淡綠色的婷婷玉立的山楊,還有婀娜多姿的白樺和紅樺。車在峽谷里走得很慢,我仔細欣賞著那滿山遍野的森林,仿佛進入了一個美麗的童話世界。那山坡上還有一條鐵路橫穿森林而過,一會兒是架的高橋,一會兒又挖的山洞。布滿森林的山坡與公路間夾著一條河流,河水清澈而湍急,叔父說那條河流叫湟水河。那森林和半山腰中的鐵路,還有那條歡騰的河流一直陪伴我沿著大峽谷走了很久才與大山一起消失在視野中。
湟源峽的那片森林給我少年的心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那片綠色時常出現(xiàn)在我的夢里。可喜的是5年后我上了林業(yè)學校,畢業(yè)后在省城從事林業(yè)工作近40年,每年不知多少次要穿越湟源峽,翻過日月山,走向玉樹,走向果洛,走向長江、黃河和瀾滄江源頭的原始森林,走向柴達木盆地中的梭梭林和胡楊林。然而留在我心中最深最美麗的還是湟源峽中的那片森林,因為那里留下我少年時對森林最初的記憶,我長大從事林業(yè)調查規(guī)劃工作后,親手把這片森林中的大黑溝規(guī)劃為森林公園。
湟源名字的來歷從字眼就看出是湟水源頭的意思。湟水河是黃河的一級支流。這是一條從青海湖北側祁連山脈流淌出來的小河,它趟過青海湖邊的草原,吸納上百條草原山澗支流, 在日月山下匯聚成滾滾河流,穿過55公里的高山峽谷。這里山高水長、坡陡崖峭,地勢險要。峽谷兩側,群山崔嵬,峰巒兀立,高山相峙,峭壁千仞。綿延的群山上,林海漫漫,萬木崢嶸。這條峽谷人們稱湟源峽。其實湟源峽只是個俗名,峽谷兩端的人因對其相對方位的不同有異樣的稱呼。西寧人因峽谷在西寧西邊且又是石峽,就叫西石峽,而湟源人因峽谷在縣域的東邊叫東峽,并在那里設了一個東峽鄉(xiāng)的建制。沿著彎彎曲曲的青藏公路走進峽里,只見兩山犬牙交錯、陡峭險峻,谷中湟水湍急,青藏鐵路、青藏公路率先占據有利地形,把西湟一級公路擠到了半空和山中。北山有名稱北華石山,南山叫照壁山,兩山森林密布,風景秀麗,特別是風景秀麗的大黑溝早在1996年就成為森林公園。
大黑溝是湟源峽中的一條支溝,溝內分三岔:即西岔、三岔、石峽三溝,溝縱深15公里,總面積3萬多畝。溝口是青藏鐵路跨湟水河的第二大橋,橋高50余米,長200米,遠遠望去,大橋猶如森林公園的天然大門,使森林公園一開始就體現(xiàn)出宏大的氣象。走進溝中,同樣是兩山夾峙的窄溝,沙路和溪流占據了整個溝谷,路和溪流相互交錯,蜿蜒延展,那溝寬不過五六十米,山高卻在千米以上。從溪畔路旁到懸崖峰顛,翠嫩蔥郁的森林將山崖峭峰遮蓋得嚴嚴實實,偶而露出沒有植被的怪峰奇石,更增加了一份神秘感。走在溝中,猶如走進了一線天,即使天氣晴朗的日子,也感覺到陰森幽暗。
森林公園中豐富的高原植物以不同的形態(tài)和顏色裝扮著大黑溝。山坡上阿娜多姿的白樺盡情展現(xiàn)著自己的風韻,挺拔秀麗的青海云杉在懸崖峭壁上扎根生長,青楊在較寬闊平坦的溝谷中悠閑地搖曳;在沒有喬木的地方,各類灌木按自己的方式占據空間,以不同的葉形和花色點綴著公園。在山上高寒地帶是高山柳和杜鵑,在漫長的冬日里,杜鵑和青海云杉用特有的綠色裝扮著寂寞的山林。在遲來的高原晚春五月中下旬,萬木復蘇,爭吐新翠,繁花似錦,一片片草地像綠地毯一樣鑲嵌在萬木叢中。紫紅色的杜鵑花開滿山坡,給寂寞的山林帶來春的氣息。盛夏季節(jié)走進大黑溝,就像走進一個清涼的綠色世界,那無邊無際的森林,隨著崗巒起伏,猶如大海的波濤,綠蔭濃郁、蒼翠欲滴、鳥語花香、姹紫嫣紅、松濤澎湃。點綴在山坡上的花草灌木種類繁多,常見的有多種杜鵑、華西忍冬、金露梅、銀露梅、秦嶺小檗、甘蒙錦雞兒、北方枸杞、扁刺薔薇、峨眉薔薇、天山花楸和陜甘花楸等。秋天的大黑溝是五彩繽紛的世界,漫山紅葉溢金流彩,簇簇紅葉中,金黃的樺樹葉、淡黃的山楊葉,黛綠的松針融在一起,色彩斑斕,景色旖旎;深秋和寒冬瑞雪飛舞,山坡銀妝素裹,石峰白雪皚皚,懸崖冰川倒掛,冰凌瓊花。
最早開花的灌木是天山花楸和陜甘花楸。它們是薔薇科花楸屬高大的灌木,在土壤肥厚、雨水充沛的陰坡上可以長成四五米高的小喬木,在森林公園中除青海云杉、白樺、紅樺、山楊外算最高大的樹木。花楸性格孤僻,在山坡上總是零星地分布。五六月,枝條上密密麻麻的復傘房花序開出一朵朵白花。在開花季節(jié)兩種花楸都開著潔白的花朵,很難辨認那個是天山花楸,那個是陜甘花楸。到了中秋,天山花楸結出鮮紅色的球果,而陜甘花楸結出白色的球果。
薔薇科薔薇屬中的灌木峨眉薔薇和扁刺薔薇也顯得異常神奇。在沒開花前它們也長得很相似,枝條上布滿密密麻麻的皮刺。五六月在布滿刺的枝條上開出白色或粉紅色的花朵,開白色花的是峨眉薔薇,開粉紅色花的是扁刺薔薇。人們把這兩種薔薇都叫刺玫花。到秋天,枝頭的果實長到小拇指頭尖大小的圓球形紅色果實。從果實顏色上又難以區(qū)分哪株是峨眉薔薇,哪株是扁刺薔薇。仔細觀察峨眉薔薇的果實是卵球形如梨,扁刺薔薇的紅果呈長圓形,尖端有微彎曲的短頸,酷似鴿子嘴。到了秋天,扁刺薔薇的名字就由刺玫花變成鴿子嘴了。
森林公園中的草花更是五顏六色。被譽為中國三大高山名花的除灌木杜鵑花外,草本的報春花、龍膽花在這里廣為分布。每年五至九月期間,各種山花漸次開放,燦若繁星的報春花、龍膽花、川赤芍、金銀花、各色馬先蒿爭相吐艷,置身其中,仿佛進入花的海洋。
森林公園中生長著許多名貴中藏藥材,如冬蟲夏草、大黃、柴胡、白芍、黃芪等,種類達240多種。
在林間草叢中經常出沒的野生動物有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白臀鹿、荒漠貓、金雕、胡兀鷲等、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有猞猁、狼、 中華鬣羚、赤狐、豹貓、石貂、兔猻、藍馬雞等,常見的省級保護動物有狍、香鼬、環(huán)頸雉等。許多野生動物在銷聲匿跡多年后隨著人類對動物保護意識的提高和森林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恢復,又回到了昔日的家園。
相傳,文成公主進藏路過此地,清澈的溪水、百鳥的歡歌、秀麗的風景令其駐足,并在大黑溝留住數(shù)日,從此大黑溝聲名遠播,吸引游人紛至沓來。
沿溝一路走一路看,山峰競聳,層巒迭嶂,有的單峰獨立,有的數(shù)峰相連,有的寸草不生,有的竟在禿禿的峰尖上點綴了云杉或白樺,風采多姿,爭奇斗妍,成為供游人觀賞的景點。較為出名的有照壁石、大廚房、黑鷹峰、千噸方臺石、石門爾、白土窟、松樹灣、大小蒜窩捶石、上下夾道、千丈羅圈崖、七層巖、尖崛石、夫妻巖、望郎峰等。
位于公園北的華石山,山頂?shù)囊蛔质⒍啥础⒋笤罨稹⑹釆y石、夫妻石、七層崖、佛兒崖、天外三峰等景點,巨石磊疊,嘆為觀止,布滿周圍山坡的石頭如同仙人牧羊,蔚為壯觀。
登上最高的峰嶺,峰上挺立著一塊上薄下厚的巨石,名曰“照壁石”,因正對西寧古城的大西門而得名,在晴朗無云的時候可看到西寧城。離開“照壁石”穿過一片草地就到了“大廚房”。“大廚房”是由許多塊巨石天然堆起的大石堆,石堆的一個大縫隙中可容數(shù)人居住。在一塊巖石上有三個坑,一個像鍋,一個像勺,另一個像盆,傳說都是二郎神放炊具的印痕。奇石怪峰可由人們隨意想象。
2013年9月11日,國家地質調查部門及青海地質部門等權威部門實地勘察,經鑒定,大黑溝低海拔冰川遺址是在祁連山地區(qū)海拔3500米處較為罕見的“古冰川”遺址。古冰川遺址中的冰斗,冰脊,冰舌,冰礫以及冰臼等能夠體現(xiàn)冰川遺址特點的景觀一應俱全,具有極佳的自然教育價值,這不僅是人們認識自然的極好課堂,也是地質教學的實地教材。
位于冰川遺址南坡的高山杜鵑園,每年七月初,千畝王母花圃杜鵑怒放,金露梅以及各種山花也爭奇斗艷,整個南坡美不勝收,將大黑溝森林公園的植物多樣性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在森林公園中有隴蜀杜鵑、百里香杜鵑、頭花杜鵑和裂香杜鵑等。杜鵑是森林公園中唯一的常綠灌木,每年五六月, 沿山坡自下而上,紫紅、淡黃和純白的三色杜鵑依次盛開,形成一個個色彩各異的花帶,持續(xù)月余。隴蜀杜鵑因其花形碩大、花色純白、潔凈素雅、氣質非凡而受到人們的追捧。
石堡城遺跡上的遐思
2023年4月9日早飯后,采風人員來到日月鄉(xiāng)的大茶石浪村。這次采風的10多個作家和攝影家分居在日月藏族鄉(xiāng)的4個村莊中,今天3個村的文友們不約而同地相遇在大茶石浪村。大茶石浪村已于2017年整體搬遷到日月藏族鄉(xiāng)鄉(xiāng)政府所在地的兔爾干新型農村社區(qū),昔日的一副副土莊廓組成的村莊還在。部分莊廓成為牛羊養(yǎng)殖戶的畜圈,有的門虛掩著,里面有圈養(yǎng)的牛羊,有的牛羊到山上吃草去了,門敞開著,滿地的牛羊糞。大部分莊廓的門都由“鐵將軍”把門。許多土墻上還隱約可見在“文革”那個特殊時期書寫標語和語錄的一個個土坨圈,我駐足在土墻前,想辨認出每個土坨圈里的字,但一個字都沒認出來。經過50多年的風吹日曬,字跡已難以辨認,只看到每個土圈的白底上用紅漆寫字留下的斑駁痕跡。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fā)展,特別是經過新農村建設,河湟谷地黃土夯筑的土莊廓墻上的標語和語錄連同那土墻都已消失了,只有在偏僻的山村還能看到。土墻上的標語和語錄成為那個特殊時期的標志,逐步消失在歲月中。
看完大茶石浪村搬遷后的遺址,大家一致提議去看看石堡城。陪同我們的大茶石浪村書記祁如忠抬眼看著我們這些由老人、婦女,還有雖年輕卻天天在辦公室上班的城里人組成的采風隊伍,抬手指著村西南遙遠的山峰說,石堡城就在那個山尖上,坡陡無路,你們上不去,遠遠地看看吧!大家齊聲要求去現(xiàn)場看看,能上去幾個算幾個,走不動的走到哪里算哪里。來湟源參加采風活動前,作家攝影家們搜集了大量的反映湟源歷史文化的史料,知道石堡城是唐與吐蕃龍爭虎斗過程中的戰(zhàn)略要地,在唐代歷史上多次驚心動魄的戰(zhàn)斗中,這里是重要的軍事要地,如今談起湟源的歷史文化,人們總要談起石堡城。
匆忙中看完土墻上的標語和語錄時,同伴們的車已不見蹤影,急忙四處搜尋,忽見左側的田間路上有車的新印痕,追了不遠看見前方飄飛的塵土,知道沒走錯路。汽車風塵樸樸中來到莫多吉村東大山山下,時間已是9點40分,除兩位腳穿皮鞋的女士遺憾地在山根轉了一圈外,其他的人開始爬山。祁書記經常在這里放羊,熟悉爬山的路徑,帶領我們沿羊腸小道爬行。他說他小時候放羊時山坡上有一條當年石堡城的守兵留下的小路,現(xiàn)在已看不清了。走了一段路,大家都開始散開選擇自己的路,坡上坡下都有爬行的影子,爬得最快的年輕詩人曹誰已到半山腰,興奮地對著手機不停地演講,告訴群里的人自己正走向石堡城。把做好的視頻即刻發(fā)到不同的微信群,顯示出詩人的激情。60歲出頭的王衛(wèi)華也不甘示弱,一會沿著山梁,一會走進小溝,緊跟在曹誰后面。神秘的石城堡吸引著作家和攝影家們喘著粗氣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一邊爬一邊留意山坡上的植物,雖然已是4月上旬,山坡上看不到一絲綠意,只看到一些灌木。最多的要數(shù)河湟人叫鞭麻的銀露梅,走幾步就能看到一叢,高度不到一米,枝叢卻密集,仔細看枝條上的葉芽已開始萌發(fā)。被河湟人稱為胡爾條的高山繡線菊,分布比銀露梅稀少,高度也只有五六十厘米,稀稀拉拉的幾根枝條總是直直向上。分布稀少,個頭矮小而枝條密集,枝條密生針狀刺的是貓兒刺,學名叫短葉錦雞兒,葉片沒長出來,枝刺更加明顯,讓人望而卻步。在河湟谷地很長的歲月里,供銷社里還沒有從南方運來的竹筷子賣的時候,人們吃飯的筷子都是用胡爾條做的,洗鍋的刷子是鞭麻做的,每年臘月二十四用貓兒刺扎的掃把打掃廚房。鞭麻、胡爾條、貓兒刺是河湟谷地分布最多、與人們的生活最密切的植物,可它們喜歡生活在高海拔、濕度大的腦山地區(qū)陰濕的森林環(huán)境或靠近森林的山地。
邊走邊說笑,偶爾聽到走在最前邊的詩人曹誰對著手機的激情演說,不知不覺時間已過11點,大家一個不落地爬到山頂。站在山頂上看,東、西、南三側都是懸崖絕壁。祁書記給我們介紹,我們腳站的地方就是大方臺,地形微有起伏,歲月已將建筑痕跡變成布滿荒草的山體,經祁書記比劃和講解,在不太平的山脊中隱約看出有房基遺址,皆為正方形,七間房連在一起,隨地形每間房大小不一,有的約5米見方,有的約7米見方。大方臺北端有一座殘缺不全,邊長約3米、高3米的夯土筑瞭望臺,也有人說是點將臺或烽火臺。站在大方臺遠眺西邊,日月山上的日亭、月亭盡收眼底。感覺腳下的山尖與日月山頂一樣高,看看手機上的海拔高度是3338米,而日月山口的海拔是3520米,也許是距離產生的視覺誤差,給人的感覺是兩山一樣高。
小方臺在山脊的西北邊,中間由一條狹窄的山梁相連,山梁上有一條約30厘米寬的小道可以走向小方臺,山脊的左側是一看就眩暈的萬丈懸崖,右側是陡險的山坡,大家互相鼓勵著走過小徑。小方臺地勢明顯低于大方臺,但地勢較平。史料記載小方臺上散布有瓦片。我們睜大眼睛希望能撿到一塊瓦片,曹誰還希望能撿到一枚唐代“開元通寶”,結果只有一位文友撿到一塊不及半個巴掌大的灰色瓦片,大家圍攏過來爭著看。瓦片證明了此地確實有過建筑。
山坡上依然長著銀露梅、短葉錦雞兒和高山繡線菊。我試圖能在山坡上看到一樁腐朽的青海云杉或樺樹的樹根,或一眼當年供守兵們飲用的清泉,都沒有見到。但我猜想,當年的石堡城一定是掩映在青海云杉和樺樹組成的天然森林中,森林里有自由漫步的馬麝,樹枝上有吃飽了歇息的藍馬雞,草坡上有成群覓食的巖羊,森林邊有一眼汩汩冒水的泉眼。一切都遠去了,只有這些灌木和花草們還實實在在地長在山坡上,年年歲歲陪伴著石堡城遺跡。
【作者簡介】董得紅,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青海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出版散文集《行走在江河源》 《江河源拾韻》 《綠意柴達木》 《江河源隨筆》等。獲得第八屆青海文學藝術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