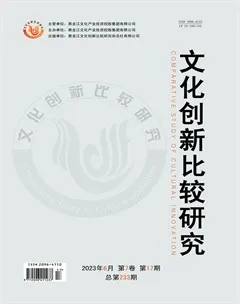林芙美子《放浪記》對日本都市化進程中女性的書寫
尹小娟
(長沙學院,湖南長沙 410022)
都市化是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也是工業革命的伴生現象。18 世紀末到19 世紀中期的英國工業革命對英國乃至整個世界的都市化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的都市化進程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創立的江戶時代。江戶時代的太平盛世,不僅使得日本全國的經濟實力大幅上升,還使得日本民眾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不再受溫飽問題困擾的民眾開始有剩余的精力和時間去發展文藝活動和商業活動等,逐漸形成了極具日本特色的原生城市文化——城下町文化。但日本真正進入都市化發展卻是從明治維新開始,明治維新提出了不少有利于發展資本主義的改革措施,使日本由一個落后的封建統治國家轉變成獨立的資本主義強國。得益于城下町文化的基礎,資本主義化的日本就像一輛裝了加速器的火車一樣,以驚人的速度推進都市化發展[1]。
大正時期,伴隨著各種工廠建立,日本的都市化進程進入了一個發展的高峰。日本人口從明治初期的大約3 300 萬增長到大正末期的近6 000 萬。這些新增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從事非農業的工作。大城市的住宅也蔓延到了近郊,電車和巴士的線路也開始延伸到城市的每個角落。以東京為首的大城市開始興建其鋼筋混凝土的高層公用建筑,個人住宅也開始流向西洋風格,瓦斯、水道和電開始在農村普及。在這期間,一身西服早出晚歸的日本的會社員也開始出現,一些受過教育的女性也開始進入職場,社會呈現出一副欣欣向榮的景象。
“都市文學”的出現離不開現代大都市的崛起和都市意識、都市文化的誕生。因為工業革命引起社會生產力驚人的飛躍,人口與資本向著城市大規模轉移與聚集,城市的數量、規模、形態與功能因此而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2]。自20 世紀60 年代以來,都市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在綜合不同城市記錄的文本資料的基礎上較為全面地研究想象的都市,打破了純文學研究視域的限制[3]。進入后工業化階段、信息社會以后,作家們開始認識到都市的多面性,文學對都市也不再一味拒斥、批判,而是“有憎恨也有歌頌,有拒斥也有擁抱”[4],情感取向和價值態度呈現出多元化特征。社會的發展必然是伴隨著陣痛的,在都市化進程中,人們在享受現代化都市種種便利的同時也面臨著不斷出現的矛盾和沖突,如對故土的眷戀、對都市生活的不適應、對自身境遇的無奈等。事實上,在日本也有很多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刻畫和記錄了都市化進程中的各色人物及他們的人生,呈現出都市化過程中的世間百態。
1 《放浪記》與新女性的出現
《放浪記》是林芙美子的第一部日記體自傳長篇小說,也是林芙美子初登文壇,確立其作家地位的第一部代表作。《放浪記》在最初長谷川時雨主辦的文學雜志《女人藝術》上以連載形式發表,1928 年,經過五、六次連載后好評如潮,于1930 年正式單獨出版,一經出版就立即成為當時最暢銷的作品。《放浪記》是林芙美子立足于自身的經歷,以記錄日常生活的日記為原型,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描寫了8 歲時離開故鄉和母親及養父一起四處漂泊放浪的經歷,成年后在都市化大浪潮下,獨自一人來到東京。作品自然如實地描繪了主人公“我”長達10 年掙扎于大都市東京底層的生活經歷與情感歷程,擺過地攤,做過女傭,在小酒館中當過女招待,還先后遭到數個男友的折磨與拋棄,飽嘗人世艱辛與屈辱。在饑饉困苦的境地中仍不甘沉淪,始終抱持粗率而真誠的生存態度,堅守文學夢想,直至迎來生活與創作的轉機。可以說《放浪記》既書寫了都市化進程中都市女性強烈自我意識的覺醒,作者對自由的無限憧憬和渴望,同時也勾勒了為女性提供各種各樣的職業,還為作家、畫家、詩人、演員、記者聚會提供空間的大都市東京。
《放浪記》 中主人公追隨初戀初次來東京是在1922 年,當時的日本剛經歷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出現的大戰景氣。1915 年后歐洲各交戰國停止出口,并且需要大量軍需物資,大批消費物資和軍需物資的訂貨涌到日本。日本對曾是歐洲各國出口市場的亞非各國的輸出也急劇增加,其經濟出現空前繁榮。工廠林立,地方的年輕人懷揣著夢想來到東京。據日本人口普查,1920 年的東京市人口為217 萬,1932年為575 萬,就是在這高速發展的都市化過程中,林芙美子來到東京,成為都市中新女性的一員。正如學者川本三郎在《林芙美子的昭和》中說道:“我們不應該僅把林芙美子當作以前所謂的貧窮的文學少女,更應該從生活在現代都市中的自由人的角度來理解她的文學。”[5]
2 都市化進程中的女性自由書寫
自大正時期開始,女性的新行業接二連三出現,雖然這些女性大部分都是為了糊口而選擇新職業,并非真的想獲得女權,但比起視女子為無能者的明治時代,女性能從事新行業已經算是一大進步。關東大地震之后至昭和初期,東京出現了一群短發短裙形象的女性,她們在眾人的注視下昂首挺胸走在繁華的東京街頭。這些大都市新女性的數量并不算多,但她們探索新的生活方式,追求新的時尚潮流,實現自我價值。她們喜歡體育,愛好音樂,擅長繪畫,主動挑選男人進行自由戀愛,她們自由且充滿智慧。女人視她們為榜樣,男人卻視她們為危險的存在。此時新女性的職業非常多樣化,如打字員、售貨員、電話轉接員、服裝設計師和演員等。
2.1 女性的獨處空間自由
在《放浪記》中,主人公“我”雖然貧窮,但好歹有一份可以養活自己的工作,在快速發展的都市東京能半夜出來喝酒、吃宵夜,享受在鄉村不可能企及的自由。
“淺草是個喝酒的好去處。淺草也是個醒酒的好去處。五分錢一杯的甜酒,五分錢一碗的湯粉,還有兩分錢一串的烤雞。這些食品令人輕松愉快。小戲屋的旗幡隨風擺動,猶若一條金魚。”
大都市為所有奔赴而來的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生活空間。即使是出生在小地方、無學歷、貧窮的女性,大都市也能提供不需要學歷的工作、低價的廉租房。林芙美子幼年父母離異,之后跟隨母親和繼父輾轉于北九州一帶行商,早期的生活很少有定居的時候,大部分浪跡于各個地方。對于這種生活,母親的解釋是“你爹他不喜歡家,不喜歡家具……”反而是到了東京之后,薪水雖然微薄,住所雖然是便宜簡陋的廉租房,但終于有了自己的容身之處,這是只有大都市才能為底層女性提供的。正如伍爾夫在著名的《一間自己的房間》里面說的,女人想要寫小說,她就必須有錢,還得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6]。女性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也就有了獨立思考的空間,這為女性提供了生存上的自由空間。有了它,才能有時間書寫思想上可能產生的價值,否則,一切創造力都會被生活腐蝕。唯有在這種封閉的空間里,女性才可能潛思默想,收心內視,清理自身異己的經驗內容,打撈自己的女性經驗,尋找那種業已稀疏的已經被社會理性層面掩蓋和遺忘的東西[7],東京為林芙美子提供了這樣的一個場所。
“借著鋼筆店老板的燈光,閱讀我的 《蘭德之死》。我大口呼吸,已能感覺到春天的氣息,春風之中似乎包藏著久遠的記憶。柏油馬路上是燈光的河流、人類的洪水。瀨戶特產店門前,落魄的大學生在賣計算器。”
這里描繪了都市化進程中都市的一個典型畫面,像河流一樣流淌的燈光,像洪水一樣擁擠的人群,坐在小小店鋪里的“我”雖然在都市中只是一顆微小的塵埃,但這顆塵埃卻能夠有一個地方容納它。相反,熟人社會的鄉村,雖然個體有一定的存在感,但卻不能擁有自己私人的“空間”,更別說用這個空間來讀《蘭德之死》。因此,在東京雖然仍然過著不富裕的生活,但“我”能感覺到春天的氣息,這其實也是自由的氣息。
2.2 女性的社交自由
都市能把個人從人群中孤立出來,同時也制造了許多相遇。1924 年,林芙美子在東京白山的南天堂遇到了一些達達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朋友,在和他們的交往中,她思想上受到很大的沖擊,對社會、政治和生活的思考更加深入。她的文學創作不再局限于廉租房里,她開始出版自己的詩歌。
“今天,《都新聞》又刊出了我的詩作,那是寫我舊日戀人的作品。算啦,別寫這種詩啦。沒勁。努力學習吧。應當寫出更好的詩歌。傍晚時分,我去了銀座的松月咖啡館,這兒正在舉辦新人詩歌展覽會。我那拙劣的字體居然堂皇地擺在前端。我還見到了橋爪氏。”
如此,林芙美子在東京開展自己的文學創作的同時,結交了眾多文藝圈的好友。在20 世紀30 年代,咖啡館作為家、公司之外的第三空間開始興起。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喜歡在那里聚會,交換各自的思想,從小鄉村來到東京的林芙美子也在這里開始廣泛吸收之前未曾接觸的思想。另外,在都市自由氛圍、年輕人開放的思潮中,林芙美子也逐漸擺脫了既有的性道德束縛,先后與男演員、詩人等不同男人自由戀愛。在歌頌新型男女關系的俄羅斯社會文化和倡導女性自由的美國文化的影響下,年輕貧窮卻自由奔放的林芙美子可以說是日本新女性的代表,這與大都市的包容性分不開。
3 都市化進程中的女性困境書寫
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千百年來,女性作為被規訓、被壓迫的對象,大部分時間保持著麻木沉默的狀態。在父權制家庭里面,她們是逆來順受的女兒,是任勞任怨的妻子,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家庭里,都沒能擺脫男性附屬品的身份。《放浪記》中描寫的女性,即使在大都市東京有了自己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比農村的女性獲得了更多的自由,但依舊面對著一直以來的困境,如彷徨、貧窮、孤單等。
3.1 女性的貧窮困境
初到東京的“我”找工作不順利,四處碰壁后勉強接受了一份本不愿做的女傭工作,在從雇主家回來的路上,開始對東京的生活充滿失望。
“寒風中商店的紅旗呼啦啦飄動。人種不同人情也不同,還是找份其他的工作吧。我沒有去乘電車,獨自走在壕溝邊沿。此時我不由得產生了想回故鄉的念頭。這樣子漫無邊際地徘徊在東京,到頭來也不會有任何結果。一列電車疾駛過而來,我想到了死。”
在《放浪記》中,女性雖然有工作,但這些工作大都為女招待、打字員、電話轉接員等不需要學歷的低等職業,薪水自然也微薄。然而作為家中聽話的女兒,即使在她自身難保的時候,還是承擔著一大家子的生活。當父親來信說遇上連陰水澇,過著饑不果腹的生活,“我”只好聽母親的話,把花瓶里藏著的十四元錢全部寄過去。不敢違背父母的命令,不僅拿出所有的積蓄寄回家,甚至在沒有積蓄時會提前預支薪水寄回家。貧窮讓她在繁華的東京步履維艱,讓她在東京站的廣場上邊流淚邊喊出“信徒呀!真的有救世主嗎? 遠遠地傳來救世軍的軍樂聲。什么叫做信仰呢? 我什么也不相信。不論是基督耶穌還是釋迦牟尼,貧窮的人們哪有時間去信那些”。林芙美子在12歲就輟學跟隨父母做生意,沒有接受教育的她卻有一個文學的夢想,在東京,光鮮亮麗的摩登女郎隨處可見,林芙美子雖與她們生活在同一個大都市,但因為貧窮,兩者之間有著不可跨越的鴻溝。
3.2 女性的孤單困境
除了貧窮,都市中女性面臨的另一個困境就是“孤單”。《放浪記》第一句就說到“我是宿命論的放浪者,沒有故鄉”,但也許正因從小四處漂泊,林芙美子對故鄉的渴望和依戀更加明顯,尤其是在東京舉目無親、遭遇不公時,這種孤單、自怨自艾的情緒書寫尤為深刻。
“好容易混到了下班,出門已是將近1 點。不知是不是店里的時鐘慢了,市內的末班電車早已過去。我算了算由神田至田端的路程,悲哀、失望地坐在地上。街燈一盞盞熄滅,像鬼火。沒有辦法,我只有上路。但是心中卻惴惴不安。走到上野公園,我已經精疲力竭,走不動了。夜里的涼風裹著雨氣,將我的舊式發型兩鬢吹拂得像鳥翅一樣呼扇。我凝視著忽明忽滅的仁丹廣告燈,茫然地瞅瞅大路。不管是誰,難道真的無人與我相伴?”[8]
“炒栗子的聲音標示著令人懷戀的時節。這是花柳巷那邊栗子店里傳出的微弱聲響。我待在昏暗的屋子里,孤零零盯著窗戶,心中產生了某種奇妙的寂寞之感。……轉眼之間,人生過半。在這羈旅他鄉的天空下,在這寂寥難耐的酒吧二樓,有時也犯牙疼。每逢此時,我便想起了故鄉的原野、山河和大海,想起那闊別日久的故人們。”
都市化對于女性個人來說,是一個空間移動、職業選擇和社會身份調整的過程,但對于社會而言,它是一個社會經濟系統轉換的過程。特別是一直以來困在家庭內部的女性,要脫離長期構筑的熟人社會,在陌生人群中重新開始謀生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換句話說,都市并非處處充滿希望、機會和選擇。女性從無工作到獲取就業機會,甚至要在都市安居下來,在這之前,她們要經歷長時間的漂泊和孤寂,要面對種種生活難題和意外風險,甚至還會被歧視為“鄉下人” 或飽嘗他者精神折磨和身心無處歸依的悲苦。
4 都市化進程中的女性希望書寫
《放浪記》描述了一個年輕女性面對饑餓、屈辱不斷威逼的困苦境地,但林芙美子并沒有沉溺于這種困苦的境地,而是以粗率幽默的筆致,從這貧窮艱難的生活中尋找希望。《放浪記》之所以多年來深受年輕讀者喜愛,與林芙美子在作品中傳達的積極生活的信念有很大關系,只要世界上仍舊存在著貧窮、屈辱和青春,喜愛《放浪記》的讀者就不會消失,這部獨特的青春之作,也的確曾對昭和初期的日本青年男女產生過十分積極的影響,即使在“自我”生存的暗郁環境中,仍然給予了他們追尋夢想的力量。林芙美子自己也在述及《放浪記》的創作動機時承認,在創作《放浪記》時根本沒有想到當什么作家,只是信筆由韁描述了傾吐不盡的內心獨白,忍不住一直不停地寫了下去。《放浪記》的寫作使她感覺異常充實,使她忘記了男人的拋棄、身無分文和饑腸轆轆。可以說,《放浪記》 在進行女性困境書寫的同時也進行了女性希望的書寫。
初到東京毫無門路的“我”經人介紹租到一個門面開店,于是到處托人幫忙,在日記中寫道:
“在東京我無親無辜,哪管什么厚顏無恥。東京是一個色彩紛呈的世界。一無所有便要拼命工作,想到在那惡劣環境的點心廠工作的經歷,眼下的困難還算什么? 我的心境不由地好轉起來。”[9]
“一無所有便要拼命工作”,這句話幾乎可以概括所有從鄉村來到都市的女性的生活。這句話乍一看是理所應當不容置疑的,但是放在都市化進程的社會中才能感知到,這并不是那么的“理所應當”。在社會現代化之前,就女性來說,拋頭露面出來工作是罕見的,更不要說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潛藏的不公平,“拼命工作就會成功”像是一個美麗的謊言。只是隨著都市化進程的發展,社會特別是都市變得更為包容了,女性才獲得了稍微多一點的生存空間。
“總算集腋成裘,有了一點點存款。于是破天荒做了一次日本發型。日本發型真美。圓形的發髻緊繃繃的,把眉毛都吊了起來。發式的兩鬢柔潤黝黑,前額的劉海兒攏上去后,蓬蓬地垂于額頭。我面目全非,居然變成一個美人。我對著鏡子直打媚眼,鏡子也對我投桃報李。做了這么漂亮的發式,我就想出外走走。我想乘上火車去很遠很遠的地方。”
在終日為生存奔波之余,“我” 仍然不曾忘記打扮來取悅自己,這是林芙美子最根本的生活哲學。事實上,不僅是打扮自己,在《放浪記》中,主人公“我”常常用美食獎勵自己或者安慰自己,都市實現了這種女性對自我的肯定,她們可以隨時踏入美容院,甚至可以半夜出來喝酒,在容光煥發之后、醉后一覺天亮之后,重新面對車水馬龍的都市。事實上,像林芙美子這樣的都市女作家在書寫女性時,往往認可自己的性別身份,力不勝任但頑強地撐起一線自己作為女人的天空; 逃離男性話語無所不在的網羅,逃離、反思男性文化內在化的陰影,努力地書寫或記錄自己的一份真實,一己體驗,一段困窘、紛繁的心路;做女人,同時通過對女性體驗的書寫,質疑性別秩序、性別規范與道德原則[10]
5 結束語
對都市化的解讀,往往是遵循男性視角,女性一直處于被冷落、被忽視的地位。都市為女性提供就業及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隨著都市化出現的“公寓”,也為單身女性提供了一塊“自己的小天地”,可以說都市承載著女性的心理特征、感情特征及價值意義。本文以《放浪記》為研究文本,考察生活在公寓、咖啡廳、百貨大樓、城市街道等大東京都市空間里的女性,闡述她們面臨的現實生活及其精神內涵。在大都市里,女性擁有了曾經只能奢望的自由,但仍然無法擺脫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困境,卻又能看到走出困境的希望。《放浪記》中都市化的社會背景為林芙美子初期文學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社會環境和現實條件,其中對女性進行的書寫可以說是她文學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