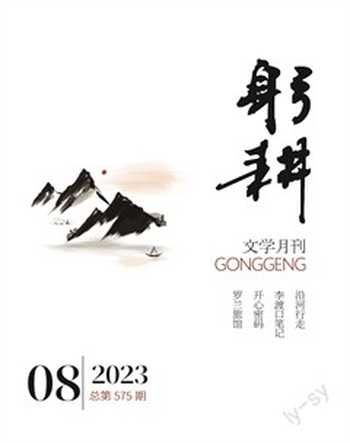鄉(xiāng)土文學(xué)的深化與拓展:馮杰詩(shī)論
張延文
1948年,著名社會(huì)學(xué)家費(fèi)孝通先生的《鄉(xiāng)土中國(guó)》出版,指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guó)社會(huì)是鄉(xiāng)土性的。鄉(xiāng)下人離不了泥土,土是他們的命根,他們身上的“土氣”是由于不流動(dòng)而發(fā)生的,人與人在空間的排列關(guān)系上是孤立和隔膜的。他們像植物一般在一個(gè)地方生根,洞悉周圍的人和物,產(chǎn)生出熟人社會(huì),在這里,人們不用文字而是用語(yǔ)言和語(yǔ)言之外的動(dòng)作表情來(lái)進(jìn)行面對(duì)面的直接交流,語(yǔ)言本身是用聲音表達(dá)的附著意義的象征體系,而不是事物或動(dòng)作本身具有的性質(zhì)。文字的發(fā)生具有“廟堂性”,不是鄉(xiāng)下人的東西。由親屬關(guān)系和地緣關(guān)系所決定的有差等的次序關(guān)系是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內(nèi)在倫理,并在男女有別的合作基礎(chǔ)上形成了靠“禮”來(lái)維持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秩序。
1795年,德國(guó)著名的詩(shī)人和哲學(xué)家席勒在《論素樸的詩(shī)和感傷的詩(shī)》一文中寫道:“詩(shī)人或則就是自然,或則尋求自然。在前一種情況下,他是一個(gè)素樸的詩(shī)人,在后一種情況下,他是一個(gè)感傷的詩(shī)人。”“只要當(dāng)人還處在純粹的自然(我是說(shuō)純粹的自然,而不是說(shuō)生造的自然)的狀態(tài)時(shí),他整個(gè)的人活動(dòng)著,有如一個(gè)素樸的感性統(tǒng)一體,有如一個(gè)和諧的整體。”“素樸的詩(shī)人滿足于素樸的自然和感覺(jué),滿足于摹仿現(xiàn)實(shí)世界,所以就他的主題而論,他只能有一種單一的關(guān)系;在處理主題的方式上,他沒(méi)有選擇的余地。”“感傷詩(shī)人沉思客觀事物對(duì)他所產(chǎn)生的印象;只有在這一沉思的基礎(chǔ)上,方才奠定了他的詩(shī)歌的力量。結(jié)果是感傷詩(shī)人經(jīng)常都要關(guān)心兩種相反的力量,有表現(xiàn)客觀事物和感受它們的兩種方式;就是,現(xiàn)實(shí)的或有限的,以及理想的或無(wú)限的;他所喚起的混雜感情,將經(jīng)常證明這一來(lái)源的二重性。”
“素樸”的詩(shī)是需要鄉(xiāng)土社會(huì)的文化土壤的,而傳統(tǒng)中國(guó)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就為其提供了一方純凈的沃土。當(dāng)然,描寫鄉(xiāng)村的詩(shī)篇本身,也依然具有象征體系的特質(zhì)。當(dāng)然,并不只是那些以鄉(xiāng)村生活為主題的田園詩(shī)才是素樸的詩(shī)篇。從某種意義上來(lái)說(shuō),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的文化倫理中一直是以鄉(xiāng)土文化的血脈根性為核心的,人與自然的和諧,表達(dá)真實(shí)與統(tǒng)一的自我的“思無(wú)邪”是崇尚詩(shī)教的社會(huì)秩序的必然要求。新時(shí)期以來(lái),中國(guó)社會(huì)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伴隨著城市化、工業(yè)化、市場(chǎng)化的快速推進(jìn),鄉(xiāng)村社會(huì)已不再是費(fèi)孝通先生那個(gè)時(shí)代的模樣,安土重遷的鄉(xiāng)下人紛紛背井離鄉(xiāng),鄉(xiāng)村的基本面貌也在快速融入工業(yè)化的浪潮。中原地區(qū)作為中國(guó)鄉(xiāng)土社會(huì)的代表,也在經(jīng)歷著同樣的變遷。生長(zhǎng)于北中原一個(gè)叫留香寨的村莊的詩(shī)人馮杰,談到自己的寫作時(shí)指出,自己的詩(shī)歌題材“其實(shí)只有兩條:一種是當(dāng)代與鄉(xiāng)土觸角的延伸,是向前走。一種是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解讀,是向后看,用我的鼠目寸光去釋析流失的漫長(zhǎng)時(shí)光。但兩種線條的中心精神只有一個(gè):那就是對(duì)大地與文化的感恩。”
詩(shī)人痖弦先生在談?wù)擇T杰的詩(shī)歌時(shí)認(rèn)為:“先以鄉(xiāng)土知名,而后觸及現(xiàn)代。選材廣博,涉古兼今,質(zhì)樸純厚,視野開(kāi)闊,恰似豐沛遼闊的大地,又不失悲憫情懷,溫馨質(zhì)感。詩(shī)作更多賦有中國(guó)古典美學(xué)特征,強(qiáng)調(diào)物象神態(tài)和客觀意趣有機(jī)結(jié)合,以我思與物情的融澈追索詩(shī)的精神;又駕馭形式,意象豐饒,如線條靈動(dòng)的童話木刻,充滿典雅與唯美色彩;讓我們聞到翰墨的芳香,認(rèn)識(shí)到詩(shī)的無(wú)邪無(wú)偽,顯出從容不迫的寧?kù)o,達(dá)到藝術(shù)的完整性。”馮杰的詩(shī)歌寫作,根植于鄉(xiāng)村生活,吸收古典文化的營(yíng)養(yǎng),以物象和我思來(lái)探尋和展現(xiàn)大時(shí)代的素樸與感傷背后隱藏著的文化倫理中折射出的人性中平凡的美。
馮杰,1964年5月生,河南滑縣人,出生于河南長(zhǎng)垣,18歲在長(zhǎng)垣縣農(nóng)業(yè)銀行工作,2008年調(diào)入河南省文學(xué)院從事專業(yè)創(chuàng)作,現(xiàn)為河南省文學(xué)院副院長(zhǎng),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全委會(huì)委員,河南省作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1981年馮杰在《綠洲》文學(xué)雜志發(fā)表詩(shī)歌處女作《牧鵝歸來(lái)》。1984年10月,組詩(shī)《故鄉(xiāng)風(fēng)景線》由《青年作家》雜志重點(diǎn)推出,后國(guó)內(nèi)多家報(bào)刊轉(zhuǎn)載。1985年9月,組詩(shī)《平原抒情詩(shī)》由《詩(shī)歌報(bào)》以“崛起的詩(shī)群”推出。1986年4月,詩(shī)集《中原抒情詩(shī)》由河南省青年詩(shī)歌學(xué)會(huì)編輯出版,列入“中原青年詩(shī)叢”第二輯。同年,馮杰與叢小樺、劉小江等人創(chuàng)辦《中原詩(shī)報(bào)》,該民刊顧問(wèn)為蘇金傘和青勃。1990年2月,馮杰的組詩(shī)《鄉(xiāng)土很新鮮》獲《青年作家》舉辦的全國(guó)青年詩(shī)歌大賽“中國(guó)杯”詩(shī)獎(jiǎng)。自此,馮杰就開(kāi)啟了詩(shī)歌屢獲大獎(jiǎng)之旅,1992年6月,組詩(shī)《逐漸爬上童年的青苔》獲《藍(lán)星詩(shī)刊》“屈原詩(shī)獎(jiǎng)”。1993年9月,組詩(shī)《第五千種荷》獲世界華文詩(shī)歌大獎(jiǎng)賽第一名;10月,組詩(shī)《書法的中國(guó)》獲第16屆中國(guó)時(shí)報(bào)文學(xué)獎(jiǎng);12月,組詩(shī)《在中國(guó)作一次茶的巡回》獲《詩(shī)刊》社全國(guó)詩(shī)歌大獎(jiǎng)賽“人民保險(xiǎn)杯”第一名。1997年6月,詩(shī)歌《喊經(jīng)的人》獲《新陸詩(shī)刊》第一屆“雙子星新詩(shī)獎(jiǎng)”。2000年9月,詩(shī)歌《在母語(yǔ)時(shí)代》獲第22屆《聯(lián)合報(bào)》新詩(shī)獎(jiǎng)。2005年,詩(shī)歌《墻里的聲音》獲第28屆中國(guó)時(shí)報(bào)文學(xué)獎(jiǎng)。除了獲獎(jiǎng)之外,馮杰在詩(shī)歌創(chuàng)作方面成就頗豐,先后出版了詩(shī)集《一窗晚雪》《田園抒情詩(shī)》《布鞋上的海》《討論美學(xué)的荷花》《馮杰詩(shī)選》《震旦雅雀:馮杰的詩(shī)》以及兒童文學(xué)詩(shī)集《在西瓜里跳舞》等多部。
除了詩(shī)歌之外,馮杰還寫小說(shuō)、散文,畫畫,書法,出版有短篇小說(shuō)集《驢皮記》《飛翔的恐龍蛋》《冬天里的童話》《少年放蜂記》等,散文集《丈量黑夜的方式》《泥花散帖》《一個(gè)人的私家菜》《田園書》《捻字為香》《馬廄的午夜·異者說(shuō)—中國(guó)鄉(xiāng)村妖怪錄》《九片之瓦》等等,以及文畫合集《野狐禪》《說(shuō)食畫》《水墨菜單》《畫句子》《非爾雅》《懟畫錄》《文字的虎皮花紋》等等。多年筆耕,馮杰可謂著作等身,詩(shī)文書畫皆佳,而他則堅(jiān)稱自己是一個(gè)詩(shī)人。在回答《晶報(bào)》的采訪時(shí),馮杰說(shuō):“小說(shuō)是一種狗皮膏藥,需要緊緊粘貼在現(xiàn)實(shí)的狗肚上,詩(shī)歌是要在天空飛翔的一種形式,散文則要緊緊匍匐在大地上,用來(lái)聆聽(tīng)大地上露水草木和萬(wàn)物之聲。”(出自馮杰《我不過(guò)是文學(xué)殿堂臺(tái)階下的小羅漢》,刊載于2013年6月17日《晶報(bào)》)馮杰的散文集非常獨(dú)特,每一部散文集中都有圖有文,他戲稱這是“看圖說(shuō)話”,圖是自己插圖,與文可謂若離若合。“我認(rèn)為好的散文是:形式上隨意道來(lái),散無(wú)定法。技巧上是欲說(shuō)還休,戛然而止;內(nèi)容上是悲天憫人,大地情懷。行文上不懷好意,骨子里卻止于至善。”而在詩(shī)集當(dāng)中,馮杰卻只是以文字示人,對(duì)于詩(shī),馮杰一直秉承著敬畏之心。就其內(nèi)在來(lái)說(shuō),馮杰的詩(shī)書畫有著其主題和美學(xué)上的統(tǒng)一性,均生發(fā)于他悉心營(yíng)造的“北中原”。
在談及“北中原”時(shí),馮杰如此自道:“我筆下的‘北中原不是具體的地理名詞,是一個(gè)虛構(gòu)的文學(xué)名詞,主要是受沈從文‘湘西和福克納‘郵票般故鄉(xiāng)這些文學(xué)符號(hào)的啟發(fā)。我編制了一個(gè)四面透風(fēng)的文學(xué)簍筐,把自己要表達(dá)的都裝到里面。紙上的‘北中原文學(xué)疆域狹隘地說(shuō)只是豫北,后來(lái)寫遠(yuǎn)了,也未嘗不是以文字在輻射中原大地。每一個(gè)作家都應(yīng)該有一片屬于自己出發(fā)的文學(xué)原地,一個(gè)作家要在上面種植生長(zhǎng)自己的植物,四周要彌漫自己的文字氣息。我從小跟隨外祖父母在豫北鄉(xiāng)下長(zhǎng)大,他們教我感恩、悲憫、寬容,且與世為善。那里是我的文學(xué)之源,生命之根,讓我通文脈,接地氣。如今面對(duì)那塊折騰過(guò)的土地和逝去的親人,我做的事情是在捻字為香,以文還愿。”這表面看起來(lái)不過(guò)是詩(shī)人常有的一種故鄉(xiāng)情結(jié),深入來(lái)看體現(xiàn)出的則是其創(chuàng)作意識(shí)上的高度自我認(rèn)同與文化自覺(jué)。
痖弦在屈原詩(shī)獎(jiǎng)評(píng)語(yǔ)中如此評(píng)價(jià)馮杰詩(shī)歌:“馮杰的田園詩(shī)從童年的回憶出發(fā),表現(xiàn)作者對(duì)大自然之美的歡喜贊嘆,對(duì)泥土鄉(xiāng)井的摯愛(ài),體會(huì)十分深刻。各篇構(gòu)思敏妙,意象豐饒,風(fēng)韻天然,充滿樸實(shí)的氣息與童稚的趣味,猶如一幅幅線條靈動(dòng)的童話木刻,也像一支支隨興吹奏的村野牧歌,耐人尋味。”馮杰的詩(shī)歌《一種寫詩(shī)的理由》:“為了撿拾? 收留那些受傷迷途的漢字/像呵護(hù)草葉? 或一場(chǎng)刻骨銘心的愛(ài)情//那些詩(shī)句如凍傷的瓦片/被現(xiàn)代忽略? 遺忘/再?zèng)]有人去攙扶? 去溫暖/讓它們能在星光下趕路//寫詩(shī)? 只是為了在一朵荷花中筑造/一座不存在的草房子//用于裝卸童話和良知/讓語(yǔ)言之瓦聯(lián)在一起? 去抵抗冬天與傷害//它們會(huì)牽著冰涼帶傷痕的手/鋪向冬天大地的盡頭/僅僅為給你一點(diǎn)亮色”。“凍傷的瓦片”“星光”“荷花”“草房子”與“大地”,這些帶有“童話”色彩的意象群為詩(shī)人的寫作渲染上了淡淡的“良知”的暖意。
在表達(dá)鄉(xiāng)村時(shí),詩(shī)人總是不吝美意,帶有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裝滿苜蓿草的房子》:是一方紗巾? 是一間紗巾? ?我是比喻一座房子/它在移動(dòng)? 地上的暖風(fēng)一如初潮? 緩緩涌起/紗巾漸漸飄遠(yuǎn)? 就是房子飄遠(yuǎn)/干草的肺葉勃?jiǎng)又?汁液是草的青春呵? 曾在時(shí)光里熬盡/我想起? 生命? 愛(ài)情? 這些單詞? 正在苜蓿與紙上穿行/想起故鄉(xiāng)飽滿的少女在風(fēng)里一天天蒼老? 如眼前的苜蓿//干草似皺紋的匯集? 草一生的皺紋/四季的干草都裝在一間房子? 這大地的抽屜/如我的一生? 只能在鄉(xiāng)村度過(guò)/草們正從窗口毛刺刺地伸出手/翻開(kāi)微霉的氣息與房子的舊事//大地上每一間掉光牙的房子都一定裝過(guò)愛(ài)情/這是一座鄉(xiāng)間的房子? 是一塊散發(fā)草氣的云朵/還有什么能比得上裝干草的房子豐富? ?在北中原/它把大地上的古典或現(xiàn)代故事都一網(wǎng)打盡/塵埃落定? 草氣飄遠(yuǎn)? 在我靜坐的今生今夜”。這首作品頗能代表馮杰的藝術(shù)風(fēng)格:表達(dá)上,敘述與抒情融合,由近及遠(yuǎn),由局部擴(kuò)展到整體,動(dòng)靜結(jié)合,虛實(shí)相生;語(yǔ)言上,盡量避免口語(yǔ)化和散文化,從而保持情感的飽滿度和新鮮感;審美上,以內(nèi)在的旋律和音韻、純粹的意象營(yíng)造優(yōu)美的意境,有意識(shí)地去弱化矛盾和丑。在萬(wàn)物生長(zhǎng),自由自在的天地中,“草”一樣的生靈引人入勝。這是詩(shī)人對(duì)大地上純樸的人群和事物的原始的生命力的贊美和歌頌。
馮杰善于描寫鄉(xiāng)村的小動(dòng)物,“暖雪下田鼠呼吸平靜/它只擔(dān)憂雪融時(shí)刻? 春天提前破門而入/春天的速度如此之快”(《暖雪下的田鼠》)。”“微小的雀舌飾以流暢的方言/在草垛頂端? 露珠之內(nèi)? 在布鞋從面到兩側(cè)范圍/在溫暖的雪層上? 雀語(yǔ)開(kāi)始陣陣撒向土地”(《雀語(yǔ)·第一樂(lè)章》)。“吸盤能觸及到最大那顆星的邊沿/向上/恐怕星子也會(huì)因傾斜而溢出來(lái)光/以手的堅(jiān)毅? 你去愛(ài)這個(gè)世界? 向上”(《向上的壁虎》)。“草籽? 米豆? 果仁? 還有遺落的青花紐扣/每一件都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黃鼬每天穿梭忙碌/像一位鄉(xiāng)間走動(dòng)的藝人”(《一只黃鼬的秘密》)。這區(qū)別于“莊生曉夢(mèng)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式的文化象征,是一種更為單純的貼近于事物存在本真的書寫,是素樸的詩(shī)。由此,馮杰嘗試打破文字的符號(hào)化的局限,進(jìn)行現(xiàn)象學(xué)上的還原,回到物自身發(fā)生的現(xiàn)場(chǎng),以生動(dòng)逼真的細(xì)節(jié)描寫鋪展出祛魅化的詩(shī)性體驗(yàn)。鄉(xiāng)村萬(wàn)物和諧相處,溫暖寧?kù)o,構(gòu)成一種彼此呼應(yīng)的宏大的意象體系,鼓蕩著鄉(xiāng)土中國(guó)律動(dòng)的脈絡(luò)和悠長(zhǎng)的氣息。馮杰以富于現(xiàn)代主體性意識(shí)的筆觸,進(jìn)行開(kāi)放式的抒情,從而達(dá)到對(duì)傳統(tǒng)的田園詩(shī)的突破性的繼承。
在馮杰的詩(shī)篇里,有馬廄、草、瓦等靜物的白描,來(lái)映射鄉(xiāng)村人的生活現(xiàn)實(shí)。“馬廄里的情話也能喂馬? 長(zhǎng)短不一/那是摻上月光來(lái)不及用鍘刀切齊的/而顯得明亮的話題/亂蓬蓬? 扎一下忽然心痛的東西”(《掌握喂馬的時(shí)間》)。“這世界上? 沒(méi)有一柱草根是重復(fù)的/即使在黑暗里? 也沒(méi)有一柱草根重復(fù)/雷同相似的只有一種顏色? 是黑/在身邊與周圍/黑的后面還是黑? 是最厚的黑//穿過(guò)土層? 往上探頭的一瞬? 草根一定會(huì)感動(dòng)/草根渴望上面灌注雷聲? 或有激情傾盆而下//也許那樣輝煌的時(shí)刻/在地下的摸索里? 草根一輩子也不能到達(dá)”(《草根在地下向前摸索》)。“誰(shuí)能耐心聆聽(tīng)大地上升騰的事情? 惟有瓦/連綿? 悠遠(yuǎn)? 一氣呵成? 瓦是鄉(xiāng)村溫暖的漢字/它們?nèi)缗思{鞋般密的感情漫過(guò)鄉(xiāng)村的額頭/瓦? 這些房子的羽毛/讓每一座房子都呈飛翔的蓑衣? 簌簌飄響/每一個(gè)雨夜? 都有瓦悄悄啜泣//在鄉(xiāng)村誰(shuí)都不愿日夜承擔(dān)苦難/連小小的綠苔與瓦松也如是說(shuō)/世界上所有的瓦其實(shí)都渴望避雨? 只是不能/只是那一片片承擔(dān)苦難的手掌必須此刻伸出//在黎明前夜的屋檐里伸出/裸露出來(lái)讓一一擊打”(《也想避雨的瓦》)。詩(shī)人將鄉(xiāng)村里那些即將被遺忘的,帶有時(shí)光的悠長(zhǎng)記憶的事物,用帶有夸飾性的意象加以著力刻畫,描繪出一幅幅動(dòng)態(tài)的風(fēng)景畫,營(yíng)造出田野里的鄉(xiāng)親在艱難困苦中堅(jiān)韌屹立的光輝群像。
在贊美之外,馮杰也將目光投向了鄉(xiāng)村正在進(jìn)行著的巨大的變革。“比喻一枝梅花伸向遠(yuǎn)處 一枝鄉(xiāng)路/巨大的梅花腳印在不斷綻開(kāi) 修定 刪改/夢(mèng)想制造新的版本與定稿? 梅花在開(kāi) 梅花在落//誰(shuí)也不能阻擋城市章魚般的觸角與鄉(xiāng)村融合/在那梅花與梅花焊接的瞬間? ?碰撞之聲/讓所有的行路人 驟然感到慌亂與心痛//如此多腳步組成的魚脊? 向另一個(gè)大海擁擠/路的全部意義與功能/用于打工 負(fù)笈 逃婚 或私奔(多么古典的當(dāng)壚逸事)/盡頭? 正泛起鋼的藍(lán)色與罌粟誘惑的亮澤/這些魚群游向另一片與草氣愈來(lái)愈遠(yuǎn)的地方? 然后/在枝頭一一陷落? 從而梅花永無(wú)寧日”(《對(duì)黎明前一條村路意象與試寫》)毫無(wú)疑問(wèn),道路是鄉(xiāng)村伸向城市的觸角,堅(jiān)貞高潔、吉祥平安的“梅花”再無(wú)寧日,“古典”里的傳統(tǒng)倫理秩序在工業(yè)化和市場(chǎng)化帶來(lái)的沖擊下快速崩毀。費(fèi)孝通先生所勾勒出的自成一統(tǒng)的東方式的鄉(xiāng)土社會(huì)正在發(fā)生根本性的變革。對(duì)此,詩(shī)人做出了由表及里的透徹剖析,試圖拆穿“每棵植物都有著的鮮為人知的秘密”:“第一塊有初醒時(shí)機(jī)器與車輪碾過(guò)來(lái)的恐懼/第二塊因吞食農(nóng)藥? 草也會(huì)彎腰嘔吐而難過(guò)/第三塊叫痙攣? 面部隆起的憤怒如小小丘陵/第四塊充滿著對(duì)燒荒者與人類誓言極端的輕蔑/第五塊向五彩的塑料與純凈水瓶表達(dá)出厭惡/第六塊因遠(yuǎn)方來(lái)的孩子叫不出草的乳名閃現(xiàn)出的失望/第七塊對(duì)草莖能從手掌上漂浮起來(lái)深感好奇/第八塊根須觸及著地下美麗少女的臉龐無(wú)限哀傷/第九塊感觸到羊蹄輕盈地踩過(guò)遺落的寂靜/第十塊是最短暫時(shí)刻? 只有蜜蜂翅能丈量的小小歡樂(lè)/第十一塊當(dāng)風(fēng)吹過(guò)來(lái)? 才去表達(dá)出來(lái)的微笑/第十二塊是所有泥石漿都擊下來(lái)也要承受的寬容/最后一塊在底層? 帶著泥屑無(wú)邊的幽怨與眷戀/這是最后一塊”(《土豆細(xì)節(jié)·植物13塊面部揭示的情感》)。這是一首對(duì)于當(dāng)代鄉(xiāng)村社會(huì)癥候群的集中描寫,通過(guò)大量的通感以及擬人化的書寫,蘊(yùn)含著詩(shī)人深深的憂慮和不安,及其無(wú)法平息的憤懣與怒火,以及無(wú)能為力而被迫唱挽歌的無(wú)奈和惶惑。
在詩(shī)歌之外,馮杰善于繪畫、書法,并將這些傳統(tǒng)文人必備的技能操練純熟,了然于胸,再融匯于詩(shī)歌寫作之內(nèi)。《雨具的信息》:“關(guān)于斗笠 蓑 雨衣和信箋上的文字/這些東西外表都能滲出汗珠 或淚珠/雨具的面龐 無(wú)論泛綠與臉紅/都預(yù)示著雨腳遠(yuǎn)涉而來(lái)的信息//起源于遠(yuǎn)方一扇半開(kāi)百葉窗? 一雙手/是否超越了時(shí)光? 超越了雨意與愛(ài)情//依舊撐傘? 依舊披蓑? 依舊穿屐/依舊/還要像少年般帶一冊(cè)蘇軾的詩(shī)集/開(kāi)門第一步? 連雨具也驟然猶豫/這是在宋朝 還是現(xiàn)代鍍銅的八點(diǎn)鐘。”馮杰曾經(jīng)饒有趣味地戲稱,自己最喜歡的朝代是北宋,希望能夠成為蘇軾的一個(gè)書童。北宋是中國(guó)文人書畫的高峰,蘇軾正是文人詩(shī)書畫三位一體的集大成者。蘇軾的《定風(fēng)波·莫聽(tīng)穿林打葉聲》寫道:“莫聽(tīng)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shuí)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fēng)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lái)蕭瑟處,歸去,也無(wú)風(fēng)雨也無(wú)晴。”馮杰的《雨具的信息》是對(duì)于蘇軾《定風(fēng)波·莫聽(tīng)穿林打葉聲》的現(xiàn)代化的仿寫或者說(shuō)是臨摹之作,其中還暗含著現(xiàn)代時(shí)期著名詩(shī)人卞之琳的《距離的組織》中的“雪意”和“五點(diǎn)鐘”意象以及詩(shī)中悵然若失情緒的化用。此時(shí)此地,斗笠和蓑衣,竹杖芒鞋木屐,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更加困難的是不為外物所困的曠達(dá)與自信。
馮杰常用具有古典意味的意象,比如荷花。“就像我只鐘情單純明澈的詩(shī)句? 此刻/聽(tīng)到一朵荷花在訴說(shuō) 陽(yáng)光如厚厚布匹/荷花的語(yǔ)言是水洗過(guò)一樣 干凈 清亮/散發(fā)清氣 荷花在用方言訴說(shuō)”(《在城市聽(tīng)一朵荷花,說(shuō)》)。“單純明澈”,“用方言訴說(shuō)”,這些體現(xiàn)的是一種自我的獨(dú)立與固守。這和蘇軾為代表的傳統(tǒng)文人有著內(nèi)在的一致性。《吃一朵花需要多長(zhǎng)時(shí)間》:“屈原在楚辭里吃一朵菊花/需要一個(gè)黃昏/他有兩種吃法//蘇軾在宋代吃一朵葵花/需要一天 主要吃形而上/摻上意象 就酒/或涼拌//梅堯臣吃一朵牡丹/需要一年? 牡丹大如皇冠/在熱鍋油炸//周敦頤吃一枝蓮花/需要漫長(zhǎng)一生/甚至還要更遠(yuǎn)/(那是吃一朵蓮花呵)//等我想吃花的時(shí)候/世界已成塑料時(shí)代/只有喊上一碟陳醋/讓我故作風(fēng)雅”。屈原、梅堯臣、周敦頤,和蘇軾一樣,皆為高潔之士,隨著時(shí)代以降,“吃花”的風(fēng)雅之舉卻愈加艱難,到了當(dāng)代,詩(shī)人已無(wú)花可食!但詩(shī)人這份雖不能至,仍心向往之的情懷依舊躍然紙上,令人欽敬。
馮杰喜臨帖,題字于畫,頗得先賢意趣,嘗以詩(shī)揣度古人。比如《歐陽(yáng)詢<張翰思鱸帖>的產(chǎn)生》:“秋風(fēng)在唐詩(shī)邊驟起/一片黃葉無(wú)意駐足鬢發(fā)/恍然菰的樣子/恍然鱸的潑刺聲//家鄉(xiāng)的蒲早已出鞘? 這小小綠劍/在遙遠(yuǎn)盡頭探首? 剁斷伸來(lái)的相思//舊宅的炊煙彎腰貼墻而行/一群想家的字繞著硯臺(tái)而行/也想去造訪一下菰的味道//探頭看看窗? 紫檀案上/一箋字帖驚得浸出一身冷汗/字? 也要飲一口菰湯/略咸? 有點(diǎn)像詩(shī)/不如把公章與官服扔掉/上浣中浣下浣的薪金卸掉/坐著一片最薄的鄉(xiāng)愁? 回家//詩(shī)人只能嘆口氣走出帖外/一幀麻紙亂若風(fēng)中菰葉/最大的字都站不穩(wěn)腳/滿紙印章一一滑倒//只有老家一尾鱸魚? 舐短一寸寸殘墨”。作為書界“初唐四大家”之一的歐陽(yáng)詢,創(chuàng)出“歐體”,被美譽(yù)為唐人楷書第一;在書論上也有建樹(shù),所撰《傳授訣》云:“最不可忙,忙則失勢(shì);次不可緩,緩則骨癡;又不可瘦,瘦當(dāng)枯形,復(fù)不可肥,肥即質(zhì)濁。細(xì)詳緩臨,自然備體,此是最要妙處。”歐陽(yáng)詢生逢亂世,歷經(jīng)南朝、隋、唐三代,書論則深得東漢書法家蔡邕的“書書肇于自然”(蔡邕《九勢(shì)》)的要義,法度與靈動(dòng)結(jié)合,遵循自然之道。《張翰思鱸帖》乃歐陽(yáng)詢的紙本行書作品,記敘晉人張翰因秋風(fēng)起而思念家鄉(xiāng)遂辭官歸隱的事跡。馮杰的這首作品,語(yǔ)言生動(dòng)活潑,神采飛揚(yáng),體現(xiàn)了其機(jī)智幽默的一面,實(shí)乃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的塊壘。以詩(shī)喻書,將作詩(shī)和處事之道融會(huì)貫通,頗得大詩(shī)人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的神韻:“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dòng)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lái)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唇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yáng)揚(yáng)。與余問(wèn)答既有以,感時(shí)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fēng)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lè)馀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fù)終,樂(lè)極哀來(lái)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zhuǎn)愁疾。”張旭觀公孫大娘精湛的劍技表演得悟書道,而杜甫看其弟子舞劍則徒增撫今追昔的滿腔愁緒。
2007年春,馮杰客居鄭州,寫下《在城市邂逅一匹白馬》:“在城市看到一匹馬? 一朵奔跑的白色荷花/透明的童話奔跑 帶著雨水長(zhǎng)鬃/一座城市在奔跑/怎么能遇到一匹馬 驚愕 冒昧 陌生 / 像一朵不敲門突然闖來(lái)的荷花/一匹馬? 一匹在想象的墻里左右馳騁的馬/一朵總要讓匆忙行人在城市去誤讀的荷花//馬眼里亮起水色? 濺起細(xì)浪/ 里面布滿草色? ?冬天干草的顏色/簌簌聲響在馬眼里剝落/是某一個(gè)被洗得干凈的清晨/是某一盤櫻桃般鮮潤(rùn)的清晨/馬和風(fēng)站齊? 一同從鄉(xiāng)村歸來(lái)/眼里灌滿村路上的泥漿/ 馬語(yǔ)灌滿縱橫交錯(cuò)的防水河壩//股票的曲線搖擺散亂如一條韁繩/在馬眼里上升或下跌/馬的白色在接近城市塑料袋的膚色/和無(wú)數(shù)張萎縮的白墻壁一個(gè)顏色/馬的顏色里講述著一場(chǎng)風(fēng)暴/消融子夜? 過(guò)濾村霜? 山嵐和暮色/躲閃著城市紅黃綠? 馬成為唯一的顏色//一匹馬最終復(fù)制進(jìn)城市塑料/被同化為另一種白/擊碎? 溶合? 之后為馬之外/ 擦肩而過(guò)的馬眼里滾出苦澀/ 馬鬃縱橫繽紛? 遮蓋城市的交通手冊(cè)”。從鄉(xiāng)村題材進(jìn)入城市,“馬”“荷花”“干草”這些意象仍在,只是都在褪色,大地上鮮活的生命力在逐漸消失,與自然遠(yuǎn)離,“馬”在被城市的交通手冊(cè)馴化,被股票的曲線控制住身形,透明的童話變成了苦澀的人造“塑料”,被城市的洪流淹沒(méi)。在描寫城市生活時(shí),馮杰詩(shī)歌的敘述性明顯增強(qiáng),抒情成分減弱,在原有的鄉(xiāng)村意象中加入了現(xiàn)代的生活素材。
2010年10月27日,痖弦到河南文學(xué)院參觀,與馮杰重逢,馮杰寫下《語(yǔ)言的化石》向前輩致敬:“你是帶著方言旅行的語(yǔ)言圣徒/失家者帶著家譜? 行腳僧帶著餓瘦的缽/去國(guó)者懷揣一泊殘山剩水/語(yǔ)言?shī)A在書里? 怕碎不忍合頁(yè)/扛在肩上? 語(yǔ)言高過(guò)頭發(fā)//蓬亂如藻如冰片的語(yǔ)言/來(lái)自一冊(cè)殘破的手掌/黃昏蹲在燭臺(tái)下/語(yǔ)言的孤舟睡在遺漏一朵棉桃里//……故鄉(xiāng)的顏色需用南陽(yáng)話推敲/化石存量最好以草木灰封存/暖著燙著/母親烙下的那一張溫?zé)嵝★? 隔著棉衣/從后背漫浸到沉重的軍靴//尤其是南方梅雨季節(jié)/方言漏掉是要長(zhǎng)出來(lái)根須/童年磨坊月光漂白的豆芽們善講夜話/灶王爺可懂馬燈可懂? 銅環(huán)和毛驢可懂/五十年語(yǔ)言成色誰(shuí)來(lái)鑒定/依靠斑鳩? 野荸薺? 地丁花? 風(fēng)信子/記錄如何聽(tīng)懂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一塊化石端坐? 像鄉(xiāng)間的神”。痖弦自1949年17歲離家后,直到1991年才第一次歸鄉(xiāng),對(duì)于故鄉(xiāng)和家人的思念無(wú)時(shí)無(wú)刻不縈繞著他。1957年底,痖弦寫出《紅玉米》,其中飽含對(duì)于故鄉(xiāng)的深沉的依戀和憂思:“宣統(tǒng)那年的風(fēng)吹著/吹著那串紅玉米//它就在屋檐下/掛著/好像整個(gè)北方/整個(gè)北方的憂郁/都掛在那兒//猶似一些逃學(xué)的下午/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表姊的驢兒就拴在桑樹(shù)下面//猶似嗩吶吹起/道士們喃喃著/祖父的亡靈到京城去還沒(méi)有回來(lái)//猶似叫哥哥的葫蘆兒藏在棉袍里/一點(diǎn)點(diǎn)凄涼,一點(diǎn)點(diǎn)溫暖/以及銅環(huán)滾過(guò)崗子/遙見(jiàn)外婆家的蕎麥田/便哭了//就是那種紅玉米/掛著,久久地/在屋檐底下/宣統(tǒng)那年的風(fēng)吹著//你們永不懂得/那樣的紅玉米/它掛在那兒的姿態(tài)/和它的顏色/我的南方出生的女兒也不懂得/凡爾哈侖也不懂得//猶似現(xiàn)在/我已老邁/在記憶的屋檐下/紅玉米掛著/一九五八年的風(fēng)吹著/紅玉米掛著”。痖弦后來(lái)定居加拿大溫哥華,仍然多次歸國(guó)探親,并把一塊母親用過(guò)的槌衣石放于住宅院內(nèi),說(shuō)等他死了就枕著這塊石頭長(zhǎng)眠。2019年,由痖弦做序言《淯流錦帶》的南陽(yáng)詩(shī)群作品集《白河詩(shī)叢》面世。
2010年春,馮杰在鄭州期間,寫出了隱喻日常生活狀態(tài)的《柚子記》:“一顆面龐金黃的柚子擁有自己的觀點(diǎn)/可睡內(nèi)部自己的殿? 可讀外面杜甫的詩(shī)/密布小巷交叉的草圖上/一枚果實(shí)只有一扇門/柚子從不發(fā)表宣言? 趁太陽(yáng)未升時(shí)/它起身提燈? 它關(guān)閉自己”。一個(gè)詩(shī)人內(nèi)心的豐富和自足,向內(nèi)是一座自我的宮殿,用充滿希望的眼光打量周遭的世界,“提燈”者,如果不能照耀外圍的暗黑,至少可以保持自我的獨(dú)立和純凈。同期還有一首《再?zèng)]有比水更干凈的衣服了》:“你習(xí)慣熨平一部詞典/ 變幻的世界如川劇臉譜//不斷嘩嘩作響/機(jī)器在工作室合成雷同的詞語(yǔ)玉片/穿過(guò)故宮的風(fēng)/也在獸脊上擱淺// 那個(gè)戳破皇帝新裝的孩子不再出場(chǎng)/被無(wú)數(shù)雙黑手擋在童話外面/皇帝多于衣服//世上沒(méi)有比水更干凈的衣服了/透澈清明? 不屑讓人類穿起/水不喜歡站起來(lái)行走/它自己躺著? 讓冰柱在鐵絲間豎著”。“水的衣服”干凈、清澈、透明,在習(xí)慣了謊言和面具的只有冰冷和堅(jiān)硬的語(yǔ)境里,寧愿獨(dú)立、沉默,但姿態(tài)是“豎著”的。2015年仲夏夜,又是荷花芳馥的時(shí)令,馮杰在畫上題句《宣紙上的曲子》:“荷梗的長(zhǎng)句子全部帶刺/再刷上一層色就是空//今夜荷花以月光制造而成/隱約而至的跫音以月光制造而成/冊(cè)頁(yè)要表達(dá)順序以月光制造而成/使一個(gè)背影填滿笛空以月光制造而成/廣告牌以一張荷葉相應(yīng)比例在逐漸完成”。月光如水,洗刷著空靈的帶刺的荷梗,以及沉重的肉身下的斑駁的影子。
兒童詩(shī)是當(dāng)代詩(shī)歌當(dāng)中看似小眾卻也非常重要的門類,在孩子的成長(zhǎng)當(dāng)中可以起到相當(dāng)?shù)慕逃c啟蒙的意義。馮杰長(zhǎng)期進(jìn)行兒童詩(shī)歌創(chuàng)作,出版了《在西瓜里跳舞》以及“鄉(xiāng)土和孩子”系列三部詩(shī)集:《一朵花就是一座果園》《吃荊芥的貓》《寶石蜜城》等。其中《一朵花就是一座果園》獲得了2023年第五屆張?zhí)煲韮和膶W(xué)獎(jiǎng)。《在西瓜里跳舞》的前言里評(píng)價(jià)該詩(shī)集:“意象單純新奇,風(fēng)格簡(jiǎn)約質(zhì)樸,純凈自然地展現(xiàn)出一個(gè)鄉(xiāng)村孩子眼里曼妙的鄉(xiāng)土世界。內(nèi)容上,將雅致的情調(diào)與活潑的童趣相結(jié)合,如此和諧美妙;形式上,馮杰吟詠的詩(shī)配送馮杰暈染的畫,實(shí)在是渾然天成。”這部詩(shī)集是以童年的視角來(lái)打量鄉(xiāng)村生活,插畫是馮杰所做,他在自序《鄉(xiāng)土的澄明與草葉的溫情》中說(shuō):“我該是第三種寫童詩(shī)的人,是用情感和情趣來(lái)寫的,用記憶來(lái)寫的,屬于‘仿童。當(dāng)我觸摸到這些關(guān)于童年的文字時(shí),那一刻,故鄉(xiāng)的星群,竟如雪花一樣涌來(lái),擋都擋不住。我知道那是貫穿在我骨子里的一種東西——鄉(xiāng)土的澄明與草葉的溫情。那種情感,是我童年的‘鄉(xiāng)土宗教”。“鄉(xiāng)土和孩子”系列里的每一首詩(shī)都配有馮杰所做的畫,在自序《每一個(gè)孩子在童年都是詩(shī)人》中寫道:“世界上,和孩子在天性上最近的物質(zhì)是泥土、植物和動(dòng)物,孩子和他們是天然相通的。孩子的本性就是接近大地,但是現(xiàn)代化急速發(fā)展的今天,大人們身子走在靈魂前面,也多多少少影響著孩子,更多時(shí)候讓孩子們和大地絕緣。我寫的那是一些紙上的童話,想讓孩子們踩著文字,從這里進(jìn)入另一種鄉(xiāng)土。其實(shí),每一個(gè)孩子在童年都是詩(shī)人。他們是自己的詩(shī)人,是社會(huì)的詩(shī)人。”《吃荊芥的貓》:“有一天午覺(jué)/小貓發(fā)癔癥了/它跑到菜市場(chǎng)/大聲對(duì)老板說(shuō)/請(qǐng)給我稱上二斤清涼”。童心童語(yǔ),天真爛漫,這些帶有原始思維特點(diǎn)的詩(shī)篇,恰恰部分還原了詩(shī)歌發(fā)生的最初場(chǎng)景,對(duì)于民族語(yǔ)言和時(shí)代文化也有著深遠(yuǎn)的意義和價(jià)值。
一個(gè)成熟的詩(shī)人往往具有穩(wěn)定的品質(zhì)和獨(dú)特的審美,并對(duì)其生活的時(shí)代做出恰當(dāng)?shù)姆磻?yīng),作品能夠?qū)r(shí)代乃至未來(lái)產(chǎn)生應(yīng)有的影響。馮杰登上詩(shī)壇就出手不凡,憑著鄉(xiāng)土的純凈細(xì)膩,和深厚的文化積淀,得到了詩(shī)歌界的廣泛認(rèn)可。馮杰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是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鄉(xiāng)土詩(shī)歌的拓展和深化,在主題和審美上都有著新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馮杰的詩(shī)歌和他的書畫、散文一起,營(yíng)造了風(fēng)格鮮明外延廣闊的審美世界,對(duì)于新時(shí)期以來(lái)的鄉(xiāng)土中國(guó)的新變做出了及時(shí)的反映和警醒。馮杰的寫作既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獨(dú)立而自覺(jué),有著極強(qiáng)的文人情懷,擔(dān)當(dāng)而非規(guī)避。馮杰對(duì)于詩(shī)歌的態(tài)度是虔誠(chéng)的,他的文化自覺(jué)就是他的價(jià)值取向,從未偏離。鄉(xiāng)土中國(guó)的文化價(jià)值不會(huì)隨著田園生活的巨變而徹底消失。相反,在一個(gè)大變革的時(shí)期,馮杰這樣擁有文化擔(dān)當(dāng)意識(shí)的書寫,在頑強(qiáng)而倔強(qiáng)地對(duì)抗著同質(zhì)化帶來(lái)的侵蝕和切割,他筆下那些根植于鄉(xiāng)村和傳統(tǒng)的書寫,正在形成著共同的文化記憶,融入了一條溝通歷史和未來(lái)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