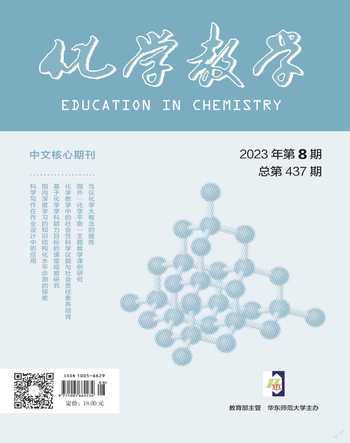試析科學本質的“整體科學”范式:基本理念、評價工具及審視展望
宗國慶


摘要: 基于主導國際科學教育科學本質研究三十余年的共識范式危機審視,近年來國際上興起了一種稱為整體科學的替代型范式。從基本理念、評價工具及審視展望三方面對該范式展開全面述評,以期為我國科學教育NOS范式變革提供理論與思想靈感,推動NOS理論研究及其實踐應用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 科學教育; 科學本質; 整體科學范式; 原型評價
文章編號: 10056629(2023)08000305 中圖分類號: G633.8 文獻標識碼: B
科學本質(Nature of Science, NOS)作為科學素養的核心組成,已成為當前諸多國家科學課程文件與國際組織政策報告的基本共識,得到了充分認可與普遍確立[1]。當前被普遍接受、NOS研究領域大量引用的是由萊德曼小組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共識范式”(Consensus Paradigm)[2]。近年來,該范式因其存在的諸多局限而廣受批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范式危機。批評者們認為共識范式已經過時,變得不再“共識”,是時候建立其替代性范式與方案了[3]。
研究者逐漸認識到應該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復雜性、系統性、開放性、整體性的NOS體系框架,并認為科學教育所需要的不是簡單、無關、斷裂的“觀念點”,而是更加上位的“觀念類”(classes of ideas)。以此為基礎,提出了家族相似性方法(family resemblance approach, FRA)與“整體科學”(whole science)等替代方案。本文聚焦于“整體科學”范式,從基本理念、評價工具及審視展望三方面進行述評。
1 基本理念
奧爾欽(Allchin, D.)于2011年提出“整體科學”范式[4],隨后又對其進行了澄清與完善[5~7]。他認為共識范式對于NOS中應囊括什么和排除什么,缺乏明確的理由和標準,而僅將其訴諸共識的權威性(課程文件與相關群體共識)。但這一共識僅是政治共識,而非理性共識。他們沒有闡明為什么選擇這些NOS特征(而不是其他)及其合理性,亦沒有說明這些特征與科學素養之間的關系。因而,共識范式的基礎只是一種浮光掠影式的表淺印象,是極其薄弱的。
1.1 范式定位
“整體科學”范式強調基于NOS理解對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社會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s, SSI)中的科學主張的可靠性與可信度進行綜合分析的重要意義。這種功能性理解使NOS發生了從抽象思辨的“是什么”到內嵌于認知性實踐能力的“為什么”與“怎么用”的轉向;發生了從學NOS(對其進行表征)到用NOS(將NOS運用于現實問題處理)的立場轉向。對功能科學素養而言,重要的不是對NOS的正式定義,而是將NOS運用于對SSI中的科學主張的可靠性的綜合分析上。要想對SSI的科學主張的可靠性進行綜合分析,既需廣泛分析科學的外部文化與社會機制,又需深入分析其內部運行機制,亦即包括社會、認知與實驗各個方面;既分析其正確性,又分析其錯誤與偏見所在。總之,需要對科學進行整體分析與把握。
奧爾欽批判性審視了共識范式,認為雖然陳述性知識是綜合分析能力的必要構成,但遠遠不夠,不能止步于對科學受其社會和文化環境影響的知識層面,更重要的是能對辨別這些影響是如何表達的。學生將“科學知識的暫定性”用于否定進化論、溫室效應時,展現出的只是一種消極的懷疑主義,還需要知道科學知識為什么會改變,以及如何改變。亦即,學生需要知道如何探索科學主張的認知結構、證據運用與解釋的不當方式,以辨別可靠主張和可疑主張,樹立針對特定錯誤來源或錯誤類型理解的積極而有組織的懷疑主義精神[8]。就是說,具有NOS知識并不必然具有運用能力。
1.2 維度表征
NOS不應如共識范式那般用一系列明確的原則表征,而應被表征為一系列維度類目。類目的概念有助于統一共識范式中的一些令人費解的矛盾。例如,學生如何協調“觀察是理論負載的”與“科學家是有創造力的”或“科學知識是持久的”和“科學知識是暫定的”。“整體科學”的最終目標是提高學生的可靠性的綜合分析能力,而非記住科學是暫定的還是持久的,是保守的還是創造性的。學生應該自由,而不是固守于某種特定意識形態。
學生的這種可靠性的綜合分析能力是一種對科學知識與實踐本質的綜合分析能力,它不是實踐技能或科學知識本身。它并不要求學生對所分析的科學社會問題具有廣博而深入的知識儲備、熟練的實驗探究操作技能,亦不要求其能夠對大量的專業證據進行評估。學生不是要成為科學家,而是要做一名理性的綜合分析家——識別各種科學主張相關的NOS維度,然后描述每個維度如何塑造相關主張的可信度。學生應該問:“我們是怎么知道的?”或者“基于證據和專業知識,我們如何能相信這個科學主張?”。
1.3 結構體系
奧爾欽在對相關案例總結分析的基礎上,勾勒出了“整體科學”的體系概貌。具體而言,該體系包含認知、社會與實驗三大維度,每一維度又包含若干類目。各一級類目又包含若干數目不等的二級類目,具體如表1所示。
2 “整體科學”范式下的評價工具
2.1 對共識范式評價工具的批判性分析
為建立整體科學范式下的評價工具,奧爾欽對共識范式下的VNOS(Views of Nature of Science Questionnaire, VNOS)評價工具所存問題進行了全面批判分析,并認為VNOS工具主要存在能力低階、效度不佳與語境缺失三方面的問題。具體而言,VNOS工具測評的是學生對于諸如“什么是實驗?”“科學理論和科學定律之間有什么區別?”等項目的低階記憶與理解,居于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的了解、知道、復述、理解水平的低階能力水平。而且,無論學生同意或不同意某些NOS陳述,其測評結果均會被VNOS評價者貼上建構主義的、經驗主義的或二者混合的等立場標簽,這就會導致事后合理化。最后,VNOS評價工具諸多項目(NOS的暫定性),可能會嚴重誤導學生——比如,學生可以用“NOS的暫定性”將達爾文主義者貶斥為“教條主義的”。
奧爾欽將NOS奠基于提高學生運用NOS去解決其日常生活所遇到的真實SSI問題的能力之時,即與共識范式劃清界限——不是要求學生能夠復述多少NOS特征,亦非能夠多么精確與完美地對這些特征進行語言學上的定義,不是單純讓學生脫離真實情境回憶、知道與復述NOS的某些特征的陳述性知識能力,而是運用NOS,對所遇到的SSI相關主張的可靠性的綜合分析能力。這種能力居于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的應用、分析與評價的高階能力水平。
2.2 “整體科學”范式下的評價工具——原型評價
2.2.1 原型評價內涵
奧爾欽認為,當將焦點轉移至功能理解時,所有諸如此類的評價工具都變得不合時宜。相反,功能性理解的NOS評價不是通過與規范陳述的一致性來進行,而是通過學生了解影響科學主張可靠性因素的廣度和深度來進行。亦即識別各種SSI中各種科學主張相關NOS維度,再描述每個NOS維度如何塑造相關主張的可信度的。
基于以上分析,奧爾欽認為NOS評價應在真實相關、標準明確的案例中進行,所評價的應是學生運用NOS對案例中的相關主張的可靠性進行分析的能力。這種案例,奧爾欽稱之為原型(Prototype),相應地,這種案例式評價,他稱之為原型評價。
2.2.2 原型評價項目及類型
原型評價的項目由一系列在科學上具有爭議的當代案例、探究案例或歷史案例組成。每個案例均要求學生“解釋與評價個人和公共決策中的科學主張的可靠性”。這些案例或來自新聞媒體、互聯網、廣告或期刊與科學史料。該評價要求學生根據他們“對科學如何運行的廣泛理解”,對案例中的相關主張的可靠性進行充分分析。
首先,學生需要識別案例中的相關NOS維度;繼而描述每個NOS維度如何塑造相關主張的可信度。通過這種方式,教育者可以評估學生NOS理解程度。原型評價避免征求學生個人觀點、立場或判斷,以及任何相應的合理化。它尋求思維的透明度,允許評估NOS理解的一致性、廣度(把盡可能多的不同的想法聯系在一起)和深度(通過使用具體NOS來有效地傳達想法)。
依據原型評價項目的類型差異,可分為歷史類原型評價、當代類原型評價以及探究類原型評價3種。不同類型的原型評價具有不同的NOS側重,各具優勢與不足,所以“整體科學”的原型評價倡導多種類型原型評價的整合,以發揮彼此的互補與協同效應,較為全面地評價學生的NOS理解。
具體而言,當代類原型評價與學生當下生活緊密相關,可以明顯提高學生NOS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使抽象的NOS具象化。同時因其仍處爭論之中,并無確定答案,有利于學生運用NOS的暫定性、主觀性與不確定性、多重視角等方面綜合分析科學家如何解釋相互矛盾的證據和彼此的社會互動、個人信念影響其主張的機制及科學和技術如何與公共生活中的其他領域相互作用;分析科學家對相互矛盾的證據的解釋和評價的可靠性。但摘自當代報紙、廣告的當代案例較少提及科學家科學實踐及方法論細節。這使其在評價學生NOS的科學實驗和某些認知維度上欠缺,因此,基于報紙文章的當代案例的原型評價是不完整的。
探究類原型評價則包含較為廣泛的科學實踐與科學認知細節——識別問題、提出問題、設計和進行調查、分析和解釋數據以及制定、溝通和捍衛假設、模型和解釋方面的內容等。學生可以運用對NOS的認知性與實驗性維度理解對其進行綜合分析。但探究類原型評價在NOS的暫定性與社會和文化嵌入性等維度缺失,使其亦是不完整評價。
歷史類原型評價因為多聚焦于科學人物史、認識史或思想觀念史等內容,便于調動學生NOS的暫定性、社會性及社會和文化嵌入性方面對其綜合分析。而這些優勢是前兩類原型評價所不具備的。但由于與學生生活距離較遠且具有一種確定性,歷史案例易使學生感到陳舊且無用。因此,如何將歷史案例不確定化,對歷史類原型評價者而言是一個很大挑戰。
如表2所示,選取1895年爪哇島的腳氣病案例作為評價學生NOS理解水平的歷史情境,便于引導學生從NOS的社會性及社會和文化嵌入性方面進行解釋與評價公共決策中的科學主張或科學行動的可靠性。這是其余兩類原型評價所不能達成的。但誠如前文所述,該案例可能因為年代過于久遠,而使學生感到陳舊無用。
因此,理想的原型評價應是歷史類原型評價、當代類原型評價與探究類原型評價的整合式評價,在“舊的、無關的、缺乏實驗性、確定性”的歷史案例和“真實的、相關的、不確定”的當代案例及“實驗性”的探究案例的結合中,實現互補協同。
2.2.3 原型評價特征
相較于VNOS工具,原型評價具有真實性、意義性、適應性等多種特征。具體而言,真實性即真實的上下文情境。本著真實評估的精神,原型評價能反映NOS知識應用的各種復雜、真實情境,要求學生對于他們在生活經歷中遇到的類似案例發表評論。亦即,學生通過一個具體案例來直接闡釋對NOS的理解。這同時可為學生構建特定視角——可能是研究人員、政策制定者、消費者或公民視角,亦可能特定性別、種族或階級視角。因為案例可以從媒體的新聞報道中獲得,亦可以從科學雜志或歷史期刊中收集,可以是當代的、歷史的或實驗探究的,因此案例的來源與類型多種多樣。這種多樣性允許教師基于當地環境及專長選擇適合學生的案例,因此其亦是開放的。
意義性即原型評價與學生日常生活相關。特別是從與學生當下生活緊密聯系的當代報紙、廣告摘錄而成的當代類原型評價可以極大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看到NOS學習的實用性與意義性。適應性即評價可以適應多種評價形式——對評價的NOS維度類目深度進行水平劃分及更精細化地描述以便于教師記錄自己與學生在課堂教學中的NOS理解水平及其發展,從而進行診斷性評價;同時亦可對不同維度類目加權,并將各類目分數累加,得到學生總NOS得分。總分可較為粗略表征學生NOS理解實際水平與目標水平的相對差距,從而進行終結性評價。由于其注重的是對于學生NOS知識理解的深廣度的客觀評價,而不需訪談評價對象,因此,評價亦可以很好地適應大規模測評。管理者可依據NOS總分評估不同層次學生群體的NOS理解水平。
3 審視及展望
3.1 范式的意義
作為替代方案的“整體科學”范式,在當前國際NOS范式更替大潮中占有重要位置,具有突出的理論與應用意義。總體而言,“整體科學”范式將其目標奠基于運用NOS以綜合分析SSI相關主張的可靠性之上,這是一種整體性功能科學素養而非共識范式那種片面化的知識性素養。相應地,這種功能性素養決定了學生所掌握的NOS維度應與其真實生活中所面對的SSI維度的一致性。又因SSI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和立場的矛盾性,所以不應如共識范式那樣將NOS表征為規范性、精確性的統一化陳述條目,而應是中立性、開放性的多樣化模糊類目。這種中立、多樣與模糊可使學生避免陷入偏狹的價值立場,而僅專注于各種SSI主張的可靠性分析上。而且,開放與模糊的NOS類目亦便于學生作為分析指南,從而不至于過分隨意或約束。故而這種類目式的NOS內部就不是單一機械關系而是多樣化功能有機關系,它們在多樣化的SSI分析中統一協調,共同指向學生的綜合性分析能力的培養與提高。
這種結構體系要求其評價工具開發首先應是真實且有意義的;其次其評價框架維度亦應與其體系一致,包含廣闊的社會、認知與實驗3維;其評價項目亦應立足于具體案例語境,聚焦于評價學生的綜合分析能力,而非單純的NOS回憶與復述的低階能力。所以案例應是多樣的,能夠覆蓋理論體系的所有NOS方面,所提問題應是認知性的,能夠調動學生運用NOS分析案例中相關主張的可靠性。
3.2 范式的不足
“整體科學”范式亦存缺陷。首先是其處于起步階段而缺乏充足的實證研究基礎,實踐效度仍待展開。對此,奧爾欽亦有清醒的認識,并認為“在進一步研究中,……很快就會知道原型評價是否符合有效性標準,其理論框架是否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整體科學范式與互補性NOS教學方法是否合理”[9]。其次,該范式所含NOS維度及其類目過多,難以在實際教學中全部教授。需要結合學生身心發展對其進一步精簡。誠如萊德曼小組所質疑道:“為什么我們希望K12學生能夠一下子理解科學的一切,或者整體科學,而不是將這種要求拓展至他們大學預科教育中呢?[10]”
3.3 研究展望
為推動NOS研究不斷發展,未來NOS研究應遵循融合化的方向。應以更為廣博的理論視角審視共識范式、“整體科學”范式以及其他范式的相應爭論、各自優勢與不足,在充分吸收彼此合理思想與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多種范式有機融合,發揮協同效應。既不能極端認為“整體科學”范式完全是一種對共識范式的歪曲,亦不能在未對共識范式充分理解與吸收之前就匆忙斷言“共識范式已危機重重、陳舊不堪”,并將其完全拋棄,徹底否定。
可考慮在凝練科學家、科學哲學家、科學教育研究者等群體共識及將各種范式有機融合的基礎上,重建新的NOS理論體系。也可開發出與其理論相適應的面向師生NOS理解、課程與教材NOS表征的評價工具,并通過大量實證研究持續反饋修正與完善,不斷提高新范式的科學性、合理性、全面性與有效性。
參考文獻:
[1]Olson, J. K. The Inclusion of the Nature of Science in Nine Recent Inter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Documents [J]. Science & Education, 2018, (27): 637~660.
[2]Jho, H.. Trends in research on the nature of science: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with R-mapping tool [J]. Journal of Learner-Centere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2018, 18(18): 937~956.
[3]Hodson, D. et S. L. Wong. Going Beyond the Consensus View: Broadening and Enriching the Scope of NOS-Oriented Curricula [J]. Canadian Journal of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2017, 17(1): 3~17.
[4]Allchin, D.. Evaluating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of (whole) science [J]. Science Education, 2011, 95(3): 518~542.
[5][9]Allchin, D.. Towards clarity on Whole Science and KNOWS [J]. Science Education, 2012, (96): 693~700.
[6]Allchin, D.. Beyond the Consensus View: Whole Science [J]. Canadian Journal of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2017, 17(1): 18~25.
[7][8]Allchin, D.. Teaching the nature of science through scientific error [J]. Science Education, 2012, (96): 904~926.
[10]Schwartz, R., Lederman, N. G., Abd-El-Khalick, F. A Series of Misrepresentations: A Response to Allchins Whole Approach to Assessing Nature of Science Understandings [J]. Science Education, 2012, 96(4): 685~69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人才啟動經費項目資助(2023r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