萸地補腎養肝方對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患者肝腎功能的保護作用
何文峰 鐘和林 米雨秋 王雪松 丁寧
肝硬化患者由于內臟動脈血管擴張,門靜脈血液處于高凝狀態,大量組織液聚集腹腔,導致有效循環血容量顯著下降,腎內血流嚴重不足,腎血管強烈收縮,腎小球濾過率、腎皮質血流量也進行性降低,出現腎功能衰竭,引發肝腎綜合癥[1]。肝腎綜合癥是肝硬化的嚴重并發癥之一,通常無腎器質性病理改變,屬于進展性腎功能衰竭[2]。中醫認為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屬于“鼓脹”的病癥范疇,該病的主要病因為脾失健運,過食肥厚,或嗜酒戀熱,引起濕熱濁毒留滯于機體,脾胃氣機升降失常,或憂思過度導致肝氣郁結,損傷脾陽,或陽氣虛弱,導致脾運化失常,水液停聚于中焦,發為鼓脹[3]。該病還與肝失疏泄有關,患者平素急燥易怒,造成肝氣郁結,氣機失常,水液停滯于腹中,可見腹大脹滿,氣滯則血行不暢,瘀血阻于兩脅,發為積聚,肝木克脾土,肝氣郁結,影響脾胃功能,水濕停滯加重鼓脹[4]。該病還與腎失氣化有關,患者平素勞欲無度,或病久不愈,耗損精氣,腎無力維持三焦功能正常,津液輸布失常,腎氣不足無以濡養肝脾,氣滯則水停,發為鼓脹;腎陽不足,無法推動血行,導致氣滯血瘀,瘀阻腎絡,水濕凝聚,加重水停[5]。中醫在改善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患者的肝腎功能的作用受到廣大醫師的關注,本研究擬通過在常規西醫治療基礎上,聯合萸地補腎養肝方治療,分析對患者肝腎功能的影響,為臨床研究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取2020年3月~2022年10月在中鐵二局集團醫院就診的81例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患者,參考隨機數字表法分為研究組41例和對照組40例。研究組38例(脫落3例)中男性30例,女性8例,年齡51~81歲,平均(62.07±6.23)歲,肝硬化病程3.5~22年,平均(11.09±4.31)年,肝腹水分級分為Ⅰ級9例、Ⅱ級17例、Ⅲ級12例;child-Pugh分級分為B級17例、C級21例;肝腎綜合征分型分為Ⅰ型6例、Ⅱ型32例;肝硬化分為乙型肝炎肝硬化19例、酒精性肝硬化15例、膽汁性肝硬化2例、丙肝肝硬化2例。對照組38例(脫落2例)中男性32例,女性6例,年齡50~80歲,平均(62.39±6.11)歲,肝硬化病程4~21年,平均(11.38±4.15)年,肝腹水分級分為Ⅰ級11例、Ⅱ級16例、Ⅲ級11例;child-Pugh分級分為B級19例、C級19例;肝腎綜合征分型分為Ⅰ型7例、Ⅱ型31例;肝硬化分為乙型肝炎肝硬化17例、酒精性肝硬化16例、膽汁性肝硬化3例、丙肝肝硬化2例。兩組基線資料無明顯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內容經中鐵二局集團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文號:20200121號)。
1.2 納入標準
(1)符合2017版《肝硬化腹水及相關并發癥的診療指南》中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的診斷標準[6],肝硬化病史,伴有肝腹水,血清Scr>133 μmol/L,停用利尿劑至少2天經白蛋白擴容Scr無改善,排除休克、腎實質性疾病,腎臟超聲檢查無異常;(2)滿足《肝硬化腹水中醫診療專家共識意見》中肝腎陰虛證的診斷標準[7],主癥為腹大脹急、目睛干澀、腰膝酸軟,次癥包括牙齦出血、面色晦暗、五心煩熱、口燥咽干,舌紅苔少,脈細數;(3)患者預計生存期不低于1個月;(4)患者自愿簽訂知情同意書。
1.3 排除標準
(1)其他因素引起的肝腹水;(2)伴有心腦血管、肺、腎等嚴重病變;(3)原發性腎臟病變;(4)近期服用兩性霉素B、氨基糖苷類抗生素等明確腎毒性藥物及擴血管藥物;(5)其他藥物或疾病引起的腎功能損傷;(6)精神疾病或認知、語言功能異常。
1.4 脫落標準
(1)主要要求退出或放棄治療;(2)病情進展迅速,需終止本研究方案;(3)失訪;(4)發生嚴重不良反應或并發癥需特殊處理。
1.5 分組與給藥
對照組:常規西醫治療,合理飲食,控制鈉攝入量和攝水量,補充人血白蛋白,積極核苷類藥物抗病毒治療,口服螺內酯片(江蘇正大豐海制藥有限公司,20 mg/片,生產批號:20200108,20210211,20220109),每日1次,每次40 mg,靜脈滴注前列地爾(西安力邦制藥有限公司,10 μg/支,生產批號:20200201,20210106,20220105),每日1次,每次劑量10 μg,皮下注射醋酸奧曲肽(上海上藥第一生化藥業有限公司,0.1 mg,生產批號:20200210,20210114,20220109),每日2次,每次0.1 mg,連續治療3周。研究組:在對照組基礎上,給予萸地補腎養肝方:熟地黃30 g、當歸15 g、白術12 g、蟬蛻15 g、葶藶子30 g、豬苓15 g、茯苓15 g、山萸肉15 g、澤瀉20 g、陳皮10 g、桂枝10 g。由中鐵二局集團醫院自動配方顆粒藥房提供顆粒制劑,每劑使用100 mL的沸水溶解后,于早晚兩次溫服。連續治療3周。
1.6 觀察指標
1.6.1 兩組的療效比較[7]在治療3周后統計療效,醫師告知患者記錄治療前后當日的24小時的尿量,擬定分為(1)顯效,癥狀顯著減輕,腎功能指標復常,24小時尿量高于1500 mL;(2)有效,癥狀減輕,尿量增加,但未超過1500 mL,腎功能好轉,但未復常;(3)無效,未達到有效標準。
總有效率=(38-無效)/38×100%
1.6.2 兩組的中醫證候評分比較 在治療前后的第2天,參考《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中量化分級標準擬定[8],對肝腎陰虛證進行量化評分,對主癥按照“無—0分、輕—2分、中—4分、重—6分”進行評分,對次癥按照“無—0分、輕—1分、中—2分、重—3分”進行評分,各癥狀評分的總和為中醫證候評分。評分由同一醫師將數據錄入電腦軟件,并反復校對后,計算出最終結果。
1.6.3 兩組主要肝腎功能指標比較 在治療前后的第2天,患者進入檢驗科進行血尿常規檢查,運用全自動生化儀(英諾華DS-301型)檢測血清中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TB)、谷草轉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γ-谷氨酰轉肽酶(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尿素氮(urea nitrogen,BUN)的水平。
1.6.4 兩組血漿滲透壓評分比較 在治療前后的第2天,運用血漿滲透壓評分對患者的預后進行評估,參考患者治療前后的血常規指標中血鈉、血鉀、血糖、白蛋白、纖維蛋白原的水平。有效晶體滲透壓評分:0分為有效晶體滲透壓≥280 mmol/L,每下降20 mmol/L則評分升高2分,最高評分為10分;膠體滲透壓評分:0分為膠體滲透壓≥25 mmHg,每下降5.0 mmHg則評分升高2分,最高評分為10分。評分由同一醫師將數據錄入電腦軟件,并反復校對后,計算出最終結果。
有效晶體滲透壓=2×(血鈉+血鉀)+血糖(mmol/L)
膠體滲透壓=6.89×(纖維蛋白原+白蛋白)-5.68(mmHg)
血漿滲透壓評分=有效晶體滲透壓評分+膠體滲透壓評分
1.6.5 兩組病情程度比較 在治療前后的第2天,運用終末期肝病模型評分(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對患者的病情程度進行評估[9],參考患者治療前后血常規和凝血指標的指標,包括血清TB、凝血酶原時間、Scr的水平。 其中病因為酒精性肝硬化、膽汁性肝硬化記為0分,其他記為1分。評分由同一醫師將數據錄入電腦軟件,并反復校對后,計算出最終結果,評分取小數點后2位。
MELD=3.8×In(TB)+11.2×In(凝血酶原時間)+9.6×In(Scr)+6.4×(病因)
1.6.6 兩組腎動脈血流動力學比較 在治療前后的第2天,患者于清晨進入我院超聲檢驗科進行腎血流動力學檢驗,檢測前禁食8小時,排空膀胱,患者取側臥位,超聲探頭設定為3.0 MHz頻率,與皮膚成60°角觀察腎的血流頻譜,檢測時囑患者憋氣數秒多次,重點測量腎主動脈主干、葉間動脈、腎竇內段動脈的血管阻力指數(resistance Index, RI),每個患者獲得3個有效數據取平均值為最終數據。
1.7 統計學處理

2 結果
2.1 兩組在治療3周的總有效率比較
研究組患者治療3周的總有效率為94.74%,明顯高于對照組的78.95%,經χ2檢驗,差異顯著(P<0.05)。見表1。

表1 兩組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患者的對比(例數)
2.2 兩組尿量比較
治療后兩組的24小時尿量明顯高于治療前,且研究組的24小時尿量明顯高于對照組,經t經驗,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見表2。

表2 兩組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患者的24小時尿量變化天)
2.3 兩組中醫證候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的中醫證候評分無明顯差異(P>0.05);兩組治療后的中醫證候評分顯著下降,研究組下降程度高于對照組,經t經驗,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見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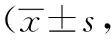
表3 兩組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患者的中醫證候評分比較分)
2.4 兩組的肝腎功能指標比較
治療前兩組的TB、AST、ALT、GGT、Scr、BUN無明顯差異(P>0.05);兩組治療后的TB、AST、ALT、GGT、Scr、BUN顯著下降,研究組較對照組降低更明顯,經t經驗,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見表4。

表4 兩組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患者的TB、AST、ALT、GGT、Scr、BUN比較
2.5 兩組血漿滲透壓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的有效晶體滲透壓、膠體滲透壓、血漿滲透壓評分無明顯差異(P>0.05);兩組治療后的有效晶體滲透壓、膠體滲透壓、血漿滲透壓評分均低于治療前(P<0.05);研究組的有效晶體滲透壓、膠體滲透壓、血漿滲透壓評分低于對照組,經t經驗,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見表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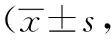
表5 兩組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患者的有效晶體滲透壓、膠體滲透壓、血漿滲透壓評分比較分)
2.6 兩組MELD評分比較
兩組治療后的MELD顯著低于治療前,且研究組的MELD低于對照組,經t經驗,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見表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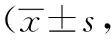
表6 兩組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患者的MELD評分比較分)

表7 兩組的腎主動脈主干、葉間動脈、腎竇內段動脈的RI比較
2.7 兩組血流動力學比較
兩組治療后的腎主動脈主干、葉間動脈、腎竇內段動脈的RI低于治療前,且研究組較對照組更低,經t經驗,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見表6。
3 討論
病毒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肝、酒精肝、自身免疫病變的因素均可導致肝臟功能損傷,若不及時減輕,肝細胞損傷可導致肝臟彌漫性纖維化,形成假小葉,進而導致肝硬化形成,隨著病情進展及肝功能進行性下降,可出現肝腹水,肝功能處于失代償期,顯著增加患者的病死率[10]。肝硬化腹水若不及時控制病情,可發展為上消化道出血,出現肝性腦病、肝腎綜合征等嚴重并發癥,甚至發展為肝癌,危及患者生命健康[11]。目前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了,可能與淋巴回流受阻、低蛋白血癥、門脈系統高壓、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失衡等因素有關[12]。肝硬化肝腎綜合征患者的1年發病率約為25%,5年發病率可達到50%。II型肝腎綜合征的臨床特征為肝功能緩慢穩定減退,預后極差,肝移植是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的首選治療方式,但由于手術難度較大、費用較高、肝源短缺等,導致大多數患者無法獲得肝移植救治。近幾年隨著對肝腎綜合征研究的深入,運用血管收縮藥治療效果取得了較大進步,通過收縮內臟血管,增加有效循環血容量,抑制局部構成交感神經系統、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顯著改善肝腎血流動力學,促進腎臟功能恢復,對改善患者預后提高生存率具有重要臨床意義[13]。
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的主要病位在肝、腎,與心脾關系密切,病變日久易產生血瘀、水停、氣滯等病理產物。有學者認為,該病的主要病因為陽氣虧虛,無法溫熙機體和推動氣血運行,瘀阻于內,水濕為患,隨著病情發展,心陽俱虧,血少水多,釀成鼓脹[14]。筆者認為該病的根本病機為肝腎陰虛,肝失疏泄,則氣滯水停,腎氣化失常,則水液輸布異常,肝腎受損,水液停聚于腹中,發為腹大脹急。肝血不足,無法濡養雙目,可出現目睛干澀;肝氣虛弱,則攝血無力,氣血運行無法固攝而妄行,肝陰不足無法斂血于肝,陰虛生火,灼傷陰絡,發為皮膚瘀斑、血溢脈外,肝氣郁結則面色晦暗,肝陰不足,則無以濡養頭面,發為面色晦暗;陰血不足,津液耗損,虛火灼傷陰液,導致腎陰津不足,陰虛則火旺,發為五心煩熱;該病以肝腎陰虛為本,以水濕、瘀血為主要標實,臨床治療當以補虛為主,兼以泄實[15]。
本文選用萸地補腎養肝方治療,方中以酒萸肉、熟地黃為君藥,能滋肝補腎,固腎攝精,二藥加強滋補肝腎陰虛之效;同時以茯苓、澤瀉、豬苓為臣藥,用以利水滲濕,健脾瀉熱。佐以當歸能養肝補血,行氣通經;陳皮、白術能健脾行氣,消痰滲濕;佐以葶藶子、蟬蛻能消腫利水,解表宣肺;桂枝能助陽補氣,陽中求陰;全方合用既能滋補肝腎陰虛,又能理氣祛除水停之邪,滋陰和利水并用。
本文結果顯示,聯合萸地補腎養肝方治療的患者3周總有效率明顯高于常規西醫治療,24小時的尿量得到進一步提高,中醫證候評分進一步降低,結果表明,萸地補腎養肝方有助于提高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患者的臨床療效,促進患者尿液排出,體現出萸地補腎養肝方明顯的“利水”作用,聯合溫陽理氣藥物可達到利水不傷陰,補陰不利濕的功效,還進一步減輕了患者的中醫癥狀,體現出中醫藥在減輕中醫臨床癥狀的獨特優勢。本研究還發現,研究組患者治療后TB、AST、ALT、GGT、Scr、BUN等主要肝腎功能指標降低程度明顯優于對照組。提示,萸地補腎養肝方有助于改善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患者的肝腎功能,對減輕肝腎功能損傷具有積極意義。血漿滲透壓評分、MELD評分是臨床常用于評估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患者患者病情程度的常用指標,與患者而后密切相關。本文結果發現,聯合萸地補腎養肝方治療的患者在治療后血漿滲透壓評分、MELD評分的降低程度明顯優于常規西醫治療。結果表明,萸地補腎養肝方有助于控制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的病情發展,對改善患者預后具有積極意義。本研究還發現,研究組治療后腎血流動力學水平改善程度明顯優于對照組。結果表明,萸地補腎養肝方有助于改善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患者的腎血流動力學水平,有助于改善腎組織的血液循環,對恢復腎功能具有積極意義。
綜上所述,萸地補腎養肝方有助于提高肝硬化合并肝腎綜合征的療效,提高患者的尿量,進一步減輕臨床癥狀,控制病情程度,改善肝腎功能及預后,進一步改善患者的腎血流動力學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