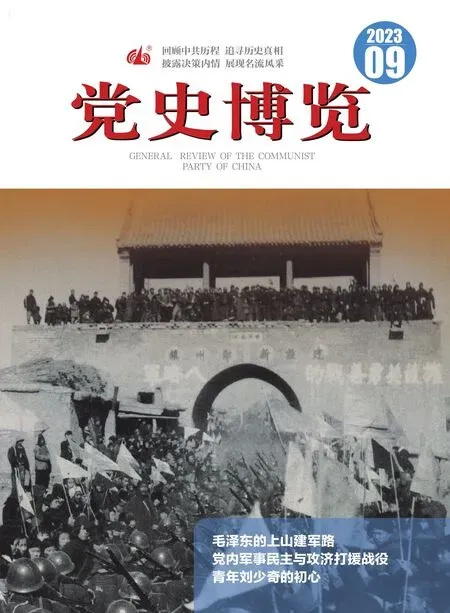毛澤東的上山建軍路
■蔣建農
毛澤東的軍事生涯是從1927年開始起步的。雖然在辛亥革命軍起時,他奮而投軍,在湖南新軍有過不到半年列兵的經歷,但和那些軍校出身的職業(yè)軍人相比,他的軍事閱歷基本上是空白。然而,在風云激變的1927年,毛澤東斷言“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率領一支臨時組合的隊伍,并且在經受秋收起義失敗的重創(chuàng)后,硬是在井岡山上闖出一片新天地,他本人也從此開始,逐步成長為人民軍隊的統(tǒng)帥。
秋收起義部隊是真正的“工農兵”結合
“毛澤東已經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領軍人物”
和五四運動時期成長起來的許多中共早期領導者一樣,毛澤東經歷了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實踐,但毛澤東參與這些社會實踐之深入和理論建樹之大,則是最為突出的。以他投身農民運動的實踐為例。1917年7月,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就和同學蕭子升以“游學”的方式,到湖南長沙、寧鄉(xiāng)、安化、益陽、沅江5個縣,進行了行程400余公里的農村調查;1923年4月,他派水口山的工人劉東軒和安源路礦的工人謝懷德(均為共產黨員)回他們的家鄉(xiāng)衡山岳北白果鄉(xiāng)開展農民運動;同年6月,正是在毛澤東等關于要注意農民運動的提議下,中共三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農民問題決議案》;1925年2月到8月,毛澤東發(fā)動和領導了韶山地區(qū)的農民運動,從進行農村調查到辦農民夜校啟發(fā)農民覺悟,再到組織雪恥會、農民協(xié)會,進而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發(fā)展黨員,對如何開展農運積累了第一手經驗。此后,他主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面向全國招收學員,其中比較著名的學員有王首道、吳芝圃和張明遠,他們后來分別成為湘贛、睢杞、冀東根據(jù)地的主要領導人。這一時期,毛澤東撰寫并發(fā)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tài)度》等理論文章,編印《農民問題叢刊》,并自1926年11月起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主持制定《目前農運計劃》。毛澤東已經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領軍人物。
槍桿子里出政權
身處國共合作第一線的毛澤東,是在同國民黨新、老右派的激烈斗爭中,認識到武裝斗爭重要性的。1926年3月18日,在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兩天前,毛澤東就鄭重地告誡“各位同志要鑒往知來,懲前毖后,千萬不要忘記‘我們不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敵人便給我們以致命的打擊’這句話”。“中山艦事件”發(fā)生的當晚,毛澤東第一時間提出武裝對抗蔣介石的挑釁。據(jù)茅盾回憶:毛澤東找到蘇聯(lián)顧問團代理團長季山嘉和中共廣東區(qū)委書記陳延年,要求動員所有的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和監(jiān)察委員,集中于肇慶,依靠駐扎在那里的葉挺獨立團,開會通電討蔣,予以嚴辦,削其兵權,開除其黨籍。同時爭取第1軍王柏齡師以外的軍官士兵和國民革命軍第2、第3、第4、第5、第6軍的力量。此事雖然得到陳延年的贊同,卻因季山嘉的堅決反對而不了了之。
毛澤東從中國農民運動的特點出發(fā),認為“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爭,政治上只是求得集會結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時破壞資產階級之政治地位。鄉(xiāng)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這個地主政權即軍閥政權的真正基礎),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這是當時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最大的特色”。因此,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的發(fā)言中,痛心地總結了中共以往在軍事方面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的沉痛教訓,進而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
拋棄國民黨的旗幟
基于“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的思想認識,毛澤東在籌備秋收起義時,于1927年8月20日致信中共中央,非常明確地提出:“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以與蔣、唐、馮、閻等軍閥所打的國民黨旗子相對。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但是,剛剛改組的臨時中央認為,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集團發(fā)動反革命政變,表明資產階級已經叛變了革命,為了抓住小資產階級繼續(xù)革命,還要用國民黨的旗幟,否則有著光榮革命傳統(tǒng)的國民黨的旗幟就會被蔣汪之流篡奪。8月23日,中共中央復信批評湖南省委和毛澤東拋棄國民黨旗幟的主張,強調“此時我們仍然要以國民黨名義來贊助農工的民主政權”。雖經毛澤東反復強調,中共中央仍堅持不同意放棄國民黨的旗幟。無奈,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一樣,也是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進行發(fā)動的。但是和南昌起義有所不同,秋收起義不再使用“國民革命軍”的番號,而是第一次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幟。9月19日,中共中央發(fā)布《關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才正式明令不再使用國民黨的旗幟。
使用“工農革命軍”的旗幟,表明毛澤東要由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領導武裝斗爭的鮮明態(tài)度,是他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正因為“旗幟鮮明”,攻打長沙受挫的秋收起義軍,才能夠在短時間內重振雄風,從而把勝利的旗幟插上井岡山。
工農兵結合開展武裝斗爭
在中共黨內,毛澤東是最早認定農民是中國革命主力軍的人之一。他認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xiàn)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因此,以農民為主力開展武裝斗爭,毛澤東是黨內最早、也是最堅定的實踐者。
在大革命失敗之際,改組后的臨時中央雖然制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也明確要求依靠工農開展武裝斗爭,但是在實際執(zhí)行中卻出現(xiàn)很大的問題。南昌起義主要是依靠中共所掌握或擁護中共主張的一部分軍隊發(fā)動的,沒有有組織的工農群眾參加。中共中央一方面不得不倚重葉挺、賀龍等率領的武裝力量,但同時又對他們心存疑慮,認為他們“仍舊是舊式的雇傭軍隊,不加入工農分子使之改組,是不能擔負革命任務到底的”,唯恐這次起義成為新的軍事投機。南昌起義軍南下失敗后,臨時中央在部署廣州起義過程中,向廣東省委提出“要矯正從前以農民為副力等待葉、賀軍隊到來的錯誤觀念(見中央前次各信),相信農民為暴動的主力”。廣州起義得到了聲勢浩大的廣東農民運動在戰(zhàn)略上的聲援和支持,但實際投入到廣州起義之中的農民數(shù)量很少。廣東省委在總結教訓時指出:“此次暴動,農民群眾很少參加,除石圍塘和黃沙的農民起來占據(jù)車站、四郊有很少的農軍參加作戰(zhàn)外,其附近各縣都未起來,以致反革命軍隊,可以毫無顧慮和障礙很快地來圍擊我們,以至于失敗。”
秋收起義則不同。毛澤東經歷和了解到“馬日事變”發(fā)生后,長沙周圍10萬農軍圍城,卻被許克祥、王東原的2個團撲滅的情況,因此認定,革命發(fā)動時必須有正規(guī)部隊參加。8月18日,他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集中共湖南省委會議討論秋收起義計劃時,明確提出“要發(fā)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團兵力,就可以發(fā)動起來。暴動的發(fā)展是要奪取政權。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wèi)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毛澤東的主張上報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于23日回信批評,認為其暴動計劃“偏重于軍力,好像不相信群眾的革命力量,其結果亦只是一種軍事冒險”。30日,毛澤東根據(jù)他與湖南省委進一步研究后的意見,復信中央,再次強調要把軍事力量與工農群眾的暴動結合起來,并解釋說明暴動的主要戰(zhàn)斗者是工農,調2個團是輔助工農力量之不足,中央的批評是因為不了解此間情形,是不要注意軍事又要民眾武裝暴動的一個矛盾政策。
最終,在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隊伍中,既有原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衛(wèi)團(以下簡稱警衛(wèi)團),又有安源路礦的工人和湘鄂贛等地區(qū)的農民自衛(wèi)軍,真正是“工農兵”的結合。
選擇恰當?shù)牡貐^(qū)開展武裝斗爭
在工人階級聚集的大城市舉行武裝暴動以奪取全國政權,是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tǒng),并有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先例可循;在中國,遠有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天下響應的成功,近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因此,以奪取和占領中心城市為主要目標的“城市中心論”,成為當時中共中央的首選和全黨的共識。大革命失敗后,根據(jù)蘇聯(lián)軍事顧問加倫的建議,中共中央把廣東作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地區(qū)。南昌起義后,起義軍馬上南下廣東;廣州起義的目標也更為明確。中共中央發(fā)動湘鄂粵贛四省秋收起義的目的,起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呼應南昌起義軍重建廣東革命根據(jù)地的計劃。
毛澤東的不同凡響在于:一是他把發(fā)展工農武裝的著眼點放在廣大農村和億萬農民群眾身上,而不是放在大中城市。長沙“馬日事變”后,毛澤東在聽取由湖南到武漢的黨員和工農骨干情況匯報時強調:長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農村去,下鄉(xiāng)組織農民,發(fā)動群眾,恢復工作,山區(qū)的人上山,濱湖的人上船,拿起槍桿子進行斗爭,武裝保衛(wèi)革命。二是他不贊同把主要力量都集中于廣東。8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指出:湖南省委要組織一個師的武裝去廣東是很錯誤的。大家不應只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眾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當前處在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他說:“前不久,我起草經常委通過的一個計劃,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占據(jù)五六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fā)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
毛澤東提出并堅持以湖南為中心依靠農民開展武裝斗爭,不是別出心裁,而是以湖南已經形成的雄厚的革命力量為支撐和保障的。首先,早在國共合作之初,毛澤東就寫信給國民黨中央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和副部長林伯渠,商量在湖南發(fā)展國民黨組織的事宜,并親自擔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的“籌備員”,以后又有多次的指導。在他和中共湖南區(qū)委的領導下,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湖南各級國民黨黨部從無到有地發(fā)展起來。正如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中所指出的:“湖南國民黨左派的下級黨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礎,15萬到20萬的左派黨員及其組織曾在我們指導之下奮斗到現(xiàn)在。”其次,湖南的農民運動是當時最發(fā)達的,到1927年5月,農民協(xié)會的會員已達600萬,占全國農民協(xié)會會員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再者,按照毛澤東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時給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他們大力在農村發(fā)展中共黨員,到大革命失敗時已經發(fā)展農村黨員2萬人,占全國中共黨員人數(shù)的1/3。湖南省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績,使得毛澤東得以堅持以湖南為中心、依靠中共和工農的力量開展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這既是他在秋收起義隊伍受挫后不再堅持攻打中心城市的原因所在,也是他后來選擇在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獨立自主探尋中國革命之路的組織條件和實力依托。
毛澤東與秋收起義部隊等的歷史淵源

1922年9月18日, 安源路礦工人慶祝罷工勝利紀念
其實,毛澤東與秋收起義軍,及后來與之會師共同開創(chuàng)井岡山根據(jù)地的部隊,即由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和湘南暴動的農軍,還有著一些直接和間接的歷史淵源。
組織安源路礦工人投身秋收起義軍
安源路礦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工礦企業(yè)和最早的產業(yè)工人聚集區(qū)之一。1921年12月,毛澤東到安源礦區(qū)調查工人生活狀況,啟發(fā)工人覺悟,播撒工人運動的火種。此后,毛澤東任書記的中共湘區(qū)委員會陸續(xù)派李立三、劉少奇、蔣先云、易禮容、毛澤民、毛福軒等多批次的骨干,到安源開展工人運動。由此,安源誕生了中共在全國產業(yè)工人中的第一個支部,組織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創(chuàng)辦了中國工人階級最早的經濟事業(yè)組織——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成立了中共歷史上最早的黨校——中共安源地委黨校。鑒于安源路礦已經形成一支成熟的工人隊伍,毛澤東于1922年5月和9月,兩次到安源進行具體的部署。9月14日,安源路礦工人舉行大罷工,并取得徹底的勝利。1923年4月,在京漢鐵路“二七慘案”后全國工人運動陷入低潮的時刻,毛澤東在去上海前,專門帶蔣先云再次去安源,召開工作會議,對以后的工作進行了部署,提出“彎弓待發(fā)”的策略原則,使得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巍然獨存”。到1927年上半年,安源有青年團員600多人,到秋收起義前,安源有3個區(qū)委、17個直轄黨支部和700多名中共黨員,最多時參加工會的工人達1.2萬多人。
安源路礦的工人成批次地匯入與秋收起義和開創(chuàng)井岡山根據(jù)地相關的軍隊,有兩批。
1927年“馬日事變”后,安源的礦工在湖南省總工會和省農協(xié)的組織下,和各地的農軍一同參加了圍困長沙的斗爭。圍城失敗后,湖南的反動軍閥在6月初對安源工人進行報復性鎮(zhèn)壓。危急時刻,在蔡和森與毛澤東的一再要求下,中共中央于6月7日和24日,兩度討論改組湖南省委問題,先后決定由毛澤東出任臨時省委書記、省委書記。毛澤東因此有機會于6月下旬短暫地回湖南,進行應變部署。毛澤東在湖南強調,“各縣工農武裝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來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桿子對付槍桿子,不要再徘徊觀望”。根據(jù)毛澤東和湖南省委的指示,為保存精干力量,中共安源地委改造礦警隊,派了許多黨、團員和工會骨干到礦警隊任職,實際控制了礦警隊。7月23日,湖南省委給毛澤東并轉中共中央的信稱:“安源可借礦警局練兵二百名,而一兩股兵力可以上山。”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楊立三作為國民革命軍第11軍24師(葉挺為師長)的新兵招募委員來到安源,順利地從安源招募了100 多名礦工組成一個連(連長黃贊)。這個連成為正在籌建的警衛(wèi)團新兵營的一部分,后來這個營被編為警衛(wèi)團第3營。
另一批就是秋收起義前以安源工人糾察隊、礦警隊和萍鄉(xiāng)等地的農民自衛(wèi)軍組建的秋收起義軍第2團。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和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奉命組織包括安源在內的湘贛邊界7個縣的秋收起義。安源路礦的黨團工會,在蔡以忱的領導下,積極籌備。與此同時,萍鄉(xiāng)、衡山白果區(qū)的農軍和王興亞率領的安福、蓮花、永新等地的農軍,齊聚安源。9月初,毛澤東趕到安源張家灣,主持召開了著名的“安源會議”。會議決定把駐修水、安源和銅鼓的起義隊伍編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下轄3個團,兵分三路,直插瀟湘,進攻長沙。5日,毛澤東把在安源的各路力量組成第2團,以王興亞為團長,蔡以忱為黨代表。第2團下轄3個營9個連,共2000余人。另據(jù)9月27日任弼時就湖南秋收起義情況給中央的報告記載:秋收起義爆發(fā)后的第三天,“安源礦警及王興(亞)部(系江西的農軍)五百余人會同工人炸彈隊、宣傳隊將近二千人于十一號清晨進攻萍鄉(xiāng)不遂,乃棄萍攻老關,十二號破醴陵城”,“十五號破瀏陽”。也就是說,至少有1400人以上的安源工人,作為工人階級的代表參加了秋收起義軍。安源工人在秋收起義中的作用,當時就得到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的高度肯定,他在10月8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在秋收暴動經過中,湖南的無產階級——安源工人、鐵路工人等的奮斗精神特別表現(xiàn)得十分堅固和勇敢,確是革命的先鋒隊。”
應使湖南每個青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
隨著北伐軍的凱歌行進,1927年初,國民政府自廣州遷至武漢。這給毛澤東開展農民運動提供了更廣闊的天地。他被聘請為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農民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委員、全國農民協(xié)會臨時執(zhí)委會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部長),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培訓農民運動骨干800余人。這一時期,毛澤東關于農民運動的活動,主要有:
一是整合全國農民運動力量,培養(yǎng)武裝暴動骨干。1927年4月9日,中華全國臨時農民協(xié)會正式成立,全國參加農民協(xié)會的農民超過1000萬。
張國基回憶,毛澤東在武昌主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時,每天都到講習所一兩次,檢查教學情況。陳克文回憶,和在廣州舉辦的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一樣,名義上同是隸屬于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但武昌農講所“實際是完全獨立的”,“所里一切訓練工作全在毛周兩人(指毛澤東和農講所教務主任周以栗) 手上”。他說,毛澤東“一方面調查農村實況,了解農民生活,找尋他的農運理論根據(jù),創(chuàng)造他的革命策略。又一方面指示他的黨徒組織農民,鼓動農民,布置共產黨的勢力,準備農村暴動。講習所的農運理論,便全以老毛的調查所得和他的意見為張本”。
二是致力于解決農民土地問題。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毛澤東贊同中共湖南區(qū)委李維漢關于應該著手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實現(xiàn)耕地農有的主張,陳獨秀等則反對把贊成與不贊成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視為區(qū)分左右派的標準,認為目前主要是滿足農民減租減息和廢除苛捐雜稅的要求,而馬上解決土地問題的條件不成熟。
在目睹了勢如暴風驟雨般的湖南農民運動后,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寫道:“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問題有兩個,即資本與土地。這兩個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了。”此后,毛澤東積極地為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奔走呼號。在撰寫和發(fā)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的同時,他和鄧演達、陳克文聯(lián)名向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提交《土地問題案》 (通過時為《關于農民問題的決議案》)和《對農民的宣言》,力圖“確定一個實行分給土地與農民的步驟”。他認為土地沒收的標準和分配的方法,是解決土地問題的中心問題,主張“所謂土地沒收,就是不納租,并無須別的辦法。現(xiàn)在湘、鄂農民運動已經到了一個高潮,他們已經自動地不納租了,自動地奪取政權了。中國土地問題的解決,應先有事實,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認他就得了”。1927 年4 月中旬,他召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連續(xù)開會三天,討論如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提出“要沒收全部出租的土地”,“進而徹底消滅土地私有制”,準備提交中共五大討論,但是被陳獨秀拒絕。
盡管如此,毛澤東仍然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方案的制定上,并認定土地問題是喚起廣大農民覺悟和投身土地革命洪流的關鍵。秋收起義前,他在湖南省委討論土地綱領時發(fā)言的精神被彭公達概括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即“現(xiàn)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權的時期,此時黨對農民的政策,應當是貧農領導中農,拿住富農,整個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對地主階級不是在沒收他們土地時候讓步,應在土地沒收之后去救濟土地已被沒收的沒有勞動能力的地主家庭,并且只要他們能耕種,仍須拿與農民同等之土地給他們耕種,以消滅地主階級”。這是中共第一個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
三是力主并力行建立農民武裝。毛澤東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時,就叮囑湖南省委要把農民武裝“確實普及于七十五個縣二千余萬農民之中,應使每個青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根據(jù)他的指示,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領導下,湖南省有45個縣組織起農民自衛(wèi)軍或工農義勇隊。這成為毛澤東發(fā)動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的重要生力軍。
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叛亂,隸屬于武漢政府的北伐軍主力正在第二次北伐的河南前線,武漢兵力空虛。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一部分學員,與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學生組成中央獨立師,國民黨左派侯連瀛任師長、惲代英任黨代表,跟隨葉挺迅速平叛,穩(wěn)定了武漢的局勢。“馬日事變”后,毛澤東在6月24日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湖南省委書記,冒著危險去湖南進行應急部署。但他很快就被陳獨秀召回武漢。7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發(fā)言,提出“上山”和“投入軍隊中去”,認為“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毛澤東不僅多次與蔡和森商議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而且他也受中央的委托起草了《湘南運動大綱》,準備以汝城為中心組織工農武裝,發(fā)動土地革命。這一計劃得到新組成的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的批準。毛澤東起草的《湘南運動大綱》 中特別提到“瀏、平農軍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領赴汝城”。秋收起義前,這支擬調往汝城的農軍一分為二:平江的農軍由余賁民(與時任警衛(wèi)團代理團長的余灑度是同鄉(xiāng)同族)率領開往修水,與在那里駐扎的警衛(wèi)團會合,作為第1團參加了秋收起義;瀏陽、醴陵的農軍則前往銅鼓,成為秋收起義第3團的一部分。毛澤東在安源召集張家灣會議后,和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一同赴銅鼓。
這一時期,毛澤東關于建立農民武裝的號召和他對湘鄂贛等省農民力量的發(fā)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賀子珍的兄長賀敏學曾憶及他被捕后,分別任贛西農軍總指揮和副總指揮的王興亞和袁文才為營救他和其他農運骨干,在7月20日發(fā)動第一次永新暴動的情況。他說:1927年上半年在江西永新就有了農民自衛(wèi)軍(游擊暴動隊),“主要是受到毛主席在湖南領導農民起義的影響,特別是毛主席當時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光輝著作對我們影響極大”。而毛澤東正是在安源張家灣會議上通過王興亞第一次得知井岡山地區(qū)有袁文才等領導的農民武裝。毛澤東當年在農民運動中的成就,不僅為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軍的組建,而且為湘南暴動,為弋陽、橫峰起義,為平江起義和紅5軍的發(fā)展,積蓄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課堂。 1926年3月, 毛澤東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
與葉挺獨立團和南昌起義軍余部的交集
毛澤東很早就主張建立中共自己的軍隊。他在廣州目睹了中共領導的第一支武裝——國民政府鐵甲車隊的作為。據(jù)鐵甲車隊隊長周士第回憶,毛澤東在廣州農講所給學員講話時,曾高度評價鐵甲車隊支持工農運動、平定楊劉叛亂、肅清廣州右翼勢力和在封鎖香港斗爭中的重要作用。“中山艦事件”發(fā)生后,毛澤東建議依靠葉挺獨立團反擊蔣介石的挑釁,也反映出毛澤東對中共自己的武裝——葉挺獨立團的信任。
葉挺部隊由中共直接領導,在北伐中聲名顯赫,是國民革命軍中的佼佼者。毛澤東與由葉挺獨立團擴充發(fā)展起來的部隊,有著直接的交集:一是隨他發(fā)動秋收起義的主力——警衛(wèi)團,直接源于葉挺獨立團;二是南昌起義軍在三河壩分兵后,朱德指揮的部隊是原葉挺獨立團的主力,該部后隨朱德、陳毅會同湘南暴動的農軍,輾轉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這里先敘述后者。
北伐軍攻克武昌后,一路斬關奪隘為國民革命軍第4軍打下“鐵軍”英名的葉挺獨立團,先是被擴充為第4軍25師(由第11軍副軍長朱暉日兼師長。葉挺任副師長,為實際主持者)的73團、74團、75團。由葉團參謀長周士第任團長的第73團,集中了葉團的骨干力量。這個團后來參加了南昌起義(陳毅這時到該團任政治指導員),在三河壩分兵時劃歸朱德指揮。南昌起義失敗后,朱德、陳毅、王爾琢等以73團余部為第1營、74團余部為第2營、南昌軍官教育團編為第3營,號稱工農革命軍第1師,轉戰(zhàn)粵湘贛邊界,后發(fā)動湘南暴動。毛澤東很關心南昌起義部隊的情況,引兵井岡山不久,即派何長工去聯(lián)絡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并打聽南昌起義軍的消息。機緣巧合,1927年10月下旬,毛澤東率秋收起義軍第1團往遂川途中受到當?shù)氐刂魑溲b肖家璧的“靖衛(wèi)團”伏擊,隊伍被沖散。張子清率領第3營一路轉戰(zhàn),于11月上旬至上猶縣營前,與正在那里集結的朱德所部會合。一個多月后,補充了彈藥物資的張子清第3營回到井岡山。這樣,毛澤東和朱德之間互通了消息。此后,何長工找到了朱德,進一步溝通了情況。朱德等于1928年1月在宜章、汝城、永興等地成功地發(fā)動湘南暴動,部隊擴充到萬余人(包括8000多人的湘南農軍)。之后,朱德派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化名覃澤,上井岡山聯(lián)絡毛澤東。最終兩支部隊于1928年4月下旬在井岡山山麓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勝利會師。這段過程的親歷者粟裕,后來寫文章稱之為“激流歸大海”。
為秋收起義尋找“發(fā)火藥”
毛澤東與葉挺部隊的另一直接交集,是組建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衛(wèi)團。1927年3月25日,葉挺由第25師副師長轉任第11軍24師師長。4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誓師開始二次北伐,葉挺部隊的主力隨軍出征河南前線。而葉挺則奉命兼任武漢衛(wèi)戍司令,率24師的72團和25師的75團留守武漢。為加強武漢的防務,在平定夏斗寅叛亂后,葉挺又組建起第二方面軍警衛(wèi)團。警衛(wèi)團起初的任務是警衛(wèi)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wèi)集團叛變革命分共后,中共中央安排其參加南昌起義。他們行至黃石時,得知南昌起義大軍已經南下,而他們的去路又被追隨汪精衛(wèi)的張發(fā)奎部隊阻斷,便輾轉江西奉新再到修水駐扎,并因此得以作為主力參加了中共發(fā)動的秋收起義。
對于警衛(wèi)團源自葉挺獨立團這一重要史實,學界很少言及。事實上,朱德就曾明確指出該團起初“也是從獨立團派出的干部組織的”。何長工也回憶該團“是葉挺獨立團的一個營改編的,是我們黨徹底領導的,秋收起義以這個團為基礎,從武昌出發(fā)三千多人”。的確,組建警衛(wèi)團的包括成建制地從由葉挺任師長的第24師抽調的一些連隊,以及由黃埔一期畢業(yè)生、共產黨員陳浩(后叛變)率領的第24師新兵訓導處的一個新兵營。警衛(wèi)團參謀長韓浚(時為共產黨員)回憶,警衛(wèi)團是個加強團,有4個營,成員多是由中共組織介紹來的,連、排長中有三分之一是共產黨員,營、連指導員幾乎都是黨員。醞釀成立警衛(wèi)團時,葉挺提議,并經時任第25師參謀處處長的張云逸(與張發(fā)奎有舊誼)從中勸說,最終使張發(fā)奎同意以盧德銘為團長。盧德銘原是黃埔二期生,葉挺獨立團在肇慶時即為該團2營4連的連長,后接替在攻打武昌中犧牲的曹淵任1營營長,再后由73團參謀長轉任警衛(wèi)團團長,秋收起義爆發(fā)時任總指揮。警衛(wèi)團在黨的領導關系上是直屬中央軍委,盧德銘就職前,中央軍委的聶榮臻專門交代他要掌握好隊伍、擴大黨團員、提高官兵的革命覺悟等。
毛澤東在領導秋收起義的過程中,對警衛(wèi)團官兵給予了充分的信任并表現(xiàn)出極大的耐心。警衛(wèi)團成為秋收起義的“發(fā)火藥”,并在后來和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成為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軍事骨干。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 中明確地指出:“至于此刻的紅軍,也是由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和接受過工農群眾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分化出來的。”
另辟蹊徑,重振旗鼓,井岡山上軍旗紅
按照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的精神,1927年9月9日,由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fā)。參加起義的隊伍共5000余人,其中以警衛(wèi)團為主力,連同余賁民率領的平江的農軍,羅榮桓等率領的湖北通城、崇陽的農民自衛(wèi)軍,編為第1團;以安源工人糾察隊、礦警隊和萍鄉(xiāng)等地的農民自衛(wèi)軍,編為第2團;以警衛(wèi)團的一個營和瀏陽、醴陵的部分工農武裝,編為第3團。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和由湖南省委任命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是這支隊伍的最高領導。關于秋收起義軍出師不利,攻打長沙的計劃失敗,一路波折的情況,已是眾所周知。毛澤東在主攻方向已失利情況下,卻能夠率領一支潰敗之師,另辟蹊徑,在井岡山重振旗鼓,除了毛澤東和秋收起義軍各組成部分,以及與南昌起義軍余部和湘南暴動農軍的歷史淵源,主要是因為:
支部建在連上
在醞釀發(fā)動秋收起義時,毛澤東就力主公開打出共產黨的旗幟,起義過程中第一次打出了“工農革命軍”的旗幟。秋收起義軍不僅繼承了葉挺獨立團和由其擴充發(fā)展的部隊在團級設置黨代表,營、連設置政治指導員,以及團有黨支部、營有黨小組的做法,而且更進一步在三灣改編時確定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班排設黨小組。毛澤東認為“紅軍所以艱難奮戰(zhàn)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秋收起義軍抵達井岡山后,毛澤東還大力在士兵中培養(yǎng)發(fā)展黨員。后來,他在《井岡山的斗爭》 中指出:“兩年前,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現(xiàn)在紅軍中黨員和非黨員約為一與三之比,即平均四個人中有一個黨員。最近決定在戰(zhàn)斗兵中發(fā)展黨員數(shù)量,達到黨員非黨員各半的目的。”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注意到在農村環(huán)境和以農民為主要成員的情況下,如何建設一支中共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1928年4月下旬,朱毛會師成立第4軍后,軍一級設軍委,團設團委,營設營委,連設支部,排班設小組,軍部設特支。毛澤東作為軍委書記兼第4軍的黨代表,健全了黨的組織,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并且針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和士兵政治覺悟低下的問題,“軍委師委團委各支部開了黨的訓練班,情形日益良好”。
實行軍隊內部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
中共最早建立的武裝——鐵甲車隊和葉挺獨立團,形成了定期公開賬目,官兵伙食標準一樣,節(jié)余的伙食費官兵一樣平分,嚴懲貪污和吃空餉,并利用黨團組織開展政治訓練和民主教育的傳統(tǒng)。毛澤東在中共七大《論聯(lián)合政府》 的報告中指出,“內戰(zhàn)時期的中國紅軍,保存了并發(fā)展了北伐時期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的民主傳統(tǒng)”。

八七會議后, 毛澤東回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圖為1937年5月9日,毛澤東在延安和當年參加秋收起義的部分同志合影
秋收起義軍從三灣改編就開始實行士兵委員會制度。紅4軍后來逐漸建立起從連到軍的各級士兵委員會,與各級黨委到支部、黨小組的黨的組織系統(tǒng),各級黨代表、政治部和營、連的政治指導員的政治工作系統(tǒng)相配套,推廣軍內民主,實現(xiàn)了全軍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官兵一致,從軍長到伙夫每天都是5分銀錢的伙食費,奠定了新型官兵關系的基礎——階級的團結,從根本上改變了舊軍隊的雇傭軍性質。毛澤東當年就指出,“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zhàn)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他深有感觸地強調,“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這一與白軍區(qū)別的重要標志,對瓦解敵軍,粉碎敵人的軍事和經濟“會剿”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井岡山時期,當紅軍內和黨內還有人在懷疑“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的時候,就先后有畢占云、張威分別率一個營的國民黨軍投誠紅軍。毛澤東這樣描述: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
團結改造有綠林習氣的農民武裝
在井岡山地區(qū)存在著袁文才和王佐兩支反抗地主壓迫的農民武裝,他們二人是結拜兄弟,在山上山下形成互相呼應的生死關系。他們在大革命時期都受到中共的影響,袁文才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他們具有濃厚的綠林習氣,殺富濟貧,占山自保。毛澤東在永新三灣村時,就通過他在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陳慕平,同寧岡縣委和袁文才建立了聯(lián)系。1927年10月3日,毛澤東在寧岡古城召開秋收起義軍前委和寧岡縣委等參加的聯(lián)席會議。他否定那種像《水滸傳》中林沖火并王倫式的建議,確定了爭取和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隊的方針。在毛澤東等的幫助教育下,袁、王二人及其部屬的政治思想覺悟有很大的提高,王佐也加入了共產黨。他們的部隊被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師第2團,成為真正的工農武裝。
“三大紀律六項注意” 和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
為了展現(xiàn)秋收起義軍人民軍隊的嶄新風貌,毛澤東率隊到井岡山伊始,就制定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井岡山的軍隊之所以能夠接受和自覺地執(zhí)行這些紀律規(guī)定,也“實由于兵士自知當兵是為的自己及工農大眾,不是為的餉銀而當兵”。“紅軍與群眾的關系非常密切,四軍在過去的經驗上使每個士兵都知道對本地工農的幫助的重要,達到某一地方每個士兵能自動向群眾宣傳與之發(fā)生親密的關系,壓迫工農是紅軍最重的犯罪。”
毛澤東在軍民關系問題上最大的創(chuàng)舉是提出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羅榮桓認為,三大任務“將革命軍人如何對待人民群眾,用最具體、最簡潔的語言固定下來”。與這三大任務相應的,就是“軍隊是戰(zhàn)斗隊又是工作隊”口號的提出。這一創(chuàng)舉改變了千百年來軍隊只是單一打仗的慣例,在更高的層次上建立起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軍隊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水乳交融的密切關系。
此后,井岡山的工農革命軍(紅4軍),每到一地,一是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作為制定政策和開展工作的依據(jù);二是對群眾進行宣傳發(fā)動。部隊設置有宣傳兵制度,每個部門(連、營、政治部、衛(wèi)生隊等)都有5個專門的宣傳兵,負責挨戶和沿街宣傳,刷寫標語,組織集會;三是幫助地方培養(yǎng)骨干,組織農會,發(fā)展黨員,建立黨組織和成立基層工農民主政權,以及組織農民赤衛(wèi)隊,進行分配土地、發(fā)展經濟、移風易俗等各項工作。這樣,不僅極大地密切了軍民魚水關系,而且有力地保證和推動了“土地革命、武裝斗爭、根據(jù)地建設”三位一體紅色割據(jù)斗爭的全面開展。毛澤東特別贊許“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fā)展的”。
形成游擊戰(zhàn)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 實現(xiàn)由正規(guī)戰(zhàn)到游擊戰(zhàn)、 運動戰(zhàn)的轉變
毛澤東和朱德于1928年5月提出游擊戰(zhàn)術的十六字訣。毛澤東曾不無自豪地寫道:“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zhàn)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zhàn)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zhàn)術,群眾斗爭的發(fā)動是一天比一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zhàn)術就是游擊的戰(zhàn)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fā)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qū)域的割據(jù),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fā)動很大的群眾。’”游擊戰(zhàn)術十六字訣,是土地革命戰(zhàn)爭前期紅軍游擊戰(zhàn)爭的基本指導原則,是紅軍全部作戰(zhàn)原則的基礎。
八七會議以來,急于從大革命的失敗中重新崛起的中國共產黨人,遇到的一個最嚴峻的現(xiàn)實問題,即如何把“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有機地結合起來。毛澤東抓住其中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創(chuàng)建起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也就是他后來所概括的那樣:“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在領導秋收起義的過程中,毛澤東把關于“上山”“下湖”的主張付諸實踐,逐步摸索出一條人民軍隊的建軍之路,其要素是:由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領導,立足廣大農村,依靠農民群眾為主力軍,以開展土地革命為主要任務,通過發(fā)展地方黨組織,建立農會、農民赤衛(wèi)隊和各級工農民主政權,開辟農村革命根據(jù)地。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和他的戰(zhàn)友們,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了人民軍隊建設當中的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毛澤東在領導發(fā)動秋收起義和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偉大實踐中,披荊斬棘,成為開創(chuàng)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新局面的時勢英雄。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井岡山地區(qū)的農民率先實現(xiàn)“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夢想,建立起全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jù)地——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壯大和發(fā)展了最具代表性的主力紅軍——朱毛紅軍,在敵人統(tǒng)治薄弱的農村地區(qū),重新點燃中國革命的火炬,獨立自主地開辟了中國式的革命道路——井岡山道路。毛澤東當年向中共中央報告:“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tǒng)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