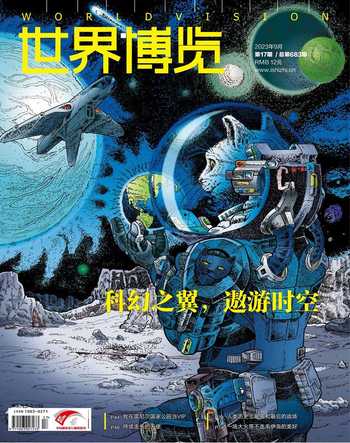不斷遇見驚喜的旅程
雙翅目

2017年,本文作者從赫爾辛基到愛沙尼亞1日游。在愛沙尼亞的塔林,街頭繪畫中也流露出濃濃的北歐式幻想風(fēng)情。

世界科幻大會期間,參會者通過cosplay,盡情展示自己的喜好。
世界科幻大會,本名為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簡稱worldcon。Con是convention,不是會議,更接近主題性展會。我小時候參加漫展,喜歡逛攤位、買周邊、看cosplay,對漫展的理解接近市集。大學(xué)時追美劇《生活大爆炸》,看到謝爾頓四人組組團逛漫展——圣迭戈國際動漫展(San Diego International Comic-Con),我才意識到Con要更豐富。Comic-Con不僅包括漫畫交流、簽售、頒獎活動,亦承擔(dān)電影、電視劇集宣傳、主創(chuàng)見面會、游戲宣傳等商業(yè)功能,同時集市、音樂會、化裝舞會等粉絲或愛好者交流活動也必不可少。于是Con在我心目中變?yōu)橐粋€充滿吸引力的集體活動。它具有政治、民族與商業(yè)傾向,卻能用文化和藝術(shù)消弭圈層隔閡。
我還沒去過國際性的Comic-Con,卻參加了兩次世界科幻大會,一次在芬蘭赫爾辛基,一次在愛爾蘭都柏林。世界科幻大會的歷史比許多漫展都要悠久。它早年主要集中于美國,H.G.威爾斯、黃金時代三巨頭、新浪潮的厄休拉·勒古恩與菲利普·迪克,都參加世界科幻大會。穿越二戰(zhàn)、冷戰(zhàn)與新千年,世界科幻大會雖然在內(nèi)部有過動蕩與變革,但仍保有了Con的某種古老傳統(tǒng):民間性、多元性、烏托邦性,以及某種意義上的狂歡。
世界科幻大會的資金籌集與組織主要依托民間。會員購票,并同時擁有參會與雨果獎投票資格。歷經(jīng)近一個世紀(jì)的發(fā)展,大會參與者的年齡分布顯得比較平均。組織方主要由中青年擔(dān)任。年長且富有經(jīng)驗的科幻從業(yè)者仍是大會常客。白發(fā)蒼蒼的老者大多十分可愛。會員又往往攜家?guī)Э谝煌嫠!:⑼c老者的參與,代表著大會全年齡親善的特性。著“奇裝異服”者自由流動,孩童與老者也樂于同他們合影。跨圈層的溝通是大會讓人倍感舒適的原因之一。
由于參會者的身份和訴求非常豐富,世界科幻大會的活動總排得滿滿當(dāng)當(dāng)。除了重要的雨果獎頒獎儀式,化裝舞會(Masquerade)、主題派對、獨立電影展和音樂會占據(jù)大會不同的黃金時段。討論會、朗讀會等活動更是從早至晚,并行舉辦。參會者不可能完整打卡大會所有日程,事實上,能夠參加自己感興趣的所有活動本身就是一個挑戰(zhàn)。
我以純游客身份參與2017年第75屆芬蘭赫爾辛基世界科幻大會,為了去聽一個晚間討論,錯過了化裝舞會。我以討論會發(fā)言者身份參與2019年第77屆愛爾蘭都柏林世界科幻大會,見到老朋友和科幻老師們,去了老城區(qū)獨特的酒吧,再一次錯過化裝舞會。今年成都世界科幻大會,我不能再錯過頗具觀賞性的化裝舞會表演了。可以說,不要小瞧大會的5天會期,只要沉浸其中,就得從早跑到晚,雖然身體疲憊,但精神絕對會高度亢奮。
進入新千年,科幻大會的世界性逐步拓展,德國、日本等國家相繼舉辦,這一方面得益于市場與網(wǎng)絡(luò),一方面也得益于大會組織模式日趨專業(yè)。
兩次夢幻之旅
地處極北的芬蘭風(fēng)光極佳。內(nèi)向型社恐是某種芬蘭人的特征。不過社恐與內(nèi)向的人有時也更加熱情。我在本科時曾參與交換項目,在芬蘭待了將近半個月,曾經(jīng)從極圈南下去赫爾辛基,中途繞路去薩翁林納的奧拉維城堡。奧拉維城堡位于俄芬邊境,直通的火車只有一節(jié),半小時一趟。圣誕老人似的老車長和高大內(nèi)秀的乘務(wù)員姐姐見我學(xué)生模樣又是中國人,特地邀我去駕駛艙圍觀,還給我講時不時從俄羅斯過境而來的熊。熊曾經(jīng)蹲在鐵軌邊不走,車長不得不停車等待。下午,我逛完古堡,去找吃的,路過大橋,聽見上面的小火車使勁鳴笛。我往前跑兩步,抬頭,原來是老車長和乘務(wù)員姐姐同時向我招手鳴笛示意。我也蹦蹦跳跳邊跑邊揮手。10多年過去,對于芬蘭人的真摯熱情,我依然記憶猶新。科幻大會讓近10年前的記憶和現(xiàn)實重疊。
參加芬蘭科幻大會時,我的自由時間比較多,一開始根據(jù)感興趣的主題給自己排了許多討論會旁聽。討論會(Panel)介于講座與閑聊之間,形式或多人、或一人。大會第一天,我發(fā)現(xiàn)晚上空出一個時間段,便隨意挑一個最晚場的多主題分享討論會,進入會議室,分享已到中途,大家非常安靜,分享者也是一位內(nèi)向型人格的人。有人迅速為我讓出座位。我很喜歡這種安靜也自如的氛圍。其中一位藝術(shù)家分享的內(nèi)容為演景(Demoscene),即純代碼寫就,可以即時運行展示的視聽藝術(shù)。早年Windows的屏幕保護程序,如迷宮、煙花等,就是演景藝術(shù)的前身。如今的演景已在制作奔跑的貓科動物、淹沒的城市、斑斕閃爍的地球,與先鋒藝術(shù)和商業(yè)項目合作較多。我第一次聽說這類藝術(shù),很感興趣,第二天重新安排日程,專門去聽了另一個演景討論會。這一場的外向型人格參會者較多,一位芬蘭參會者介紹,其實舉辦科幻大會前,這一場館剛舉辦完演景大會。大會設(shè)置限時的演景競技賽。DJ在舞臺上表演,參賽者分組面對電腦,實時在臺下編程。主辦方準(zhǔn)備成打的啤酒和可樂。時間截止,隨即展示作品并評獎。真刺激。演景藝術(shù)家大多也是“科幻迷”,他們將自己的作品直接平移到了科幻大會。
我感覺討論會是在造就科幻大會的偶遇。許多未成形的、少為人知的藝術(shù)和觀點直接展示,或許隨意進入一個場館旁聽,便能獲得意外驚喜,這樣一來,我的排日程強迫癥獲得緩解。芬蘭科幻大會時,我盡量一有時間就去討論會,但不執(zhí)著于主題。我聽了芬蘭童話中姆明形象的創(chuàng)作史、西方龍的傳承與分類、多種游戲理論分享,還有非常火爆的“塔迪斯在中土”的討論會。主持人細致地分享了《神秘博士》歷代劇集對《魔戒》系列的致敬和元素引用。他的T恤上,正面印著《星球大戰(zhàn)》的標(biāo)記,背面印著《星際迷航》的圖案,至于他究竟更喜歡其中的哪一個,大家一眼就看出來了。旁聽者排隊入場,中途時不時爆笑或竊笑。

2017年芬蘭世界科幻大會的一場討論會上,芬蘭博士生分析了蒲松齡與中國科幻的關(guān)系。。

2017年,赫爾辛基會展中心(Messukeskus)歡迎著每一位來到第75屆世界科幻大會的游客。

“塔迪斯在中土”討論會現(xiàn)場。一位小哥的襯衫上印著《魔戒》中矮人的如尼文。塔迪斯(TARDIS)是英國電視劇《神秘博士》中主人公乘坐的飛船,看起來是一個普通的藍色電話亭,實際上可以在時空中自由穿梭

“塔迪斯在中土”討論會現(xiàn)場。一位小哥的襯衫上印著《魔戒》中矮人的如尼文。塔迪斯(TARDIS)是英國電視劇《神秘博士》中主人公乘坐的飛船,看起來是一個普通的藍色電話亭,實際上可以在時空中自由穿梭
著名科幻文學(xué)編輯姚海軍老師參與了一場科幻雜志制作的分享,其中一位老頑童編輯頭戴小花帽,非常吸睛。當(dāng)然,討論會也包含專業(yè)的學(xué)術(shù)發(fā)言。我還聽了美國華裔學(xué)者宋明煒老師的講座,也旁聽了芬蘭博士生分析蒲松齡與中國科幻的關(guān)系。在一場微型系列分享會里,年輕的學(xué)生和從業(yè)者用自己編織的行星和衛(wèi)星形狀的毛線球,講解引力問題;有的則展示自己對動畫《小馬寶莉》的學(xué)術(shù)研究。2017年,國內(nèi)的科幻奇幻學(xué)術(shù)研究還未形成潮流,我在科幻大會習(xí)得了很多思路。
2019都柏林科幻大會,我提前做了準(zhǔn)備。因為積累了一些作品,我決定申請參加討論會。2019年5月前,我在官方網(wǎng)站提交了個人簡歷和希望參會的議題方向。因為比較匆忙,我沒有申請討論會的主辦,只申請作為一般的討論者參與其中,因而有些忐忑,不知會被分配到哪一類討論。最終大會安排我參加三場討論:“新技術(shù)與藝術(shù)家”(New Technologies for Artists)、“來自不同文化的藝術(shù)”(Art from All Cultures)和宋明煒老師主持的“中國科幻的國際視野”(Global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我雖是新人,并不認識大部分同組討論者,現(xiàn)場氛圍卻很放松。我特地分享了藝術(shù)家徐冰用英文方塊字拼寫的“藝術(shù)為人民”,現(xiàn)場外國友人認出單詞時驚喜又開心。“中國科幻的國際視野”討論會中,我有幸與王德威老師、嚴鋒老師、三豐老師、陳楸帆老師、金雪妮老師、王侃瑜老師等學(xué)者和作家一同參與分享。有趣的是,國內(nèi)外學(xué)術(shù)會議也不一定能聚齊這么多人,世界科幻大會卻做到了。內(nèi)容展示的多元與自由的確是大會最吸引我的地方。
充滿無數(shù)可能的活動
討論會外,私人會談(Kaffeeklatches)和朗讀會是接近作者的好機會。前者的名稱來自德語“咖啡”和“聊天”二詞的組合,意思是邊喝咖啡邊閑談,只是活動有人數(shù)限制,一般10人內(nèi),先到先占位。兩次科幻大會,我都沒排上私人會談。朗讀會雖限制少一些,也時常人滿為患,近距離聽作者朗讀自己的作品,能獲得更感性的體驗:原來作者寫這一段落時的情感是這樣的。

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因為共同的愛好相聚在世界科幻大會上。會場的裝飾品也充滿了幻想的趣味。

著名科幻作家伊恩·沃森和翻譯家克里斯蒂娜·馬西亞,這對堪稱完美的夫婦是各種科幻活動的常客,他們當(dāng)然不會錯過2017年芬蘭世界科幻大會。
簽售活動是另一種接觸作者的經(jīng)典方式。劉慈欣和喬治·馬丁出席了芬蘭科幻大會。傳聞中保持1米社交距離的芬蘭人排起大長隊,那陣勢讓中國人頗感親切。此外,獨立的幻想作品畫展、類似跳蚤市場的粉絲攤位、前沿科技公司向粉絲展示產(chǎn)品,都是參加活動時需要刷一下的項目。各類展覽是偶遇心儀作家的好機會。參會者們或者直接購買畫作,或者直接3D打印手辦。我購買了真菌似的星球植物明信片和迷你牛皮書耳墜兒。成都科幻大會的攤位宣傳也自2017延續(xù)到2019年。舉辦多元、巨型的科幻大會,需要長期且嚴肅的準(zhǔn)備。只有如此,大會才能充實而豐富。
身為作者,我在兩屆科幻大會都有幸遇到前輩。我非常喜歡特德·姜的作品,抵達芬蘭,便聽說姜來參會的消息。我興奮又社恐,想見見作家,又知道特德·姜性格內(nèi)斂(這可能也是姜選擇芬蘭科幻大會的原因),便琢磨不要打擾,遠遠瞧一眼便好。大會日的一個中午,我與友人到附近的尼泊爾簡易自助餐廳吃飯。我端了一盤灑了薄荷葉的咖喱走出自助區(qū),差一點撞上一個身穿白襯衫的大個子(我比較小只)。我們倆都不好意思看對方眼睛,迅速道歉,擦身而過。走出兩步,我意識到:特德·姜!社恐本能沒讓我回身去追特德·姜,去正式打招呼。我只是三步并作兩步返回餐桌,激動地悄悄宣布:特德·姜來了,在那兒。之后的吃飯時間,我和友人一直糾結(jié)是否找機會求合影。我最后還是沒好意思。我為自己保留了一個充滿可能的假設(shè):在另一條時間線上,我真的一頭撞上了特德·姜,我一定已經(jīng)讓他印象深刻。而在這一條時間線上,我便可以選擇用作品說話啦。
包容和友善的聚會
2017年初次見到賽博朋克科幻女作家帕特·卡蒂根(Pat Cardigan)時,她身患疾病,2019年,她仍給了我們大大擁抱。都柏林科幻大會上,我主要同編輯友人Vera一同參會,她帶著我見了不同國家的作家和編輯老師。其中伊恩·沃森(Ian Watson)和他的太太克里斯蒂娜·馬西亞(Cristina Macía)特別有趣。沃森生于1943年,見證了科幻大會的成長,也是見過威爾斯等科幻諸神的作家。他身材不高,笑起來親和快樂,非常像霍比特人比爾博。當(dāng)然,他是一位沒有受過魔戒侵蝕的比爾博。馬西亞同沃森差不多高,更為活潑。兩位站在一起,是我心目中博學(xué)多識的完美霍比特伴侶。沃森是英國人,曾經(jīng)是教師,也在坦桑尼亞和日本授課。他是最早在英國開設(shè)科幻課程的教師之一,1976年后全職寫作,多次獲英國科幻協(xié)會獎。馬西亞是西班牙人,職業(yè)生涯源自翻譯美漫,如今是著名的翻譯家。《冰與火之歌》的西班牙語版便出自她手。喬治·馬丁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圖書銷售量的百分之十都仰仗于她。年長的他們非常外向,是各種科幻大會的常客。沃森講了一次法國科幻大會的住宿風(fēng)波,他還以元科幻手法,寫過一篇名為《2080年的世界科幻大會》的文章,收錄于《科幻之路(第四卷)——從現(xiàn)在到永遠》中。國內(nèi)譯者在翻譯他的作品時,大多選取具有元科幻或元文學(xué)氣質(zhì)的篇章,他本人確實像一位來自夏爾的英國紳士。我們同沃森和馬西亞一起逛了博物館,吃了午餐。馬西亞想吃冰淇淋,我們又一邊逛公園,一邊舔冰淇淋球。他們問了許多中國的情況和我們的生活,也給我們講他們在巴塞羅那附近海濱小城的趣事。臨分開前,沃森說,他是個預(yù)知天氣的高手,讓我們快些上車,會下雨。他說從他的預(yù)測發(fā)布,到雨水降落地面,需要五六分鐘。真的,5分鐘后,天降太陽雨,我和Vera錯過一趟車,趕緊找地方躲雨,并發(fā)消息告訴他們,他們哈哈笑。2020年疫情封閉期間,沃森也發(fā)來慰問,說他嘗試在家中運動,邊走路邊想象自己是一列流動的玩具小火車。馬西亞則開始制作各種手工皂。他們就像科幻小說中會出現(xiàn)的受人喜愛的人物。

世界科幻大會給每一位參與者提供了美好想象和現(xiàn)實融合的機會。在這里,大家可以暫時或部分放下社會身份,以科幻或奇幻角色、以創(chuàng)作者或粉絲身份,進入多元文化包容的此時此地的烏托邦。
今年,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將在成都舉辦。大會是一種聚落關(guān)系,也是科幻精神的一種跨國與跨代際的交流。它提供了美好想象和現(xiàn)實融合的機會。每一位Con的參與者都可以暫時或部分放下社會身份,以科幻或奇幻角色、以創(chuàng)作者或粉絲身份,進入多元文化包容的此時此地的烏托邦。陌生人似乎不再陌生。邊緣人似乎也能獲得更多共情。希望友善、分享與創(chuàng)造構(gòu)成世界科幻大會帶給中國本土的快樂體驗。
(責(zé)編:李玉簫)
TIPS
元科幻,一種帶有文字游戲色彩的創(chuàng)作手法,往往取材于已有的科幻作品,或是以現(xiàn)實生活中的科幻作家、科幻活動及科幻歷史事件為中心,虛構(gòu)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