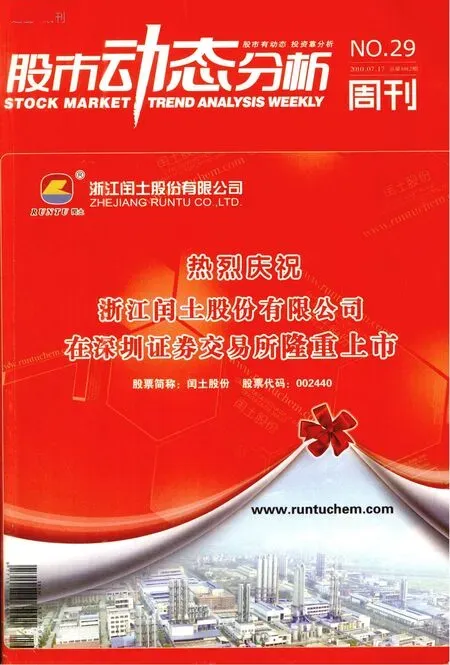偉星新材:把工業品做成品牌耐用消費品
偉星新材創建于1999年,是國內最早、規模最大的塑料管道生產企業之一,產品廣泛應用于給水、排水、排污、燃氣、采暖、電力和礦山等產業。公司秉持"以品牌統領營銷、以服務支撐品牌"的經營理念,建立了覆蓋全國及輻射海外的營銷網絡,著力打造誠信共贏的市場服務體系,傳播"健康、可靠、喜悅"的品牌理念。
整合空間大 替代空間大
塑料管道行業過去十年保持了25%以上的高增長,尤其是2007 年后一直增長較快。2010年,我國塑料管道總產量為840.2萬噸,比2009年增長31.1%,成為全球最大的塑料管道生產和應用國。2013年全行業產量1100萬噸,預計2015年全國塑料管道生產量接近1320萬噸,在全國各類管道市場中占有率超過50%。分區域來看,華東、華南產量占比最大,分別為29%和23%,華北次之,占比21%。
根據統計數據,筆者發現塑料管道行業生產環節進入門檻很低,全行業固定資產2200億,折合每噸對應固定資產只有3.6萬元,而每噸的產值約為12000-16000元。中國有3000多家塑料管道企業,平均單產500多萬。2011年由于行業受擠壓,不少企業虧損關閉,最近大規模企業維持在700家左右,小企業更是不勝枚舉。目前大企業的單一品種市場占有率也不超過5%,行業集中度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提升的契機在于消費者對品質和品牌的要求,和廠家對渠道的布局和掌控力。以家裝水管PPR為例,每平米裝修成本1000元中,水管只占50元。但是一旦水管爆裂意味著千元的裝修全部報廢。因此,這種準終端產品,企業對消費者的引導滲透會有一定作用,不像塑鋼門窗那樣混亂不堪。
扁平渠道主攻零售市場
偉星新材主營四大類塑料管道,并集成地暖等產品以及PPR系列、PE系列、HDPE系列和PB系列。市場地位方面方面,PPR全國前三是偉星、金德、金牛,偉星優勢明顯。
偉星新材的模式是代理加直營。各省都有銷售公司,然后往下做地市級經銷商,在沿海發達地區直接下沉到縣城,最大的總代在地區級,代理最多兩三級,實現扁平化管理。這種模式不利的方面在于偉星的營銷人員眾多,有利的是砍掉了各級經銷商的利潤分流,可以激勵基層經銷商;貨款回籠快,小經銷商依賴偉星生存;價格策略的執行十分靈活,避免庫存減值。用別人的營銷渠道可以快速做大,需要生產企業的談判能力強,找到好的經銷商。風險在于投入的營運資金和周轉率低。公司的銷售分公司和經銷商直接利益分配合理,相互彌補,不會限制經銷商。目前公司有20多家銷售公司和1000家一級經銷商,通過區域經銷商管理的網店則達7000家,經銷商網店則達到約1.4萬家。一級經銷商專營偉星品牌,下層經銷商則的不受限制。
從財務角度看,零售市場由于扁平化同時面向單一消費者,對手沒有議價能力,所以毛利率較高;代理制需要讓利給各級經銷商,毛利率低一些;凈利率方面,規模效益和營銷費用的不同,導致公司間差異。
應收賬款周轉方面差異最明顯,給政府做工程回款最慢,給代理商次之,零售市場周轉最快,每個月周轉一次。這樣也就推導出經營現金流的差異,做市政工程換來的是應收賬款,做BT之后換回固定資產;聯塑回款不算差;永高在惡化;偉星的現金流最好,凈利潤含金量最高。
從實際經營效果看,在模式摸索期,偉星新材的銷售費用偏高,隨著單一銷售公司產值提高,人員單產提高,公司的利潤增長逐步超過收入增長。2012年之前,偉星處于投入期,既包括渠道建設也包括全國的產能布局。2009-2011年公司員工數增長76%,收入增長82%,凈利潤增長65%。人均單產來看,這三年徘徊在50萬上下,與聯塑相差一倍。2012年 是公司重要的轉折。公司目前在PPR管道行業占5%的市場份額,仍處于快速提升階段。在去年四季度以來房地產轉淡的環境下,公司反而增速提高,一方面是渠道布局進入收獲期,銷售員單產提高;二是推出了“星管家”。
“星管家”服務
對于生產壁壘低的行業,渠道至關重要,同時為了避免重蹈塑鋼窗被假貨淹沒的覆轍,公司推出“星管家”,打通了傳統建材企業和最終消費者,讓公司掌控了從銷售到安裝維護的商業鏈條,從而一定程度上化解渠道管理的中假冒偽劣、擾亂、價格體系等頑疾,并以增值服務提振產品價值鏈。公司本身要做的就是把一個工業品做成品牌耐用消費品,以達到與同類產品重要區分的目的,而“星管家”就將加強了這個特征。
并且,近年來家裝e站之類的家裝網站的出現,將家裝這個龐大的市場進行分割和標準化,解決了裝修公司與業主巨大的摩擦成本問題,也讓不透明的中間環節成本有明顯下降。“星管家”有望將水管工程標準化,成為家裝電商的一個供應商,繼而擴大客戶。
值得一提的是,“星管家”服務對客戶隱蔽工程管路數據的留存記錄將為公司拓展新業務打下基礎,公司統計一年中使用偉星管轉型的客戶達150萬戶,這將為公司向其延伸推銷水暖等產品積累了客戶資源,實現低成本銷售。
多年效益優良
公司2010年上市持續分紅,2011年以來的三年內都是每股稅前派發現金0.7元,對應過去三年的均價的分紅收益率有4.8%,是個良好的價值型品種。2014年1 月公司管理層完成了第二個行權期390 萬份股票期權的行權,體現了管理層對公司未來發展的堅定信心。同時,公司公布2014年經營目標營業收入力爭達25.30億元、成本及費用控制在20.50億元左右,營業利潤目標在4.8億元左右,較2013 年增長近30.8%。筆者認為,隨著公司渠道布局和“星管家”的實施,公司將走上領先行業的增長之路。(雪球ID:杉再起-倍霖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