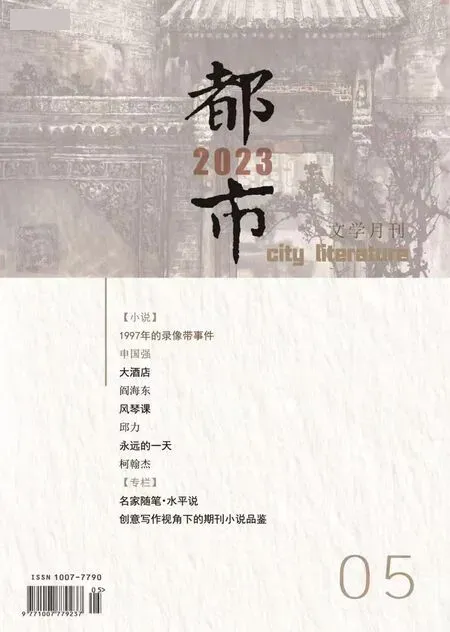純粹的童年敘事
——讀趙志明小說《怪客》
○李葦子
提到童年敘事,最先想到的兩位作家便是魯迅和蕭紅。前者的《社戲》和《孔乙己》,后者的《呼蘭河傳》。然而,細細研究,還是發現了一些問題,這些童年敘事的作品并非嚴格意義的童年視角,而是成年后對于童年生活的一種回望,屬于典型的回溯性敘事。《社戲》有兩個版本,流傳最廣的是刪減版,原版小說中開頭寫的是“我”在北京看戲的兩段經歷,這兩段經歷都很糟糕,由此引出“我”對童年那次看戲經歷的懷念。文本中潛藏著一個若隱若現的成年者的敘事聲音,縱然是童年視角,也是經由成年敘事者過濾后的,有了成年人的情感認同與價值判斷。縱觀魯迅這些關于童年的作品,不難看出無論他如何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孩子總是美好的,他們與成人世界形成一種涇渭分明的對立關系。這一點從少年閏土和中年閏土的對比可窺一斑。《故鄉》里成年后的迅哥兒和閏土有了巨大隔膜,但是,小侄子宏兒卻在想念僅有一面之緣的水生,作者經意或不經意間將我們引入更遙遠的思考,宏兒和水生這段短暫的情誼不過是迅哥兒和閏土少年時情誼的翻版。在《孔乙己》中,兒童世界的澄澈與成人世界的渾濁更是形成了鮮明對比,作為浮游于兒童與成人世界夾縫間的一個怪物,孔乙己只能在孩子群體中尋找認同與共情。《呼蘭河傳》當然也是成年后的“我”對于在呼蘭區那段生活的回憶式敘事,盡管也有大量關于孩童的感受性描寫,但,那份濃郁的懷舊情緒,顯然是屬于那個成年敘事者的。
嚴格意義的童年視角必須要用兒童的心理、眼光、認知等,去打量、觀察和體驗這個世界,無論是情感評價還是認知深度,兒童都迥異于成人。作為思想的外衣,孩子的語言充滿了想象力,不受現實邏輯的羈絆,表現出那種信馬由韁、天馬行空的任性和自由。偶爾他們能說出一兩句類成人的語言,也不過是對成人的模擬與效仿,但,倘若一個孩子始終在用成人的語言表達,則是一件叫人毛骨悚然的事。另外,兒童世界感性大于理性,那是一種無序的、眾生平等的慈悲,超越了成人秩序井然的現實經驗。兒童的這些特點,讓小說家獲得了部分掙脫現實邏輯引力的特權,極大地實現了敘事自由。
趙志明的短篇小說《怪客》(《小說界》2022 年第3 期)也是一篇童年視角的小說,作者完全以童年的感覺和經驗去敘說并非全是孩童的人和事。他虛構了一條憂郁且神秘的街道,以及一個孩子被昏黃的路燈拉長,拍扁,再拉長,再拍扁的投影。“我”的母親不顧眾人反對,在一條尚未成型的街上,傾盡所有,造了一棟很氣派的三層樓房。在孩童天真的意識里,世界以自己家的房子為圓心朝四方擴散,所謂全世界不過是我們生活的那個鎮子以及周邊幾個鎮子的組合。因此,在《怪客》中,“我”家房子矗立的那條、未來會變得繁華的小街,似乎被高度提純,濃縮了全世界的風景與可能性,由此也開啟了“我”在這條街上的“歷險”。
童年視角在這篇小說中意義非凡,在附于文后的“自問自答”里,作者坦言“小說里若有若無的詩意,得益于兒童視角……特別是在語言上,經常會旁逸斜出”。作為成年人眼中稚嫩的孩童,他們的邊界意識最是淡薄。在孩子們看來,萬物有靈,他可以與世界上的一切有生命體或無生命體對話。《怪客》中的“我”便是如此。“我”和鄰居家的花貓是好朋友,經常與它交流,“花貓告訴過我,它從不吃素菜”。花貓在文中頻繁出現,這不能不讓我想起蘇童小說里的那些貓,作為暗夜精靈,貓給人的感覺總是神秘莫測,它們像游魂一般在江南水鄉低矮的屋檐上閑庭信步(作為江南人的趙志明應該擁有相類的童年經驗吧)。由于家庭貧困,母親在房子后面開辟了一片菜園,種了很多蔬菜,“我”認為那些菜蔬全是用母親的淚水澆灌長大的,因此,“吃起來有一股苦澀味”。和李白的“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一樣,“我”也將月亮視為一只白瓷盤,黛青色的天空則恍如湖泊,好友花貓邀請“我”去天空獵魚,當魚這個意象出現后,前邊的白瓷盤瞬間便貼切起來。這簡直就是一幅稚拙樸素的兒童畫——暗沉沉的夜空,寥落疏星,雪白的瓷盤似的月亮上橫著一條魚,憨態可掬的花貓端坐于夜空下的泥鰍脊上,手里抓著一副雪亮的刀叉。
除了修辭的陌生化,視角的選擇同樣能實現陌生化效果。《紅樓夢》第六回,劉姥姥一進榮國府,周瑞家的帶她去找王熙鳳,關于鳳姐家廳堂里的陳設便是通過劉姥姥的視角展現出來的。在現代人看來不足道的鐘表,卻唬得她一展眼。讀者跟著視角人物,重溫了這一司空見慣的物件,同時,也會感嘆于貧富懸殊對于視域絕對化的局限,當然,這種視角也會讓人物更加立體飽滿,顯得真實。莫言的《生死疲勞》用幾種動物的視角來描寫1949 年后風云變幻的社會家國,借由動物的眼睛去凝視那些超越人類理解能力極值的種種瘋狂和狂熱。阿來的《塵埃落定》則經由一個傻子來講述。此傻子非彼傻子,他的內心世界相當豐富,那些所謂正常人無法理解、無法看見的,他都能理解、能看見,簡直就是一位智者。
《怪客》中最富有意味的角色便是一個被稱為怪客的家伙。這一角色幾乎沒有正面出場,卻像一種暗黑的力量,從故事軀體的每一只汗毛孔滲透出來,彌漫出一片淡紫色霧靄和籠罩全文的神秘感。一直將自己當作這片區域主宰的花貓,對怪客卑躬屈膝。“只要怪客出現,它就很安靜,也很聽話,簡直就像最出色的仆人。”看上去,怪客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母親恰恰是聽信了他關于這條街未來會出現市集的預言,才毅然決然地建造了那棟樓宇,目的是開家庭旅館養活自己和孩子。怪客住在“我”的隔壁,“我”另一邊住著母親。怪客、“我”、母親,三個人住了三樓的三個房間。這情形多么像一張全家福,爸爸在左,媽媽在右,孩子居中。
“我”家旅館的生意越來越好,形形色色的客人住了進來。住在“我”家202房間的一位女客,常常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有時候,母親會去陪她,兩個女人的哭聲能穿越最厚的墻壁。后來,母親帶她去了怪客的房間。“我”卻認為,這位女客人肯定是遇到困難了,去找怪客求助。
怪客唯一一次正面出場,是在小說中間偏后的位置。某個晚上,二舅讓“我”去街上買酒和下酒菜,“我”怕黑,便讓怪客陪著。怪客笑了,眼神炯炯發光,并且是一言不發地陪“我”出門。“我”像一位向導,引領著怪客,以及怪客身后的一眾讀者,從那條有路燈的老街走過,依次路過了糧管所、水電站、鎮政府、醫院、藥店和派出所。于是,我們遇見了老鼠、花貓、黃貓、一條無精打采的狗、蝙蝠,以及那些“我壓根看不清楚的生物”。歸途,“我”建議走另一條小路,于是我們又一起領略了那條正在建設中的,未來商業街的雛形。整個過程,無論“我”說什么,怪客都不開口,只是微笑,“眼睛像星星一樣明亮,只要他眨一下眼睛,夜空中就會劃過一顆流星。”而一顆流星的劃過,在童話故事里,代表著一個人的死亡。
就這樣,我們從彌天大霧中窺見了殘酷真相,所謂怪客,壓根就不存在,那不過是“我”用孩童一廂情愿的天真虛構出來的角色。根據全文中父親的缺席,我們不難猜到,怪客便是父親。怪客雖有形(作者數次眼睛的刻畫)卻無實(從不開口講話),因此,我們不妨做個大膽的猜測,怪客,其實是“我”隔壁房間墻上那幅父親的遺照。在文末的“自問自答”里,作者也證實了這一點。若不是借由特殊視角,這種虛構便很難成立。
張悅然在《較遠的觀察者》一文中說,視角像阿莉阿德尼的線團,帶領讀者穿行于敘事迷宮,并最終走出來。我們仰賴于它才沒有迷失,并且,收獲了一些意義。然而,我們也受制于它,無法看到故事的另一面。世界是無序的,視角為我們建立了一種秩序。視角的選擇對于一部小說的成功與否起著決定性作用。余華曾在《活著》的序言中說,最初他采用旁觀者視角,故事很難推進,后來改成第一人稱自述,于是奇跡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