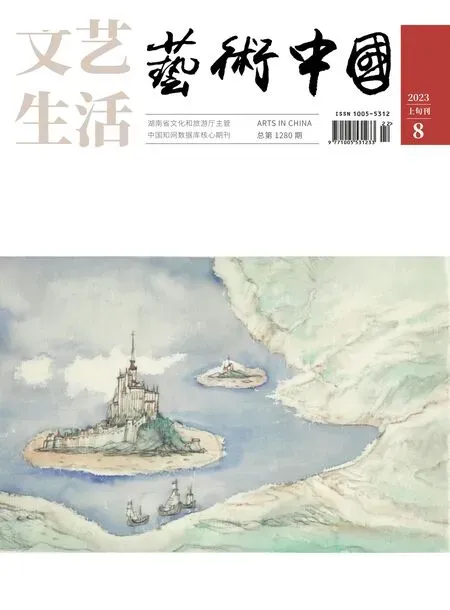追溯漢唐氣象
——淺談當代硯雕藝術的創作問題
◆陳興旺( 長沙 )
“雕刻為立體藝術,書畫為平面藝術,豈可盡廢立體藝術,而代之以平面藝術?故竹刻中書畫之趣若愈多,雕刻之意趣必少,竹刻豈能為書畫之附庸哉!” 20世紀40年代,晚年金西厓于《刻竹小言》中有此感嘆,不得不令人深思。竹刻如此,硯雕又如何?
一、明清傳統影響下的當代硯雕現狀分析
明清以來越來越多官方以及文人參與到硯雕藝術中來,硯臺由原來的純實用功能轉變為更趨向審美功能。裝飾圖案和詩詞書畫的融入越來越多,讓硯臺的審美趣味和藝術價值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時硯雕風格也受到竹木牙雕、磚雕、玉雕的深度影響,民俗類題材、裝飾性風格的硯作也日益增多。技藝快速發展,細節上的精致到達更高的層級,由此硯林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繁瑣堆砌之作,呈現匠氣有余而韻味不足的局面;硯臺的形制方面呈現更多的扁平化傾向,硯雕創作時習慣于平面上的深度介入,較少關注硯臺的整體氣象。
少數推崇素硯者,多注意到宋代的傳統硯式,執著于古代的器型、比例、尺寸。此類硯雕,形制規范、尺度嚴格,實用功能上表現突出;但規矩有余,浪漫不足;硯石的自然之美也幾無所剩。硯雕人若能領悟宋硯背后的思想邏輯,以及它與當時社會風貌的呼應關系,也許不會局限于刻舟求劍。
在國家大力提倡創新精神的背景下,偶有硯雕人直接從西方抽象雕塑中吸收形式感,融入硯雕創作。此類硯雕作品由扁平化轉向立體化,豐富了硯臺形制,作品的空間感、形式感增強;也因為片面追求形式的夸張,所以實用性大大減弱,作品的精神性容易陷入空洞。
綜上所述,明清以來硯林的常態化現象,實際就是因為硯雕人在追隨繪畫或傳統圖案時,已經無意中局限于明清硯雕的傳統。我們并不完全反對硯雕中的文人畫傳統或宮廷裝飾風傳統,但我們必不可局限于此,盲目追隨。雕刻和繪畫在古代中國美術范疇內,常彼此融合不分,但是二者畢竟和而不同。中國畫以軟性之毛筆,在平面的紙張上勾皴點染,毛筆運動中墨色浸潤,形成二維空間的視覺傳達。而硯臺雕刻是以硬性而鋒利的刀錐,在立體三維的自然石頭上雕刻而成。它由刀與石的碰撞而引發形體的變化,留下刀錐的運動軌跡,進而呈現三維空間的融合主觀意識的藝術形體,可360度視覺體驗立體空間(基于形體、肌理的光影表現),甚至觸覺感受。繪畫與雕刻兩者基于不同材料,不同技法而呈現,對應不同的審美體驗,意趣迥異。
當代中國經由幾代人的艱苦奮斗,已經呈現包容開放的大國風范,欣欣然蓬勃發展的大國氣象,時代已然對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所謂“筆墨當隨時代”。那么當代硯雕工作者在藝術創作時如何反映盛世氣象,也將面臨考驗。
二、追溯漢唐氣象
“氣象”一詞早在戰國時期就已出現,《黃帝內經素問》中就有《平人氣象論》,這里的“氣象”即指人的生命活力和精神面貌。唐代詩人、畫家王維所撰《山水論》:“觀者先看氣象,后辨清濁。”這里的“氣象”是指整個作品所創造的意境。北宋畫家郭熙《林泉高致集·山水訓》:“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須遠而觀之,方見得一障山川之形勢氣象。”這里“氣象”指藝術形象所散發出來的氣勢和神采。南宋詩論家嚴羽《滄浪詩話》:“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這里“氣象”則傾向于人物所具有的氣質、風范和時代精神。由此可知“氣象”一詞,涵義豐厚,但一定是就形象渾然一體的整體面貌而言,絕不是一枝一葉、精致入微的細節所能呈現。
中國歷史上最具有重要影響的漢唐時期,由于發達的經濟、繁榮的文化,一度成為世界各國經濟交流的中心,同時也是各國文化交流的中心。漢唐氣象不僅是漢唐時期地域的遼闊,更是自由開放、豪邁宏闊的精神。那個時代的精氣神,包容大氣、雄渾寬厚,充滿陽剛之氣。這種漢唐的氣象直接影響到當時人們的審美,既影響了詩詞、繪畫的氣息和風貌,也直接反映在那個時代的雕塑和器物之上,這種表現與當代硯雕的面貌大相徑庭,所以我們不妨以古為師、以今為用,在追溯中去重新認知。
梁思成《中國雕塑史》中有言:“藝術之始,雕塑為先。蓋在先民穴居野處之時,必先鑿石為器,以謀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乃作繪事,故雕塑之術,實始于石器時代,藝術之最古者也。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藝術,向為國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鮮有提及;畫譜畫錄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詳。”
中國書論畫論或詩論,皆可謂汗牛充棟,而雕塑方面卻是“考之古籍,鮮有提及”,就連“雕塑”一詞也是源自明治時期的日本美術史學者大村西崖的相關論述。同樣以石為材料,以雕刻為表現方法的硯雕藝術創作者卻不可不高度重視。而中國漢代雕塑的雄渾寫意風,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開創了因材雕刻的創作方式。
“總是保持著一定的自然形態,稍加雕琢,便神氣活現、巍然磅礴。這種風格至漢代達到鼎盛,所憾的是漢代以降,此風漸衰。”
這個時期的石雕藝術不僅規模宏大,而且藝術成就卓爾不凡,意象表達與自然之美的結合,彰顯出雄渾厚重的盛世氣象,尤其值得硯雕藝術創作者深入研究。比如漢代霍去病墓石雕:

西漢 石雕馬踏匈奴 茂陵博物館藏
“霍去病墓石刻都是用整塊石頭雕刻而成的,體量很大,在雕刻時巧妙地借用石頭的天然形狀‘因石施刻’,按其自然的形態稍加雕琢,去粗求精,融合圓雕、浮雕和線刻等手法,在關鍵部位加以雕鑿。藝術趣味的粗放古樸,形態統一完整,并沒有停留在外行的模擬上,而是以突出對象的內在精神為目的,從中可以看到漢代雕塑雄渾厚大、質樸自然的風格。”
大唐盛世擁有非凡氣度與格局,社會充滿生機、朝氣,佛教藝術朝向自信、成熟的風格發展,豐腴優美、磅礴大氣,為此時期重要特征。唐朝也是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發展的高峰時期。唐代佛教造像的典型代表龍門石窟大盧舍那佛,通高17.14米,典雅豐滿、含蓄靜美,充分顯示了唐代的恢宏氣派和精神力量,是一個偉大時代的象征。
“在欣賞一尊中國佛造像時,你往往會感受到深厚的中國情懷,那是一種亙古以來的親切感。在觀看佛像時你能感受到那種安詳、寧靜,而不會去關注佛像的身體結構合不合理,臉部比例是否失調,他似乎就是那樣才是合理的,才是最自然的,盡管有時候甚至看起來不美,但它確實合理得不能再合理了,形式已經不重要,情緒則直達內心,這是花非花、物非物的道理,這就是中國雕塑的魅力,美到高處的大境界。”
石雕佛教造像強調的是雕刻家通過感性認識,于石材和創作對象中捕捉抽象的形態元素,突出雕塑的線條感,弧度輕松而舒暢,表達概括簡約,充滿韻律之美,同時發揮了主體對雕塑空間感的精神滲透。
“漢代的工藝美術在歷史上的成績突出,意義深遠,魯迅先生以‘深沉雄大’予以高度評價。工藝美術作品具有注意整體刻畫、大局安排,樸素而不單調、粗獷而不鄙野、渾厚而不凝滯、豪放而不疏散,充滿著大膽的想象、夸張,有一種飛揚、流動的感覺,有一種‘氣勢’之美。”
以上海博物館藏東漢時期臥虎蓋三足石硯為例:
此硯圓形,三足,最大徑6.2厘米,連蓋高4.5厘米,青石質,硯蓋和硯體兩部分,以子母口相合。硯蓋上一虎盤踞,回首微抬、遠望,具有一種隨時躍起的氣勢。絕無精雕細刻卻已形神兼備,其神 “威而不猛”。正所謂“深沉雄大”。
“帶有高浮雕動物蓋的三足硯是硯史上十分奇特的硯形,其流行的時期僅限于東漢至魏晉,以后便不復存在。”

唐代 洛陽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


東漢 臥虎蓋三足石硯 上海博物館藏
但是基于圓形三足加高浮雕的硯雕形式,粗獷的雕刻手法,整體小中見大的氣勢,漢代雄渾氣象的彰顯,這些都特別值得當代硯雕藝術創作者回首追溯、深入領會。
唐硯的浪漫恢宏與豪邁大氣,相對于明清以來傳統的扁平化的硯作,顯然更加關注硯臺整體造型的立體效果,也絕無過多紋飾細節的斤斤計較,更加注重空間感和力量感。
以故宮博物院藏十二峰陶硯為例:
“硯為細灰陶質,硯面呈箕形,前高后低,三面環塑十二山峰,中峰下似為龍首,可貯水滴入硯面;左右山峰下各塑人像,呈負山托重之勢。內外兩重山峰錯落,與硯邊相連,自然形成半圓形硯堂。底部三足,也刻成層巖疊立狀。此硯造型新穎,雕塑山峰奇特,并以簡練的線條刻畫而成,頗顯雄偉生動。”
數千年歷史長河中,中國雕塑蔚為大觀,然而記載不專、敘述甚粗,更何況作為書房小器的硯臺。硯臺雖也伴隨中華文明一脈相承,但是從藝術審美的角度來論硯者古來少有。漢唐的硯臺沒有詩書畫印和圖案的附加,它們本身就如同一首詩,絕不是僅僅作為一首詩的載體而存在。追溯漢唐氣象,當然不是為了再現漢唐硯臺的外在形貌,只為當代硯雕藝術在創作時的,能夠以實在的雕刻形體來彰顯鮮明的當代氣象。
三、當代硯雕創作的探索
立足于當下,深入感受時代氣息、深入了解當代審美需求的基礎上去追溯漢唐氣象,不僅在于形式上的學習,更需要雕刻者自覺回到石雕技藝中,去領悟和把握硯雕的題材、形體、表現方法以及作品精神的協調統一,達成自然而然的萬物化生的“中和”狀態。作品要有氣象,首先需要創作者胸中自有非凡氣象,氣象的養成需要社會環境的熏陶、生命體驗的滋養、主觀意識的追求,藝術表達的經驗累積,方能渾然而成。當代硯雕創作要能達成圓融和諧之美、氣象渾成的藝術高度,有幾點特別需要注意:
漢代石雕尤其尊重石材的自然之美。當代硯雕藝術創作時,首先需要認識自然石材內在的品質之美,因為硯有研磨的功能需求,所以它的硬度、細膩度、礦物含量,是硯雕藝術家首先需要考量的因素,對于硯石內質的鑒別力是硯雕創作的最基礎的要求。其次,石材作為硯臺的基本材料,每一塊都具有獨特的形狀、紋理和色彩,蘊含著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氣息。比如,通過人工開鑿的方式,采自礦坑的端石,與通過自然風化、水流搬運的形式被硯雕藝術家從溪流獲得的歙石,其形狀、肌理、氣質都必然大相徑庭。硯雕人需要尊重石材的天然狀態,可以通過打磨,觸摸和觀察的方式,深入感受石材的質感和紋理以及色彩特點,避免過度加工而完全喪失自然之美。根據石之形態、色相、質地等特質,因材施藝,強調存天地之形、圓宇宙之美、天人合一的原則,藝術家們可以呈現出更加獨特、生動和充滿生命力的硯雕作品。
硯雕藝術畢竟不是平面藝術,創作時應該強調立體形象的空間意識,注意表現方式與作品精神性的高度契合。這一點完全可以借鑒唐代的佛造像藝術,它不僅有獨特的理想的形象創造,也有三維空間中線條所散發出的強烈韻律之美。線條的韻律與造像的精神性和諧統一、高度圓融。瑞典藝術史學者喜仁龍在1925年出版的《西洋鏡:5——14世紀中國雕塑》一書中已有相關論述:
“一件藝術品的藝術價值主要由韻律之美而非外在的表現形式決定,注意力重點放在表現物‘神韻’之上,清晰地展示韻律,需要既抽象又便于形象化的闡釋形式。在雕塑和繪畫作品中,韻律可以借助線條、色彩、形狀、明暗等表現方式傳達出來。但是,機械模仿外在的表現形式創造不出韻律,藝術家必須與作品融為一體,韻律才能由內而發。”
漢唐硯臺并不拘泥于細節的具象表達。中國傳統藝術向來崇尚“境生象外”⒁,“妙在似與不似之間”⒂的藝術意境。一味斤斤計較于紋飾上的精致,并不能突顯藝術上的精神力量,所以硯雕創作中應正確地認識具象、抽象、意象的關系,強調主觀意念對客觀形象的審美改造或審美升華。
當代硯雕藝術創作應該立足當代審美,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而不是陷入傳統形式的局限,更不能為形式而形式,忽略作品的精神屬性。探索性、試驗性的雕塑造型可以在硯雕創作中出現,新觀念、新材料、新技術的跨界融合也可以嘗試,但硯臺的實用功能不可忽視。當代硯雕藝術創作中,造型與表現方法上與環境空間的協調統一是基本要求。硯雕創作可以借鑒當代實驗性雕塑藝術,結合當代設計的理念和方法,注重功能性、人體工程學和審美體驗的綜合考量,以適應時代的需求和審美趨勢。
結論
在明清以來的傳統下,當代硯雕創作出現了傳承有余而發展不足的局面。尤其從硯臺整體形制上而言,雄渾大氣的陽剛之美,難得一見。所以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漢唐去尋找屬于硯臺的陽剛之氣,無論是漢代霍去病墓石雕的雄渾厚重,抑或是唐代佛教造像莊嚴宏大的韻律之美,還是漢唐硯臺本身的氣宇軒昂,都特別值得深入研究與借鑒。
當代中國正在偉大的民族復興之路上穩步前進。廣大的藝術工作者,欣逢盛世,理當與時俱進,以大胸懷大格局,以豪邁雄健之姿觀照時代氣象,創作出更多承載偉大時代之精神風貌的作品,這是當代硯雕藝術創作者的使命和擔當。如此,硯雕藝術才可以得到更廣泛的傳承和發展,才能更加適宜于當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千里江山硯 陳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