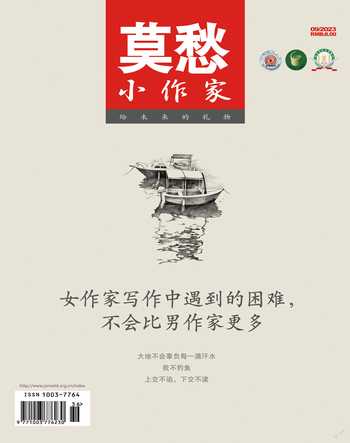塵心洗盡興難盡
梅雨季節,清溪流過王家村,在村中形成了四五個池塘。我住的民宿就在一個池塘邊。坐在臨窗的茶席前,執杯添茶,喝著溫厚的茶湯,隔著落地玻璃窗,看村外的青山在細雨中朦朦朧朧,看落花幽草在圍墻內的角角落落和夯土墻的縫隙中努力地擠出來,頑強生長著去覆蓋更多的地方。池塘就在腳下,但雨中看不清魚兒在水中的游動。晚唐詩人張蠙寫有“墻頭雨細垂纖草,水面風回聚落花。井放轆轤閑浸酒,籠開鸚鵡報煎茶”的詩句,與眼下的鄉村生活,倒是很契合。
雨時斷時續。忽然放晴了,我趕緊把洗好的衣服晾出來曬一曬。才轉過身呢,淅淅瀝瀝的小雨又來了。唉,梅雨季節的天氣,像一個愛使小性子的娃娃,瞬息多變,讓人很無奈。
1
“白茶之鄉”溧陽不僅有著蜚聲全國的茶產業,更有幾十家星級茶舍。茶舍, “茗居”也,烹茶待客的地方,它們如一張張茶香氤氳的請柬,邀來四方賓朋。“茶旅融合”,成為溧陽發展的靚麗名片。
站在村口往外看,王家村似乎處處都有茶園。村東面的松嶺頭,是溧陽最早引種白茶的地方,也是“天目湖白茶”主要生產基地之一。山坡上的白茶,葉片的顏色比一般的茶葉要淺得多,呈鵝黃,甚至金黃,與翠綠的山林、多彩的山花,構成一幅鮮活的山地美景。開春后,經過陽光雨露、春風厚土的滋養,茶樹將蘊藏了一整年的能量積聚尖梢,釋放于一芽一葉。制作天目湖白茶是很講究的。采茶,不可使蠻力掐斷,而應順勢輕輕一彎,巧妙地摘下長度2.5厘米左右的嬌嫩茶芽。鮮葉經過攤晾、分揀、殺青、揉捻、理條、焙干、提香等多道環環相扣的程序,才能成為成品茶。天目湖白茶賦予了松嶺頭鮮活的朝氣。這個山頭之所以稱作“松嶺頭”,是因為它扼守松嶺古道的北端,為皖南深山里那些鎮村的物產輸出到太湖邊的商埠,進入流通市場,發揮過重要作用。松嶺古道留有大量人文遺跡,有講不完的往昔故事。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交通方式的革新,歷經風雨的松嶺頭和周邊的古村,乘著鄉村振興的東風,正煥發出新的光彩。
越來越多的游客慕名而來,因為天目湖白茶,因為王家村,因為翡翠湖邊的青峰仙居。除了在網紅點打卡,游客還可以在臨湖觀景的茶座,或者村口的驛站,品一杯好茶,靜聽溪水潺潺,頗有一番閑雅的滋味在其中。若是夜幕降臨,雖然只能看到燈光照射范圍內的一段欄桿和幾盆鮮花,但配上舒緩的音樂,品茶的感受又不一樣了。
2
王家村的老漢們不講究這種小資情調,但也愛茶,春日里百花綻放的時候,看山里茶樹又吐出新芽,就心癢癢地期待春天第一杯新茶。當然,他們最中意的還是清明前后自制的“口糧茶”。自制茶葉在王家村有久遠的歷史。擔任過村黨支部書記的萬曉松說,老輩人大多在房前屋后、村頭地邊,有一小塊屬于自己的茶地。清明前后采摘茶葉,在自家的大鐵鍋里完成殺青、搓揉、烘制等工序,然后裝進陶罐,面上鋪幾層黃表紙,壓上兩塊生石灰,再用塑料紙封口、麻線扎緊,擱在床腳邊。這就是老漢們自己享用或招待親友的“口糧茶”。
老輩人的“口糧茶”,產自無人照看的野茶地。這種在荒蕪中悄然生長的茶葉,悄無聲息地汲取營養,厚積薄發。“口糧茶”雖然品相粗糙,卻有一種回歸本源的質樸之氣。那是經歷過世事滄桑的老人最喜愛的滋味。村里年長的農民,年輕時肩扛生活重擔,白天開礦、采石,砍竹子、打板栗,晚上劈篾、編竹器,為舒緩身心,就養成了喝茶的習慣。忙碌一天后回到家中,先坐下來泡壺茶,打開收音機聽著戲曲,喝著香味濃郁的粗茶,疲憊的身心似乎立馬就有了緩和的感覺。
每一壺茶的背后,都有一代代人的傳承和血脈相連。71歲的老站長周志清告訴我,山里待客泡茶,有幾種不同的方式。用紫砂壺泡茶,然后注入白瓷杯分享,那是常見的。講究一點的是用瓦罐煮茶。先將瓦罐中的水煮沸,再抓一小把粗茶投入,然后撤火,用余火慢熬出棕褐色的茶水。更講究的,是將茶葉放入陶罐中,先用文火烤炙,除去潮氣,再倒入滾燙的開水,“呲啦呲啦”爆響的同時,竄出一股撲鼻的茶香味。這樣熬煮出來的茶,稱為“釅茶”,滋味十分香濃。釅茶招待的都是懂茶的知己。一般人覺得釅茶太濃、太苦,而年輕時以體力勞動謀生的山里老人,卻覺得喝釅茶長精神,干活有勁。“喝幾盅釅茶,就能精神一整天。”80歲的老隊長吳順法,年初病了一場,手術后恢復得不錯。跟我閑聊時,他滿意地說:“年輕時天天干重活,透支了健康,現在身子骨還算硬朗,就是長期喝茶的效果。”老吳每天喝釅茶,不僅是一種生活習慣,似乎也是除躁止咳的長壽良藥。就像現在的梅雨時節,在小火爐上煨一瓦罐茶,伴著水煮沸的聲音,茶的濃香飄出來,老兩口一遍又一遍倒騰手中的器具,互相斟茶,雖然言語交談甚少,卻是相互陪伴的最好方式。
這幾年,村里的產業興旺起來了。松嶺頭茶場、白蓮茶場有近500畝茶園,松嶺部落的鄉村旅游項目、云袖文旅等多家民宿,還有剛開張的溫德姆溫泉度假酒店,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如今,村里七八十歲的老人,只要身體健康,都還在上班,從事農園維護、環境保潔、旅游安保等行當。萬曉松笑道,83歲的老母親,每天去茶葉地里拔草,工資一百元一天,身體好,心情更好。社會安定、經濟富足,老人們也注重養生與享受了,喝的“口糧茶”也升級了。茶場的采摘期結束,修剪之前,老人們自己去采點茶葉,或者收十幾、二十斤鮮茶,到加工點做兩三斤茶。沒人在家做粗茶了。論起喝茶,萬曉松品著茶杯里的天目湖白茶說,這滋味畢竟要比粗茶好得多。
村里的老人飲茶,看似隨意,卻蘊含著他們對生活的滿足感。早上起來,飲一壺茶,頓時渾身神清氣爽、舒心暢快。勞作之余的茶歇,邊喝邊話家常、聊八卦,其樂融融。忙了一天回到家,泡一壺好茶,喝上幾小口,悠閑地與老伴聊天,也是身心放松的一種養生方式。
用清明后的茶葉制作的“口糧茶”,沖泡出來,茶湯濃醇厚重。村里老漢們飲茶,重的就是淳樸厚實的味兒。從茶中慢慢地品味著陽光的味道,當年的豪情,有一種心醉神馳的圓潤甘甜。王家村里有好多古樹,數銀杏樹最醒目,長在池塘邊,枝丫伸向老宅子的瓦屋頂。村里老人多,他們白發、佝僂、腳步蹣跚,比起大樹,他們并不老;走進他們的內心,聽他們講述屬于他們的故事,也許很古老。
在悶熱的梅雨季節,喝鄉土風味的釅茶,需要心態的沉淀。祛除急功近利,回歸本真,才能品出釅茶的本味,發自內心地感覺到:勞動和人生,都是苦盡甘來。在王家村,在煮茶、喝茶的氛圍里,我們又找到了庭前花開、天上云卷的感覺。
湯全明: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多部散文集。
編輯??? 沈不言?? 7865596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