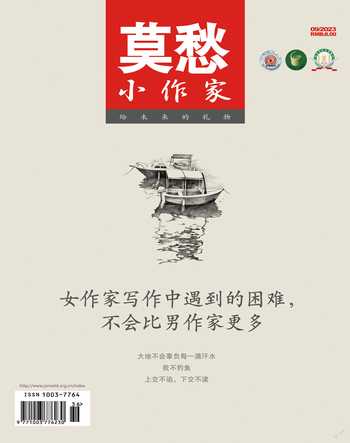遇見西溪
從未想過,離開數年之后,我還是會無數次想起那片土地。
我的青春,我對這個世界最初的認知,以及綿延了我日后職業生涯的理念與熱愛,都是在那個叫“西溪”的地方形成的。我在那片土地上工作生活了七年,離開時,雖有不舍,但依然滿心歡喜——我進城了。我曾以為,那片土地于我,只是人生旅途的一站,會隨著光陰的流逝,越來越淡……
1
1980年,剛剛考入中學的我,有幸參加了江蘇省東臺市首屆中學生夏令營活動。活動的內容豐富多彩:參觀雷達部隊基地、學習制作簡易飛機模型……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步行穿過三里路去西溪古鎮看寶塔。
三里路,素有“馬脊梁”之稱,形象地道出這條連接西溪古鎮和臺城的要道的窄而險:路的一側是陡峭的坡面,一條幾十厘米寬的水道躺在坡底,水道過去是一大片農田;另一側是水勢滔滔的泰東河。領隊老師一路叮囑大家不要東張西望,注意腳下安全。窄窄的小道上,不時有拖著板車的菜農迎面而來,交錯時,我們只能側著身子,挪步通過。
走過三里路,我們去參觀那座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唐塔——海春軒塔。遠遠望去,夏日湛藍的天空下,一座敦實厚重的磚塔穩穩健健地矗立在廣袤的田野間,與鄉野的蔥翠活潑渾然一體。古樸滄桑的唐塔,歷經漫長的歲月風霜,安寧淡泊地站在如水的光陰里,與這片古老的土地相依相伴。
2
也許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數年之后,大學畢業的我回到家鄉,被分配到西溪中學工作。校園偏僻,地處西溪八字橋以西,規模很小,初一到初三共六個班級,學生大多來自西溪小鎮和周圍的幾個村莊。
學校大門朝北,朝西的那面有兩排教工宿舍,校園的南端是泰東河。校園南邊,三間平房做了食堂。食堂只有一名員工,大家叫他王爹。王爹做的飯菜簡單而可口。蔬菜是他自己種的,米飯是用大灶燒的,金黃的飯鍋巴香脆誘人,比平常家中的飯食香得多。王爹隨和,見人總是一臉笑。我們吃飯的時候,王爹總在一旁忙活,我們說:“王爹一起吃吧。”王爹擺擺手:“我不忙,你們先吃。”我們吃好后,王爹連聲說:“走吧,走吧,我來收拾。”
我常常在午飯過后,站在河邊眺望往來穿梭的船只。沿著這條水道一直往西,就可以到達泰州,然后,可以到更遠的地方。
校園往西不多遠,有一個叫“五神廟”的渡口,渡口下去就是董永七仙女故事的發生地——臺南。我總想著,我也要從那兒擺渡過去,看看渡口的那邊有些什么。那時,我狂熱地癡迷席慕蓉的愛情詩,渴望一場刻骨銘心的相遇,或送別。不久,這樣的想象變成了現實,我的一個同學畢業分配到了臺南稅務所。未曾提前告知,我擺渡過河,騎自行車去看他。不巧的是,那天他恰好回了臺城。一顆心,悵然若失,所有對他的祝福,在襟袖之上,婉轉流年。
校園里,十二棵高大的銀杏樹都有著上百年的歷史。摘下的果實經去皮處理,分給每個老師,這讓我們期待又欣喜。待到秋風四起,備課、改作業的間隙,抬頭可見旋舞的金黃,樹下一地燦爛,整個校園籠罩在一片溫暖柔和的光里。那是秋天的好記憶。
西溪的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特色,譬如“工農村”以長蔬菜為主,“花園村”以培育各色花卉見長。有孩子夜里隨父母上街卸蔬菜,從我家的院墻外扔進來大蒜、青菜、芹菜等。早晨起床,但見院子里躺著一捆水靈靈的蔬菜,到了班級,也沒有孩子跟我言語,我一頭霧水,吃了許久“霸王餐”。很久之后,才聽到一個孩子無意問起:“老師,青菜好吃嗎?”孩子的臉上帶著羞赧的笑,而我年輕的心,從那時開始,被孩子純真的愛充滿。
3
多年之后,這片土地上的滄桑巨變叫人目不暇接。曾經的三里路、馬脊梁,早已隱在草叢深處。新修的泰山大道寬敞流暢,古色古香的海道橋在夜幕下華光璀璨,嫵媚動人。夏夜,橋邊納涼之人不絕,也有人拋竿夜釣,往往一人垂釣,看客四五。有幾回,我散步經過,停下腳步,愣是看了許久。眼見半個多小時過去,水下全無動靜,垂釣者仍氣定神閑。不由想起一句話:水清魚讀月,山靜鳥談天。想來水下的魚兒,都乘著這美好的夜色,賞月去了。
去年,我的第一屆學生請我吃飯。那天,紛紛揚揚的雪花漫天飛舞,十多個孩子一一過來敬酒。言辭懇切,讓我心生暖意。
這一生,我不知道還會遇見什么人,發生多少事,但所有的遇見和經歷,都將成為生命中的財富。就像村上春樹說的,人生沒有無用的經歷,當你經歷過一些事情后,眼前的風景已經和從前不一樣了。
明媚的春光下,我去郊外走走,看樹,看河流,去西溪植物園看花草。陽光正好,微風柔柔吹拂,送來枝條抽青的氣息。我在春天的水邊駐足,看春水起漣漪,看蒹葭輕舞蒼黃,用暖暖的色調抒寫年年春來的美麗。
嚴宜春:作家,江蘇省東臺一中高中語文教師。
編輯 閆清 14533370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