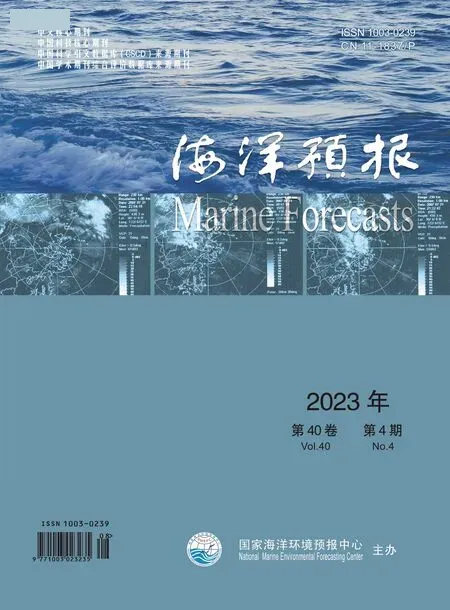不同海浪數值預報產品在渤海和黃海的預報水平評估
李文博,李銳*,王彬,張薇,高山,侯喬琨,孫雅文
(1 山東省海洋生態環境與防災減災重點實驗室山東青島266100;2 自然資源部北海預報減災中心山東青島266100)
0 引言
海浪災害是人類在海上和近岸活動的最主要威脅,對生命和財產安全可能造成巨大損害[1-5],因此,準確的海浪預報是海上活動的最基本保障。隨著數值預報技術的發展、數值預報產品的豐富和改進以及計算機運算能力的提高,以海浪數值模式為核心的海浪數值預報系統已成為海浪預報和業務研究的主要手段,海浪預報水平也有了較大提高[6-9]。目前常用的海浪預報數值模式主要為第三代海浪數值模式WAM[10-12]和WAVEWATCH-Ⅲ[13-15],兩種模式均可模擬大洋和近海的海浪生成、傳播與耗散過程。
隨著海浪數值預報產品的廣泛應用,對其預報誤差的系統檢驗也必不可少。目前已有不少學者在海浪數值預報產品的評估方面做出研究。20 世紀 末21 世 紀 初,TOLMAN 等[16-18]通 過 對 比WAVEWATCH-Ⅲ模式計算結果與浮標數據,改進了模式源函數;BIDLOT[19]對21 a 的數值預報結果進行檢驗評估,發現包括歐洲中尺度天氣預報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 - Range Weather Forecasts,ECMWF)海浪預報產品(簡稱EC)在內的幾種產品的預報準確性均有提高;WANG 等[20]首次利用中國近海的波浪浮標觀測數據檢驗了EC海浪預報產品的誤差,并分別從離岸距離、水深等方面討論了EC 產品的誤差分布情況;李燕等[21]對WAVEWATCH-Ⅲ在渤海的預報結果進行了檢驗;梁 小 力 等[22]對 基 于SWAN(Simulating Waves Nearshore)模式的全球海浪預報結果進行了初步驗證。然而,目前的海浪數值預報產品評估僅限于對不同站位的誤差開展統計,而對于誤差的時空分布、尤其是不同天氣過程下的誤差分析卻鮮有研究。另外,目前海浪預報水平評估主要聚焦于大洋和開闊海域,渤海和黃海作為半封閉海,海浪風區短、水深淺,與大洋海浪生成傳播機制有較大不同,對現有海浪預報產品在渤海和黃海的預報能力缺少系統分析。為了系統評估渤海和黃海的海浪數值預報水平,本文擬對EC、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NCEP)的全球天氣預報系統(Global Forecasting System)海浪預報產品(簡稱GFS)和自然資源部北海預報減災中心(North China Sea Marine Forecasting Center of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海浪預報產品(簡稱NMFC)在渤海和黃海海域的預報能力進行初步檢驗與評估,充分發揮數值預報產品在海洋環境預報中的作用,為今后渤海和黃海海浪預報技術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值預報產品
EC產品所用海浪模式為WAM。NMFC與GFS兩種產品所用海浪模式均為WAVEWATCH-Ⅲ,其能量輸入耗散項均采用ST4 參數化方案,其中NMFC主要參數化方案設置包括ST4風浪模型和海浪耗散項、JONSWAP 底部摩擦方法、線性風時間插值、三階傳播方案等。
考慮到資料的連續性,本文收集2021 年EC、GFS、NMFC 3 種預報產品24 h、48 h、72 h、96 h 預報時效的有效波高預報結果用于評估。EC 和GFS的時間分辨率為3 h,NMFC的時間分辨率包括3 h和1 h兩種,其中3 h分辨率的NMFC用于與EC和GFS橫向比較,1 h分辨率的NMFC用于日極值誤差分析。各預報產品的簡要情況介紹見表1。EC模式的整體預報效果優于GFS,其中24~72 h 的均方根誤差(RMSE)比GFS減小了6.8%~8%,EC 24~72 h風速預報偏差中位數在0.19~0.25 m/s之間,GFS同類中位數在0.33~0.41 m/s之間,兩種預報產品風速的預報結果整體略偏大,EC的偏離程度相對更小。

表1 各機構海浪數值預報產品及驅動風場情況Tab.1 Brief list of different ocean wave forecast products and wind forcing
1.2 觀測資料
觀測資料包括10 個10 m 大型海洋觀測浮標以及5 個海洋站觀測的2021 年有效波高數據,數據均通過嚴格的質量控制。渤海有3個浮標,位于119°~121°E,37.5°~40°N這一矩形海域內;渤海海峽有兩個浮標,為南北分布;黃海北部有1 個浮標,位置約在該海域中心處;黃海中部有4個浮標,位于120°~124°E,35°~36.5°N 這一矩形海域內;5 個海洋站分別為東營港、小長山、龍口、小麥島和日照港。觀測結果分別與上述3 種海浪預報產品進行直接對比,并利用雙線性插值將3種數值預報網格數據插值到觀測站點進行誤差統計。
1.3 誤差統計方法
采用相對誤差、均方根誤差和平均偏差來評估數值預報產品偏離實際觀測的情況,誤差統計的具體方法如下:
①相對誤差(Er,單位:%)反映了預報偏離觀測的相對程度。計算公式為:
②均方根誤差(Erms,單位:m)反映了預報偏離觀測的離散程度。計算公式為:
③平均偏差(Ebias,單位:m)反映了預測相對于觀測的整體偏離程度。計算公式為:
2 誤差分析
2.1 誤差總體分析
2021年3種預報產品到報率均超過95%。將預報產品24 h、48 h、72 h 和96 h 的有效波高預報數值插值到10 個浮標站位和5 個海洋站位,將所有結果與實測有效波高進行對比分析,并制作預報與觀測數據對比圖(見圖1),其中紅色線為利用最小二乘法擬合出的線(簡稱LSF 線),誤差統計見表2。從圖1 可以看出,渤海和黃海2021 年低于2 m 的有效波高出現概率超過60%,2 m 以上有效波高出現概率較小,最大有效波高超過5 m。從表2 可以看出,不同波高分段情況下EC 的RMSE 均為最低。3 m以上有效波高的預報相對誤差、均方根誤差和平均偏差均為EC最小,GFS最大,NMFC居中,三者24 h預報相對誤差均在21%以下;3 m 及以下有效波高的預報均方根誤差也是EC 最小,說明EC 對于海浪有效波高的整體預報水平高于NMFC 和GFS。從圖1 的LSF 線和表2 平均偏差統計結果來看,3 種預報產品對于2 m 以上有效波高的預報結果整體偏小0.2 ~0.6 m,且GFS 大浪預報結果偏小的情況最為明顯,這可能與現有海浪預報模式的風能輸入參數化方案和參數設置更適用于開闊海域,渤海和黃海風區較短且波浪成長機制與開闊海域不同有關。

圖1 預報有效波高與實測有效波高對比Fig.1 Comparison of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forecasts with observations

表2 有效波高預報誤差統計Tab.2 Statistical parameter of the comparison of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forecasts with buoy observations
圖2 為3 種產品的偏差箱線圖,用來體現不同預報時效下預報偏差的離散程度和數據的集中趨勢[23]。從圖中可以看出,EC、NMFC 和GFS 24~96 h 有效波高的預報偏差中位數分別在0.06~0.08 m、0.04~0.09 m、0.01~0.02 m 之間,預報結果整體均略偏大。考慮到3 種產品對2 m 以上有效波高的預報偏差偏小,說明它們對2 m 以下有效波高的小浪預報偏大。從圖中箱子和虛線長短來看,3種產品中EC 的離散程度最小,GFS 的負偏離較多,NMFC 的正偏離較多,說明EC 與觀測更為接近,GFS 漏報較多而NMFC 誤報較多。另外,從圖中可以看出,3 種模式預報偏差的離散度隨著預報時效的增長而不斷增大。

圖2 不同模式24~96 h預報偏差箱線圖Fig.2 Different model's box diagram of 24~96 h prediction
2.2 誤差空間分布
根據10 m 大型海洋觀測浮標所在的不同位置,將其劃分為渤海、黃海北部、黃海中部3個海域分別進行誤差統計分析,其中預報有效波高為0~2 m 的均方根誤差結果見圖3a,有效波高大于2 m 的均方根誤差結果見圖3b。從海區來看,當渤海區域的預報有效波高為0~2 m 時,EC 預報結果的均方根誤差最小,NMFC 24 h 和48 h 預報結果次之,但72 h和96 h 預報結果的均方根誤差大于GFS 預報。在有效波高為0~2 m 時,EC 24 h、48 h、72 h 和96 h 預報結果的均方根誤差分別為0.33 m、0.37 m、0.38 m和0.44 m;而有效波高大于2 m時,EC 24 h、48 h、72 h預報結果的均方根誤差分別為0.48 m、0.57 m、0.66 m,這3 項結果均為3 種產品中最優,96 h 預報結果的均方根誤差為0.86 m,高于NMFC 的預報結果(0.83 m)。GFS 預報產品的均方根誤差在有效波高大于2 m 時均為最大。在黃海北部,除有效波高大于2 m的96 h預報結果外,其余情況下EC預報結果的均方根誤差均為最小,GFS次之,NMFC最大。在有效波高為0~2 m 時,EC 24 h、48 h、72 h 和96 h 預報結果的均方根誤差分別為0.28 m、0.30 m、0.32 m和0.38 m;而有效波高大于2 m 時,EC 24 h、48 h、72 h 和96 h 預報結果的均方根誤差分別為0.36 m、0.41 m、0.52 m 和0.61 m。在黃海中部,EC預報結果的均方根誤差均為最小,GFS 預報誤差多數情況下小于NMFC。

圖3 不同海域有效波高預報均方根誤差Fig.3 RMSE of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forecasts in different sea areas
從3 個海區的預報誤差來看,EC 的預報效果在大多數情況下為最好,NMFC 和GFS 的預報結果在不同海區、不同預報時效以及不同有效波高范圍下各有優劣。橫向比較來看,3 種有效波高預報產品在渤海和黃海中部的誤差大于黃海北部,其中GFS預報誤差在渤海區域尤其大,可能是由于GFS 產品的參數化方案不適用于渤海這種短風區、淺水深海域,也可能與GFS 模式在渤海所用地形數據不準確有關,具體原因需要對GFS的模式設置進行分析。
考慮到海上浮標與海洋站的位置區別,將結果分為外海和近岸進行誤差分析,結果見圖4,其中近岸部分為所有海洋站結果,外海部分為所有海上浮標結果。從圖中可以看出,3 種產品在近岸的誤差均高于外海。對于2 m 以下有效波高的預報結果,3種產品在近岸的均方根誤差比較接近,在外海EC的均方根誤差最小;對于2 m 以上的有效波高,GFS在近岸的均方根誤差嚴重偏大(超過1.3 m),EC 在外海的均方根誤差最小,NMFC 在近岸的均方根誤差最小,這可能與NMFC 的模式分辨率較高(1/36°)并采用了海圖水深數據有關。

圖4 近岸與外海有效波高預報均方根誤差Fig.4 RMSE of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forecasts in the nearshore and open sea areas
泰勒圖由TAYLOR[24]于2001 年首先提出,近年來被廣泛應用于模式的評估與檢驗。基于余弦定理,泰勒圖可巧妙將模式的相關系數、中心均方根誤差和標準差之比3個評價指標整合在一張極坐標圖上,圖5 是3 種預報產品在所有觀測站位的泰勒圖,圖中從圓點出發的徑向距離表示模式與觀測的標準差之比,比值越接近1,表示模擬能力越好;中心均方根誤差是以觀測點為圓心的半圓弧,模式點越靠近觀測點,表明模擬越接近觀測值;相關系數由方位角的余弦決定,當模式模擬結果與觀測值較一致時,相對系數越接近1。從圖中可以看出,在3種預報產品中,MF03007 浮標(位于黃海中部,最遠離陸地)的誤差均為最小,說明3種模式對該站的預報效果最好;從對近岸站位(尤其是小長山)的預報效果來看,NMFC 的預報效果好于其他兩種模式,小長山站EC 和GFS 結果的標準差之比均大于1.0,中心均方根誤差均大于0.8 m,相關系數均小于0.7;而GFS 對龍口站的預報效果十分不理想,中心均方根誤差都大于1.0 m。從對海上浮標的預報效果來看,EC 整體好于其他兩種模式,中心均方根誤差相對較小,相關系數更接近1。

圖5 EC、GFS和NMFC的48 h預報泰勒圖Fig.5 Taylor diagram of 48 h prediction from the EC,GFS and NMFC products
2.3 誤差時間分布
圖6 為3 種產品48 h 有效波高預報誤差的時間分布。從圖中可以看出,3種產品在有效波高為0~2 m 時的均方根誤差變化趨勢較為一致且全年變化不大,冬季均方根誤差略高于其他季節。當有效波高大于2 m時,3種產品的均方根誤差顯示出較大的差異,其中GFS 的預報結果在8 月和11 月誤差偏大,經過統計發現是由于其對8 月的一次低壓過程和11 月的3 次冷空氣過程預報誤差較大造成的,而NMFC 和EC 對這4 次過程的預報誤差較小;EC 的預報結果在6 月誤差偏大,這是因為EC 對6 月的一次低壓過程有效波高預測偏小從而導致漏報。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渤海和黃海2 m 以上的有效波高來說,夏季海浪模式的預報水平主要取決于其對溫帶氣旋、低壓倒槽等低壓過程有效波高的預報誤差,而秋冬季則主要取決于對冷空氣過程有效波高的預報誤差。

圖6 各月份不同有效波高48 h預報均方根誤差Fig.6 The monthly evolution of the RMSE of 48 h forecasts for different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2.4 不同波向過程分析
挑選8 個海上浮標海浪觀測數據,根據實測波向將其分成8 個方向,分別對3 種預報產品在不同波向時的預報進行誤差分析,計算均方根誤差并評估其在不同波向下的預報結果準確性,具體結果見表3。以24 h 結果為例,從表中可以看出EC 預報結果在8 個方向差別不大且均為最好;GFS 在E 向、S向效果較好,在W 向、NW 向效果略差;NMFC 在S向、SE向效果較好,在W向效果最差。

表3 不同波向有效波高預報均方根誤差統計(單位:m)Tab.3 RMSE of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forecast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unit:m)
2.5 強天氣過程分析
根據海浪觀測數據挑選2 m 有效波高以上的天氣過程時間窗口,并按照冷空氣、溫帶氣旋、臺風、低壓倒槽、東高西低(即東面為副熱帶高壓帶,西面為大低壓帶)5 類天氣過程進行分類,依照分類分別對不同天氣過程的預報誤差進行評估。分類結果顯示,2021 年渤海和黃海大浪過程主要由冷空氣(26次)和溫帶氣旋(10次)兩種天氣過程導致,臺風(3 次)、低壓倒槽(3 次)和東高西低(1 次)的天氣過程發生頻率較低。由于東高西低過程只出現了1次,缺乏代表性,故本次分析不考慮東高西低過程。
將4種不同天氣過程下的數值預報結果與浮標實測結果進行對比并分析2 m 以上有效波高的預報均方根誤差,結果見圖7。通過分析可以得出,冷空氣期間,EC 的預報誤差(均方根誤差為40~80 cm)最小,GFS 的預報誤差最大,NMFC 的預報誤差居中,NMFC 的96 h 預報誤差比EC 的略小;溫帶氣旋期間,3 種數值預報結果的總體誤差水平接近,NMFC 在24~72 h 的預報誤差較小,但96 h 的預報誤差偏大;低壓倒槽期間,NMFC 的預報誤差小于EC 和GFS;臺風及臺風外圍影響期間,NMFC 的24 h 預報誤差最小,而EC 的48~96 h 預報誤差最小。由于2021 年影響渤海和黃海的低壓倒槽和臺風過程均僅有3 次,所以該結果的可參考性仍需進一步研究。總體來說在3 種產品中,EC 對于冷空氣作用期間海浪的預報效果較好,NMFC 對于溫帶氣旋等低壓過程期間海浪的預報效果較好。

圖7 不同天氣過程有效波高預報均方根誤差Fig.7 RMSE of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forecasts in different weather situation
圖8 是在2021 年10 月3—5 日冷空氣過程中渤海中部浮標有效波高隨時間的變化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3 種產品的有效波高預報峰值比較接近,但都小于觀測值。在有效波高下降的過程中,EC的預報結果和實測更接近,所以EC 的預報誤差最小。EC對于此次冷空氣過程的預報波高衰減更慢,可能是由于其海浪數值模式中的能量耗散參數化方案更有利于冷空氣期間海浪能量的長距離傳播。

圖8 一次冷空氣過程有效波高隨時間變化曲線圖Fig.8 Comparison of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forecasts with observations for the waves during a typical cold air activity
圖9 為在2021 年6 月14—16 日低壓倒槽過程期間黃海中部浮標有效波高隨時間的變化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到,EC 與GFS 對此次低壓倒槽過程的有效波高極值的預報水平相當,但與實測相比均偏小,預報值與實測極值相差約1 m,而NMFC雖然對于極值出現時間的預報比其他二者略有提前,但預報結果與實測極值最接近,僅相差不足0.5 m,這可能與NMFC所使用的風場驅動較為準確有關。

圖9 一次低壓倒槽過程有效波高隨時間變化曲線圖Fig.9 Comparison of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forecasts with observations for the waves during a typical inverted trough activity
我們使用逐3 h預報數據,針對4種過程下預報與實測波高極值的出現時刻進行分析,得出相應相位差。定義在某次過程中某個浮標/臺站實測波高極值出現在預報時間之前為預報滯后,反之為預報提前。篩選4種天氣過程下具有代表性的實測數據進行統計,具體結果見表4。在冷空氣發生時,3 種預報產品預報滯后出現次數明顯高于預報提前,NMFC 產品平均滯后時間約為5.58 h,EC 和GFS 產品為5.61 h 和5.55 h;而當預報提前時,NMFC 產品平均提前時間為5.19 h,EC 產品為5.31 h,GFS 產品為5.19 h。溫帶氣旋下3 種預報產品預報滯后出現次數略高于預報提前,NMFC 產品平均滯后時間約為5.61 h,EC 和GFS 產品為5.94 h 和6.03 h;而當預報提前時,NMFC 產品平均提前時間為6.36 h,EC產品為6.33 h,GFS 產品為6.14 h。臺風和低壓倒槽過程發生次數相對較少,此處不做分析。

表4 有效波高預報極值結果與實測結果出現時間差Tab.4 Occurring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orecasted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extreme and the observed extreme
2.6 極值預報誤差分析
考慮到預報機構對外發布的海洋預報結果通常以天為單位,本文對日極值預報結果進行誤差分析。采用NMFC的逐時預報數據、EC和GFS的逐3 h預報數據統計每日預報的最大有效波高且結果大于2 m 的時刻,并與利用逐時觀測數據統計得到的每日觀測最大有效波高進行對比,結果見圖10。從圖中可以看出,對于有效波高極值NMFC 的預報最好,EC 的效果略差(96 h 預報誤差變大),GFS 的預報誤差最大。結合表3可知,盡管EC有效波高的總體誤差低于NMFC,但在極值預報方面卻不如NMFC。這是因為NMFC為逐時預報產品,而EC和GFS 為逐3 h 產品,在捕捉極值方面逐時預報產品更有優勢。

圖10 2 m以上有效波高日預報誤差統計Fig.10 RMSE of daily significant wave height(>2 m)forecasts
3 總結與討論
本文收集整理了2021 年NMFC、EC、GFS 的海浪數值預報產品以及渤海和黃海浮標和海洋站的海浪觀測數據,將模式數據和觀測數據進行比較并統計分析了多種誤差指標。總體來說,3種數值預報產品對2 m 以上有效波高24 h的預報誤差不超過19%,EC 預報誤差最低,3 種產品對于大浪過程的預報結果都偏低。從空間上看,渤海和黃海中部的有效波高預報誤差大于黃海北部(其中GFS在渤海的誤差尤其大);近岸的有效波高預報誤差均高于外海;EC 有效波高預報誤差在外海最小,NMFC 誤差在近岸最小。從月份來看,GFS 的有效波高在8 月和11 月誤差偏大,EC 有效波高誤差在6月偏大,NMFC 有效波高預報誤差全年變化不大,總體來說夏季預報誤差偏大。在天氣過程方面,EC對冷空氣和臺風期間海浪的預報效果更好,NMFC對溫帶氣旋和低壓倒槽期間海浪的預報效果更好。在極值預報方面,NMFC 對有效波高極值的預報最好,EC的效果略差,GFS的預報誤差最大。
本文僅對2021 年3 種預報產品的預報性能進行了初步研究,今后應針對多年的預報產品開展更加系統的評估,以期為日后進行的實際有效波高的預報訂正和釋用提供有意義的參考。另外,在渤海和黃海,海浪的預報水平既取決于海浪模式的參數設置,還取決于海面風的預報水平,拋開海面風誤差只分析海浪誤差,不能完全確定海浪誤差的全部來源。因此,下一步應將海面風預報效果和海浪預報效果進行關聯分析,明確海浪預報誤差中的模式自身誤差和強迫場誤差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