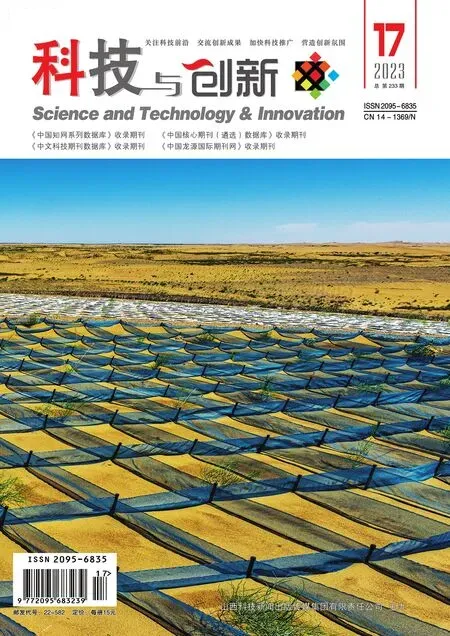某淺埋偏壓隧道出口段圍巖與支護力學響應數值模擬分析
潘朝,張著彬,鄒勇
(湖北省水利水電規劃勘測設計院有限公司,湖北 武漢 430064)
隧道及地下結構是一個由圍巖與支護結構構成的復雜系統,往往具有“地質因素復雜且變化眾多,受多種因素影響,施工較為困難”等特點,施工設計不當易引發一系列安全問題,如塌方、冒頂等事件,更嚴重會造成人員傷亡,因此,確定圍巖的穩定性是隧道設計和施工中研究的重點和難點。然而圍巖條件的復雜多變性、載荷效應的動態特性及支護結構構造性能的不確定性,使得本學科的理論指導作用不像其他學科更易于實現定量化[1]。
目前國內外對隧道圍巖與支護結構力學特征的研究較多,但對特殊地段、特殊地質條件的相關研究卻很少。為此,本文首先對隧道圍巖變形與初期支護機理進行理論分析,然后通過現場監控量測和ANSYS數值模擬對比分析,研究了淺埋偏壓隧道圍巖變形與初期支護力學響應特征,旨在指導支護設計與現場施工,保證隧道安全、快速貫通,為類似工程研究提供參考借鑒。
1 工程地質概況
某隧道是滬昆客專長昆湖南段重難點隧道,起止里程為DK387+174.24—DK388+075,全長900.76 m,最大埋深127.4 m,寬約14 m,為來回雙線。
該隧道出口段屬于低山丘陵地貌,巖性為青灰色凝灰質板巖及紫紅色砂質板巖,巖體較為破碎,節理裂隙發育,強風化,風化層厚度較大,呈塊狀、碎塊狀,結構松散。該段埋深20~30 m,DK388+055 斷面通過斷層F150,存在偏壓現象,為淺埋偏壓隧道段。隧道區板溪群馬底驛組二段與板溪群馬底驛組三段為整合接觸[2]。
2 圍巖與支護結構監控量測
2.1 監測項目及內容
主要監測項目及內容如表1 所示[3],各監測項目布置如圖1 所示。

表1 監測項目及內容
2.2 隧道出口段現場監測成果分析
對DK388+025典型斷面進行監測分析,結果如下。
2.2.1 拱頂沉降與水平收斂
DK388+025 斷面拱頂下沉、收斂差值及累計沉降量、收斂量隨時間變化曲線如圖2 所示。

圖2 DK388+025 斷面拱頂下沉、收斂差值及累計沉降量、收斂量隨時間變化曲線
DK388+025 斷面拱頂下沉、水平收斂當日變形速率及平均變形速率隨時間變化曲線如圖3 所示。

圖3 DK388+025 斷面拱頂下沉、水平收斂當日變形速率及平均變形速率隨時間變化曲線
由圖2 和圖3 可知,拱頂沉降在初期階段變化非常顯著,沉降速率達到7.54 mm/d 出現在隧道開挖后的4 d 左右,隨后變形開始趨于穩定,但是當日沉降速率需要34 d 左右才能降低到0.1 mm/d 以下。
水平收斂上下測線所需要的時間分別為32~42 d、13~23 d,均比較長。其變形速率降到0.1 mm/d以下,上測線大約需要34 d,占收斂總時間的80.9%;而下測線只需11 d,占收斂總時間的36.7%。
結合分析可知,拱頂沉降變形與水平收斂變形趨勢比較相近,都是呈現3 個階段,即增長和急速增長階段、緩慢增長階段和趨于穩定階段,但各階段歷時有一定差異。拱頂沉降變形在增長和急速增長階段的時間大約為15 d,是水平收斂變形的2 倍左右;而水平收斂變形在緩慢增長階段的時間長達22 d;兩者趨于穩定階段的時間相差不大。拱頂總沉降量比水平收斂位移量大得多,高達17 mm 左右,但其收斂速率也不太相同,這與隧道的埋深、巖體的各種物理力學參數及監測部位有著不可否認的關系。
2.2.2 地表沉降
在隧道出口段地表布設了2 組地表下沉監測測線(DK388+025 斷面、DK388+022 斷面),每組布設7個地表觀測點(P11—P17、P21—P27),隧道軸線縱斷面正上方地表埋設P14 和P24,然后向兩側依次均勻布設,間距3 m。鑒于篇幅有限,僅對部分時間段典型觀測點P11、P14、P17、P21、P24 及P27 進行統計分析,其地表測點累計沉降量隨時間變化曲線如圖4 所示。

圖4 地表累計沉降量隨時間變化曲線
監測表明,地表各監測點沉降速率變化也分3 個階段,隧道軸線上的監測點(P14、P24)表現更明顯些,兩側監測點沉降速率變化稍顯平緩。各監測點沉降趨于穩定階段較晚,大約都在37 d 之后。
地表各監測點的沉降量遠遠大于拱頂沉降量與水平收斂量,這與隧道上方巖體的類型、物理力學參數、破碎程度及施工工藝與方法有重要關系,還與施工期處于霉雨季節有直接關系。
2.2.3 鋼支撐壓力
根據工程經驗和相關文獻資料,鋼支撐在拱頂和拱肩這些部位受力比較顯著,所以對DK388+022 斷面左拱腰、拱頂和右拱腰分別布置了635#、636#、637#GYL 鋼筋應力計,所得鋼支撐壓力隨時間變化曲線如圖5 所示。

圖5 DK388+012 斷面鋼支撐壓力隨時間變化曲線
從圖中可以看出,拱頂和兩側拱腰處鋼支撐所受的壓力都比較大,說明在淺埋偏壓隧道施工過程中鋼支撐承受了來自圍巖的大部分壓力;在鋼支撐所處的拱頂和拱腰部位上所測得的壓力隨時間變化呈現“快速增長—緩慢增長—快速增長—緩慢增長”的規律,這種規律表示鋼拱架所受到的壓力受到現場施工非常大的影響;拱腰處受到的壓力左側比右側明顯大一些,主要原因是隧道處于偏壓狀態,使得左右兩側拱腰處受力不均。
2.2.4 錨桿軸力
根據工程經驗和相關文獻資料,錨桿在拱腰處受力會比較顯著。受條件所限,本次僅對DK388+020 斷面B、D 測孔處布置測點。B 測孔的各測點B1、B2、B3 的埋深分別為2.8 m、1.6 m、0.4 m,D 測孔的各測點D1、D2、D3 的埋深分別為2.8 m、1.6 m、0.4 m。
監測結果表明,錨桿被監測的軸力隨著深度增大從0 逐漸增大,隨后又慢慢變小,直至減小到0。其淺中部錨桿軸力變化規律為“快速增長(軸力下降)—緩慢增長—趨于平穩”,深入巖石內部測點的軸力呈“上升—平緩—平緩”波動的特征。由于受到隧道偏壓的影響,左側量測錨桿的軸力分布均值比右側的要大,具體如圖6 所示。

圖6 DK388+020 斷面B、D 測孔錨桿軸力曲線
3 圍巖與支護結構力學響應數值模擬
3.1 計算模型假設條件及圍巖邊界條件
將隧道圍巖材料特性視作為均質彈塑性體,并且其材料力學的屈服條件選取Drucker-Prager 屈服準則[4];隧道巖體變形時滿足各向同性;可用二維平面應變問題代替隧道圍巖的受力和變形。
大量的實踐證明,洞室應力重分布在以洞室為中心3~5 倍洞徑范圍以內。因此,本文使用的計算模型在水平方向取3 倍洞徑,在豎直方向向地層深部取4倍洞徑,在地表處采用實際的埋深及地形地勢。將初始應力場側壓力作用考慮在內,施加均布荷載邊界條件作用在計算模型的水平兩側及上側,豎向上部荷載數值可以通過隧道埋深進行確定,通過反算確定水平荷載大小,一般認為位移在開挖前已經完成,因此在模型下部作用位移約束[5]。
3.2 單元類型及參數
圍巖及二襯襯砌通過4 節點等參平面實體單元(PLANE42)來進行模擬,初期支護通過2 節點等參平面梁單元(BEAM3)來進行模擬,環向錨桿通過2節點等參桿單元(LINK1)進行模擬[6]。
本次模型模擬過程中按照實際施工采用的設計參數選取各單元的參數,其具體內容如下:①初期支護厚度取0.30 m;②Φ22 mm 錨桿長度取3.6 m,布設36根在隧道壁環向180°,圓心角取5°,間距為0.6 m。
圍巖性質參數主要通過考慮按規范及現場實測V級圍巖的參數確定,具體如表2 所示。

表2 圍巖與結構的物理力學參數
3.3 計算模型及模擬施工步驟
3.3.1 計算模型的選擇
隧道仿真模擬斷面歷程為DK388+025,該斷面埋深27 m。
隧道實際斷面形狀具體尺寸如下:①水平跨度最大達14 m,高度達9.8 m;②由四心圓構成,半徑分別為7.35 m、19.3 m、3.1 m、3.1 m。
二維平面ANSYS平面模型如圖7所示。

圖7 有限元計算模型
3.3.2 施工步驟模擬
由于隧道圍巖失穩事故一般發生在低級別圍巖中,并且隧道貫通的關鍵在于出口段V級圍巖段,因此本次選取某隧道V級圍巖進行模擬計算分析。根據現場實際施工的3臺階7步開挖方法來進行本次模擬,在整個模擬過程中,可分為14個荷載步進行模擬。要想與監控量測結果進行對比分析,同時也要滿足實際施工步驟,可以把初期支護單獨進行模擬,二次襯砌作為應力儲備,在此不做模擬計算。隧道3臺階7步的土體荷載步分布如圖8所示。模擬計算初期支護的具體荷載步如下:模擬計算初始應力(自重應力場)—上臺階環形土體①進行模擬開挖—激活上臺階的支護—中左臺階②開挖—激活中左臺階的支護—中右臺階③進行模擬開挖—激活中右臺階的支護—下左臺階④進行模擬開挖—激活下左臺階的支護—下右臺階⑤進行模擬計算—激活下右臺階的支護及全部錨桿—核心土體⑥進行模擬開挖—仰拱土體⑦進行模擬開挖—激活仰拱土體的支護。

圖8 3臺階7步施工荷載步
3.4 數值模擬成果及與監控量測數據對比分析
3.4.1 位移場分析
隧道開挖后,由于受圍巖應力重分布的影響,位移云圖在隧道附近出現顯著變化。Y方向位移及合位移最大值仍然出現在錐角處,均為206.1 mm,如圖9、圖10所示。相比其他部位,隧道左拱肩到拱頂沉降明顯較大,其范圍值為170.3~183.2 mm,這是由于隧道處于偏壓造成的。而X方向位移基本變化都較小。

圖9 開挖模擬前Y方向初始位移云圖

圖10 開挖模擬后Y方向位移云圖
DK388+025斷面實測沉降數據與模擬值對比如表3所示。分析得出,實際監測與ANSYS模擬的各個位移變化值中,地表沉降最大,拱頂沉降次之,周邊收斂最小。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原因是隧道上方土層因開挖及施工擾動,會造成應力重分布,從而使土層更密實。

表3 DK388+025斷面位移變化實測值與模擬值對比分析
3.4.2 應力場分析
隧道開挖后會擾動初始應力場,產生二次應力重分布。開挖模擬前應力基本呈均勻層狀分布,隧道右上方地表邊緣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拉應力。
開挖模擬后,無論是水平方向還是豎直方向,應力最大值都產生在邊墻中部位置,最小值出現在拱頂及仰拱部位水平和豎直方向。同時,仰拱部位水平方向主要產生拉應力,豎直方向多承受壓應力,這也就是為什么隧道在施工中會出現仰拱突起現象的原因。在Y方向和第3主應力云圖上,圍巖的應力分布在拱頂形成一個 “V” 字形槽,如圖11、圖12所示。

圖11 開挖模擬后Y方向應力云圖

圖12 開挖模擬后第3主應力云圖
對比開挖模擬前后應力云圖可以得出,隧道開挖后對初始應力擾動將使二次應力產生重分布現象,通過模擬可發現,其支護結構受到的第一主應力方向大致與水平方向相近,同時第三主應方向也與豎直方向趨近,這種現象符合實際情況。隧道開挖前,隧道周圍巖體所受應力均勻分布,不存在應力集中現象。而隨著隧道開挖的進行,應力在邊墻中部位移出現逐漸集中現象,尤其是在左邊墻。在左側從拱肩到拱頂處,雖然不是隧道所受應力最大值部位,但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應力集中。
3.4.3 塑性區分析
隧道開挖模擬后周圍圍巖塑性區分布云圖如圖13所示。

圖13 圍巖塑性區分布云圖
圍巖塑性區即周圍荷載產生壓力超過圍巖極限承載力,使局部圍巖產生變形不可恢復的屈服區域。分析圖13 可知,塑性區域主要集中在左側拱腳處,其次是兩側拱墻和拱腰位置,右側拱腳處不存在塑性區域。這是由于隧道處于偏壓狀態,周圍巖體與隧道初期支護在拱腳相互擠壓在左側更加嚴重造成的。
另外,圍巖塑性集中區都處于各個開挖臺階的下邊緣處。實際施工過程中,每一臺階開挖時都會及時進行初期支護,然后一般由于支護沒有封閉成環,在邊緣處多以周圍巖體結合支撐。因此施工期中,開挖臺階下邊緣周圍巖體比較容易出現應力集中現象,導致后期初期支護及時封閉成環,這些位置也會出現塑性區。
3.4.4 初期支護受力圖
開挖模擬后錨桿軸力分布圖如圖14 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隧道開挖模擬后錨桿軸力值在隧道的拱頂及兩側拱腰處較大,尤其是左側拱腰。左側拱腰處最大軸力值為15.8 4 4 kN ;拱頂位置最大軸力值為7.688 kN;右側拱腰處最大軸力值為11.766 kN。將上述模擬數據與實際監測數據進行統計對比,如表4 所示。

圖14 開挖模擬后錨桿軸力分布圖

表4 各關鍵點錨桿最大支護軸力的模擬數據與實際監測數據對比
由表4 可知,實際監測和ANSYS 模擬的錨桿軸力相差不大,并且左側拱腰處錨桿軸力都比右側大很多;無論是實際監測還是ANSYS 模擬得到的錨桿軸力數據,兩側拱腰位置錨桿淺部位置(0.4 m 處)軸力最大,中部位置(1.6 m 處)軸力次之,深部位置(2.8 m 處)軸力最小;結合圖4—圖13,可以總結出錨桿從淺部位置到深入圍巖的深部位置,其軸力呈逐漸減小趨勢。
4 結論
淺埋偏壓隧道水平收斂、拱頂沉降及地表沉降隨時間變化均呈現增長和急速增長階段、緩慢增長階段及趨于穩定階段這3 個階段,但地表沉降量一般遠遠大于拱頂沉降量與水平收斂量,這與隧洞巖土體特性及施工工藝等因素有直接關系;受偏壓影響鋼支撐壓力和錨桿軸力左側均明顯大于右側,表明隧洞處于嚴重偏壓狀態。
淺埋偏壓隧道拱頂及地表沉降量較大,開挖后應加強支護并及時施作;拱腰和拱腳處應力集中,易發生剪切破壞,與一般隧道圍巖塑性區的分析較吻合。施工開挖對圍巖位移變化影響較大,淺埋偏壓隧道的初期支護要與一般隧道支護區別對待,實際施工中要高度重視,宜采用復合式襯砌,對噴層適當加強或加固。
數值模擬成果與監控量測數據分析相吻合,模型及參數選取正確,實際監控量測數據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