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戰略的基礎性問題
魏江
以“ABCD+5G”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洪流正在顛覆傳統產業結構和市場結構,引致了環境、市場、企業和個體關系的重構。產業組織正處于快速變遷期,企業組織資源與能力正被重塑,給傳統企業組織戰略形態、戰略行為和表現方式帶來了挑戰,也對數字經濟時代的戰略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理論需求。

企業戰略是特定經濟情境下企業主觀能動性對外部情境變遷的反應,數字戰略就是企業面臨數字經濟時代的情境特征,由公司高管發起的對外部場景的響應。經濟發展的核心生產要素變了,必然會引致企業戰略關鍵要素的變化。因此,本文首先要討論什么是數字,然后再系統闡述數字戰略本質、戰略形態、戰略組織、競爭格局等核心問題,以期為數字產業組織中的戰略這一問題提供思考。
今天,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管理學者,都言必稱數字,數字時代、數字經濟、數字管理、數字社會,等等。數字是什么?數字經濟是什么?數字為什么有的翻譯成Data或digital,有的翻譯成Digitalization或Digitization?對此,首先需要解決基本概念問題,然后再來理清底層邏輯。
當大家想當然地認為我們已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時,有沒有想過數字究竟是什么,數字是生產要素嗎?如果沒有弄清楚什么是數字,就沒有辦法理解什么是數字經濟、數字管理或者數字社會。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要判斷一個新的經濟時代是否到來,主要看有沒有出現新的生產要素以及這個生產要素是否成為關鍵要素。從廣義上講,當前,數字確實是一種新的生產要素,“ABCD+5G”和元宇宙的背后就是數字技術,數字技術以數字為技術元素。然而,數字技術的發展并不表明數字已成為一般意義上的關鍵要素,數字技術仍屬于技術的一種,因此,本質上當下仍屬于“技術經濟”階段。數字要成為關鍵生產要素,前提是能夠被確權、被資產化、資本化和股權化,也就是說擁有者可以把數字作為生產要素用于投資并參與分配。
要理解數字經濟,不妨先看看經濟形態演化的歷史。1997年,有一個詞非常熱,叫“知識經濟”。美國微軟一家公司的市值超過美國所有汽車公司市值的總和。大家分析原因時,提出“知識經濟”這個概念。理論界和實踐界都認為“知識”成為了生產要素。浙大還舉辦過很多“知識經濟”論壇,也出了不少書,我也承擔過幾個知識經濟的課題。但今天,似乎不太提知識經濟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至今仍沒有回答清楚“知識到底是什么”,知識至今仍難以確權,難以參與分配。
再往前追溯,還有很多流行的概念,其中最為大家接受的是“技術經濟”——科技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既然科技是生產要素,那我們擁有的某一項技術、專利,或者一篇論文,能被資產化和資本化嗎?高校和實驗室成千上萬的發明專利,真正能以股權投資的有多少,能參與分配的有多少?事實是,技術要素的確權問題雖然解決了,但其價值仍難以評估。科技金融至今仍舉步維艱。
眾所周知,生產函數中有三大類基本生產要素,分別是資本、勞動力和科技。假設一瓶水的毛利是一塊錢,根據生產函數,這瓶水的利潤是科技、資本和勞動力共同創造的。其中,資本、勞動力價值是可以通過市場交易來衡量的,科技的價值卻沒有辦法評估。所以,在全要素生產函數的測度中,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用“剩余值法”測算的,也就是把資本要素和勞動力要素貢獻扣除后,剩下來的都籠統地算作科技進步的貢獻。
按照這樣的方式計算,組織資本、社會資本、知識、數字、政府的貢獻都被忽略了,好像這些都不創造價值似的!結果是,在創新動力不足、創新投入較低的情況下,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70%。如果科技的貢獻那么大,企業和區域對科技創新的追逐不就“趨之若鶩”了,為什么企業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動力那么弱?
我們比照知識的貢獻來理解數字的力量。知識經濟之所以“偃旗息鼓”是因為知識難以評估價值,難以資本化,因此難以成為生產要素。打個比方,假如一位優秀的大學教授擁有豐富的知識,這個教授去銀行申請信用貸款,銀行能夠給60萬信用額度已經很客氣了;如果這個教授有一套價值1000萬的房子去抵押貸款,銀行可以貸給600多萬:房子價值可評估,用房子抵押,銀行不怕你違約。這就出現一個悖論:究竟是這個教授有價值還是房子有價值?按照銀行的信用評估,這個教授的價值僅僅是房子價值的1/10。那么,究竟是教授的知識值錢,還是房子值錢?顯然是房子!可見,個體擁有的知識和技術,從資本市場角度看是“不值錢”的。
知識尚且如此,數字肯定更加不值錢。由于至今不知道“數字”為何物,數字要成為生產要素就更加困難。現在,數字技術越來越重要,數字技術的產業化發展一日千里,但產業數字化非常困難,因為數字沒有辦法參與價值分配。由此,我認為目前主體仍處于技術經濟時代,還沒有真正進入數字經濟時代。
據觀察,我國能將數據變成資本的企業比例不會超過0.01%,走向數字經濟的路還很長。我多次呼吁,雖然數據在高速迭代,但別被大數據“忽悠”了。我們真正要重視的是對數字技術的應用,不能把“數字”等同于“數字技術”,不能偷換概念,要正確認識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發展的規律。數字經濟的發展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管理學者要嘗試回答的根本問題是,如何讓數字以最小的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創造最大的價值。
數字經濟的主體是企業,數字時代的企業嵌入在產業組織中。那么,我們需要判斷現在有多少企業已經是“數字企業”?有哪些產業組織已經是“數字產業組織”?對于第一個問題,答案已經闡述清楚了,99.99%的企業還不能算是“數字企業”,只能說采用了“ABCD+5G”數字技術的企業正在快速增長,但把數字作為生產要素的企業極少。對于第二個問題,數字產業組織主要是數字平臺企業、數字生態企業。比如,浙江大力推動的數字經濟系統,就是把數字平臺建立在“產業大腦”基礎上,形成“產業大腦+未來工廠”的產業組織形態,形成未來工業互聯網的基本形態。
數字戰略包括“數字企業的戰略”和“數字化轉型企業的戰略”兩類,前者是數字技術企業的戰略,后者是依托數字技術實現產業轉型發展的企業的戰略。眾所周知,無論哈佛學派還是芝加哥學派,都認為戰略研究的關鍵是弄清楚企業所處的產業組織情境,因此,我們也從產業組織切入來探討數字戰略。我們要思考這兩個問題:如何認識數字時代的產業組織變遷?產業組織情境變遷是否意味著戰略本質改變?
首先必須再次強調戰略是研究什么的。企業戰略要回答的三個核心問題是“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如何去”。要回答從“哪里來”,需要分析企業的內部條件以把握發展基礎,“到哪里去”是分析客戶和利益相關者的需求以確定發展目標、愿景和使命,“如何去”回答業務選擇和發展路徑以確定持續競爭優勢。不管經濟形態如何變化,以上基本問題是確定的——企業戰略解決的就是內外部環境、目標使命愿景、業務選擇和組合、戰略實施方案等。
在過去的十年、二十年,戰略有變化嗎?就我的觀察,變化似乎并不大。帶著這樣的思考,我寫了《數字創新》《數字戰略》兩本書,試圖系統回答關于數字時代的戰略規律和創新規律問題。
要真正弄清楚數字戰略的“變”和“不變”,需要從底層邏輯上講明白企業管理研究的三個最基本要素:個體、組織、產業。如果不去管數字形態,只孤立地去看個體,會發現今天的個體特征與一千年前并沒有多大區別。但如果去觀察數字化背景下產業組織內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關系,會發現這些關系及鏈接方式確實都發生了顛覆性變遷,即組織形態變了。這必然引致組織間關系和組織形態的革命性變化。由此,我提出三個基本猜想。
猜想一:萬億級營收規模的產業組織將開始出現并參與全球寡頭競爭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萬元戶就是富豪;九十年代,擁有千萬產值的企業就是巨型企業;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千億規模的民營企業在我國達到了上百家;今天,萬億級營收已經出現。一家企業的營收可以超過幾個省GDP總和,比如蘋果的年營收額接近4000億美元,市值已接近2.3萬億美元,華為2021年收入接近9000億人民幣。
之所以出現了如此強大的產業組織,是因為數字技術賦能產業組織變革,打破了傳統的產品供應規模(規模經濟)、產業邊界(范圍經濟),極大地提高了運營效率(速度經濟)。如果沒有數字技術的發展,就沒有組織間、組織與客戶間的關系和結構的重構。
我把產業組織演化的過程概括為從原子式結構、小分子結構、大分子結構到“平臺+微粒”的結構變遷,最終形成生態化組織體系。隨著萬億美元市值規模企業的不斷發展,產業組織形式還將繼續演化。未來全球經濟競爭就是生態系統的競爭,最終形成全球寡頭競爭。管理學者如果不能洞悉這樣的產業組織情境,研究創新創業和戰略行為將是沒有生命力的。
猜想二:“平臺+微粒”的產業組織是數字經濟系統下國家競爭優勢的利器
全球經濟競爭主體是產業組織,從企業到集群、區域、生態系統。原來國家競爭優勢建立在原子式、分子式組織基礎上,未來這樣的組織仍很重要,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如此重視專精特新的原因。然而,比專精特新更為重要的是能夠把專精特新企業協同起來的產業組織——數字平臺組織,這是構筑未來國家競爭優勢的利器。
數字平臺組織是平臺領導者主導形成的“平臺嵌套+產業群落+微粒組織”體系,我把這樣的系統稱為“平臺+微粒”的產業組織。這類產業組織在我國的快速形成和發展,得益于互聯網快速發展和數字企業轉型。“平臺+微粒”的數字產業組織集合了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速度經濟的優勢。我們沒有辦法回答今天的海爾是做什么的,因為它是個產業生態,突破了產業邊界。家電、制藥、數字、生活、物流、文化等,都在海爾這個生態中形成和發展。我們也沒有辦法回答吉利是做什么的,吉利不僅僅是做汽車的,它還做生活服務、無人駕駛、數據技術、航空航天、能源電池……按照傳統的戰略管理理論,我們沒有辦法給出一個企業可以沒有邊界地擴張的理由。
今天的數字平臺企業確實已經不是傳統的企業了。我曾經說過,今天的企業已經難以用科斯的理論來解釋,今天的戰略管理難以用波特的理論來解讀,今天的多元化也不可能用魯梅爾特的理論來分析,我們需要構建新的“數字戰略”理論。因此,國內有戰略管理學者給我取了個名號,叫“五恨”教授——“恨”SWOT(態勢分析法),“恨”FiveForce Model(五力模型),“恨”Valuechain Model(價值鏈模型),“恨”Three General Strategy(三種最一般競爭戰略),“恨”Integr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一體化和多元化)。我“恨”不是說這些理論是錯的,而是這些模型是建立在工業經濟基礎上的,已經不適應數字經濟時代了。多少教材和課程內容還在喋喋不休地給學生講五十年前的理論,沒有將最新的發展納入其中。既然已進入新經濟形態,當然需要以“數字戰略”來指引企業戰略實踐。
猜想三:經濟社會將進入“新原始社會”,個體自由生產、部落化生存
在數字經濟時代,產業組織的變遷引致市場、企業、個人關系的重構,人的價值也在微妙地變化著。在“平臺+微粒”的產業組織中,市場與企業的邊界日益模糊,組織與個人走向了統一。在這樣的組織內部,個體如何參與生產和消費活動,是一個全新的命題。
數字經濟時代,出現了“躺平”“無腦”“廢柴”等熱詞,這些詞刻畫了這個時代不少人的生存狀態。我也造了個詞——“新原始社會”——來描述未來人們的經濟生活和生存狀態。未來,0.1%甚至0.01%的人將“主宰”整個經濟社會,他們依靠智慧把數字變成生產要素,依靠數字把智慧變成核心競爭力,其中極少數的人通過技術、制度、產權等手段,把數據變成資產,掌握核心競爭力。另外99.9%的人則選擇活著或者“躺平”。無論是資本結構、資源集聚還是數字創新、經濟治理,一定是0.1%的人“支配”99.9%的人。這個“新原始社會”可能會由0.1%的個體“控制”,剩下99.9%的個體在躺平中生存,在“部落化”的虛擬現實中“躺平”,“宅”在虛擬社區,過著“數字人”的生活。
越來越多年輕人工作的意義不是追求財富或者責任,而是活著和自由。他們無所謂對組織忠誠,無所謂事業追求,無所謂考核激勵,而是尋找躺平的最好方式。浙江金華有一家非常杰出的上市企業,是做汽車輪轂的,一線員工數量有一萬多人。這些年,這家企業每年至少要招募五千多新員工,因為上一年招聘來的員工一年內離職率超過50%。為什么會這樣呢?有的員工會說“工資這么低,我怎么拼命努力也買不起房子”,還有的會說“工作那么累,我憑什么給你的企業加班”。公司董事長采用的解決辦法是“機器換人”,因為他實在沒有“招數”把這些剛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人留下來,即使增加“可承受的成本”也解決不了問題。當機器替代人后,人就成為了追求自由生產的個體。
在這樣的產業組織演化格局下,要如何認識數字戰略,認識數字資源的性質?要看清楚戰略形態變化態勢,需要回答好五個問題。
第一,數據是什么?
我建議用“陌生問題熟悉化策略”來回答這個問題,即可以通過與熟悉的事物如水、土地、技術、空氣等進行對比來理解數據。如果數據是像土地這樣的生產要素,就可以明確評價其價值,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把數據看作貨幣,那它的價值就更能夠直接體現了,這顯然更加不可能;如果把數據看作是水,它就可以賣錢,因為今天的水都要花錢才能買到;如果把數據看作空氣,那它就是公共產品而非商品。通過這樣的對比,我認為數據更像空氣,是“不值錢”的公共產品。
第二,數據如何用?
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繼續以“空氣”打比方。如果誰有能力從空氣中分離出氧氣,比如制氧機公司從不值錢的空氣中提取出氧氣,氧氣就可以賣給化工廠和醫院“賺錢”。數據也一樣,如果誰能研究數據的使用、開發、生產等,設計出企業大數據處理系統,就有能力從數據中算出“用戶畫像”,此時的數據就像裝在氧氣瓶里的氧氣,可以“價值化”了。
第三,數據屬于誰?
從法律上講,數據從誰那里生產出來,所有權就是誰的。但問題是,數據可以轉來轉去,變成公共產品,很難解決所有權問題,因為數據難以被標簽化、物質化。特別是數據不具獨占性,不具可評價性,因此,數據確權是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無論如何確權,我們永遠不可能把每個數據貼上所有者的標簽,也就是沒有辦法回答清楚“數據屬于誰”的問題。
第四,誰來管數據?
數字資源的特殊性在于其難以資本化、所有權模糊、生產可供性和分配不確定等,這些都是開發利用數字資源面臨的挑戰。例如,企業數據是由數據提供方、需求方還是政府管理?數據作為公共產品由政府管理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因為數字經濟具有極大不確定性,政府管理會把數字經濟拉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由供應方或者需求方來管理呢?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每個數據的供應方是誰,需求方是誰,要管理好數據也不可行。
第五,如何用數據?
數據是否可交易?幾乎不可能,因為難以估值。是否具備可供性?數據是具備可供性的,但難以確定,因為數據為極少數壟斷平臺掌握,要在市場上獲得成本很高,知網的壟斷事件就是例子。是否可動態跟蹤?很難也沒有必要,因為數據瞬息萬變,高頻覆蓋,等把積壓在數據庫里的數據分析出來,消費場景已經變了。所以,我主張用好“小數據”,也就是把自由掌握的私有屬性的數據收集好、處理好、應用好,盡量不要去碰公有屬性的數據。
可以說,以上五個問題基本無解,數據/數字要成為關鍵生產要素,還任重道遠。因此,目前應關注的是數字技術應用,依托數字基礎設施獲取和利用好數字資源,將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及多媒體技術融合起來建好數字平臺,發布、存取、利用數字資源。企業一旦掌握了數據資源,就可能打破傳統資源稀有、不可模仿、不可替代等屬性限定,拓展出具有自生長性、時效性、動態性和交互性等特征的生產要素。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數字技術的發展決定組織形態的變遷方向,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變化。既有生產關系總是會限制生產力發展,學術研究就要回答好這樣的問題——什么樣的生產關系能更好地支持生產力的發展。無論社會學、經濟學還是管理學,都需要先認清市場、企業、組織、個體之間的關系,梳理清楚組織內部的關系和結構之后,再來分析數字技術發展對戰略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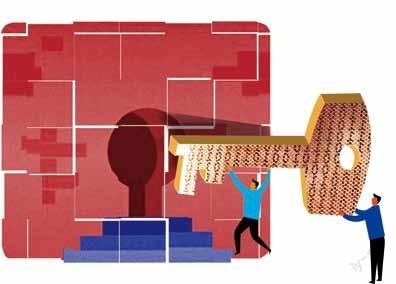
無論企業組織形式如何千變萬化,從底層邏輯看,不外乎內部個體、組織和外部市場交易等維度。數字時代下,傳統勞動關系開始弱化甚至消亡,個體可以擺脫組織科層束縛,雇主-雇員關系消失,出現直接參與市場交易的以個體或小團隊為單元的項目組織。科層組織被顛覆為小組織群落、小微創客組織、平臺生態系統,企業內部各層組織可以直接面向市場交易,子組織之間也可以打破組織官僚治理的束縛,開展組織之間交易、項目之間交易。
以上產業組織變遷就引發了市場、企業、組織、個體等各層關系的重構,這種重構確實在改變人類的生存、工作和生活場景,也改變了企業的戰略活動方式、競爭方式和合作方式。毫無疑問,這些變遷為戰略管理研究者帶來了很多新的研究選題。比如,戰略主體的多層次性與競爭行為的復雜性,生態組織的復雜性與競爭戰略的組合性,平臺組織內部中間交易機制的形成與演變研究,內部項目邊界的演化與治理邏輯調整,“平臺+微粒”的生態系統內小組織群落形成機理和路徑研究等。
對于數字技術發展下涌現出的“平臺+微粒”的組織體系,需要深入研究系統內部不同組成單元及其競爭行為的特點,解構組織體系的多層次性與市場行為的多樣性之間的關系。我提出過生態組織的幾個特征:基礎模塊微粒化,基礎模塊可以微粒化為一個個體(如人單合一);組織架構平臺化,組織架構發展為前臺+中臺+后臺;組織關系網絡化,組織關系演化為扁平的網絡結構;組織情境生態化,無論是外部情境還是內部情境都呈現生態化特點。
內部組織體系的演化對企業戰略的影響也是非常顯著的。從微觀基礎上看,企業是很多個體微觀模塊的組合,個體形成多樣化組合服務于整體體系的架構,這個過程需要組織單元之間的鏈接標準和共享接口。如果各組織沒有建立有效的共享接口,就沒有辦法推進整體戰略的實施,因此,需要從理論上回答清楚組織模塊、組織架構及其鏈接標準對企業戰略的作用機理。
把這樣的組織結構推演到產業組織會發現,今天的產業組織其實就是各個企業單元的生態化組合。因此,需要揭示數字產業組織在社會分工演變態勢下的協調整合機制,探索生態化組織架構下個體與組織的關系、企業與市場的關系、個體與市場的關系,以及組織與企業、市場之間的關系,從而解析新型生態關系內部的組織競爭行為、組織間合作關系等。可以說,從組織-個體、市場-企業兩個維度的交互去考察戰略主體變遷,為我們戰略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