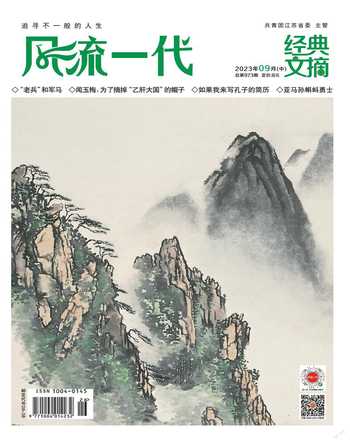為什么記憶常常不靠譜
【美】大衛·伊格曼 譯閭佳
大腦和身體在我們的一生里改變了很多,但就像時鐘時針的變化一樣,要察覺這些變化很困難。例如,每4個月,紅細胞就徹底更替一遍,皮膚細胞每幾個星期就換一輪。在7年左右的時間里,身體里的每一個原子就會徹底被其他相同的原子取代。從物理層面來說,你在不停地翻新,變成一個全新的你。幸運的是,或許有一個恒定的元素——記憶,連接著所有這些不同版本的你。記憶說不定能擔此重任,成為編織起你身份形象的線索,令你成為你。它是你身份的核心,提供了連續的、獨一無二的自我意識。
然而,其中或許也存在一個問題:這種連續性會不會只是幻覺?想象一下,你走進一個公園,與不同年齡的自己相會。公園里有6歲的你、10多歲的你、20多歲的你、50多歲的你、70多歲的你,以及生命最后階段的你。在這種情境下,你們可以坐在一起,分享相同的人生故事,梳理出你唯一的那條身份線索。
真的能做到嗎?你們的確有著相同的名字和歷史,但事實上,你們是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和目標。你們人生記憶的相同之處說不定比你預想的還少。你記憶中15歲的自己,跟你真正15歲時不同;而且,對同一件事,你有著不同的回憶。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記憶就是這樣的。記憶并不是一段視頻,不能準確地記錄你人生的每一個瞬間;它是來自往昔時光的一種脆弱的大腦狀態,你要回想,它才浮現。
舉個例子,你來到一家餐廳,為朋友過生日。你經歷的一切,觸發了大腦特定的活動模式。有一種活動模式,由你和朋友之間的對話觸發;另一種模式,由咖啡的氣味激活;還有一種模式,由美味的法式小蛋糕的味道激活。服務員把拇指放進你的杯子里,是又一個難忘的細節,觸發了又一種神經元放電模式。在海馬體龐大的相關神經元網絡里,所有這些模式集群彼此連接,反復播放,直到連接方式最終固定下來。同時激活的神經元會建立起更有力的連接:一同啟動的神經元,連接在一起。由此產生的網絡,是該事件的獨特標志,代表了你對生日聚會的記憶。
假設6個月以后,你吃到了一塊法式小蛋糕,味道就跟你在那次生日聚會上吃到的一樣。這把特殊的鑰匙,能夠解鎖相關的整個網絡。突然之間,你回到了那段記憶里。
雖然我們并不是總能意識到這一點,但記憶或許并不如你期待的那么豐富。你知道朋友們在那里:他穿的一定是西裝,因為他總是穿西裝;另一個女性朋友則穿著藍色的襯衫,不對,也可能是紫色的,說不定是綠色的。如果真的深究那段記憶,你會意識到,你完全不記得餐廳里其他食客的細節,盡管當時是滿座。
所以,你對生日聚會的記憶已經開始褪色。為什么?因為神經元數量有限,而且它們都需要從事多重任務。每個神經元參與不同時間的不同集群。你的神經元在關系不斷變化的動態矩陣中運作,繁重的需求不斷要求它們跟其他神經元連接。隨著這些“生日”神經元協同參與到其他記憶神經網絡里,你關于生日聚會的記憶變得模糊起來。記憶的敵人不是時間,而是其他記憶。每一件新的事情都需要在數量有限的神經元里建立新的關系。然而,褪色的記憶在你看來似乎并未褪色。你感覺,或至少以為,完整的畫面始終存在。
你對一件事的記憶更是值得懷疑。比方說,聚會之后的某一年,你的兩位朋友分手了。回想起那次聚會,你現在或許會錯誤地記起兩個人的關系在當時就亮了紅燈。那天晚上,他是不是比平常更安靜?兩個人之間好像有些尷尬的沉默?這些細節很難說得準,因為你神經網絡里的相應知識改變了相關的記憶。你情不自禁地用現在涂改過去。因此,對同一件事的感知,在你人生的不同階段很可能有很大差異。
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的伊麗莎白·洛夫特斯教授進行了一項開創性的研究,發現了記憶的可塑性。她展示了記憶有多么容易受到影響,為記憶研究領域帶來了巨大變革。
洛夫特斯設計了一項實驗,請志愿者們觀看車禍的影片,接著問他們一系列問題,測試他們記住了哪些內容。她所問的問題,影響了志愿者們的答案。她解釋說:“我使用了兩種問法:一種是,兩車相碰時,車速有多快?另一種是,兩車相撞時,車速有多快?志愿者們對速度做出了不同的估計。我用‘撞字的時候,他們認為車速更快。”誘導性問題可以干擾記憶,這令她深感好奇,于是她決定再做進一步的探究。
有沒有可能植入完全虛假的記憶呢?為了尋找答案,她招募了一群參與者,讓團隊接觸其家人,了解這些參與者從前的生活點滴。掌握了這些信息之后,研究人員針對每一名參與者拼湊出來4段童年故事。有3段是真實的。第4段故事包含了若干似是而非的信息,但完全是編出來的。它講的是小時候在購物中心迷路,在一位和善老人的幫助下,最終跟家人團聚的事。
研究人員通過一系列的訪談,把這4段故事講給參與者聽。至少有1/4的人聲稱自己還記得商場迷路事件,盡管它從未發生過。不止如此,洛夫特斯解釋說:“他們一開始也許只能‘回想起一點。一個星期之后,他們回憶起來的內容更多了。他們還會說起幫助了自己的老婦人。”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細節被悄悄填入虛構的記憶里:“老婦人戴著一頂很夸張的帽子”“我抱著自己最心愛的玩具”“媽媽急得都快瘋了”。
所以,不光有可能往大腦里植入虛構的新記憶,人們還會欣然接受它,為其增加細節,不知不覺地把幻想編織進自己的身份認同里。
我們都很容易受到這種記憶的擺布。我們回顧自己的人生記憶時,應該帶著這樣的認識:不是所有的細節都準確無誤。一些細節是別人講給我們的,另一些是我們自己補充的,我們認為當時肯定就是那樣。所以,如果你完全根據自己的記憶來回答你是什么人,你的身份就變成了一段奇異的、不斷變化的、搖擺不定的故事。
(依依摘自浙江教育出版社《大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