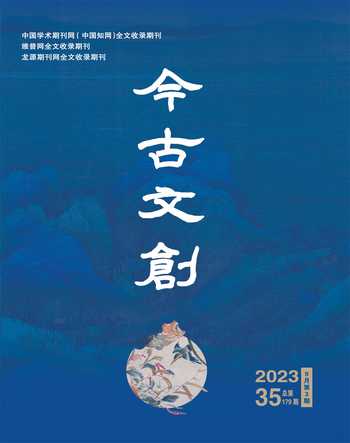論《棋王》的世俗性
【摘要】研究現當代文學的許多學者都將阿城作為尋根文學的一員,他的一些作品也是帶有尋根文學的色彩。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產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阿城的作品不同于文化尋根小說,而是偏向于世俗小說,作品中充滿著濃濃的世俗性。阿城始終保持著冷靜客觀的態度,公正地去描寫世俗社會。他的作品中一方面表達出了生活的素樸性和本真性,贊美了世俗鄉野中的生命力和活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世俗社會的弊端。他的創作令世俗文化這一主題重新回歸文壇。關注文學創作的世俗性有利于還原生活的素樸性和本真性,使文學創作充滿活力。本文從阿城具體的作品《棋王》出發,探究《棋王》所包含的世俗性。阿城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他使中國傳統的文化與當代的文化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使中國社會當中的世俗精神重新蘇醒,使世俗文化煥發著勃勃生機。
【關鍵詞】阿城;《棋王》;世俗性;世俗生活;世俗文化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35-001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5.003
一、《棋王》世俗性的呈現
(一)吃飽是福
阿城在寫作的時候,關注的是現實存在的世俗社會。阿城的小說《棋王》主要講述了在那段特殊時期,名為王一生的知識青年將下棋視為他的愛好,并且到處找人切磋棋藝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就是生活中的普羅大眾,充滿著濃厚的世俗性。阿城在寫作的時候盡量減少時代文化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他并沒有像當時的主流文學那樣將關注點放在歌功頌德上,而是一改筆觸將關注點放在和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他寫出了知青一代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焦慮。世俗社會關注的第一需求便是“吃”,古往今來也有許多的作品對“吃”進行過描寫,但是阿城卻是第一個將“吃”作為小說重點描寫要素的作家。汪曾祺曾經評價阿城時說過:“阿城是敏感的,他對生活的觀察很精細,能夠從平常的生活現象中看出別人熟視無睹的特殊情趣。”[1]阿城在《閑話閑說》中,探究“吃”的文化意味,并且將吃的文化上升到了藝術的高度。“世俗之人嘴越吃越刁,終于造就一門藝術。”[2]這也體現了藝術來自生活,取材于世俗社會。
“吃”的情結在阿城的小說中同樣得以體現,《棋王》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小說圍繞著“吃”這一平凡而又常見的方面展開敘述。人們生活在世界上,當然離不開吃飯這個話題,這也是生存下去所必需的物質方面的條件。在小說中,吃飯是知青們非常特殊的一段經歷。物資匱乏的年代,一起煮蛇肉便也成為美好的回憶。王一生非常重視吃,他對待吃飯是誠摯和敬重的。作者運用了動作和神態上的描寫,對王一生吃飯的情形進行了生動的刻畫。在王一生看來,憂愁那都是閑來無事的文人們的雅興。他要追求的是“人要知足,頓頓飽就是福”這種世俗的生存之道。在王一生到達知青點后大家煮了蛇肉來招待他,在吃蛇肉的過程中,和王一生切磋棋藝的腳卵在談話間表現出了對于飲食文化的豐富了解。腳卵在家里吃螃蟹、吃燕窩的情節,對當時與貧困饑餓做斗爭的王一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在腳卵的話語中可以得知他父親的身份是一位文人,但是阿城并沒有具體說明文人的政治身份。由此可見,阿城是想通過知青一代對飲食方面的回憶來揭示政治身份和吃方面的關系。
(二)棋道至簡
除了吃這個物質活動,阿城還著力刻畫了王一生在下棋方面的故事。在小說中其他知青與家人難分難舍的時候,王一生卻獨自一個人在火車上坐著。當他注意到身邊有人過來的時候,他的眼睛里突然放出光來。作者在后面運用了一串簡短的語言描寫,揭示出王一生是因為遇到熟人可以一起下棋而這么開心的,他對下棋的熱愛,達到了一種如癡如狂的境界。在其他知青的對話中可以得知,王一生綽號為“棋呆子”,并且棋藝精湛。當被問到為何妹妹來找也要下棋時,他說外人不知道他們這些人咋回事,可見是內心有所憂愁。在去往農村的火車上,王一生表現出對吃的虔誠。在他看來,下棋是可以排解生活中的憂愁的。在日常生活中,飲食是人們最基本的生存欲望,是物質層面的。下棋是一種娛樂休閑活動,屬于精神層面。在小說中,阿城并沒有去主觀地評判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地位。事實上,小說中王一生只是把下棋當作了某種逃避現實社會的興趣愛好。這是一種帶有消極傾向的,所以這個層面的下棋其實文化意味并不是那么的明顯。研究阿城創作《棋王》的相關文章后可以發現,小說原稿的結局是在車輪大戰后,王一生并沒有選擇進入省隊下棋,而是愿意留在地方棋隊里面。原因是在王一生看來,地方棋隊的伙食相對來說好一點。如此看來,他內心其實已經把吃和下棋進行了比較,而且吃的地位實際上還要比下棋的地位重要一些。在那一段特殊時期,大多數人喊著“用青春激情燃燒歲月”的口號,這在知青的生活中也是不能避免的。而對于王一生這樣貧窮,在饑餓線掙扎的普通知青看來,下棋也不過是在灰暗無光的歲月中聊以慰藉的事物罷了。這帶有樸素的哀怨的色彩,而做出這樣的選擇也正是他對于世俗社會生活非常了解的結局。
(三)語言亦雅亦俗
阿城在吸收鄉野民間俗語和世俗生活口語的基礎上,對文字進行了藝術化的提煉,使文字既有世俗社會的濃濃煙火氣,又飽含著文人行文的深沉與高雅,實可謂之雅俗相間。蘇丁和仲呈樣曾經這樣評價《棋王》的語言特點“能活用中國文字構成相當精確的意念和情緒”[3]。這兩人的評論字少卻精辟,點出《棋王》的獨到之處,也就是說阿城運用短小形象的文字去描寫世俗社會的真實。阿城并沒有用激越的文字去控訴或者贊頌那個年代,而是用真實的筆觸去描摹特定時代背景下鄉野世俗社會中普通而又具有英雄特點的人物。這些人物是毛茸茸的,帶有生活的本來面目。王蒙曾經也對阿城的語言進行過評價“異于現時流行的各家筆墨,但又不生僻。”[4]這一評價實際上點出了阿城與那個特定年代的格格不同。在那個時期,有人熱烈謳歌那一切,也有人批判或者厭惡那一切,因此這些人的文字是激越的。而阿城與當時的主流文學的方向大不相同,他用平和的文字描摹著真實的存在,用娓娓道來的口吻講述一代知青鮮活真實的人生經歷。雅俗相間是阿城《棋王》語言顯著的一個特點。
雅,顧名思義就是文雅,文中并沒有使用很多的現代復音節詞,而是運用了古代漢語中眾多的單音節詞。比如在小說的高潮部分,王一生和老者進行對決的時候,作者運用了一系列的單音節詞。“抻”字生動鮮明地刻畫出了老者的動作,文字也具有古漢語的文風雅韻。文中還有一處是在描寫王一生和腳卵下棋后,腳卵送別王一生,文中寫道,腳卵“掮著鋤來送”,這一個“掮”字,質樸而又傳神,表達出人們之間這種古樸的依依惜別之情。阿城在渲染王一生和眾人下棋緊張的氣氛的時候,寫道:“我的心里忽然有一種很古老的東西涌上來,項羽劉邦都在目瞪口呆。”他運用了中國古典人物形象來側面襯托王一生身上的英雄意味。文中在描摹老者和王一生的對話時,運用了一系列古色古香的語句,比如“匯道禪于一爐,神機妙算,遣龍治水,古今儒將”,這些都增強了文章的古典氣息,可謂之為雅。
“俗”顧名思義就是通俗,這里的俗實際上指的是語言不晦澀,充滿著鄉野世俗的真情味。阿城作為知識青年,在日常的生活中早已經和村民打成一片,因此,《棋王》中使用了許多口語化的文字。這些口語并不粗俗與鄙陋,而是賦予了文字以鮮活的生命力,讀來令人拍手稱贊。比如在小說的開頭部分,當被詢問到有什么憂愁的時候,王一生回答:“‘憂這玩意兒,是他媽文人的佐料兒。”這句話充滿著濃濃的生活氣息,也在側面表現出特定年代下由于物質匱乏人們很少去重視精神層面的憂愁。文中描寫大家一起煮蛇招待王一生的時候,運用了大量的語言描寫,極富口語化,十分貼合物質匱乏年代下人物的形象。其中有一句是這樣描寫的“誰來看著,別叫豬拱了”,這一句話是寫在煮蛇的時候要多加小心,千萬不要讓豬給拱了,讀起來真是又好氣又好笑。由此可見,之前應該是發生過類似的事情,這是大家在世俗生活的體驗中得出來的經驗。文中在描寫王一生對戰九人的時候還寫道“一個樵夫,提了斧在野唱”,這句話非常具有意境。雖然這句話的語義成分都是鄉野中的,但是并不粗俗,而是讀來讓人眼前出現這一個畫面,有一種蒼涼的肅穆感,在文中是渲染了緊張刺激的狀態。文中在刻畫人物形象的時候,極具生活氣息。“王一生把衣裳脫了,只剩一條褲衩,呼嚕呼嚕地洗”,這一句傳神地描寫了王一生的麻利,呼嚕呼嚕非常形象地寫出了水的聲音,襯托了王一生動作的快,這也是和世俗生活脫不開的。
二、《棋王》世俗性的原因
(一)獨特的文學觀
1.主流文化排擠
由于時代環境的原因,阿城父親在1956年寫的《上海在沉思》在當時被廣泛討論,他的想法被當時一部分人曲解。正是這個原因,阿城也受到牽連,被所謂的主流所不接納。阿城曾寫道:“我習慣沒有尊嚴。”[5]在他看來,正因為這種原因,所以他可以安心地在家附近的琉璃廠舊店鋪里受到教育的熏陶。雨果、曹雪芹、羅貫中等中國和外國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他在學生時期就已經讀過了。正是由于被主流邊緣化,他的教育啟蒙背景和正規的學堂教育不同,所以他和同時代人的知識結構也大不相同。在這段特殊時期結束后,阿城重新回到北京,幫助父親編寫《電影美學》。在這一個時期里,他和父親共同研究討論黑格爾的《美學》和儒家思想、道家文化。這一段經歷豐富完善了他的知識結構,奠定了他日后文學創作的風格。他也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小說里吸收了世俗含義,這對他日后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2.反思文學熱潮
反思文學與傷痕文學相繼在中國現代文壇興起,成為當時主流社會認可的文學。這一方面反思了過去,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另一方面也過分脫離了現實生活,造成另一種層面上的虛無。阿城反思當時的文學創作,在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傳統小說中得到靈感,將描寫對象定位在世俗社會中,他所描寫的正是與世俗鄉野密不可分的。時代環境影響人們的思想,當時的人們處于一種極端和偏激的思維中,這就造成人們處于兩個極端。在那一個時期,人們都將目標作為追求的重點,而過程卻是被忽視的。這種觀念阿城并不認可,他認為人們應該注重過程,過于注重理想化最后往往會受打擊。阿城認為,“過程主義者離開世界時是快快樂樂的,‘這個我見過,那個我見過。玩物喪志,我取玩物。”[6]思想觀點必然會影響一個人的文學創作方向。阿城遵循著他的想法,從中國傳統古典小說和對歷史文化的反思下,放棄了帶有厚重感的歷史主義寫法,也和同時代的一批知青作家不同,他另辟蹊徑,將關注點放在了世俗現場,將敘述的角度下沉到世俗民間社會,他并沒有仰視或者歧視世俗文化,而是采取一種平視而又溫和的角度,賦予鄉野世俗以最本真的色彩,描摹那個時代人們面對苦難來臨,平和對待追求精神上的平衡的現實。什么是世俗文化呢?阿城曾經如是說就是活生生的多重實在。活生生說明關注點在現實場景,多重實在說明關注的視角是多樣的。在特殊的文化和生活經歷影響下,阿城將關注的重點放到世俗文化和現實中。他明確提出過,在一些掃除運動中,有很多的世俗文化被批判和破壞。他“總是喜歡看日常生活”[7]。這里他喜歡的日常生活,并不是20世紀80年代文壇上所推崇的那一種向日常生活所靠攏。“世俗小說中呈現的‘日常生活不是‘非日常的某種宏大敘述的對立面,只是‘日常本身。”[8]正是有著這樣獨特的想法,他并沒有將知青這一部分生活經歷看作對青春美好時光的浪費。他也并沒有陷入甘愿揮灑青春的自我感動中,而是欣賞和著迷于世俗生活,注重著一些活生生的現實存在。
(二)文學傳統的繼承
1.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
阿城說過,用自然的心態來看,中國文化和世俗文化具有某種共通性,這是早已經成熟的實用文化。他舉例說明發掘出土的商周時期的甲骨文上出現的大多數是一些非常實際,和現實世俗生活緊密相連的問題。比如說女人懷孕了會不會難產,豬跑了是什么寓意等等,盡管都是一些非常生活化的問題,但是人們卻詢問得非常真誠和迫切。由此可以看出,世俗作為一種傳統在中國源遠流長。阿城又進一步對儒釋道思想進行分析,闡明了世俗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在他看來,道家講的大部分是治理國家的方法,使天下安居樂業的社會理想。阿城還使用魯迅先生的觀點來證明道家的世俗性:中國人把道教放到重要位置的原因不僅是因為道教是起源于中國本地的宗教,而且是因為道教以人民為主題,始終為世俗生活服務。阿城曾經說自己是一個十分現實、入世的人。阿城特別欣賞孔夫子積極入世的思想,在他看來,儒家的入世思想不同于總帶有標榜味道的道家,他認為儒家思想的實用性非常強。阿城認為后世之所以把孔子尊稱為圣人,正是因為圣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俗人當作俗人的范例,是可以學習的。中國的古人把這樣一個鮮活的,有溫度的人作為世俗人們的樣板,這里面的世俗性令人深思。佛教不同于以上兩種宗教,它并不是中國本土宗教,自從傳入中國后就處于被改造的地位。在印度,佛教的意義是實現靈魂的永恒,這與追求現世美好的中國社會大不相同,因此,印度佛教里的一些神仙被改造為和世俗生活息息相關的送子觀音和慈祥的佛祖。很明顯的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現著世俗意味。
2.中國傳統小說的繼承
班固曾經說過,只有不入流的人才會寫小說。阿城認為,班固的貢獻主要是他在于提出了小說這一個含義。司馬遷是非常擅長寫小說的,他的小說大多數是以世俗生活為主要題材。魏晉時期的志人和志怪小說,唐傳奇代表了世俗小說的發展,宋元話本在民間大量流傳,元雜劇是中國世俗藝術史上一大奇觀。明代的《水滸傳》《金瓶梅》是把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作為描寫對象的。阿城認為被譽為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在文化意義上是可以被看作世俗小說的。曹雪芹將中國古代傳統的一些詩歌引入文中,這一點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很大。在《紅樓夢》以后,中國近代的世俗小說在清朝末年達到頂峰。到了“五四”時期,中國小說的目的是改造國民性,反對世俗化。一直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小說才開始重視世俗精神。阿城非常專注在世俗生活和鄉野民間尋找一種文化意義的支撐。他認為,由于主流社會的傳統意義的文化傳統被破壞,所以可以去充滿生機與生命力的世俗民間去尋找丟失的文化傳統。他的《棋王》便是創作于世俗精神重塑的一個時期,也是在中國小說一脈相承的世俗性影響下創作的。
參考文獻:
[1]汪曾祺.汪曾祺說阿城小說《棋王》[J].名作欣賞,2005,(01).
[2]阿城.閑話閑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3]蘇丁,仲呈祥.《棋王》與道家美學[J].當代作家評論,1985,(03).
[4]王蒙.且說《棋王》[J].文藝報,1984,(10).
[5]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6]阿城.行走的智者[J].鴨綠江,2001,(05).
[7]阿城.威尼斯日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8]林建法,王景濤.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1.
作者簡介:
吳傳瑋,女,漢族,山東濟南人,海南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