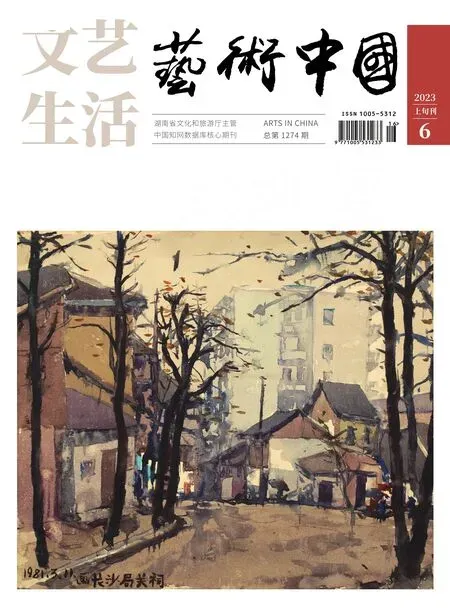略論齊白石人物畫的獨特性
◆薛超(湖南博物院)
如果提及齊白石的藝術創作,大多數人會談及他筆下充滿童趣、飽含生活情感的花鳥蟲魚,以及“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真山真水。這些為人熟知的繪畫題材已然成了齊白石藝術生涯的“標簽”。其中,我們對其山水圖像的熟知度相對于他筆下的花鳥、水族、動物昆蟲而言,還略顯“遜色”。而人物畫受到后人珍視的程度也是略顯一般。但是,目前陳列或收藏在部分博物館、畫院、紀念館、美術館中的齊白石人物作品卻為人們揭開了其藝術發展全貌的“缺口”。那么,齊白石的人物畫是否如同他筆下的其他繪畫題材,也是其獨特藝術個性的彰顯?
眾所周知,齊白石早年以木匠為業,20歲始以《芥子園畫譜》自學繪畫,50多歲后進行“衰年變法”,開創了“紅花墨葉”的大寫意花鳥畫風格。齊白石的花鳥、山水、人物等諸多繪畫題材皆具有個人獨特的面貌。根據湖南博物院收藏的齊白石306件繪畫作品來看,目前發現的齊白石有年款作品中最早的一件作品《佛手山茱萸扇面》的創作時間應為1892年,而該院收藏的他的一幅《黛玉葬花圖軸》約為1892年完成,加之與該院收藏的他的早期作品《水牛圖軸》(約1895年)、《山水扇面》(1896年)等作品相比,可知他開啟人物畫創作的時間并不晚于其他題材的創作時間。
一、 早 期 人 物 畫( 約1892—1918年)
目前可以看到的齊白石最早的一幅肖像畫是他于1895年創作的《黎夫人像》(現藏于遼寧省博物館)。畫作的主人公為黎丹的母親胡老夫人。黎丹(1873—1938),湘潭人。黎丹的舅父是齊白石的老師胡沁園,其母是胡沁園的親姐妹。該畫像為齊白石33歲所畫,他于正面像中,利用西方繪畫的明暗透視關系體現人物的外貌特征;同時在精細逼真的視覺效果中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點,并通過畫面下方的裝飾圖案實現其與人物服飾的線條、色彩的呼應。齊白石早期的這幅肖像畫讓觀者看到他具有較強的寫實功底,而這種寫實手法相較于閻立本等人刻畫的人物形象而言,更富有真實的肉體質感;同時與郎世寧筆下的帝后像相比,齊白石早期的這幅肖像畫將人物與空間相融合,有別于傳統人物畫重形象刻畫、輕環境交代的圖式特點,這也體現了齊白石在繪畫創作初期,已經具有了創新思維。
齊白石在26歲以后開始拜師胡沁園、蕭傳鑫等人學習詩文書畫。因謀生的實際需求,他在30歲左右主要為他人畫像,此時的人物畫在繪畫題材上受制于買方的要求。齊白石在《齊白石自述》中寫道:“我的畫在鄉里出了點名氣,來請我畫的大部分是神像功對,每一堂功對,少則4幅,多的有到20幅的。畫的是玉皇、老君、財神、火神、灶神、閻王、龍王、靈官、雷公、電母、雨師、風伯、牛頭、馬面和四大金剛、哼哈二將之類。”盡管這些神像功對由于年代較早,已被使用或者沒有署名的原因,現已無法找到實物,但是從《齊白石自述》中,可以了解齊白石早期人物畫描繪的一些題材。
除上述題材外,齊白石早期所畫的仕女圖深受鄉親喜愛,甚至有“齊美人”的美譽。他的仕女圖現今存留較多。湖南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北京榮寶齋等地均有收藏。其中,湖南博物院收藏的《黛玉葬花圖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畫無論是在人物態勢、筆墨運用還是刻畫的精細程度來講,都與清代人物畫家改琦的繪畫風格較為相似,體現了齊白石對中國傳統人物畫繪畫風格的臨習。同時,通過畫中的署款:松盦道兄教,弟齊璜少年時作,衰年補識。時己巳春,同在燕京,可以了解到這段署款為補跋,此畫是齊白石早年贈送給家鄉友人黎培鑾之作。款中的“松盦道兄”應為黎培鑾,湖南湘潭人,收藏名人字畫極富,能治印,齊白石初學篆刻時,常與其切磋。畫中補寫的這段署款兼具了識讀與辨識的功用,而這種原創性的“說明”也成了齊白石的作品能夠貼近人心、擺脫孤芳自賞的緣由之一。此外,該畫兼工帶寫的刻畫風格于細膩處反映了齊白石扎實的工筆畫功底,且舒展有力的線條掌控能力也為他日后開創大寫意繪畫風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齊白石自述》和目前有據可查的文物資料來看,齊白石早期人物畫的創作題材涵蓋了神像功對、仕女以及熟悉的人物等等。他在或中西融合或兼工帶寫的繪畫技法中描繪人物的正面或四分之三側面像,為觀者呈現了影像技術無法展現的內觀感受,并且使這些人物特有的性格特征躍然紙上。據考證,湖南博物院現有一幅齊白石早期創作的《人物圖軸》。其中,署款為:濱生齊璜戲作。畫中繪有一位身著寬松衣褲、肩上扛有拐杖,拐杖上端懸掛一個葫蘆的“長者”形象。通過鑒賞齊白石早期的人物畫,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作品涉及了道教、佛教和民間傳說中的人物。其中,在他曾經創作過的一幅《鐵拐李》的作品中,題詩為:形骸終未了塵緣,餓殍還魂豈妄傳。拋卻葫蘆與鐵拐,人間誰信是神仙。再結合這幅《人物圖軸》中的人物形象,可以推測畫中的人物應為道教中的八仙之首—鐵拐李。齊白石利用看似單一的寫意技法精煉地揮寫出了人物特有的“標識”特征,同時粗獷與細膩并存,給予觀者既可觀其神情亦可賞其技法的雙重感官體驗。而這種人物畫的寫意技法在齊白石藝術變法期和鼎盛期的大寫意人物畫中得到了進一步“升華”,成了齊白石極具個性的人物畫“標簽”。
二、變法期人物畫(約1919—1928年)
齊白石于1919年正式定居北京。但其冷逸疏簡的畫風并未得到廣泛認可,因而畫作的市場接受度較差。此時,他聽從陳師曾的勸告,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衰年變法”,開創了“紅花墨葉”的大寫意花鳥畫風格。從湖南博物院收藏的齊白石這一時期的作品來看,動物昆蟲、花鳥、山水題材的作品居多,且以寫意技法為主。同時,少量的人物畫讓觀者看到了齊白石在藝術變法期對“大寫意”繪畫風格的駕輕就熟。盡管“大寫意”繪畫風格在其多類繪畫題材中均有呈現,而這一時期的人物畫與其早期的人物創作相比,對于人物體貌特征的提煉概括更為簡練精準,對于線條的勾勒更顯其寫意技法的日趨成熟,從而也使他筆下這一階段的人物畫已具有個人風格。
《齊以德像》是湘潭齊白石紀念館收藏的一幅齊白石的人物畫,創作于1927年。1926年,齊白石父母親去世。次年,他為父親齊以德繪制遺像,他將父親的照片按比例放大后,運用西方素描畫黑、白、灰的明暗表現形式,以及塊面結構的凸顯,使人物形象更為鮮活和立體。如果將其父親的攝影像和這幅畫像進行對比,二者幾乎如出一轍。從中也可見進入藝術變法探索期的齊白石,并不是為了“變”而“變”,“出新”而“出新”,而是依舊具備了較強的造型能力并作為其進行藝術創新的基礎。正是因為他將這種內在的扎實的寫實功底與外在的藝術的個性化進行充分融合后,才得以呈現其變法期人物畫的又一特點。
目前,湖南博物院收藏了齊白石約在20世紀20年代創作的一幅《李鐵拐圖軸》。這幅人物畫與他早期創作的《人物圖軸》相比,更具有水墨畫的趣味性和筆墨韻味。雖然同為側面像,但《李鐵拐圖軸》通過簡化人物服飾的刻畫,側重突出人物最鮮明的形象特征,以此來展現水墨人物畫特有的細膩傳神。同時,該畫直觀地反映了齊白石在這一時期筆墨技法的靈活運用與自我肯定。無論是頭部的刻畫,還是被衣物包裹的軀體的描繪,都借以筆墨凝練的線條得以再現,而這些線條無一多余,且可見其書法功力。可以說,此時齊白石的人物畫已突破傳統人物畫的局限性,將傳統與現代進行“區分”,彰顯了筆墨的時代氣象。當然,齊白石對于人物畫的這種“變法”給予了觀者“似曾相識”的視覺感受。善于汲取個性派藝術家繪畫風格的齊白石,在《李鐵拐圖軸》中呈現的筆墨效果與南宋畫家梁楷的“減筆人物畫”在相似中又有差異,由此可以看出齊白石對梁楷繪畫風格的借鑒學習。與梁楷的《潑墨仙人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相比,二人均敏銳地捕捉到描繪對象的本質特征,以極簡的筆墨傳達了對象的神情,并且于神形兼備中有的放矢,寥寥數筆卻意味十足。齊白石在《李鐵拐圖軸》中主要以“線”再現物象的輪廓,并結合書法的“金石味”、水墨的“韻律感”,以及意象表現的“趣味性”,從而使其描繪的對象給予觀者輕松愉悅之感。梁楷在《潑墨仙人圖》中側重以“面”呈現物象,通過濃淡墨色構成的塊面呈現人體的結構與外在的體貌特征,相較于齊白石人物畫的“實”而言,梁楷人物畫的“虛”則帶有另外一番筆墨意境。但是,二人的人物畫皆開創了中國人物畫發展史上的新局面,以“簡”與“精”取代傳統人物畫的“繁”與“細”,在筆墨游戲中抒情寫意。可以說,齊白石在這一階段對于人物畫繪畫風格的探索與實踐也成了日后他在藝術鼎盛期人物畫獨具特色的基石,其后來被抄襲模仿的人物畫真跡的藝術形式皆源于此時他在人物畫創作方面形成的藝術基調。
三、鼎盛期人物畫(約1929—1948年)
在經過長達十年的“衰年變法”之后,齊白石大器晚成,此后的二十年達到了他繪畫生涯的鼎盛期。目前觀者所熟知的齊白石的作品多出自這一時期,尤其以蝦蟹、“紅花墨葉”的花卉作品最受歡迎,山水、人物雖數量較少,但也體現了齊白石超凡的藝術表現力和創新能力,最終呈現了觀者所熟知的“齊派”風格。
就目前收藏或陳列在博物館里的齊白石作品來看,有年款的作品是在他八十歲左右創作完成的,沒有年款的作品需要結合其藝術創作經歷、繪畫風格、署款的字體風格,以及鈐印的特點對相關作品進行斷代的推定。可以說,處于藝術發展鼎盛期的齊白石,在花鳥、山水、人物等諸多繪畫題材的創作上都實現了“質”的突破,奠定了其在中國畫壇不可取代的歷史地位。這些實物的考證,可以為觀者梳理出齊白石的人物畫在創作鼎盛期的藝術特色,從而勾勒出齊白石人物畫創作整體的發展脈絡。
《五童紙鳶圖》是齊白石于1940年“衰年變法”之后創作的一幅人物畫,現收藏于遼寧省博物館。透過畫面,一股熟悉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這顯然與齊白石早期和變法期的人物畫主題有所不同,它與觀者產生了更多的“互動”,同時簡練的線條所描繪出來的合乎人體比例和動勢的人物形象,以及結合接地氣的繪畫主題,使這樣一幅人物畫具有齊白石這一時期其他繪畫題材的天然之趣,并且讓他的人物畫帶有兒童簡筆畫的純真之美,且不失中國畫的線條韻味。
曾有學者統計齊白石僅有三次超過十天的時間沒有作畫,一生中創作的作品數量有三萬幅之多,有些專家甚至認為齊白石一生創作數量大概有六萬件。盡管關于齊白石一生創作作品的數量無法得出定論,但是“勤奮”應該是其取得藝術成就的關鍵因素。此外,對藝術的“執著”和“堅守”也是其擁有藝術自信不可或缺的要素。雖然處于藝術鼎盛期的齊白石已步入花甲之年,但是他在八十歲左右仍然處于藝術鼎盛期,可謂是真正的“老當益壯”。或許“老當益壯”也深入齊白石的內心,使得他將這種積極樂觀的心態流露于筆端。《老當益壯圖》是齊白石晚年常畫的主題,北京畫院收藏了他這個主題不同的畫稿和作品,透過這些作品來看,齊白石的《老當益壯圖》具有一些共性:畫面均刻畫了一個須眉皆白的老者,挺腰舉杖,神情透露出專注與倔強;長者的形象經過了藝術化的“夸張”處理,以“寫意”取代“寫實”,同時人物的身材比例為非常規的“站七座五蹲三半”;眼手的細膩刻畫與服飾的粗獷筆觸形成了鮮明對比,凸顯了人物畫特有的眉目傳神,增進了人物內心深處情感的傳遞;簡潔明了的“署款”直入畫面主題,讓“畫外音”與觀者產生更多共鳴。
齊白石終其一生致力于貼近生活題材的繪畫創作,無論是致廣大的自然山水,還是盡精微的花鳥蟲魚,這些富有靈性的生命在紙張的方寸之間具有了不同于影像的靈動鮮活,使它們獨特的“美”成了永恒的定格。這些雖寥寥數筆卻韻味十足的寫意作品,展現了中國筆墨獨有的博大精深。而齊白石晚年的人物畫更是兼具筆墨與情感,營造了如同漫畫的視覺沖擊力,簡潔且精悍。這些前無古人的水墨人物畫涵蓋了生活中最為平常的“小事”,以及齊白石對社會和生活的洞察與感知。現收藏于北京畫院的《人罵我我也罵人》是齊白石藝術鼎盛期創作的一幅人物畫,雖無年款,但通過對比他在藝術鼎盛期創作的《山水圖軸》(約20世紀20年代晚期)和《南瓜圖軸》(1940年)中的署款字體和筆墨特點,我們可以推斷《人罵我我也罵人》的創作時間應為其藝術鼎盛期。畫面中,一位長者盤腿而坐,怒目橫眉,左手扶著大腿,右手指向外面。畫面采用濃淡墨色的寫意線條進行勾勒,而濃墨的運用之處正是畫面想要凸顯的主要內容之一,即手的姿態表明了人物的心態。同時,濃淡色彩的鮮明對比將觀者的視覺中心聚焦于人物的面部,使人物的神情與觀者的感受產生了碰撞。通過整體觀察,我們可以發現人物占據畫面近乎三分之二的空間,并且布局較為靠上,而畫面另外三分之一的空間則留給了署款。“人罵我我也罵人”的署款文字強化了觀者對此畫的感知,同時也使這幅“圖文并茂”的人物畫帶有了幽默詼諧和現實諷刺的深刻寓意。可以說,齊白石筆下的人物畫真正實現了“創作”,他將“創意”與“技法”相結合,呈現了傳統人物畫缺失的社會寫照,以及能夠給予觀者的深思與醒悟。人物畫,有人,有畫,更有話,或許,這正是齊白石鼎盛期人物畫的非凡之處。
目前可以瀏覽到的齊白石人物畫,應該可以說讓觀者看到了“驚喜”。在他為數不多的一幅幅人物畫中,主要呈現了單個人物形象,并以坐姿為主,同時他以嫻熟的寫意筆墨技法,將勁健有力的線條與富有層次的墨色平涂相糅合,展現了一個個走近人心的人物形象。這些有別于傳統人物畫的呈現方式,正是齊白石在人物畫創作方面,由寫實轉向寫意、由寫意融入情感、由客觀再現到主觀表達的傳遞,在人物畫也可以具有的“由小見大”的視覺圖像中彰顯他對生命和生活的獨特見解。
相對于齊白石筆下充滿靈性的花鳥蟲魚和自然山水而言,他的人物畫創作略少。但值得慶幸的是,在這些獨具面貌的人物畫中,我們可以有所思,有所想,有所悟。或許,這就是文人畫家齊白石以“筆墨”代替“文字”、以“畫”為“話”所展現出來的一位藝術家的個性與自由。人物畫,可以是人物形象的真實再現,亦可以借“人物”抒“情感”,而這樣的圖像在齊白石的畫筆下兼而有之,倍顯難得。
畫吾自畫,齊白石的人物畫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