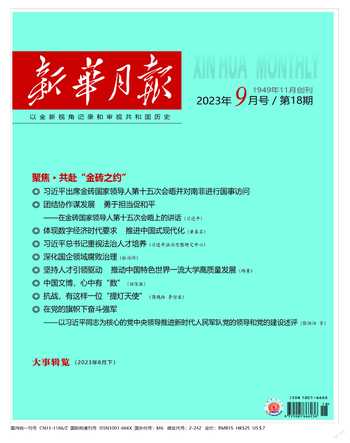中國邊疆學研究的史鑒功能
李大龍


中國古人對邊疆的關注由來已久,先秦典籍《左傳》中就多次出現有關“邊疆”的記載,而司馬遷的《史記》為邊疆政權和族群立傳更是開啟了所謂“正史”記錄邊疆經濟社會發展、歷代王朝治理邊疆歷程的先河,定位了中國邊疆學研究的史鑒功能。
古籍經典中的“邊疆”
“邊疆”一詞,一般認為首見于《左傳》,并多次出現,如“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盡管在《左傳》中“邊疆”一詞含義也是用于指稱疆域的外圍地區,但是在正史中該詞的出現相對較晚,首見于《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繼之在《晉書》中“邊疆”一詞多次出現,如該書卷一百二十一《李壽載記》有:“代李玝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其后延至清代,“邊疆”頻見于所謂“正史”。
秦漢是開創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王朝,有關秦漢時期的史書中,雖然沒有“邊疆”一詞,但有“邊境”“邊徼”“邊地”“邊郡”等含義相近的詞匯。
如,《漢書·宣帝紀》有:“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漢書·匈奴傳》有:“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
《漢書·食貨志》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其下引注:“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御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又有:“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
《漢書》卷二十四《晁錯傳》有:“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
以上史書中記載的“邊疆”“邊境”乃至“邊徼”“邊地”“邊郡”等,多是指王朝直接管轄區域的外圍地區。這種情況一直沿用到明代。
至清代,從《清實錄》檢索到的對“邊疆”一詞的使用情況看,盡管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與俄羅斯簽訂了具有近現代主權國家意義的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清朝的疆域也具有了明確的“邊界”。“邊疆之地,民夷雜處”是乾隆皇帝對“邊疆”給出的特征描述,而“云貴四川等處,俱系邊疆,殊為緊要”“熱河、察哈爾均屬邊疆要地”“鞏邊疆而固藩服”等對“邊疆”一詞的使用也印證了這一說法,但“諭吏部、兵部,狹西幅員遼闊,邊疆重地,防御宜周”,則將傳統被視為中原腹心之地的“狹西”也稱之為了“邊疆”,應是和康熙皇帝時期尚未鞏固對陜西的管轄有關。也就是說,清朝的“邊疆”具有兩重含義:既強調“民夷雜處”的“藩部”區域是“邊疆”,又強調處于直接統治區域的外圍地區,也稱為“邊疆”。
民國時期,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黃慕松認為“邊疆”的基本含義是指接近鄰國的地區,即“普通多指四周接近鄰國之地域”,即“遠離中原,既接強鄰,又與內地情形稍有差別之領土”,但“地帶、氣候、民族、語文、政俗諸端,均與中原同,則雖在極邊而不視之為邊疆,如閩粵諸省是。否則雖不在邊徼,亦可視為邊疆,如青康諸省是。”進而認為“我國之邊疆,自當以蒙古、西藏、新疆、西康為主,察、綏、寧、青等省次之”,而“東三省、云南、兩廣及沿海諸省,雖處邊疆,民情風俗,一如中原,法令規章,普遍使用,已無特殊行政區域之性質,故不能與邊疆同視”。黃慕松的認識既兼顧了“臨近鄰國”,同時也強調了“文化”的差異。但是,在相關政策條文中“邊疆”的界定則是存在差別的。民國三十三年(1944)教育部頒布的《邊疆學生待遇辦法》有對“邊疆學生的界定”:“本辦法所稱邊疆學生,謂蒙古西藏及其他語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質地方而其家庭居住于原籍者之學生。”同年召開的“邊疆教育委員會第三屆大會”對“邊疆教育”做出了明確規定:“所謂邊疆教育,系指蒙藏及其他語文文化具有特殊性質之地方,即西藏、新疆、西康、青海、寧夏、綏遠及甘肅、云南、廣西等省一部分地方而言,其中情形復雜較難著手者,為西藏、新疆二地。”二者的界定存在著較大差異,可知民國政府對“邊疆”的含義也沒有達到統一的程度。
新中國成立以來,“邊疆”往往和“民族”連用,依然經常見諸各種政府報告和政策文件之中。
《全國國土規劃綱要(2016—2030年)》是對我國疆域的規劃,其中對我國的國土面積有如下闡述:“我國的國土包括陸地國土和海洋國土,其中陸地國土面積960萬平方公里,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和我國主張,管轄海域面積約300萬平方公里。”盡管沒有明確“邊疆”的范圍,但其后卻將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統稱為“特殊地區”進行闡述。“邊疆地區”對應的表述是:“推進邊境城市和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等建設,支持新疆建成向西開放的重要窗口、西藏建成面向南亞開放的重要通道、云南建成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廣西建成面向東盟的國際大通道;支持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建成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和東北亞區域合作的中心樞紐;加快建設面向東北亞的長吉圖開發開放先導區。”據此,新疆、西藏、云南、廣西、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等都是“邊疆”的范圍。
國務院頒布的《興邊富民行動“十三五”規劃》中雖然沒有對“邊疆”的認定,但有對“邊境地區”的解釋:“本規劃實施范圍為我國陸地邊境地區,包括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廣西、云南、西藏、甘肅、新疆等9個省區的140個陸地邊境縣(市、區、旗)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58個邊境團場(邊境縣)。參照‘十二五期間做法,海南省6個民族自治縣繼續比照享受興邊富民行動相關政策。”將其和《全國國土規劃綱要(2016—2030年)》中的表述進行對比,差別是多了一個甘肅省,因此其所謂的“邊境地區”應該等同于“邊疆地區”。
綜上所述,出現在國家正式公布的規劃中的陸路“邊疆地區”最大指稱范圍是指有國界線的9省區,也就是說“邊疆地區”是和“國界線”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有國界線的地區才能稱為“邊疆地區”。盡管“邊疆”一詞出現得很早,但從“邊疆”一詞的發展和具體使用情況看,存在著一定差異,不過將直接管轄疆域的外緣地區視為“邊疆”是大體一致的用法。
“天下”“族群”觀:多民族的凝聚與交融
多民族國家中國形成和發展于東亞遼闊的中華大地上,而伴隨著農耕族群所建政權的出現,最遲在先秦時期就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天下觀”和“族群觀”。

囿于對周圍地理環境的認知,一般情況下中國古人將東亞區域稱為“天下”。“天下”的范圍隨著人們對周圍環境的認知水平而擴展,“天下”也有理想化和現實中的差別。《詩經·小雅·北山》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是對理想中“天下”的描述;而經常見諸史書記載的“大赦天下”則說的是現實中的“天下”,即秦漢及其之后以郡縣為核心的皇帝政令可以實施的范圍。費孝通先生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對中華民族生存空間的描述:“中華民族的家園坐落在亞洲東部,西起帕米爾高原,東到太平洋西岸諸島,北有廣漠,東南是海,西南是山的這一片廣闊的大陸上。這片大陸四周有自然屏障,內部有完整的體系,形成一個地理單元”,可以視為是當今學者對中國古人理想中“天下”范圍的現實理解。多民族主權國家中國,就是在這一遼闊區域內自然凝聚形成的。
“天下”有理想和現實之分,“天下”的人群相應也有“夏”“夷”之別。較早創建政權的中原農耕族群,很早就看到:自然環境對人群凝聚的影響,并有了“五方之民”的族群劃分,《禮記·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期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重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這是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人們最早對不同族群的認識,明顯有別于基于種族而來的民族國家理論,其劃分的標準不是相貌、膚色等人種特征,而是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等生產生活方式,劃分的標準屬于文化的范疇。
“五方之民”隨著秦漢“大一統”的實現及對農耕族群的凝聚和整合,演變為“夏”“夷”兩大群體。在兩大群體劃分的基礎上,司馬遷在《史記·西域傳》中將西域的眾多族群和政權分為農耕/“城國”和游牧/“行國”,很明顯是以中原地區被稱為“漢”的族群與草原地區被稱為“匈奴”的族群的居住特點之間差別為標準劃分的。民國時期的地理學者胡煥庸在1935年以璦琿和騰沖為兩端,將中華大地上的人口分布劃分為東西兩部分,這就是著名的“胡煥庸線”。“胡煥庸線”雖然和司馬遷的劃分不完全吻合,但基本上也可以將中華大地上的人群分為農耕和牧業兩大群體。回顧中華大地上眾多族群和所建政權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不難發現上述中國古人對族群的認識對后代處理不同族群之間的關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歷朝各代奉行的“因俗而治”“用夏變夷”“以夷制夷”等觀念和政策都基于這些認識,同時這些認識也為不同族群之間的凝聚和交融、中華民族(國民)初步實現的凝聚轉型提供了理論依據。
無論是稱為“夏”“夷”,還是稱為“農耕”“游牧”,在中華大地上互動的這兩大族群的事跡幾乎占據了古籍記載的絕大部分,不僅推動了多民族國家由傳統王朝國家向近現代主權國家轉化,成為共同的締造者,同時也是當今我國56個民族的祖先。
深入認識“中國”與“邊疆”

和“邊疆”相比,“中國”一詞出現得更早且含義更復雜。目前已知最早出現的“中國”一詞是在1963年出土于寶雞的西周青銅器“何尊”之銘文中:“……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下:‘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相應地,先秦時期的典籍中也存在著有關“中國”的記述。《尚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詩注疏》卷二十四:“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
對于“中國”,今人也給予了很多關注。著名史學家翁獨健先生的觀點即有代表性:“中國一詞,從《詩經》上就可以找到,不過古代‘中國之稱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或者是一種褒稱。”(翁獨健《在中國民族關系史研究學術座談會閉幕會上的講話》)翁先生揭示了“中國”這一詞匯在不同時期所具有的復雜內涵,但“中國”最初的含義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則是不能否認的,因為后人對于“中國,京師也”的注疏,就將“王畿”“中國”“京師”有機聯系在一起,詮釋了“中國”最初是指周王的“王畿”及其所隱含的“天下政治中心”的內涵,前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
從文獻記載看,古人對“中國”一詞的使用,或指代王朝國家,或用于人群,或指稱中原地區等,具有不同的含義。今人對“中國”的使用一般是指960萬平方公里領土的多民族國家。
從地域的視角審視,“中國”用于指稱京師、郡縣、中原地區,青銅器銘文中的所謂“宅茲中國”即是。
從人群的視角審視,“中國”則用于指稱源自炎黃部落的人群,先秦時稱“中國”“諸夏”,秦及以后稱秦人、漢人,然其后漢人的指稱范圍多有變化,但原則上是指繼承傳統典章制度的中原地區的農耕人群。
從文化的視角審視,“中國”用于指稱源出于黃帝的中華文明,其核心內容今人多認為是儒家文化,實際上其核心內容應該是指以皇帝為核心的“大一統”政治秩序,即“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其外在的體現則是傳統的典章制度和禮儀制度。
從“天下正統”的視角審視,“中國”用于指稱“正統”王朝,二十四史記錄的從夏到明王朝以及清王朝即是“中國”的代表。
從中心與邊緣的視角審視,“中國”則與“夷狄”“四夷”相對,構成了“天下”。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這些用法中的“中國”含義并不是固定的,即便是指稱的政權、人群、文化等對象也都不是固定的,“中國”及其衍生出來的“諸夏”“中華”及其與之對應的“夷狄”“四夷”等,其指稱對象都不是固定的,其具體所指對象取決于擁有話語權的一方。如東晉南朝稱占據以黃河流域為主的北方眾多政權的建立者為“五胡”,而“五胡”之一的氐人前秦則稱東晉為“夷”等。即便是源自“諸夏”的“漢人”概念,其指稱也是變動的。三國時期,“漢人”一分為三:魏人、蜀人和吳人。元代的“漢人”則包括了內遷中原黃河流域的契丹、女真、渤海等人。
“邊疆”與“中國”結合而成的“中國邊疆”,雖然明確了“邊疆”的主體,但由于“中國”在中華大地的歷史和現實中指稱的對象復雜,導致不同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分析“中國邊疆”依然會存在認識上的差異。其原因一方面源自學者的視角不同,審視的結果自然存在差異;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內涵的多樣性和動態的特征,不同學者聚焦的“中國邊疆”的具體面相也有可能不同。在這種情況下,明確“中國邊疆”的基本面相不僅有助于我們討論的進一步深入,更有助于深刻理解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形成與發展、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
所以,基于中國邊疆學是研究中國邊疆的一門學科的認識,就當前的中國邊疆研究而言,多學科理論與方法的應用對于中國邊疆研究繁榮無疑是必須的,這不僅是學科發展的需要,更是我國邊疆地區穩定與發展的迫切需要。多學科學者的介入盡管有助于我們從不同視角對中國邊疆的歷史與現實進行全方位的探討,但是在“百花齊放”之后作為一個完整研究對象的“中國邊疆”則依然需要學界給出一個綜合的符合中國邊疆實際的客觀認識,這是中國邊疆當前和今后穩定與發展的需要。
(摘自7月31日《人民政協報》。演講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國家與疆域理論研究室主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雜志主編)
■ 本欄編輯 朱湘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