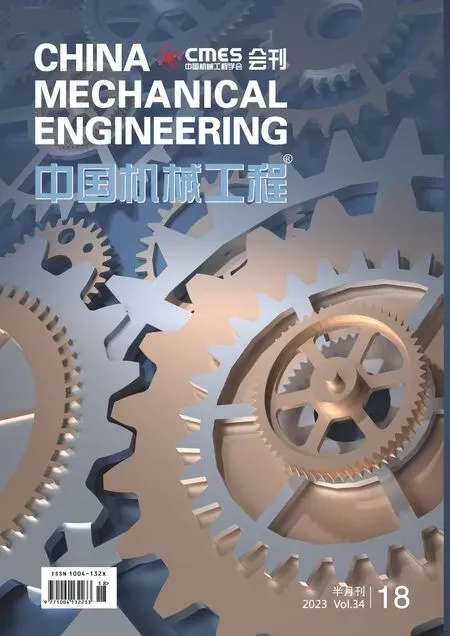負載條件下RV減速器動態傳動誤差分析與試驗
許立新 夏 晨 楊 博
1.重慶大學高端裝備機械傳動全國重點實驗室,重慶,4000442.重慶大學機械與運載工程學院,重慶,400044
0 引言
RV減速器因其具備高精度、高剛性和小體積、大速比等優異傳動性能,被廣泛應用于工業機器人、精密機床等智能機械裝備中。傳動精度是RV減速器最重要的性能指標,也是RV減速器產品在出廠前必須檢測并標識的關鍵性能參數。目前,RV減速器傳動精度的測試與評價是在空載條件下進行的,無法反映減速器在負載情況下的真實傳動精度性能。工程應用表明,隨著工作負載的施加,RV減速器傳動誤差將增大,遠遠超出產品出廠標稱指標,因此,如何考慮負載作用,揭示關鍵傳動件公差設計與RV減速器動態傳動誤差之間的映射規律,從而準確評估RV減速器傳動精度性能,是目前亟須解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難題。
近年來,眾多學者圍繞RV減速器傳動誤差建模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YANG等[1]建立了考慮多曲柄軸過約束傳動結構影響的RV減速器傳動誤差等價模型,模型中將關鍵傳動件制造誤差等效為桿長誤差模型,該模型的準確性得到了試驗驗證。基于靜力學理論,LI等[2]建立了考慮齒廓修形和輸出柱銷間隙影響的RV減速器擺線針齒傳動齒廓接觸分析(tooth contact analysis,TCA)模型,對擺線傳動靜態傳動誤差進行了分析。基于TCA分析模型,SHIH等[3]分析了齒廓修形和針齒銷位置度加工誤差對擺線傳動精度和回差特性的影響。LIN等[4]針對擺線傳動提出了一種新的運動誤差分析方法,該方法采用蒙特卡羅模型對傳動件公差設計進行優化,可以獲得擺線減速器較高的傳動精度。SUN等[5]提出了一種改進型TCA分析方法,并針對國產新型擺線減速器(China bearing reducer,CBR)進行了傳動誤差分析。考慮擺線齒輪制造誤差的影響,LI等[6]分析了RV減速器擺線針輪傳動特性,探討了擺線針輪嚙合接觸狀態與減速器傳動誤差之間的映射規律。針對RV減速器高精度裝配問題,CHU等[7]提出了基于遺傳算法的零部件精度選配設計方法并驗證了該匹配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李兵等[8]采用作用線增量法,建立了RV減速器傳動誤差分析模型,研究了各個構件的原始誤差對輸出轉角誤差的影響規律,揭示了各個構件原始誤差的傳遞過程。
上述研究主要基于運動學或靜力學理論研究RV減速器傳動誤差特性。在RV減速器動力學建模以及動態傳動誤差研究方面,韓林山等[9]綜合考慮各傳動零件的加工誤差、安裝誤差、配合間隙及齒輪嚙合剛度、軸承剛度等因素影響,建立了RV減速器的動態傳動精度計算模型,完成了RV減速器全局誤差敏感性分析[10]。鄭鈺馨等[11]采用集中質量法建立了五自由度純扭轉RV減速器動力學模型,分析了傳動系統在啟動和穩定過程中各部件的動態響應曲線以及整機傳動誤差頻譜圖。REN等[12]建立了RV減速器多自由度非線性動力學模型,研究了不同修形間隙下減速器轉角位移和轉速隨時間的變化規律。將多體動力學方法與有限元方法相結合,CAO等[13]提出了一種考慮剛柔耦合作用的RV減速器動力學分析方法,研究了幾何誤差與構件彈性變形之間的耦合效應對系統動態傳動精度的影響。在前期研究中,筆者基于接觸多體動力學理論,考慮多曲柄軸過約束傳動結構影響,建立了RV減速器擺線針輪傳動機構的參數化動力學模型,研究了擺線修形齒隙和滾針軸承間隙對傳動系統動態響應的影響[14]。
考慮輸出扭矩負載作用的RV減速器動態傳動精度分析必須依據動力學方法。基于前期研究,筆者提出建立兩曲柄軸標準型RV減速器接觸多體系統整機動力學模型,模型考慮漸開線齒輪傳動、擺線針輪傳動以及多組轉臂軸承和支承軸承動態子結構對傳動精度的影響。此外,給出了RV減速器關鍵傳動件如曲柄軸、擺線輪和針輪的幾何形狀誤差與加工位置度誤差表達方法。通過接觸多體動力學分析,探討了負載扭矩變化對RV減速器動態傳動誤差的影響規律。最后,通過試驗對動力學模型的精度以及分析結果的準確性進行了驗證。
1 RV減速器接觸多體動力學建模
1.1 RV減速器整機動力學建模架構設計
RV減速器傳動原理如圖1a所示,以兩曲柄軸標準型RV減速器為對象,在多體系統動力學理論框架下,建立其整機動力學模型架構如圖1b所示。建模過程中完整地考慮了RV減速器第一級漸開線齒輪傳動和第二級擺線針輪傳動子結構,同時考慮了多組轉臂軸承和支承軸承的影響。模型中,假設行星齒輪與所在曲柄軸為同一個運動構件,輸出盤與壓緊盤為同一個運動構件(又稱為輸出行星架)。傳動系統中共包括六個運動剛體,分別是一個輸入齒輪軸、兩組行星齒輪與曲柄軸組件、兩片擺線輪和一個輸出盤與壓緊盤組件。圖1b中,ωp表示輸入齒輪軸轉速,ωg表示行星齒輪轉速,ωo表示輸出盤轉速,Tload表示減速器負載扭矩。

(a)RV減速器傳動原理 (b)RV減速器動力學建模圖1 RV減速器傳動原理及其動力學建模架構設計Fig.1 Transmission principle and dynamic modelling architecture design of RV reducer
傳動系統廣義坐標共18個,具體表示為
(1)

系統質量矩陣可以表示為
Μ=diag(mp,mp,Ip,mg,mg,Ig,mg,mg,Ig,mc,mc,Ic,mc,mc,Ic,mo,mo,Io)
(2)
式中,mp、Ip分別為輸入齒輪軸的質量和轉動慣量;mg、Ig分別為行星齒輪與曲柄軸組件的質量和轉動慣量;mc、Ic分別為擺線輪的質量和轉動慣量;mo、Io分別為輸出盤與壓緊盤組件的質量和轉動慣量。
系統約束方程可以表示為
(3)
式中,t為時間。
上述約束方程的作用在于保證減速器的輸入齒輪軸和輸出行星架僅保留回轉自由度,同時約束輸入齒輪軸以ωp勻速轉動。系統中其他各傳動構件的運動特性將由構件彼此之間的動態接觸特性決定。
傳動系統的動力學方程可以表示為
(4)

1.2 第一級漸開線齒輪傳動部分接觸建模


圖2 RV減速器漸開線齒輪傳動建模Fig.2 Involute gear transmission modeling of RV reducer

(5)
式中,R′A,BP為與行星輪A和行星輪B分別嚙合時的主動輪節圓半徑;Zp為主動輪齒數;s′A,Bp、s′A,Bg分別為主從動齒輪的節圓齒厚;bo為初始齒側間隙;α′A,B為嚙合角。
嚙合角與實際中心距之間的函數關系可表示為
(6)
式中,a為齒輪理想中心距;a′A,B為行星輪A和行星輪B實際中心距;α為標準壓力角。
由式(5)和式(6)可得齒輪副動態齒側間隙表達式為
(7)
式中,inv(·)為漸開線函數。
齒輪嚙合線方向上的相對位移可表示為
(8)

(9)

(10)
式中,km為平均嚙合剛度;ka為時變嚙合剛度幅值;ωm為齒輪嚙合頻率;φA,B為變剛度初始相位角。
(11)
式中,Cm為嚙合阻尼給定值;d0、d1為接觸深度臨界值,d1>d0。
齒輪副動態接觸嚙合力可采用下式計算[15]:
(12)

1.3 第二級擺線針輪傳動部分接觸建模


圖3 擺線針輪接觸分析模型Fig.3 Contact analysis model of cycloidal pinwheel
(13)

擺線輪齒廓與各個針齒銷中心之間的相對位置矢量可以表示為
(14)
式中,j為針齒銷序號。
在動力學計算中,將式(14)執行i×j次循環計算,即可完成某一瞬時下擺線輪與針輪之間的接觸分析。
擺線齒廓與各個針齒銷是否形成接觸的判定條件為
(15)
式中,rrp為針齒銷半徑。
形成接觸后,彈性接觸變形可以采用下式計算:
(16)

對應各個針齒銷,接觸線方向單位法矢量可以表示為
(17)
在接觸線作用方向,擺線齒廓與針齒銷相對法向速度可計算為
(18)

針齒銷與擺線齒廓之間的接觸力可以采用下式計算[14]:
(19)
式中,Kpc為擺線針齒銷接觸剛度;Cpc為擺線針齒銷接觸阻尼;cc為阻尼調節系數。
受擺線齒廓曲率半徑變化影響,針齒銷與擺線齒廓接觸位置不同,接觸剛度大小會有所不同。為簡化計算,模型中將擺線針齒銷接觸剛度設為常數,其值由擺線平均曲率半徑基于Hertz接觸公式計算得到。
此外,阻尼調節系數的主要作用是保證接觸分析過程的穩定性,其表達式如下:
(20)
式中,δ0、δ1為接觸深度臨界值,δ1>δ0。
1.4 轉臂軸承與支承軸承部分接觸建模
RV減速器中轉臂軸承為滾針軸承,支承軸承為圓錐滾子軸承。由于所采用的非標準圓錐滾子軸承接觸角較小,因此建模中僅考慮圓錐滾子軸承的徑向支承作用,同時將圓錐滾子軸承的軸向預緊量根據接觸角大小轉化為徑向預緊量。以擺線輪a中的一組轉臂軸承和支承軸承為例,轉臂軸承接觸建模如圖4所示,支承軸承接觸建模如圖5所示。

圖4 轉臂軸承接觸建模Fig.4 Arm bearing contact modeling

圖5 支承軸承接觸建模Fig.5 Supporting bearing contact modeling
針對轉臂軸承接觸建模,首先將曲柄軸偏心外圓柱面和擺線輪軸承孔內圓柱面視為軸承滾動體內外滾道。在廣義坐標系OXY下,軸承內外滾道幾何中心Pc和Pn的位置矢量可以表示為
(21)
(22)

(23)

受間隙與彈性變形的影響,轉臂軸承受力后內外滾道幾何中心之間的相對偏心矢量可表示為
(24)
式(24)對時間求導,可得相對偏心速度矢量
(25)
軸承偏心距離可采用下式計算:
(26)
假設各滾動體在軸承套圈內均勻分布且同步轉動,則滾動體公轉角速度可采用下式計算:
(27)
式中,Rn、Rc分別為轉臂軸承內外滾道半徑;ωin、ωout分別為軸承內外滾道角速度,由曲柄軸和擺線輪角速度決定。
在軸承回轉過程中,各個滾動體的轉角位置可確定為
(28)

軸承內部各個滾動體在不同位置處的徑向偏移可以采用下式計算
(29)

各滾動體在其相位方向上的相對偏心速度可以表示為
(30)

在不考慮徑向游隙條件下,軸承各滾動體與滾道之間的法向接觸力可以表示為[14]
(31)
式中,Kb、Cb分別為滾動體與滾道之間的接觸總剛度和阻尼。
支承軸承的接觸建模過程與上述轉臂軸承類似,不同之處在于支承軸承需要考慮預緊作用。如圖5所示,在廣義坐標系下,支承軸承內外滾道幾何中心Pg和Po的位置矢量可以表示為
(32)
(33)
式中,ro為輸出盤與壓緊盤組件局部坐標系原點在廣義坐標系下的位置矢量;so為支承軸承外滾道幾何中心在輸出盤與壓緊盤組件局部坐標系下的位置矢量;Ao為坐標轉換矩陣,用于描述輸出盤與壓緊盤組件局部坐標系在廣義坐標系下的方位。
支承軸承內外滾道幾何中心之間的相對偏心矢量可表示為
(34)
軸承內部各個滾動體在不同位置處的徑向偏移可以采用下式計算
(35)

考慮軸承預緊影響,在式(31)基礎上,支承軸承各滾動體與滾道之間的法向接觸力可以表示為
(36)

2 關鍵傳動件誤差建模
根據工程制造經驗,曲柄軸、擺線輪和針輪的加工制造精度是影響RV減速器傳動精度性能的關鍵,因此,建模中將考慮上述關鍵傳動件主要幾何形狀與位置度誤差影響。
2.1 曲柄軸形位誤差表達方法


圖6 曲柄軸形位誤差建模Fig.6 Crank shaft position error modeling
(37)

理想情況下,曲柄軸兩個偏心圓的偏心距相等且相位角相差180°,考慮位置度誤差后,偏心距大小及相位角可以采用下式確定:
(38)
(39)

2.2 擺線輪軸承孔形位誤差表達方法


圖7 擺線輪軸承孔形位誤差建模Fig.7 Modeling of bore position error of cycloidal wheel bearings
(40)

理想情況下,擺線輪兩個軸承孔分布圓半徑相等且相位角相差180°,考慮位置度誤差后,分布圓半徑大小及相位角可以采用下式確定:
(41)
(42)

擺線齒廓也存在加工誤差,這種齒形誤差難以精確表達。此外,在工程設計中,也需要擺線齒與針齒銷之間形成合理的齒側間隙,以便于裝配與潤滑。考慮到這些影響,擺線輪將采用正等距修形方法進行修形,從而對齒形誤差與齒側間隙進行簡化模擬。
2.3 針輪形位誤差表達方法
針輪形位誤差將考慮各個針齒銷半徑誤差和針齒銷位置度誤差,如圖8所示。理想情況下各個針齒銷半徑相同為rrb,計入加工隨機誤差后,各個針齒銷實際半徑將不同。采用隨機函數表達各個針齒銷實際半徑大小為

圖8 針輪形位誤差建模Fig.8 Pinwheel shape error modeling
(43)

理想情況下各個針齒銷位于同一個分布圓上,分布圓半徑為rb,計入加工隨機誤差后,各個針齒銷分布徑向距離將不同。采用隨機函數表達各個針齒銷位置誤差:
(44)
(45)
3 算例分析、討論與驗證
3.1 RV20E模型參數
以工業機器人兩曲柄軸標準型RV20E減速器(圖1)為分析對象,該減速器傳動比為121,其幾何結構設計參數如表1所示,傳動構件質量慣性參數如表2所示,關鍵傳動件公差設計參數如表3所示,動力學分析參數如表4所示。此外,設定漸開線齒輪初始齒側間隙為2 μm,擺線等距修形量為2 μm。

表1 零部件幾何結構設計參數

表2 傳動構件質量慣性參數

表3 傳動構件公差設計參數

表4 動力學計算參數
3.2 動態傳動誤差計算
通過動力學計算,可以得到減速器輸入端和輸出端轉角θp和θo的變化規律,結合減速器傳動比ireducer,計算減速器傳動誤差:
ε=θp/ireducer-θo
(46)
通過修改負載扭矩Tload的取值大小,能夠得到不同扭矩負載條件下的減速器動態傳動誤差變化規律。
圖9和圖10分別給出了空載條件下減速器動態傳動誤差時域與頻域響應曲線。可以發現,在空載情況下減速器最大傳動誤差為57.5″,誤差曲線周期性波動非常明顯,在頻率比為40附近,誤差幅值貢獻量最大。傳動誤差的頻率用f表示,fo表示輸出法蘭盤的旋轉頻率,頻率比f/fo代表了輸出法蘭每轉一圈的傳動誤差變化量。圖11和圖12分別給出了在額定負載扭矩(167 N·m)條件下減速器動態傳動誤差時域與頻域響應曲線,此時,傳動誤差最大值達到99.52″。顯然,考慮額定負載作用后,減速器傳動誤差顯著增大,相比于空載情況,額定情況下的最大傳動誤差增幅為73.1%。進一步分析,在空載情況下,減速器傳動件之間的接觸力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導致傳動誤差的因素只能是因公差配合和擺線修形引入的傳動界面間隙。而在負載情況下,除了受上述因素影響外,零件傳力界面之間的彈性變形量將不能忽視。此外,由于漸開線齒輪傳動部分位于減速器高速級,它對減速器輸出誤差影響非常有限,且分析中未考慮齒輪齒形幾何誤差的影響,因此在頻域分析中觀察不到齒輪傳動對減速器輸出誤差的影響。

圖9 空載條件下傳動誤差時域分析Fig.9 Time domain analysis of transmission error under no-load conditions

圖10 空載條件下傳動誤差頻域分析Fig.10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of transmission error under no-load conditions

圖11 額定負載條件下傳動誤差時域分析Fig.11 Time domain analysis of transmission error under rated load conditions

圖12 額定負載條件下傳動誤差頻域分析Fig.12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of transmission error under rated load conditions
受機器人運動工況影響,RV減速器經常工作在變負載情況下,為探明負載變化對減速器傳動誤差幅值的影響,對不同負載作用下的減速器最大傳動誤差值進行了統計,如圖13所示。在0.2To(To為額定扭矩)條件下,減速器傳動誤差幅值為72.09″;在0.4To條件下,減速器傳動誤差幅值為82.59″;在0.6To條件下,減速器傳動誤差幅值為88.99″;在0.8To條件下,減速器傳動誤差幅值為95.42″。總體表現出,隨著負載扭矩的不斷增大,減速器傳動誤差幅值隨之增大,但幅值增長率卻在下降。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隨著負載的增大,減速器傳動零件接觸界面之間的彈性接觸變形隨之增大,從而引起傳動誤差的逐漸增大。隨著負載扭矩的增大,傳動零件之間將逐漸克服配合間隙,傳動零件之間的有效接觸點逐漸增多,減速器整機扭轉剛度逐漸增大,因此隨著扭矩的線性增大,接觸彈性變形量并非線性增大,導致減速器傳動誤差幅值增長率逐漸降低。

圖13 不同負載扭矩條件下傳動誤差幅值變化Fig.13 Change of transmission error amplitude under different load torque conditions
3.3 動態傳動誤差試驗
RV減速器傳動精度測試試驗臺如圖14所示,包括驅動裝置、被測RV減速器、測量裝置及加載裝置。驅動電機為減速器提供動力,中間是被測試RV20E減速器,測量裝置主要包括輸入端與輸出端的角度編碼器以及數據采集設備,采用力矩電機作為加載裝置,各部分之間用聯軸器連接。該測試試驗臺的主要性能參數詳見表5。

表5 試驗臺參數

圖14 RV減速器傳動精度測試試驗臺Fig.14 RV reducer transmission accuracy test bench
圖15和圖16分別給出了空載條件下減速器動態傳動誤差測試曲線及其頻域分析結果。測試結果表明,該減速器空載條件下最大傳動誤差為69.34″,同樣在頻率比40附近,誤差幅值貢獻量最大。圖17和圖18分別給出了加載額定扭矩后減速器動態傳動誤差測試曲線及其頻域分析結果。此時,傳動誤差最大值達到110.25″,相比于空載情況,最大傳動誤差增幅為58.9%。此外,加載額定扭矩后,傳動誤差在頻率比80附近誤差幅值貢獻量最大。需要指出的是,減速器傳動誤差測試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受試驗臺本身裝配精度、檢測精度和系統剛性的影響,因此誤差幅值將比理論分析值略大,但基于時域與頻域測試結果所反映出的傳動誤差變化特性與理論計算結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足以驗證理論模型的有效性。

圖15 空載條件下傳動誤差時域測試結果Fig.15 Time domain test results of transmission error under no-load conditions

圖16 空載條件下傳動誤差頻域分析結果Fig.16 Transmission error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results under no-load conditions

圖17 額定扭矩條件下傳動誤差時域測試結果Fig.17 Time domain test results of transmission error under rated torque

圖18 額定扭矩條件下傳動誤差頻域分析結果Fig.18 Transmission error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results under rated torque
4 結論
(1)針對扭矩負載作用下RV減速器動態傳動誤差分析問題,考慮關鍵傳動件幾何形狀與位置度多源誤差影響,建立了兩曲柄軸標準型RV減速器動力學模型,模型中考慮了漸開線齒輪傳動、擺線針輪傳動以及多組轉臂軸承和支承軸承動態子結構的影響,深入探討了扭矩負載作用下減速器動態傳動誤差特性。
(2)基于理論模型得到空載情況下減速器最大傳動誤差為57.5″,額定扭矩情況下最大傳動誤差達到99.52″,傳動誤差增幅為73.1%。隨著負載扭矩的不斷增大,減速器傳動誤差幅值隨之增大,但幅值增長率卻在逐漸下降。
(3)基于試驗測試得到空載情況下減速器最大傳動誤差為69.34″,額定扭矩下最大傳動誤差達到110.25″,傳動誤差增幅為58.9%。基于時域與頻域測試結果所反映出的傳動誤差變化特性與理論計算結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