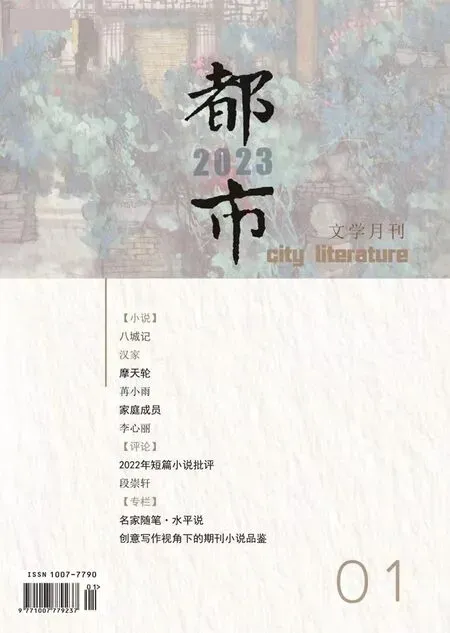靜謐的謎語
文 陳思諺
1
此地民居慣帶天井,在一樓用鐵柵欄圍起一塊小小園地,有些人家在欄上開一扇門,與天井外的綠化帶連通,稍加整理,鋪上鵝卵石小路,里外一起設計成一個小花園。
也有人在綠化帶的草坪上支起晾衣桿,天氣好的時候晾曬潔凈的衣物,這時候天井就可以當作洗衣房,很有趣味。另一些天井干脆開起店來做生意,理發(fā)店、收發(fā)快遞、小賣部,或者搭成一間小小的茶室,常見到有人在里頭打牌,一問,原來是房產中介的辦公室。我還見到有賣雜糧煎餅的,細煙和香氣從天井處飄出來,攤主一早出來,賣到十點半收攤兒。更常見的處置方法是干脆拿磚砌起來,加個隔熱頂,置辦上一些廉價家私,當作正常的房間出租給謀生的年輕人,平常屋子里只有三四個房間可供出租,如果加上天井改造出來的兩個,可以租出去六個房間。這當然是違規(guī)的,但是如此坐享其成之法,還是誘惑了不少房東。
住進這處房東用天井改造成的一室戶時,我正站在生活的路口,羈旅疲憊,行囊沉重。工作三四年,所得甚少,只養(yǎng)成花錢的習慣,又生疾病,住院、手術、療養(yǎng)種種下來,好長一段時間我都不敢打開銀行卡軟件頁面看一眼余額。與曾經的戀人分開半年有余,仍舊少歡暢,多憂愁,一個人在上海,每每黃昏日落,看見家家窗戶亮起燈來,心腸就像被揉成一團的宣紙,皺巴巴的,勉強展開了還不如團著。
正是這樣的當口,原本一起合租的室友決定離開這個城市,我必須重新規(guī)劃住所。說來慚愧,我在生活事務上長期習慣依賴別人,說是獨立生活,其實總是得到別人的幫助,住的房子是室友找的,搬家是戀人幫忙的,連過冬的羊毛被都是上班地方的領導幫忙買的,在那之前,我連“天冷了可以換被子”都不知道,一個勁兒地喊冷。如果離開了各路好心人,我的日子指不定要過成怎樣的一團亂麻。這一回我決心打起精神來,重新建立我的生活。尋尋覓覓,最后租下這個天井改造的房間時,與其說欠考慮,不如說是故意的,貪它看起來有意思。朋友朝我翻白眼,講了不少住天井的壞處,一問價錢,更是覺得我腦子肯定不好使。無奈我就是被鬼迷了心竅,非要住下不可。想來我生活中的許多決定都是如此,糊糊涂涂,卻莫名堅定,盡做些不經濟的事情。
在一個春天,我就這樣糊里糊涂地抱著一肚子破碎心腸搬進了這個天井違規(guī)改造房。隨之而來的,當然是朋友向我預言的無盡麻煩,與一些偶得的趣味。
住在天井第一頭疼的地方就是潮濕,江南地區(qū)的一樓,就算是朝南透氣的房間也難以擺脫濕氣纏繞的煩惱。尤其到了淫雨霏霏的黃梅時節(jié),一不留神,墻上、家具上就會結上淡淡的霉斑。我那些皮包悄無聲息地長滿灰白的霉點,我拿酒精濕巾去擦,想著可以消毒,誰知過幾天皮子就起了碎屑,破損了,我一籌莫展地瞧著他們,不愿去想為它們花過的鈔票。更不用提我費了大價錢、大工夫搬進來的幾箱子書。居室拮據,搬進來之后一直委屈它們待在箱子里,突然有一天發(fā)現(xiàn)有棕色的靈活小蟲從箱子里鉆出來,嚇了我好大一跳,鼓足了勇氣才敢打開箱子查看,蟲子倒沒看見,只是翻開書頁,果然這里也難幸免于霉菌的侵害。若學古人曬書倒是雅事,只是梅雨連綿不見晴天,這幾箱子書,成了負擔墜在我心頭。看來,讀書固然是再民生不過的事了,但是買書藏書卻屬于貴族行徑,需要居室寬敞,有人有閑來管理,才不至于浪費辜負。
不過潮濕天氣也有好處,潤物細無聲。在濕潤的空氣中,日光流淌得也緩慢些,春天因而十分確鑿。落地窗外的植物漸漸豐滿,碧色由淡漸濃,好像擁有私人庭院,“細雨濕流光”之景唾手可得,再漸漸,淹沒了我的窗口。玉蘭、矮櫻默默地抽枝拔條,開出繁盛的花,煙雨里吐露光芒,繡球不知不覺攢出新的花苞,讓人心生期待。
意外的“訪客”也叫人頭疼。經常是晚上下班回來一開燈,地上橫著一條胖乎乎的鼻涕蟲,正慢慢地路過,長得是一副蝸牛拋棄了殼的模樣,有兩個小觸角。看起來還算溫和無害,翻著白眼拿紙巾把它捏出去就是了。有時候也能看見蜘蛛,第一次見到的時候差點嚇死我,黑乎乎地趴在墻上,這種我是看都不敢細看的,更別說怎么對付它了。只能反復安慰自己,家里來蜘蛛是喜兆。不是有那種說法的嘛,晚上在家里看見蜘蛛,明天就會有客人來訪。古人膽大包天,居然非常歡迎蜘蛛來訪,稱它們?yōu)椤跋沧印保呦Φ臅r候還要捉小蜘蛛放在盒子里,第二天去看誰家蜘蛛網結得好。唐代的時候是看哪個網結得多結得密,到了宋時,好像就是看網的形狀了。
《東京夢華錄》里有一段:“七月婦女望月穿針:或以小蜘蛛安盒子內,次日看之,若網圓正,謂之‘得巧’。”我雖做不來這樣的風雅事,但也不好不解風情地將它殘忍打死(也是不敢),只好低聲下氣,恭迎恭送,試圖與之和善相處。漸漸發(fā)展出一些“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智慧來,在一些我與蜘蛛沉默相對的夜晚,我總是想,如果我對別的不如意不歡迎之事也像對待這八腳客人一般,是不是會少很多無謂的煩惱?
天氣晴好的時候外面已經是一副草木深深的做派了,草坪長成了草叢,昆蟲藏在里面,因此收獲了蟲鳴之夜,蟲鳴使對面人家窗口的燈光更有意味了,仿佛回到小時候,夜晚寄宿在農村外婆家,暗野中蟲鳴四起,夜風中竹濤陣陣,望著若隱若現(xiàn)的燈火,我總是覺得這樣的夜里醞釀著什么故事,就在那些窗口里、燈火中。黎明的時候聽到外面機器聲嗡嗡作響,拉開窗簾一看,是修剪草坪的工人,青草汁液的氣味撲面而來,嗡嗡一陣過后,又是嶄新的草坪。早開的花落英紛紛,繡球則日漸飽滿,風景令人貪看。
夏日漸深之時處處浸在秾綠之中,花事不如春季繁盛,但四下葳蕤生光。雨一停,日頭高懸,一切明晰可見,紋理昭然。閑下來的時候突然發(fā)現(xiàn)一叢叢的綠色之中突然迸出點點白花,繼而開成燦燦的一片。據園藝工人說這是大花六道木,花期很長,可以一直開到入冬。
小區(qū)里的貓有時候會來探望。這里的貓?zhí)嗔耍乙膊挥浀迷囊恢淮蜻^招呼,反正就是有一只兩只的,熟門熟路地經過我窗前的園地,遇上我在窗邊的時候會停下來行一會兒注目禮,不知道是想打招呼還是想瞪我。貓的心情真是難以捉摸。
更多的是蚊子,我第一次發(fā)現(xiàn)蚊子還有這么多種類,有苗條腳長的、長著花斑的、其貌不揚的,還有細細小小成群結隊的,從前課文里寫“夏蚊成雷,私擬作群鶴舞于空中”,我沒有這種童真心境,只能一邊苦苦裝紗窗,一邊埋怨不知道躲在哪個角落里的蜘蛛室友,為何不勤勞捕獵,當作交租?
雨夜是很快樂的。屋頂是用空心的隔熱材料搭成的,雨點落在上面敲出很清脆的聲音,綿密不止,毛毛雨聽起來像羽毛瘙癢,雨大了就像磅礴的鋼琴聲從巨大的琴腔里發(fā)出來,無休無止連成一片。讀書讀到人家形容大鋼琴曲“如同群馬踏過鐵皮屋頂”,不住點頭。小鳥來訪時也有聲響,是與雨聲不同的咚咚聲,有時候咚咚咚地跳著落到窗前來,能看見它的真面目,我見過一只,有身材高大的男生的手掌那么大,青灰色的身軀上飾以白色的羽毛,非常漂亮,落到草地上踱幾步打個抖,側頭看我一眼,展開翅膀走了。
2
從我的房間開門出去,是晾衣服的公共區(qū),搭著透明的屋頂,追著小鳥的腳步聲抬著頭出來的話,能看見它竹葉似的腳一下一下地印在屋頂上,也很有趣味。對面是另一個房間,租住著一位年輕人。我上班時間與他錯開,少有見面的時候,偶爾見到,他也是沉默寡言。他總是背著個碩大的電腦包,附近有著名的互聯(lián)網公司,公司建筑極具科幻色彩,兩座樓體凌空而起,半空相會,仿佛時空通道。我猜想他是那里的員工,在那半空中的建筑里,一個一個亮亮的小格子里,有一個他的位置,他白天在那里敲電腦,夜晚回到這個天井。在我忙著晾衣服、掃地、曬書的日子里,對面總是緊閉門扉,如同一道沉默的風景,和四周的植物沒什么兩樣,久而久之,我放下戒心,總是開著房門,以此來拓寬我的領地。
在這所房子里,還住著好幾個人,但每一扇門都像石壁一樣堅硬無言,我像是這片王國唯一的居民。開門進來,穿過陰涼的走廊,經過每一扇房門,拐彎穿過房間縫隙,才來得到天井,我總覺得自己隱居在山洞里,外面是平常的樓房街道,充滿人間事務,洞中則別有一方小小天地,雖然逼仄拮據,卻也剛好可以躲藏此身。
第一個與我搭話的鄰居是隔墻的女孩。那會兒我正肆無忌憚地開著門,躺在床上煲著電話粥,突然探出來一個腦袋,皺著眉提醒我夜晚已深。我的山洞隱居幻想一下子被打破,此處盡管僻靜,卻不是無人,那些門后面、墻后面,另有一些生活在按照自己的節(jié)奏進行。這并不使我煩憂,反而撫平我心中某處的寂寞。我感到自己像一枚琴鍵,安靜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旁邊是別的琴鍵,我們看起來一模一樣,卻擁有不同的聲音。身處在一首樂曲中間,成為流動的聲音中的一個音節(jié),使我安心。
自從注意到隔墻的女孩,她的存在就越來越鮮明。我能聽到那邊細碎的聲響,有時候還能聞到熱氣蒸發(fā)沐浴露那種特有的氣味,我們在晾衣區(qū)的相遇也多了起來。漸漸地我知道了一些她的事情。她比我小一歲,在這附近的日企上班,出租屋條件有限,她仍然嘗試自炊帶飯,在狹窄的洗手間小心地洗干凈肉和菜,唯一的桌子既當書桌又當料理臺,切完食材倒進電飯煲之后再把桌面擦干凈。她與我分享了不少簡便的電飯煲食譜,有一道南瓜雞塊燴飯,確實方便美味,離開天井好久之后,我才想起來試試,可惜沒機會與她分享心情。她有一個戀人在軍中,偶爾休假過來,是一個高大黝黑的男孩,她帶他騎著電動車去吃宵夜到深夜才回來,那會兒是她房中少有的喧鬧時刻,音樂聲和笑聲人語一直起起伏伏,直到黎明。
但這樣的時刻是很少的,大部分時候她非常安靜,是一位時刻約束自己言行的好鄰居,連晾衣服也絕不越界,常令我慚愧。我總是越界,我的衣服、鞋子、書,總是占據著公共區(qū)域的位置,她一直包容我,我老去找她,屋里有蟑螂啦,墻面有裂痕啦,洗衣機壞了啦,她不厭其煩地向我施以援手。秋天來的時候,她失戀了。那男孩眼看著就要退伍,卻說家中另有一個女孩,與他的未來計劃更加符合。這理由真是無懈可擊,一個獨自在大城市漂泊,容身于狹窄的出租屋里的女孩,她所有的優(yōu)點,包容堅定獨立種種,對他的未來生活其實意義不大。她使盡渾身解數,在洗手間和書桌間烹制的電飯煲料理,她所營造的那些,騎著電動車穿越夜色去吃宵夜的夜晚,播放音樂笑鬧到天亮的夜晚,悄聲講電話舍不得睡覺的夜晚,確實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個房間像貝殼一樣容納著那些夜晚,這城市隱秘的歷史只在這些貝殼的張張合合間吐露。一個音節(jié)融入樂曲之后,仿佛無聲。
琪琪是后來搬進來的,住在房子最深處。她長著一張圓臉,眼睛周圍種植著粗黑的假睫毛,小扇子一般撲閃撲閃。她是個安徽人,這個小區(qū)的外來者里約有一半來自安徽,我們總開玩笑,“上海是安徽的后花園”。琪琪在美甲店工作,美甲師們的手總是很晶瑩很柔潤,她們雖然用手勞動,但是這雙手卻是她們全身上下看起來最遠離生活塵土的部分。琪琪嫌棄我的手糙,不知道保養(yǎng),也不涂油彩,她給我涂抹護手霜的時候撫摸著我的甲床感嘆,這樣好的形狀,留長了貼上水鉆不知多好看,女孩子要對自己好一點,手是女孩子的第二張臉,繭子死皮,倒刺豎棱,一概不能有,命好的女人手都珍貴。從她手心傳來的柔滑觸感令我有些自慚形穢。
有一回,琪琪的母親從老家過來,寄居在她的房間里。像所有的母親一樣,她一來,就洗了大堆的衣服被子,堆堆疊疊地晾在天井,我一打開門就嚇了一跳,我的門口變成了染坊晾曬池似的,布料遮天蔽日,參差垂墜,那個正忙活著的黝黑瘦小的中年婦女見我出來,有些討好地朝我笑笑。下午琪琪帶她出去“逛逛上海”,回來的時候聽到她抱怨上海人太多啦,路太窄啦,樓房太舊啦,這讓我想起我的媽媽,她一直想看看我現(xiàn)在住的地方,我一直不敢,視頻的時候都要先找好角度。琪琪和她母親在我門口聊天,“媽,快收一些回去,占太多地方啦!”“怕什么,人家也沒說什么。”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象著,在這樣狹小的空間里,琪琪和她媽媽是如何擠在小床上入睡的,睡前在聊著這令人失望的上海嗎?也許更多的時候是沉默的,小房間容不下太多的對話。她媽媽拿抹布把到處擦得干干凈凈的時候,把椅子上堆著的女兒沒有閑暇和精力料理的大堆衣服和床單收拾起來丟進洗衣機的時候,懷抱著怎樣的心情?我又想,如果是我的媽媽呢?恐怕這居所中的一切都要令她傷心的,上海的一切都要令她傷心的,在一座偉大的城市做一個觀光者固然新奇有趣,還可以目光挑剔,但在她身邊手足無措得像站錯了地方,卻是令人傷心的。琪琪媽媽在這里待了一個星期,她走后,琪琪看起來比加班到深夜回來的時候還要累,但她仍邀我去她房間做指甲。她將各式工具一一擺開,身處在它們中間,她露出主人般的驕傲,她的一雙手,十指蔥蔥,柔滑如脂,如同某種理想生活的模型,從所有的疲憊和失望中延伸出來,凝聚著所有的希冀和想望。
3
門前有一條河,橫穿過這個小區(qū)。我時常對這條河心懷感激。她光耀如練,岸邊花木豐盛繁美,木槿映襯著垂柳,還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水草,層層堆疊。穿過陰暗的走廊,盡頭竟有這樣一條河等待著我,簡直如同小小的神跡。那年春天雨季很長,綿綿的雨籠罩著她,巨大的老樹把那沉沉的影子投向她,淡薄的波光與如錦繁花交織出一個憂郁的故事,使我長久地躑躅在她身旁。到了夏季,一切晴朗起來,一切變得很深,夏季就是這樣的,既清晰又神秘,河流在深深草木間閃著光,萬物如同坦白的謎題。河邊有人垂釣。太陽西偏的時候就有人來了,一直到夜深人靜也還有人舍不得走,在岸邊點一盞燈,一盤蚊香,長長久久地靜坐。或許那就是想要解謎的人。
我認識其中的一個兩個。常坐在北岸十三棟門口的那位陳叔是我們房東的丈夫,他的妻子是一位女王一般的人物,潑辣又狡猾。二十多年前他們剛來到上海的時候,她不顧勸阻從老家借了錢在這個小區(qū)買了好幾處房子,如今每個房子都被改造成群居“洞穴”,她每天嘩啦啦地帶著一大串鑰匙,逡巡在她的“領土”上。陳叔坐在他妻子的辦公室——那間供房產中介們休息來往的茶室里的時候,一問三不知,這個過分普通的男人,像無數人到中年的男人一樣,被自己的無能擊敗而不再驚訝,安于平穩(wěn)的溫和中帶著一絲垂頭喪氣。但當他坐在河邊的時候,仿佛搖身一變,變成了不出世的哲學家、高僧、武林高手,那些無能為力的事情統(tǒng)統(tǒng)在眉目不驚的等待中得到了和解。
另一位河邊常客是獨居的蘇爺爺。他就住在我們對面,出出入入間,常有微笑言語。老人家的生活極其規(guī)律,我九點多出門的時候正好是他散步買菜回來的時候。到了下午四點多,他就會慢吞吞地帶著一整套家伙,到河邊去坐上兩個多小時,他的動作里帶著一種有條有理的緩慢,令人安心。他的妻子幾年前去世了,兒子常年在國外,人生的暮年,他每天就這樣安靜地度過。那段時間,我剛從病中痊愈,推掉了很多工作,時日閑散,常常往圖書館跑,傍晚的時候坐在戶外長椅上讀書,眼前就是河流,蘇爺爺坐在岸邊。波光水影中,他的背影也微微蕩漾起來。
這個小區(qū),這個小小的人類聚居地,這里流動著的生活里潛伏著一個重要的主題。它有時候以“孤獨”之名示人,有時候又使人感到“徒勞”,它還有個名字似乎是叫“荒謬”,它是一道靜謐的謎語。每個人用自己的方法與它周旋,它卻如影隨形,越是對抗越是強烈。在房東阿姨叮當作響的鑰匙串中,在深夜河邊的點點燈光里,在一個個狹窄的居室里,在匆忙開著電動車路過的房產中介們身上,甚至是在那些茶室的牌局里,它展露神秘的微笑。我抬頭望著河水旁垂釣的背影時,仿佛看到它坐在蘇爺爺的身旁,微微蕩漾。在諸種與之周旋的方法之中,也許蘇爺爺找到了一條自己的道路,我愿意這樣相信。一種節(jié)制的、規(guī)律的生活,一種把它請到身邊平靜共處的生活,當然還不足以解決它,但是在這種生活的深處包含著一種尊嚴,一種人棲身于萬物之間應當擁有的尊嚴。
人有多少無能之事?又有多少可能之事?樂曲無時無刻不在流動,我感到那靜謐的謎語輕輕地撫摸著我的發(fā)膚,暮色從遠處降臨,草坪上有層毛茸茸的金光,低頭讀到宮澤賢治的句子:即使沒有足夠的冰糖,我們也能夠品嘗純凈透明的清風和桃紅色的美麗晨光。為了擁有更多的快樂,我決定明天早上起得早一點,去品嘗桃紅色的美麗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