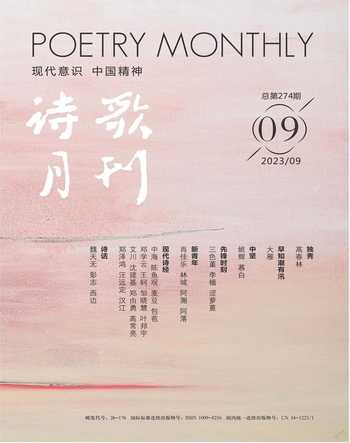詩,被靈光一閃的詞語所照亮(創作談)
高春林
詩是什么?似乎從來就未有一個定義。作為一個詩人,一定要給的話,要給出語言的形象。孔子曰“詩言志”,以及對《詩經》那個概述“詩無邪”。這幾乎就是說,詩是對內心情感與世界認知的一種修辭學。漢字的出現意味著詩的出現——人類從蠻荒時代開始走向文明,人們開始了一個內在的喚醒——人類之初的本能欲念就是走出黑暗、走向光明。如此說也就回到了“本源”的藝術——形象、淳樸、本質。海德格爾說,藝術是本質的詩。事實上,詩就是最本質的語言。這是一種靈光——一種異己的神秘力量,帶來了靈光閃現的一個瞬間,由此建構了詩的生命。
詩歌的“靈光一閃”是如何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呢?帕斯也曾發出過這樣的疑問。在中國,《詩大序》中說:“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是最初的記憶,也為一種精神存在——在詩人發出聲音的這一刻,我們的精神有了另外的向往、意志以及由此生發出天地間的一縷光輝。最初的詩歌或許就是語言的啟蒙,是人與詞之間的彼此喚醒。
當代詩的語言,也即我們生活的經驗。詩歌是一種本源的藝術,詩歌也是再造的語言。這里的二元論在于,一方面詩歌的藝術在指向本源的藝術,即它的語言在指向并揭示事物本質的時候,是指向世界的本質也是歷史的本質,這正是詩之為詩的一個前提和終極所在。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為詩而求索的——語言的創造,這幾乎是所有擁有詩歌意志的人的一個行動方向,當我們在日常的生活中,一些事物或事件會突然呈現在面前,那種模糊的事物甚至是如此鮮明又可疑,我們的眼睛在最初的發現之時或許是漫不經心的,我們會誤認為這不過是一些事物以及由事物組成的意象群,但我們說出這事物的含義的時候,語言便回到了它的本色——一種現實的存在。這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文學經驗生成的過程。人們常說,生活模仿了藝術,歷史的現象有著諸多的面孔。詩歌的語言就是我們生活的經歷轉化為詩時,日常經驗生成了詩的情感、思想和指向,詩的經驗就是這一過程中的語言創造。一首詩是被靈光一閃的詞語所照亮的,一首詩更是當語言在深入我們生活內部時那些無法言傳的事物促成的意會或指向。這時的詞語即是生命,它行走于世界,它是世界的核心和靈魂。面對生活的日常,以及“冷風吹打的話語”,詩人埃利蒂斯寫道:“我唯一關心的是我的語言,在荷馬沙岸上……我唯一關心的是我的語言,帶著黑色的震顫。”這就是語言的本性,有震顫之力。
如上所說,從最初的語言到當代詩的語言似乎都布滿了神秘主義色彩。關于語言的神秘性,耿占春有過精辟的論斷,他說:語言的神秘性也許在于“語言既是一種使事物更加神秘的力量,又是一種分析性的力量。語言是事物的隱喻,又是隱喻的分解或反諷。這是一種和經驗領域接觸而更加有效的語言神秘主義。”也許作為詩人的我們都是語言的神秘主義者,當我們開始寫作,我們就是語言的幽靈,在語言的表征世界里,我們的意識像一個微分子,在游走、感知和喚醒,這時我們有了另外的知覺——當然重要的是我們的知覺只屬于詩人獨特的意識與極具個人性的經驗。這是一個銳度,我們所擁有的詞也即眾多的尖銳簇擁著某個事物或事實。這時的詞不僅賦予我們自身以清醒的知覺,更賦予了生活中的現實一種高辨識度和強感受力,因為語言不僅是一個內心生活的傳達,關鍵還來自于對社會現實的形態化的敘述。這也可以說是詩歌語言的現代性,或直接說詩歌話語神秘的現代意義。詞這時是詩的靈魂,語言這時是詩人的行動。事實上,我們的行動就像我們的經驗總是處在未完成時的一個狀態,換一種說法,語言在其行動的過程中有著持續的力量,以及持續的更高的品性要求。
有一種內在的精神一直貫穿在語言的行動之中,尤其是當修辭批評從社會、政治,甚至某些日常的場域退居到只有文學承載其旋律時,這種精神作為語言功能的存在,更是突顯了詩性的力量,無疑這是一種詩歌意志。我們說,詩在遠方,那么詩歌語言就是向著遼闊奔走,是從“此岸”到“彼岸”的橫渡。詩的語言正是如此,像是普羅米修斯的呼喚,讓詞自由飛翔,之后方有一個闊大的遠方。這是精神內部的聲音,是冥冥之中語言的召喚,如曼德爾施塔姆的那句詩:“黃金在天空舞蹈/它命令我歌唱。”從歷史上看,唐朝詩人杜甫就懷著這種詩歌意志“百年歌自苦”地完成了他的一生,讓他的人和他的“史詩”一起成為一個時代偉大的存在。詩歌這種史詩般的見證,一次又一次地突顯了語言的自由和正義的力量。百年歌自苦,新詩也正好歷經了一百年,不得不說這一百年的語言探索,正是詩人們的詩歌意志在塑造一個象征的世界。
有一種語言的自覺是詩人所應有的詩歌意識,甚至是詩歌必須保持的寫作狀態。這是自古就有的一種文學自覺,魯迅曾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自覺的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這里的藝術是一種境界,在強調詩回到個人化的寫作價值。漢末魏晉時期,是社會現實苦痛,但精神上的自由與探索最為個性主義的時代,一種人格化的藝術心靈與藝術追求建構了獨特的“魏晉風骨”。《古詩十九首》為什么能夠開一代詩聲之先河,因為在對時世、包括日常的一種感喟詩學中,詩的語言“突出的是一種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的悲傷”,如李澤厚所論,一種生命意識、生死與現實的喟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這種詩的元音,是詩人的理性精神,也是一種語言的自覺。新詩百年,詩歌的語言是一個孤獨的探索途程,語言在返回現場,語言在創造屬于詩的世界。從五四時期白話運動的語言突圍,到穆旦所呈示的語言的現代性;從20世紀80年代詩的理想化抒情語言放逐,隨著90年代初的社會轉型到個人化敘事寫作;從個人經驗出發的一種抒寫到多元化、信息化的新世紀詩歌話語的碎片化解構性方式。詩歌的語言不再是狂歡,而是一個精神自覺的語言途程,語言的內質、境界都在營造一個象征世界的新可能。這種自覺是語言內部的,它既是語義上的一個確認,因為古今詩歌所承載的都是人類的精神史,詩歌語言就是自我精神價值的確認,同時它又是詩藝上的創造,“為藝術而藝術”,并抵達詩的一個境界——一個純粹的情感升華與凈化的過程。詩之所以為詩,就在于,在這個自覺的意識上賦予語言以詩性的節奏和華章。詩以其語言的自覺來完成詩的修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