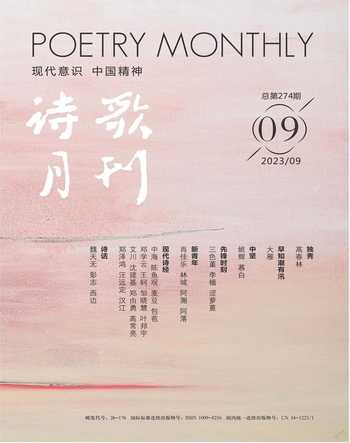深沉的夜色(組詩)
試劍石
還能聽見當時“嗨”的一聲大叫
石頭,即刻一分為二
如此鋒利,該是一把削鐵如泥
相當了得的好劍,不然
如此堅硬的一塊完整大石頭
不會一劍下去齊嶄嶄分成兩爿
劍早已不知去向,只留下石頭
和石頭上這道永遠無法愈合的裂口
——還好,不是人頭
站在那,有一刻突然躍躍欲試
“唰”地一下從體內拔出劍來
向著其中一爿,但僅舉了一舉
卻沒有砍下去,發現自己
已沒了那種氣概和勇氣
遙想當年,身懷刀劍
利刃閃爍,寒氣逼人,不是
把它提在手里,就是擱放在臉上
那時年輕,一身血氣,路見不平
大聲一吼。不知何時
劍收進肉體的刀鞘,越藏越深
甚至連殺只雞也猶豫半天
摸全身已無一根硬邦邦的骨頭
身上光滑如河床上的卵石
一個安靜的夜里,將劍取出
斑斑銹跡,仿佛一把鈍齒的鋼鋸
想起那些郁積在心的不平之事
雙手將它高高舉起,向書桌
狠命砍了下去……桌面毫發無損
把桌上的玻璃茶杯震落在地
破碎的聲音在寂靜的夜里
清脆而刺耳,驚醒睡夢中的
妻子,也將自己嚇了一大跳
扶劍四顧,深沉的夜色
一片荒蕪,如中年的生命
空蕩,迷離而茫然
老井
深邃的眼睛,向著天空
小時候不敢靠近,擔心掉下去
甚至做夢都害怕掉入井中
驚醒時大汗淋漓
仿佛真掉進去了,全身濕透地
爬出來,臉色紙一樣慘白
青石的井圈凸出地面
仿佛突起的乳頭,不竭的乳汁
喂養整個村莊,包括飄上天空的
炊煙,笑聲、哭聲、罵聲
雞鳴、犬吠以及父親的寡言
母親治不好的風濕病
每個早晨都是從錫皮桶投進井里
開始的,桶與井壁碰撞的聲音
清脆而又沉悶。老人說,兩人不看井
一個人我更不敢看,感覺
井里游曳看不見的幽靈
說不清它究竟有多深,還小時
曾壯著膽,趴在井沿向著它
大聲呼喊,還沒等到回音
就被一只大手冷不丁拎起來
屁股上響起嚴厲的噼啪聲
從小不敢正視父親,正視他
眉峰下的兩口老井,害怕從中
窺見自己的一生和命運
后來老井因修路填埋了,父親
也在墻上安靜地看著我們
老井一直都在,在我心里
不時發出咕咚的回音
老鐵軌
一條廢棄的老鐵軌,像是一把
放倒在大地上的長長梯子
早晨,太陽剛剛醒來
原野上還很安靜。鳥在不遠的
灌木叢中啁鳴,干枯的蘆葦
舉著滿頭白發,像年邁的母親
踩著有油污的黑色陳年枕木
時間的臺階,往回走
遇見追著火車奔跑的童年
父親雙手托著屁股從窗口硬把
自己塞進車廂的第一次遠行
遇見站臺上的依依相送
送走的人從此卻杳無音訊
遇見一次次離別,一次次相逢
一次次出發,又一次次歸來
秋風習習,飄散了思緒
它已銹跡斑斑,仿佛一卷鋪開
在荒野將被遺忘的電影膠帶
里面記錄多少奔走的腳步
多少的憧憬、希冀、熱盼、愛
多少的激動與興奮,無望和傷痛
多少個日出日落,白晝與黑夜
剪輯出來該是無數部人生紀錄片
現在它已成為網紅打卡點
許多人跑來拍攝落日里的風景
有一刻,一列披著朝霞的火車
從鐵軌盡頭,自四十年前的清晨
徐徐開來,父親肩挑我求學的
全部行囊。多好的清晨呀
那時有夢,有用不完的明天
父親也剛踏入中年的門檻
離離開我們,還那么遙遠
鄧學云,有作品發表于《詩刊》《星星》《草堂》《詩潮》等。著有詩集《如果沒有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