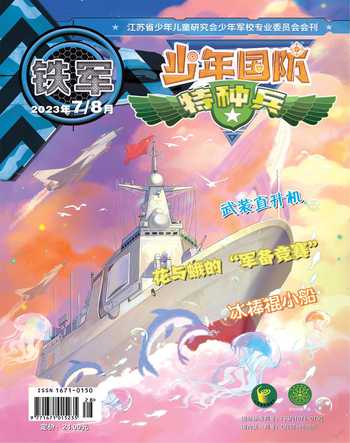花與蛾的“軍備競賽”
郗旺
1862年1月25日,英國著名博物學家、“演化論”之父查爾斯·達爾文收到了一個來自比多福莊園的包裹。給達爾文寄送包裹的是他的好友詹姆斯·貝特曼。貝特曼是一位實業家,同時也是一名狂熱的植物愛好者,不但一手建立起了以植物花園景觀著稱的比多福莊園,還雇傭了許多“植物獵人”到世界各地去搜集獨特的植物,尤其是蘭花。而貝特曼寄給達爾文的包裹里裝的就是一份采集自馬達加斯加的蘭花標本。
達爾文小心翼翼地打開包裹后,眼前的蘭花標本令他瞬間興奮起來:盡管標本已經干燥,但是依然能夠看到每個花朵都具有一個細長的被稱為“花距”的突起——長度足足超過20厘米,最長的可達40厘米。盡管達爾文對蘭花的研究頗深,但具有如此長花距的蘭花達爾文還是第一次見到。這種蘭花花色為白色,六個花瓣如六芒星一樣排列,宛若天上的星星,而長長的距又如彗星的長尾,因此被命名為長距彗星蘭。
依照達爾文以往觀察、實驗的經驗,蘭花距的尖端通常是分泌花蜜的蜜腺所在,昆蟲要到達這個部位才能吸取到花蜜。但是,長距彗星蘭如此細長的距,又有哪種昆蟲能夠吸取到花蜜呢?達爾文立即提出了一個猜測:在當地一定存在一種蛾子,它的口器可以達到相當的長度,從而能夠伸到長距彗星蘭花距的尖端去吸食花蜜。
達爾文將這一推測寫入了自己繼《物種起源》之后又一本傳世著作《蘭花的傳粉》中。但是,著作一發表,就引來了演化論懷疑者們( 包括很多昆蟲學家)的質疑,因為從來沒有人見到過有這么長口器的昆蟲,而一只昆蟲具有長達30厘米的口器也是不可想象的。達爾文的好友生物學家阿爾弗雷德·華萊士站出來支持達爾文的推測,并提供了依據:他在非洲探險時曾見過一種具有很長口器的天蛾——非洲長喙天蛾,盡管它的口器長度還不足以達到長距彗星蘭花距的尖端,但已足夠從側面證明天蛾類昆蟲是有可能具有與長距彗星蘭花距長度相當的口器。
這一爭論激發了眾多探險者、博物學家們前往馬達加斯加尋找這種預測中的天蛾。在1 9 0 3 年,也就是達爾文提出這一預測41年后,同時也是達爾文逝世21年后,探險家們終于在馬達加斯加找到了一種天蛾,它的口器盤旋在頭部最多可達20圈,展開后長度最長可達30厘米。達爾文的預測是完全正確的!而為了紀念達爾文的這一天才預見,這種天蛾被命名為“預測天蛾”。直到1992年,科學家們才在紅外攝像機和高速攝影機的幫助下,首次拍攝到了預測天蛾用超長口器吸食長距彗星蘭花蜜的畫面,而這一畫面,和當年華萊士基于想象而繪制的圖畫竟毫無二致。
達爾文關于長距彗星蘭和預測天蛾的故事,是證實演化論中“協同演化”的著名案例。但是,有一個問題的答案始終等待人們去完善,那就是長距彗星蘭的花距和預測天蛾的口器是如何通過協同演化變得那么長的呢?其實這種雙雙變長的現象,是蘭花和蛾子之間一場曠日持久的“軍備競賽”造成的。
生存的“ 軍備競賽”
昆蟲在花間飛舞,時不時停留在花朵上取食或收集花蜜、花粉,這一過程看起來溫情滿滿,但對于昆蟲和花朵來說,實際上雙方都“心懷鬼胎”。
知識鏈接:
昆蟲的口器由頭部后面的3對附肢和一部分頭部結構聯合組成,主要有攝食、感覺等功能,由于昆蟲的食性非常廣泛,口器變化也很多。如果你仔細觀察,你會發現蝴蝶和蛾子都是用一根吸管似的嘴巴從花朵中吸取花蜜的。這根長長的“吸管”是它們的特殊口器,科學家們給這種結構取了一個形象的名字——虹吸式口器。因為虹吸式口器只有吸的功能,所以蝴蝶和蛾子只能吸花蜜,吃流食。
對于昆蟲來說,無論花蜜還是花粉,本質是食物的來源,生存所必需。而花朵也正是利用昆蟲要采食這一行為,讓昆蟲身體攜帶上自己的花粉,以便將花粉運輸到另一朵花的雌蕊上,以完成授粉過程,二者各取所需。
對于昆蟲來說,如果身體上附著了額外的花粉,那么花粉的重量就會影響自己的行動,尤其是飛行效率。身上帶有的額外花粉越多,對行動的影響就越大,意味著被天敵捕捉的概率越大。在這種壓力下,昆蟲的演化方向便趨向于“能夠吃到花蜜、花粉,但不額外攜帶”這一目的。而對于花朵來說,提供花蜜和花粉需要耗費大量的能量和有機物,這對植物的代謝是一個負擔,因此花的演化方向趨向于“讓昆蟲吃得更少,但是要盡可能多地攜帶花粉”。
可以看出,昆蟲和花朵的需求是完全相反的。因此在這一過程中,演化表現出了它的力量,而長距彗星蘭和預測天蛾就是一對極端的表現。
長距彗星蘭的傳粉策略很簡單:天蛾為了取食花蜜而湊近花朵,觸碰到花中心的蕊柱,從而攜帶花粉塊。和其他絕大多數蘭科植物一樣,長距彗星蘭的花粉集合在一起,形成球狀的花粉塊,一塊花粉塊中就含有成百上千粒花粉,以此提高花粉的傳播效率。此外,長距彗星蘭的花粉塊底部還有一個帶有溝的黏性小塊,這樣花粉塊就能夠更容易地粘在預測天蛾長長的口器上。因為這種傳粉策略,在演化中具有較長花距的彗星蘭個體獲得了更大的生存優勢:花距越長,天蛾要離花更近才能吸取到花距頂端的花蜜,從而提高昆蟲攜帶花粉塊的幾率。
但是對于預測天蛾來說,攜帶花粉塊會影響自己的飛行狀態,如果花粉塊粘在自己的口器上,口器就不能很好地盤起來,更加影響自己的飛行和取食。另外,離花朵太近還會有致命的風險,因為有很多種類的蜘蛛會埋伏在花朵上,等待天蛾飛近之后發起突然襲擊,將倒霉的來訪天蛾當成美味佳肴。
因此在花粉塊和蜘蛛的雙重壓力下,具有較短口器的天蛾被捕食的概率更高,而具有較長口器的天蛾則更容易存活到繁殖時期,繁衍出更多具有長口器的后代。
在這一演化過程中,長距彗星蘭的花距越來越長,預測天蛾的口器也越來越長;而預測天蛾的口器越長,反過來又促使長距彗星蘭的花距變得更長。這種雙方加碼的“軍備競賽”,最終產生了我們看到的具有超長花距的長距彗星蘭和長著超長口器的預測天蛾。
“ 軍備競賽”的終結和物種起源
看到這里,你可能想問“軍備競賽”會有結束的一天嗎?畢竟,作為花和昆蟲的固有結構,花距和口器是不可能無限變長的。因此,“ 軍備競賽”可能會在某些情況下被“ 終結”。如果預測天蛾的習性發生變化,更多地取食其他花朵的花蜜,不依靠長距彗星蘭也能生存,那么長長的口器就成了生存劣勢。而對長距彗星蘭來說,也許會演化出依靠氣味或其他分泌物吸引昆蟲靠近花朵的特性,那時長花距和花蜜也就成了不必要的特征。到了那個時候,“軍備競賽”就自然結束了,同時另一種天蛾和另一種蘭花的形成也將悄然開始,這是演化驅動的物種形成機制。
新的物種的形成則意味著又一輪“軍備競賽”的開場。只要演化還在繼續,不同物種之間的“軍備競賽”就將不斷發生和延續下去,而這也正是“協同演化”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