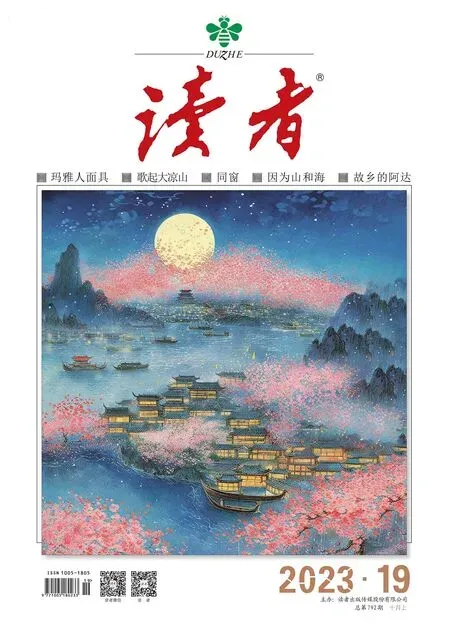瑪雅人面具
☉徐則臣

那段錄像很多朋友看過,我沒有瞎說。錄像中,那座傾圮的金字塔像廢墟一樣癱在奇琴伊察。除了金字塔,除了通往金字塔頂端的隱約小路,以及石頭與土堆間的荒亂草木,只有畫外音般植入的解說。
那人當(dāng)時說的是英語,他說每年他都會來幾次,帶有緣人過來看一看。我問他:“何為有緣人?”他說:“比如你。”
錄像里有兩句話極突兀地高亢地說出來。我找墨西哥的朋友鑒定,他說,那是瑪雅人的土語,比當(dāng)?shù)胤窖赃€要古老一點,大意是:我看見的在極高的高處,我想象的在很遠的遠方。我轉(zhuǎn)了一下文,即:我所見者高萬仞,我所思兮在天涯。只見他背靠一塊打磨過一半的大石頭,突然像主持人那樣張開雙臂。擁抱完我看不見的東西之后,他垂下手臂,繼續(xù)引領(lǐng)我沿著那條布滿碎石的荒蕪小路往高處走。我跟在他身后,與他保持三四米。這個距離既可以隨時調(diào)焦,把廢墟般的金字塔的整體和局部自如地呈現(xiàn)出來,又能保證他一直都被框在鏡頭里。
只是現(xiàn)在,你再看那段錄像,金字塔和人聲、風(fēng)聲、鳥鳴聲都在,人卻不見了。
他叫胡安。在墨西哥叫這個名字的有幾十萬人。胡安是做面具的,純手工制作面具,一刀一刀地刻出來,然后叮叮當(dāng)當(dāng)背到金字塔景區(qū)附近賣。
朋友說:“墨西哥的面具,你一定要帶一副回去。”這是必須的,我是木匠的兒子,見到好木工活兒就起貪心,這是遺傳。我爸是全鎮(zhèn)最好的木匠,我爺爺也是木匠,據(jù)說我爺爺?shù)陌职忠彩悄窘场?/p>
好木匠從來都不只做家具,必然是做著做著就有了“藝術(shù)”上的野心。比如我爺爺,除了做家具,最拿手的就是做臉譜面具。我爺爺是個好木匠時,我們那里還很窮,戲班子化裝買不起油彩,就讓我爺爺把張飛、關(guān)羽、包公的臉譜做成面具,往臉上一扣,可以反復(fù)用,又不傷皮膚。全縣大大小小的戲班子、文藝宣傳隊用的大大小小的面具,都出自我爺爺之手。而我爸,藝術(shù)抱負就放在了木雕上。我爸不做面具,因為沒市場,但我家堂屋的東山墻上掛著幾十副面具,里面有我爺爺?shù)氖炙嚕嗟氖菑奈搴暮K蚜_來的。我有義務(wù)為那面墻再添一件展品。
看見胡安手工制作的面具,我兩眼一亮。這些面具造型奇特,面部和面具上方的裝飾處理充滿了想象力。胡安穿著瑪雅人的民族服裝,留著一頭長發(fā),下巴垂下一綹小胡子,盤腿坐在一堆面具后面的地墊上。刻刀平穩(wěn)地在木頭表面前進,一條條木頭片輕微卷起,刀停,木條即掉落下來。一條馬尾辮在他腦后搖蕩。刀起木片落,幾個動作過后,他開始給面具開眼。那些規(guī)制統(tǒng)一的面具,眼睛部位就是兩個核桃形狀的空洞;他刀下的眼睛也是挖出的兩個框,但你就覺得那眼睛是有神的,好像框里面真有兩只會轉(zhuǎn)動和能聚焦的眼睛。面具在他手中變換位置,我分明覺得一雙眼睛正從不同角度盯著我看。我悚然一驚,天似乎也不那么熱了。我蹲下來挑了一副太陽神和蛇神臉對臉、頭像下面有山巒起伏和叢林密布的面具。
那副面具的空眼眶同樣是可以聚焦的。我用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語問:“多少錢?”
胡安頭都沒抬,刀搭在膝頭正做的面具上,右手五指張開,在我眼前晃了晃,然后又拿起刀,繼續(xù)雕刻。五百比索,折合人民幣兩百元左右,挺劃算。我朋友用英語提醒我:“有點兒貴,三百比索就能拿下。”
我回他:“不貴,值。”
胡安抬起了頭,真正讓我震驚的事來了:他比很多中國人長得更像中國人,黃皮膚,黑頭發(fā),黑眼睛,脖子比別的瑪雅人的都長,身材也比其他瑪雅人瘦高。看見他那張“中國臉”,我確定他應(yīng)該在四十歲左右。
關(guān)于瑪雅人是中國人的后裔之說,我略有耳聞,也零零散散看過一點資料。比如,有學(xué)者說,商周時期,商朝被周朝打敗,二十五萬商朝人集體東渡,一部分抵達墨西哥高原,由此締造了偉大的瑪雅文明。中國人和瑪雅人的確外貌相似,文化也十分接近,甚至有科學(xué)家研究發(fā)現(xiàn),古代瑪雅人與中國人的“線粒體DNA 中含有三十七個相同的基因”。
胡安抬起頭,用英語對我說:“謝謝!”
“值。”我又說。
“第二副,”胡安說著,拿起另外一副面具,“三百比索。這上面有金字塔,跟其他的都不一樣,平常賣八百比索。”
他沒把金字塔雕成上下結(jié)構(gòu),而是讓塔尖沖正前方,整個金字塔就像面具額頭上長出的棱錐形獨角。面具上鼻子凸起,金字塔的角比鼻尖還高。正所謂鼻子不到人前,角先到了。這造型我喜歡。
“先生喜歡我們的金字塔?”胡安問。
我點頭。
“我就知道您是喜歡瑪雅金字塔的人。”
“何以見得?”
“直覺。”胡安一笑,真是太像中國人了,“有一座金字塔您肯定沒見過。”
“在哪兒?”這回是我朋友接的話。他自詡整個墨西哥沒有哪座金字塔他去過的次數(shù)少于五次。
胡安比畫了一個位置。對于那地方,我朋友顯然也蒙了。為了說明白,胡安用西班牙語跟他解釋。
“值得你去。”朋友對我說。他們倆用西班牙語談好了行程和價錢,由胡安開我朋友的車帶我去。
胡安把他的面具打包,寄存到旁邊一個小店里,坐到了我朋友奔馳車的駕駛座上。車打火之前,他向我伸出手,說:“我叫胡安。幸會。”
奇琴伊察不大,南北長三公里,東西寬兩公里,這座意為“在伊察的水井口”的城市一馬平川,不存在連當(dāng)?shù)厝硕己币姷慕鹱炙裕易龊昧伺苓h路的打算。出了城二十分鐘不到,駛過一條兩邊灌木和樹林如屏障的沙石路,路越走越窄,在一塊覆滿青苔的方形巨石前,胡安停車熄火。我跟著他穿過一片熱帶雨林,完全辨不出方向,就像穿行在某個史前巨型動物燠熱的盲腸里。五分鐘后,天亮起來,豁然開朗,一座荒蕪散亂的高臺矗立在一片開闊的林中空地上。
毫無疑問,這個傾圮的高臺曾是古代祭祀用的金字塔,灌木、荒草、苔蘚和碎石遮蔽不了它內(nèi)在的秩序。荒蕪和散亂自有其方向,草木或成片分布,或沿線蔓生,各自遵循隱秘的邏輯。我突然生出一種強烈的感覺:它靜靜地矗立在這塊平地上,已經(jīng)等了我很多年。歷史與當(dāng)下,從來不會無端地劈面相逢。我決定把它拍下來。打開手機的拍攝功能,我讓胡安一邊講解,一邊帶領(lǐng)我沿著我看不見而胡安無比熟悉的小路,跌跌撞撞地向上攀爬。胡安善解人意,為了讓我聽明白,便用英語解說,關(guān)鍵處還不厭其煩地重復(fù)。
天降大風(fēng),四周的雨林和高臺上的草木開始涌動。熱帶雨林我極少去,長風(fēng)浩蕩的經(jīng)驗我完全沒有,在大風(fēng)里拍攝的經(jīng)歷我更缺乏。我大聲地問,胡安就大聲地答,我聽見了,我以為手機也聽見了,沒想到鏡頭里留下的,只是有限的一點沒被大風(fēng)擠走的含混聲音。你只能辨出那是人聲,僅此而已。直到胡安背靠一塊巨石,布道般抒發(fā)他之所見與所思。
我們在大小石頭、泥土和灌木中登臨高臺之巔。金字塔并不比周圍的雨林高多少,我們僅看見一片由熱帶雨林樹梢組成的浩瀚海洋;大風(fēng)經(jīng)行遼闊的水面,綠色波浪前呼后擁。
回到墨西哥城,我做了幾場新書的推廣活動,回國的日期就到了。回到家,收拾停當(dāng),我把兩副面具拍照,跟胡安帶領(lǐng)我前去金字塔遺址時拍的錄像一起發(fā)給了我爸。
先反饋回來的是他對面具的意見:“做得真好,高人!”
十分鐘后又發(fā)來一條微信:“錄像里誰在說話?”
我回:“胡安啊!鏡頭里的那個瑪雅人。面具就是他做的。”
“哪有什么瑪雅人?”
我剛要回微信,我爸就打來了微信語音電話。
“連個人影都沒見著,”我爸說,“你確定他是什么瑪雅人?”
“當(dāng)然是瑪雅人。您說什么?人影都沒見著?”
“就是沒人。”
我查看發(fā)給我爸的視頻,果然沒人。我又拖著進度條前前后后看了三遍,真的沒人。我后背上出了一層汗,像身上突然長出了毛。天地良心,我的鏡頭完全是追著胡安走的,拍的不是他的正面,就是他的背影。他的聲音在,但人不見了。該有他身影的地方,現(xiàn)在像空氣一樣透明;或者說,胡安透明的身體沒有遮住任何景物,金字塔和它的亂石草木一樣不少。我快進到了胡安那段慷慨激昂的抒懷處。我爸在電話里問:“他說的是啥?”
“我哪知道,聽不懂。”
“聽著,有點,耳……耳熟。”我爸結(jié)巴了。
我們倆的微信語音電話都開著,誰都沒出聲。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
“有時間你回來一趟,”我爸先開口,“把面具帶著。”然后沒打招呼就掛斷了微信語音電話。
顧不上時差,我給出版商朋友打去電話。他從睡夢中清醒過來后,首先對我發(fā)誓,我們的確見過胡安,他對胡安印象還挺好的。我在電話里讓他聽胡安的那段抒情的話。反復(fù)聽了幾次,他才嘗試著用英語向我解釋大概意思。他讓我用電子郵件把視頻傳給他。半小時后,我收到郵件回復(fù)。他說他認真比對了我的拍攝角度和聲音來源,他斷定,鏡頭里應(yīng)該是有人的,但他確實連個人影也沒見著。在郵件末尾他寫道,最近他會回梅里達,如果時間寬裕,他就再去一趟奇琴伊察。
如果不是我媽打來電話,我會推遲幾天回去。我媽說:“你爸臉色不大對。”當(dāng)晚我就買了機票回老家。我爸一向不茍言笑,若不細心真看不出他的臉板得更硬了,像經(jīng)年的土地板結(jié)了一樣。他把兩副面具翻過來掉過去地看,最后目光都落在空眼眶上。他用手指肚一寸寸摩挲那四個空眼眶。
“手法像。”我爸說。
“手法像誰的?”
“老二。”
我看看我媽。我媽小聲說:“你二叔。”
“他不是早死了嗎?”
“是失蹤。”我爸糾正道,“再沒回來,就當(dāng)死在外頭了。”
有點兒蒙,我竟然被騙四十年。
我爸一屁股坐到老式藤椅上,讓我給他根煙。“老二發(fā)火時,嘴里吼的跟錄像里那聲音一模一樣。”
二叔是我二爺爺?shù)膬鹤樱瑥男『臀野忠黄鸶覡敔攲W(xué)木工。他天賦極高,學(xué)啥像啥,做啥成啥。我爸說:“他最拿手的是面具,得你爺爺真?zhèn)鳌D銈兊奈脑拑涸趺凑f?對,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勝在眼睛。”十八歲,我二叔就跟胡安一樣,能把空眼眶挖出眼神來。
我爸也是個木工好手,其他的活兒都不比二叔的差,但面具之眼不及。他們的師父是我爺爺——我爸的親爹,我爸比我二叔長兩歲,所以面子上一直過不去,心里也不舒坦,長年跟二叔較著勁兒,隔三岔五也會給二叔找一點兒不痛快。他給二叔找了不少茬兒,也使了不少小壞。最后一樁,是在一副面具上動了手腳。
那是二叔代我爺爺給縣淮海劇團做的道具。某天早上,我爸先到工房,看見我二叔頭天做的面具放在案子上,雖然尚未徹底完工,但那空眼眶里流轉(zhuǎn)出的眼神已然誘人。我爸說,他的嫉憤之火瞬間拔地而起。那眼神太精妙了,也很微妙。正因為精妙和微妙,所以經(jīng)不起半點兒差池,關(guān)鍵處多那么一兩刀,眼神必會散掉。我爸關(guān)上工房的板門,拿起刻刀。刀刃剛切進木頭,二叔推門進來,大吼一聲,把我爸掀翻在一堆木屑和刨花上。我爸說,他第一次聞到木屑和刨花散發(fā)出來的味道如此酸臭。我二叔拿起面具,對著右膝蓋猛地一磕,薄薄的面具裂成五瓣。接著,他繼續(xù)大吼。
“爸,您確定二叔吼的跟胡安說的一樣?”
“年頭太久,又不像人話,哪記得清。”我爸的聲音衰弱下去,“聽到那個什么瑪雅人胡安的聲音,我好像又想起來了。就算不是一模一樣,也差不離。那個味兒,不會錯。”
“然后呢?”
“你二叔第二天沒來干活,第三天也沒來。從此,他就消失了。”我爸木頭一樣的臉上,皺紋開始細密地游動。我爸三十三歲時有的我,在此之前的十年里,他走街串巷,是個云游的木匠。活兒從江蘇做到山東、安徽、浙江和河南,最遠到過江西和湖北,卻沒打聽到二叔的一點音信。
二叔僅存的遺跡,是掛在山墻最高處的兩副臉譜面具,一副是張飛,一副是碎成五瓣又拼接到一起的顏回。沒錯,張飛雙目圓瞪,炯炯有神;顏回的右眼五十年前被我爸挖了一刀,就成斜視了。這些我過去都沒注意過。我爸讓我把兩個瑪雅人的面具也掛上墻,躋身于近百副面具中間。我爸盯著掛好的兩副面具,背著身問我:“你說,那個胡安是什么人?”
“墨西哥瑪雅人啊。”
半個月后,墨西哥的出版商給我發(fā)來郵件,說他去了奇琴伊察。但很遺憾,掘地三尺也沒能找到胡安,胡安帶我去的那座雨林中的金字塔也沒找到。胡安寄存過面具的那家雜貨店的店主說,他完全不記得有一個扎著馬尾辮的叫胡安的瘦高個男人。叫胡安的人太多,做面具的人也不少,全世界的人出入他的小店,你來我往,誰有那么大的腦袋全記住。照我的描述,出版商雇了一名當(dāng)?shù)氐南驅(qū)В?qū)車到了那條沙石路的盡頭。他看到那塊大石頭,但左轉(zhuǎn)進熱帶雨林后,披荊斬棘走了兩個半小時,也沒發(fā)現(xiàn)哪兒有林中空地,更沒見著視頻里的那座金字塔。
“全都是樹,一棵接一棵的樹。”他用誠摯的文字跟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