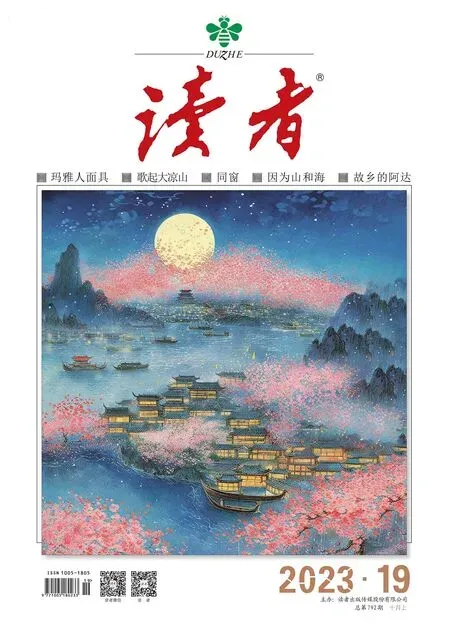醫學思維:與醫生最短的距離
☉王興

首先,從兩個誤會說起。
第一個,是我對疾病的誤會。
2006 年,我進入北京大學醫學部,開始了為期8 年的醫學學習生涯。我從中學開始,就一直堅信自己有某種疾病。我從小到大一直非常瘦,及至后來長到一米七幾的個頭兒,體重卻只有110 斤左右,“麻稈”這個詞真是伴隨了我充滿自卑的學生時代。我特別希望世界上有一種神奇的藥丸,我吃過之后就可以獲得像健壯的男同學那樣的男子漢氣概。在學習臨床知識時,我經常覺得自己好像得了什么病:刷牙流血,我以為自己得了白血病;經常便秘,我以為自己患有腸癌;學習和甲亢有關的知識時,我就感覺甲亢的癥狀和自己急躁的性子非常符合。但是后來經過漫長的學習和自我檢查,我慢慢意識到,我得的病其實叫作醫學生綜合征,很多醫學生或多或少有過這樣的經歷。
學醫會讓你產生迷思——是不是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些不那么正常的地方,只要服一種神奇的藥物或者做一種巧妙的手術,就可以“一鍵恢復出廠設置”了?但是在學醫、行醫的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這只是一種美好的幻想。醫學不是萬能的,在很多時候甚至是無力的。
與學醫產生的無力感的抗爭持續了很久,直到我認識到這個世界終究還有一些事情我可以做,有一些人我可以救。后來,通過健身,我的體重增長到了140 斤。我這才發現,我所謂的瘦弱,只是因為怎么吃也不胖的體質。這哪里是我的弱點,明明是我的天賦啊!
但是,這個持續了十余年的誤會告訴我,與疾病的斗爭以及和解,是每個普通人一生的必修課。
第二個,是我對醫生的誤會。
我最開始對醫生的理解和想象,來自動漫里的船醫。這個角色非常吸引我,我也愿意成為別人戰斗時背后的依靠。于是,在填報高考志愿選擇專業時,我兩個志愿都報了醫學專業,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學醫學部,第二志愿是北京協和醫學院。但我大三因為跑馬拉松而腳受傷去看病時,覺得醫生真的很冷漠。作為一名醫學生,我準備了一整套說辭,想請已是醫生的學長好好幫我看看。但我進了門診后,他并沒有仔細問診,也沒有好好檢查,就對我說沒事,我再想多問哪怕一個問題,收到的都是不耐煩的逐客令。當時的我雖然不知道自己要成為什么樣的醫生,但至少明白自己不要成為怎樣的醫生——我學長那般冷漠的。
無巧不成書,當我進入臨床學習時,這位醫生學長成了我們的帶教老師。盡管有之前的情緒,我仍然瞬間就被他的睿智、熱情和個人魅力感染,我堅信我要成為像他那樣的醫生。為什么對同樣一個人,我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后來我也做了醫生,我終于理解,醫生在門診時,更多的職責是快速判斷病人是否有病,需要吃藥還是做手術,要不要住院。簡單地說,就是“篩查”。我的腳傷當時確實沒用藥就很快好了,沒有浪費一分錢。從這點來看,那位醫生學長其實高標準完成了任務。我寫這個誤會并不是想說明醫生就應當冷漠,而是它讓我可以從醫生的視角去思考,什么才是“有效的醫療”。
醫生也是基于對疾病、醫學、醫療的基礎認知,才訓練出一套屬于自己的思維方式。一旦普通人對這種思維方式有更多的理解,恐慌和不安就會減少很多,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分析與決策,從而實現“有效的醫療”。因此,學會醫學思維,可能是縮短普通人與醫生之間距離的最有效方式。
那什么是醫學思維呢?
我們有的是醫療信息,卻沒有醫學思維。隨著信息的開放,醫學知識不再高深莫測。一個人在來到醫院和他的醫生溝通之前,可以輕松地通過網絡對這個疾病的來龍去脈做一個大致的了解,甚至能查閱到目前所有最新的文獻綜述。從理論上講,病人在對信息的獲取上與醫生是一樣的,信息不對等更多是因為醫患雙方對信息整合和理解的能力不同,而并非信息獲取本身。
任何思維走到最后,都可能會成為一種直覺。這種直覺不是猜測、不是臆斷,而是建立在大量的學習和實踐之上的一種經驗性的本能判斷。對醫生來說,醫學思維就體現在,他可以迅速地判斷一個人到底有沒有生病,是不是需要治療。例如,兩個人同時來到急診科,一個酒氣熏天、大吼大叫,另一個捂著肚子悶不作聲,也許悶不作聲的那位才應該是第一順位被搶救的。
所謂醫學思維,就是醫生在掌握有關人體和疾病的生物學規律之后,根據病人的癥狀、體格檢查和實驗室檢查做出相應的診斷,依據診療指南為病人做出合理的診療建議,并在指導或者直接為病人完成治療的過程中,貫穿始終的思維模式。
醫學思維包括幾個維度。首先,是理性思維。怎么解決問題?對于一個病人的病情,我的判斷是什么?對他來說有效的醫療是什么?如何選擇性價比最高的方案?
其次,是批判思維。我的判斷有沒有可能是錯的?有哪些不支持我判斷的依據?
再次,是科學思維。臨床的指南是否需要改進?新的臨床發現是否可行可信?一個可能的病因和疾病之間是相關性還是因果性?
培養了醫學思維,能做什么呢?一旦有了醫學思維,你在看病時會發生什么神奇的變化呢?
很簡單,你就可以輕松地理解為什么你明明只是吃壞了肚子,醫生卻會詢問你的性生活史;你也可以理解為什么你明明肚子已經很疼了,醫生還要按你的肚子,直到你嗷嗷叫為止。以及你會了解,醫生在聽診之前為什么總是把聽診器的聽頭用手攥一攥,在按你的肚子之前會讓你把腿蜷起來。你會明白,這些“講究”都是為了什么。
你可以理解醫生行為背后的思考方式和動機,從而至少可以獲得以下幾種能力:第一,尋找及判斷最適合的醫生的能力;第二,為自己和家庭選擇最合適的健康規劃方案的能力;第三,理解疾病和現狀的局限性,從而不再焦慮、從容生活的能力。
你如果仔細看醫生寫的病歷,會發現除了細致描述癥狀,有的還會寫上很多的“否認”,比如否認咳嗽、咳痰,否認背部疼痛,否認發熱等不適,這些你沒有表現出來的癥狀,就是所謂的陰性癥狀。
“否認”是病史的一種標準書寫方法,它的嚴謹之處在于,它表示醫生問了,病人說沒有,而不是沒有問到。這一串“否認”代表什么?代表醫生的思考。醫生寫的每一個“否認”都代表著他考慮過你有沒有可能是其他疾病,但是由于缺乏相關的證據,他才最終得出“穩定性心絞痛”這個診斷。很多上了歲數的老大夫在看病歷時,看得最仔細的也是這些所謂的陰性癥狀,陰性癥狀最能反映醫生是不是考慮得全面,是不是具有科班訓練出來的醫學思維方式,是不是一聽到病人自己說“心絞痛”3 個字,就立馬準備開檢查、開藥。
我在自告奮勇地詢問病史時,犯的錯誤其實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面面俱到,把幾十種癥狀一一問到,病人只是胸悶,我卻盯著他問是不是排尿困難。我的道理是什么?我是否考慮過這可能是什么疾病?都沒有。所以這不是醫學思維,而是背書。
以上更多的是我對疾病、醫生相關的認識。但醫學思維涵蓋的范疇不止于此,它還包括和醫療整個流程相關的一切,因為做一名有同理心的醫生,不僅要懂人文,更要懂世俗。
美國哈佛大學醫院的教授在挑選學生時,采用這樣一條有趣的標準:對學醫的人來說,那些非醫療的部分才是我們與眾不同的地方。
那些“非醫療”的部分指的應當是關愛、共情、傾聽等這些人文范疇的東西,但我們身處實際醫療環境中,更常見的是“錢”“關系”等社會經濟范疇的東西。
幾乎每個人都能理解“一分錢一分貨”這個道理,但是唯獨在面對生命時無法理解。在醫療這件事上,任何國家、任何組織、任何醫療模式都不完美,但是反思可以讓我們靜下來想一想,我們究竟從哪里出發,才能尋找到“有效的醫療”,而不是“昂貴的醫療”和“浪費的醫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