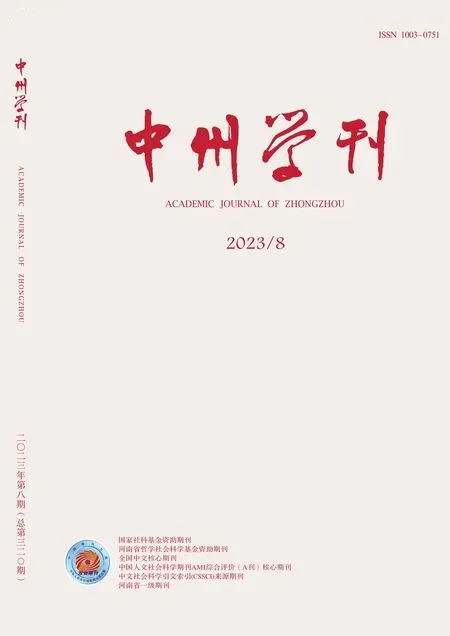路程·生活·經驗:唐詩之路的三重構境
羅時進 陳家愉
“唐詩之路”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的提出,已有30多年的歷史。它最初由本土學者提出,2021年因當代著名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與北京大學董強教授合著的《唐詩之路》而進入世界文學的視野。然而,唐詩之路的概念如何界定,它對唐詩、唐代文學研究意味著什么,應該如何在理論上認識、在學術上把握其內涵和本質,仍是需要探討、闡釋的重要問題。“唐詩之路”這個概念內在地確定了它是唐詩研究的一個專題方向,是唐詩研究大樹上的一個重要分枝。我們既不應忽略它本有的豐富內涵,又不應無視它與唐詩、唐代文學研究的邊界。這方面需要討論的問題很多,本文由具體性向抽象性延展,從路程、生活、經驗三個維度討論唐詩之路研究的三重構境。
一、路程:唐詩創作的“現象表征”
海德格爾指出:“存在論只有作為現象學才是可能的。”[1]作為一個概念,唐詩之路能否作為唐代詩人的行為現象在創作中凸顯?答案是肯定的。迄今為止,在尚能夠較為完整地描述出生平大概的唐代詩人中,很難發現某個作者始終處于極小范圍的靜默狀態,他們總有自己的位置移動。道路山重水復,路上行人往來,這是現實社會的日常,在唐詩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并由此產生了多種唐詩意象。唐人詩題中“發、辭、過、渡、游、涉、行、經、旅、次、宿、歸、赴、使”等動詞以及大量地方名詞表達的就是路程現象。如:“度嶺方辭國,停軺一望家。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宋之問《度大庾嶺》)“琴劍事行裝,河關出北方。秦音盡河內,魏畫自黎陽。”(薛能《送馮溫往河外》)“浮云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高樹里,秋河隔在數峰西。”(韓翃《宿石邑山中》)唐代詩人因各種原因,經常處于“在路”狀態,形成了重要的唐詩現象表征。
路程,是一個有關行走的總體概括,而分析是基于具體事實的,這就需要對路程有具體的理解。雖然無須做過細的分類,但基本的層級區分仍有必要。唐人行走的路程,一般看來有大區域、中區域、小區域之分,下面分別論述。
1.大區域
每個時代的文人,一般都有屬于本時代的“東游記”“西游記”,或“南游記”“北游記”,唐代詩人寫作最多的是“西北游記”和“東南游記”,這與唐代政治中心在西北,而休養棲息地在東南有關。如此就從宏觀上見出唐代詩人“向北(西北)”與“向南(東南)”的唐詩之路,這是大區域的道路。唐代以西北為帝京所在,其南面而治天下的威嚴常常受到漠北少數民族或其他游牧族群的威脅,戰事頻發。為此許多詩人遠赴邊塞,其中較多部分屬于大區域道路。京官外任或貶謫邊遠地區,其路程絕大部分也屬于大區域道路,至于官員派任羈縻州的情況,自不待言。唐人往往有壯游、漫游的習慣,路程遠近不同,大區域行走情況頗為常見。唐代還有某種較為特殊的行旅,如崔致遠自新羅乘船西渡入唐,留唐16年后,以“充國信使”的身份東歸新羅,他的履跡形成一條獨特的唐詩之路,自然也應歸入大區域之列。
這里需要提示的是,唐人大區域范圍的行走雖然有一些屬于特殊現象(如官員派任羈縻州、崔致遠入唐),但絕大部分屬于普遍現象。這種普遍現象中最突出的是以長安為目的地和出發地的行走路線,以及以西蜀為主要方向的行走路線。后人所說的“從古詩人多入蜀”或“古來詩人每入蜀”中的“古”即指唐代①,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杜甫、高適、岑參、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賈島、李商隱……,唐代向西蜀行走的詩人形成了一個規模浩大的隊伍,在唐詩史上留下的跋涉作品、景觀作品極為豐富,幾乎不少于由北方下吳越、向嶺南的詩篇。
2.中區域
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大致可以看作北方和南方的兩條東西軸線,而北方與南方如何界分呢?如果要找一個標志的話,無疑就是秦嶺,其為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分水嶺。在普遍認知中,我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是秦嶺-淮河一線,秦嶺即為最顯性的界線。“唐代的資料證明:當時行政體系中的南北分界位于秦嶺淮河;唐人地理感知中的南北分界,西段仍在秦嶺,而東段卻在長江。”[2]
唐代詩人中,有部分作者(如初唐一些出生于北方的學士),平生未曾越過長江,沒有在江淮以及更南向地區留下足跡,其行走路線即使偶爾涉及邊庭,也應看作是中區域的行走。唐代顯慶二年(657年)正式以洛陽為東都,武則天改唐為周之后,一度以洛陽為神都,洛陽成為全國政治中心。分司東都制度的建立,賦予了洛陽特殊的政治功能,使其具有了重要地位。唐代西京至洛陽,其間數百里,是唐代詩人往還頻繁之道,終唐之世“京洛道”都是最顯要的唐詩之路。唐人行旅大致出于公私二道原因,主要有應舉、下第、游幕、銓選、出使、赴任、遷官、貶謫、量移、訪友、避事等。其中游幕、量移、避事多發生在中區域范圍。另外,五代十國時期,十國文人之間有所流動,其長江流域之行亦屬于中區域行走。
3.小區域
唐代歷史上有許多重要的驛道、驛站,嚴耕望先生考證,“唐制三十里一驛,開元盛時,凡天下水陸驛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量閑劇置船馬。……按實考之,驛距疏密無定準,交通繁忙大道或不到三十里,而邊遠地區,有疏距八十里以上者,平均距離當在四十里以上,則全國驛道踰六萬五千里”[3]。這是考察唐詩之路的重要依據。唐代詩人經過驛站行至遠方,蓋歸于大、中區域范圍,數個短距離驛站之間則往往屬于小區域。
另外,唐代運河與長江沿岸的都會往往是區域性交通樞軸②,也是文人行走、集聚的中心。由此中心向外輻射,就形成了若干唐詩之路。如韋應物、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期間,蘇州成為江南詩學重鎮,湖州、杭州、常州的詩人從三個方向向蘇州匯集,顯示出江南詩學昌盛的景觀。在唐代江南,吳越文化具有突出的共軛性,其間就自然存在一條詩路。浙東唐詩之路,本質上也是區域共軛形成的文化共軛,其中一部分也具有小區域詩路屬性。在小區域內,個體詩人的行走路線非常值得注意。如杜牧偏愛淮南、江南,在揚州、潤州、宣城、池州、睦州、湖州等地均有履歷行跡,這些地方勾連起來便是一個杜氏“小長三角”③行走版圖。
以上三個區域層次的劃分,大區域有數千里之廣,中區域有數百里范圍,小區域則為百里、數十里不等。地理范圍的大小與作為一種精神生產活動的詩歌創作數量之間沒有必然等約性,地理范圍的大小雖然與詩人分布的密度有一定的關系,但也不是絕對的。然而,通過不同層次的區分可以看出,唐詩之路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也不是一種解釋唐詩生成的簡單工具。唐詩之路作為一個學術概念,仍然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再省思、再界定。這種省思和界定不應遵循某種既定模式,只有突破既定模式、習慣思維,才能有新發現,發掘出“路程”所具有的豐富詩學內涵。
二、生活:唐人行走的“日常”與“事件”
唐人的居處與行走,都是其生活的組成部分。而唐人的生活史,可以成為唐代社會史的憑證,因此生活無疑也具有歷史性。唐代詩歌史是唐代歷史的一個分支,其歷史性的存在所憑借的就是那種感性的、鮮活的、具有社會性本質的詩人,而詩人是生活中的人,只有映照在具體生活影像中時,才能被看見,被寫入詩歌發展史。
唐代詩人是通過現實生活來生成具有社會本質的自我,也生成兼具社會屬性和文學特性的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居處相比,也許行走更能表達現實生活的狀態、意愿,更能突破某種日常生活的感受,激發出情感與靈感,更可能創造出新的意義。這就使行走自然走進了文學天地,走進了詩歌勝境。嚴羽《滄浪詩話·詩評》稱:“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這道出了行走對于唐詩創作的意義,而這也正是唐詩之路的意義所在。對此應關注以下三個問題。
1.“事”的世界
這里需要對日常生活做一些意義闡述和延伸。人生活在“事”的世界中,而“事”的生活有“日常”與“事件”之分。“日常”具有重復式、均質化的性質,體現出一般性、同類性;“事件”是日常的斷裂,即打破日常,消解了均質化,具有較大的片段性、不可預見性。“常人安于故俗”④,“故俗”具有日常性,是共知而熟悉并形成長期習慣的樣態,這種生活即日常生活。而詩人,尤其是有個性的、優秀的詩人顯然異于常人,他們不能安于故俗,要走向新場域,探索新可能。如果說故俗多通過“時間性”證成生活,那么去俗則往往通過“空間性”證成生活。行走是進入時間流程中的空間,突破了居處的日常性,更多表現出事件性。就此而言,唐詩之路的生活視域是一個事件性視域。
那么行走是否就絕對歸于事件,而非日常呢?答案并非如此,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做具體、恰切的分析。如王維《輞川集序》云:“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萊萸泮、宮槐陌、臨湖亭、南坨、欹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坨、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閑暇,各賦絕句云爾。”[4]值得注意的是,王維所說的“游止”就是一份“路線圖”,本質上這條“游止”之路也是唐詩之路。盡管文學史家將王維的隱逸生活看作一個事件,但由于這種猶如“魚龍隱蒼翠,鳥獸游清泠”(儲光羲《同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的隱逸生活,表現出極為明顯的重復性、均質化,這種高雅的事件已經轉化為另一種更高層次的日常了。其實,不少唐代詩人經常為了同樣的目的,行走在相同的道路上,其結果并不具備不可預見性,這樣的行走也并非事件,而應屬于日常生活。由此又可以延伸出一個觀點,即行走的事件性與目的達成的某種或然性,以及行走空間范圍的廣度有關。而唐詩之路肯認的必要性、重要性,描述的精彩度也正與此關聯。
2.隱匿的力量
人與世界的關系并非主體支配客體那樣簡單,事實上,當人進入復雜的世界以后,人與世界的關系往往轉化為人與某種隱匿力量的關系。因為那種力量是隱匿的,人的自我努力并不能必然達到預設目的,這就具有了或然性。或然性越大,事件性越突出。眾所周知,唐代文人普遍追求科舉的成功,但很多人總是在成功與失敗之間徘徊、掙扎。一舉及第是小概率事件,3年、10年乃至30年方能登科,是大概率事件。王定保《唐摭言》卷八《憂中有喜》條所記公孫乘的求舉之事人所熟知,毋庸贅述。公孫氏“垂三十舉”畢竟有一個與妻闊別而再見面“后旬日登第矣”的喜劇性結局,而李昉等所纂《太平廣記》卷七十四《陳季卿》篇所述半真半幻的赴舉之事則充滿了悲劇色彩。陳氏先有書寫10年不第悲情的《江亭晚望》詩云:“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云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垂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發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陳氏即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棹。”又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風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即將登舟,陳氏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歧。北風微雪后,晚景有云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后,陳氏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子慟哭于家,謂其已為鬼物矣。
這三首詩都屬唐詩之路范疇的作品。陳季卿的行走從江南到西北,空間范圍極為廣闊,在唐代科舉類作品中,這三首詩作為一組詩,空間現場特征非常鮮明,構思也相當奇幻,充滿了悲情。就唐代某個舉子而言,進京趕考之路和歸去之路一般都是固定的。而將舉子們一條條行走路線的作品匯集起來,就構成了唐人被隱匿力量控制的科舉生活史,在唐代社會史中具有重要的史料證明力,其作品則因情感復雜、強烈而深深觸動讀者的心靈。
3.人生的跌宕
唐代詩人進入臺閣后,有時會因遭受貶謫而走出宮廷。他們遠距離行走在闊大的地理空間中,巨大的人生跌宕和心理落差也充斥于所歷之時空。唐人“行走詩”中,此類例子甚多。
如韓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中描述自己被貶潮州的情況與感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朝奏”而“夕貶”言其事件突發性極強,“潮州路八千”形容此行何其艱難!與韓愈最終尚能重返京城相比,柳宗元等一批詩人卒于貶所,更顯示出行走的或然性和悲劇感。文宗朝,相國宋申錫謀去宦官,反為宦官所構,遭貶謫而死。如此悲劇引起詩界震動,產生相當數量的作品,如許渾在《靖恭里感事》中云:“乾坤三事貴,華夏一夫冤。”永貞革新失敗后,劉禹錫在十多年間經歷了貶謫、量移、召回、再貶的過程,這構成了深烙其心境的個人的唐詩之路,不僅為唐詩史拓展了事件維度,也增加了唐詩的思想深度。
較之一般意義上的行走,唐代詩人的征戍、行旅、離別等,往往具有更大的或然性和空間感,其作為唐詩之路的特征更明顯,可論性也更強。由此可以理解,唐詩之路往往與事件具有內在聯系,事件性是唐詩之路的內涵屬性,以事件性為基礎,可以構建具有唐詩之路本質意義的知識觀。
三、經驗:唐詩之路上的詩人感知
“唐詩之路”本身是一個命名。命名是一種語言活動,即用某個語詞概括對某些事物、現象的認知,這種概括得到普遍肯認便成為概念。但從初始命名到概念形成有一個從始端不斷發展的過程,始端命名的意圖是指稱的起源,這個意圖在后來人那里未必一定得到遵循。事情往往總是這樣:已有的言說本身會被再言說,后來的言說者所具有的時代性會影響表達,再言說就成為言說鏈條中的新環節,時代在不斷發展,新環節會不斷產生。
今天作為言說對象的唐詩之路,與最初具體摹狀性的唐詩之路意義同中有異。“路”是唐詩之路堅硬的物理基礎,其“形”其“狀”的物質性作為基本要素不可或缺。但長期以來,隨著對唐詩研究的不斷深化,加之知識生產、地方知識、身體美學、空間哲學等理論有新的發展,對“路”之“性”的感知和認識也會不斷深化和發展。我們不必用一個新的命名對始端名加以區別,但需要用新的感知和認識去進行區別——既區別于始端名的摹狀意圖,又區別于一般的唐詩研究。這種新的感知和認識,形成兼有形下與形上意義的唐代詩人行走大唐的經驗。“經驗是完全異質性的,其中無所不包,以至于其主要的形式難以數清。經驗作為沉淀下來的經歷,承載著使我們的身體與其他有意義的身體相關聯的意義。”[5]雖然經驗的主要形式難以數清,感知的積淀源非常復雜,但它與對象的主要邏輯關系是可以從不同維度去認識的。
1.對行走履跡的感知
雖然唐人的行旅中經常有詩歌作品產生(有些已經亡佚了,有些至今尚存),但并不意味著唐人走過的所有道路都可以視為唐詩之路。唐詩之路既是唐人經歷中的,也是后人意識中的。對唐詩之路的認知基礎是對唐人行走履跡的確認,“履”是行走,“跡”是留痕。行走的普遍性不代表留痕的典型性,沒有典型意義的留痕,需要在唐詩之路的研究中作排他性處理,否則這一問題研究的總體品質將會降低。如果將過于蕪雜的行走納入專門研究,唐詩之路研究將會混同于唐代詩人行履考證與描述,研究的專門性將會被消解。
事實上,在唐代歷史上已經形成一些成為經驗意識的唐詩之路,如南北貫通的汴河道,北方的京洛道、商洛道、塞上道,南方的向吳路、剡溪路、嶺南道等。有學者認為,在唐代存在著多個以都城為中心,以區域名城為支點的交通-文學三角,它們既是穩定的交通框架,也是唐代文學的空間構架,還是研究唐代交通與文學之關系的視角⑤。這個空間架構和關系視角中包含著原生性的唐詩之路,學界已有認知。但我們并不應局限于唐人的意識和經驗,研究中發現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唐人行走履跡如果與唐詩(尤其是經典性作品)的生成緊密關聯,也可以認作唐詩之路加以命名。
2.對行走空間的感知
唐詩之路具有空間概念的意義。空間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象限,“空間從來不是空的:它總是體現出一種意義”[6]。這種意義具有多種內涵:一是自然地理的意義,體現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在一定心境下經過或流連某地,能夠體察地理環境與人類情感相通而形成立體感受。二是社會歷史意義,體現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行走于一個空間,就走進一個社會網格,成為社會的主動或被動的力量⑥。三是人地相須意義,體現主客體之間的互動關系。“文學作品不能簡單地視為是對某些地區和地點的描述,許多時候是文學作品幫助創造了這些地方。”[7]
這里需要特別說明,前文提及唐詩之路的成立與行走空間范圍的廣度有關,這是指的一般情況,也有某種特殊情況,即小空間的行走也可能成為唐詩之路。在西方有著名的海德堡“哲學家小路”,在日本有聞名遐邇的京都“哲學小道”,“一個在西方,一個在東方,相距遙遠,但意境相同,都是在一條靜謐的小路上漫步著人類最活躍、最智慧的頭腦,孕育著啟迪人類靈魂的偉大思想”[8]。那么,在唐代,有沒有這樣的“唐詩小路”呢?我們已知的有杜甫的草堂小路和天臺山的寒山道,應該還有其他。這方面的研究,頗有意味。
3.對行走目的的感知
作為事件的行走總是具有某種背景、動因、目的,行走絕不是一個無意識、無因果的行為。唐人的壯游、漫游既有認識世界、深化對自然的了解的目的,也有積累人脈、擴展人際網絡的目的。具體來說,南人北上往往與干世求名、愿為世用的意識有關;出塞征戍多出于驅胡衛疆、立功報國的志向;貶謫遠方則有某種政治事件或黨派之爭的背景;避難趨行顯然與國家、家庭、人身的嚴重困境相關。這些都屬于常識,即便如此,我們也未必能夠展開歷史大帷的皺褶,真正走進當時社會的“無知之幕”,共享其中所有的信息。我們還需要從歷史史料中勉力發現一些沉寂的真相,使對行走事件的認識更加清晰。
但越是既成的唐詩之路,學者對于“路上人”的背景知識掌握越多,對其目的性了解越清楚;而對一些有待發掘的唐詩之路,相關認識和經驗并不充分。如安史之亂中到江淮逃避戰火者甚多,一些詩人的行走情況昭然,一些詩人的行跡卻較為隱晦。唐代詩歌史上,還有一些詩人生平的末端已是傳說,他們是否還曾有過行走,這種行走與唐詩生成是否具有關系,與他們曾經走進的唐詩之路是否銜接,我們無從了解和把握。在對歷史的考索中,如果有新的發現或合理推斷,都是對唐詩之路的經驗的豐富。
4.對行走美學的感知
中國古代長期存在著行走美學,“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是最典型的表現。行走美學的生發主體是人,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或徒步)行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使身體的感知進入心靈,產生美的感悟,用一定的文學體裁加以表現,美學感知便得以傳達。唐詩之路,是表現唐人行走美學的極佳工具。人們熟悉的陳子昂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登幽州臺歌》),是行走中孤獨而堅韌情感的生發;許渾的“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殘云歸太華,疏雨過中條。樹色隨關迥,河聲入海遙。帝鄉明日到,猶自夢漁樵”(《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其中表現出的凄涼而壯闊的中原秋景非有目的和憂郁感的行走不能道出。
唐人的送別詩,頗似遠行人與送別者共同進行的一種行為藝術表演:近景在周邊,遠景在前方,詩人利用目擊與想象將一實一虛組合起來,構成美學空間,而行者與送者的肢體語言與表情為這個美學空間作出詮釋,達成了完美的統一。唐詩之路的研究,應向哲學思想表達的最高境界努力,至少應有顯示思想傾向的觀點。美學感知介于這兩者之間,使唐詩之路研究在歷史性之外增加了審美意義,這恰恰是唐詩研究不可或缺的。
以上四個方面是唐詩之路概念形成的主要經驗,單獨來看具有基礎性,組合來看具有遞進性。以往研究者在討論唐詩之路時,是以唐詩文本為據的,是在紙上山川中尋找唐人行走的蹤跡、路線、規律,但這是唐詩之路研究的一般路徑,而不是特有企境。只有充分認識唐人的行走目的、行走履跡、行走空間、行走美學,對其加以思想性和美學性的思考,才能由形向意,構成唐詩之路研究審美形態層面的意義。唯有如此,唐詩之路的命名才具有真正的詩性。
結 語
雪萊說:“詩人是世間未經承認的立法者。”[9]這是詩人的榮耀,也揭示出詩歌這一文體的重要意義。唐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典范,從最高意義上說,唐代詩人是一種文化乃至一種文明形態締造的參與者。從這一層面來看,唐詩之路研究獨特的重要意義毋庸置疑。但有一點必須注意,在研究唐詩之路問題上,只能適當吸收、借鑒研究唐代詩人和一代唐詩的理念與方法。對唐詩之路研究,我們不必過度高置其位,以其攝引唐詩學的發展,而是要實事求是將其作為唐詩研究的一個部門、一個方向,回到專門化研究的實際上來。
宇文所安認為,中國文學最為獨特的屬性之一就是“斷片形態”,“作品是可滲透的,同作詩以前和作詩以后的活的世界聯結在一起。詩也以同樣的方式進入它的讀者生活的那個時代”[10]。筆者認為,唐詩之路研究是典型的唐詩“斷片形態”的研究,對于唐代詩人來說,學者研究的是其生命中的一個“斷片”;對于整個唐詩研究來說,唐詩之路也是一個“斷片”。我們不要期待這一研究涉及所有唐代詩人,更不能期待這一研究能覆蓋全部唐代詩歌。在研究中審視全部作品是必要的,試圖調用全部作品則無必要和可能。如果那樣,就是唐詩研究的泛化,而過度泛化會消解唐詩之路研究的學術建設意義和特殊價值。
筆者做這樣的分析、判斷,并不是要降低唐詩之路研究的重要性,恰恰相反,這正是基于其價值性的考量。傅璇琮先生在《唐詩之路:中國文人的山水走廊》中指出:“在世上所有的路中,唐詩之路是一條浪漫而特別的路,是一條隱匿在歷史中的山水人文道路。”[11]這雖然是針對浙東唐詩之路而言的,但其強調的“特別性”對我們今天探討更廣義的唐詩之路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特別”的唐詩之路需要“專門”的研究方法,我們期待這種專門性、特色化的研究在唐代文學整體研究格局中自成其類:通過唐人的行走路程,表現唐人豐富的生活和情感,抉發唐詩書寫的經驗貯存和審美意識。相信路程、生活、經驗作為唐詩之路的三重構境,可以使唐詩研究“依類成化境”⑦——開辟出一片新的人文天地。
注釋
①如寶廷在《偶齋詩草》中云:“從古詩人多入蜀,前有杜高后黃陸。”陳衍《石遺室詩集》亦稱:“古來詩人每入蜀,少陵玉溪及放翁。”②參見史念海:《隋唐時期運河和長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會》,《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頁。③這里的“長三角”是借用現代區域地理的概念,江、浙、皖正在“長三角”范圍內。④司馬遷《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第八》。⑤具體論述參見李德輝:《唐代交通-文學的三角形架構及其文學意義》,《唐代文學研究》(第20輯)2021年第3期。⑥列斐伏爾指出:“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參見列斐伏爾:《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王弘志譯、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頁。⑦“依類成化境”為唐君毅先生之語,參見唐君毅著、黃克劍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唐君毅卷》第四章《依類成化境——觀類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