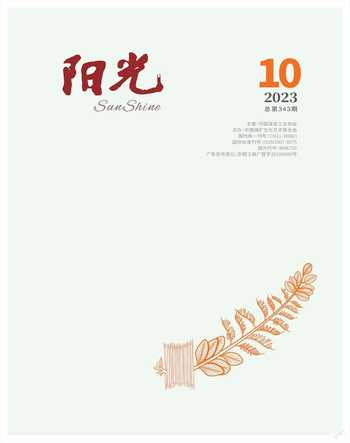我總是寫到雨水和月光
雨水和月光,是兩相悖逆的。因此,雨水浸不透月光,月光洗不白雨水。
縱使如此,我依然總會在我的詩中寫到它們,有時同時寫到,一起氤氳著拆解不開的闌珊詩意。雨水代表著骨子里的灰暗部分,而月光,讓軟下去的骨頭不至于坍塌。
這些年,我親歷的雨水,短促而急迫,蜻蜓點水,羞羞答答,大多數時候似試探和回眸。雨水落下來,在水泥地上濺起短暫的水花和霧氣,然后天放晴,人潮重新淹沒大街,大家永遠平行,各自忙碌,消解著匆忙的人生。月亮越過樓頂的時候,生澀,冷硬,有時蒙著灰暗的面紗,因此我總是懷念它越過山頭和樹梢時的跳脫和靈動,而月光落在水泥大街上和落在飄著麥香的泥地里,是兩種判若云泥的情境。
我想大多數同齡人的人生軌跡都和我差不多,求學后都寄居到小鎮、縣城或都市里,遙遠的故鄉成了人世底色的一種。我總是寫到的雨水和月光,潛藏在遙遠的鄉下,童年的記憶里。那時的雨水,一下就是十天半月,淅瀝如絲,困孩子們于家里,于是象棋、撲克、小人書……成了幼時的主題,而大人們,總是忙碌地披著雨水,孑身如霧,操持著雨天的一切。當月上三竿,院子成了天然的樂園,月光的粉末鋪滿了光滑的青石板,墻上的蓑衣保有人形的勤奮,卡于墻縫中的鐵器泛著幽幽的青光,廢棄的石缸中月亮在埋頭凈身或渴飲,孩子們的黑夜故事、游戲、分享的樂趣,曝于月光之下,充盈著整個村莊。
像一幀幀黑白膠片,夜夜回放于淺眠之巔,回不去的種種消隱于暗影。回憶驅動追思,我寫下的一首首詩都是以此為背景的,雨水和月光,沖刷著一條暗河的始末,上游清冽,中游激蕩,下游略微渾濁,耗盡一生的筆墨,也無法使一條帶著濁意的河流回到雨珠。
然而,我還是要寫。
我寫到高大松樹杈上裸露的鴉巢,不畏懼我們高舉于竹竿頂端的鐮刀;我寫到被母親鋤成兩截的劇烈蠕動的蚯蚓,疼痛在泥巴里明目張膽而熱烈;我寫到母親為了讓開一個圓鼓鼓的土豆眼睜睜看著鋤頭狠狠砸到腳踝;我寫到土豆們借著自己的肉體凡胎奮力長出墻縫,心懷壯大家族的美好愿望;我寫到落日越過峽谷時掀動垂于江面上的茅草,釣出了沾著黃金顆粒的魚骨;我寫到月光藏身寄居喜鵲的墻洞,多年后醉成了思鄉的佳釀;我寫到爺爺生前躺過的烏竹搖椅,月色里永遠保有健朗的高大人形;我寫到黃土和白蟻群斷開的生死,墓碑上加黑框的文字,大風揚起落滿霜跡的紙幡;我寫到微甜,寫到酸楚,寫到苦澀;我寫到欣喜,寫到憂傷,寫到夜長夢短……
在雨水和月光中,自己的前半生才會飽滿且明亮。我的中學時因錯誤選擇而反復迂回的迷津,高校中未志得意滿而反復碰壁的迷惘,畢業時不知所措倉皇前往異域,回國后悻悻然客居小城,后調動,后辭職改行……這一路上,雨水大于日光,月色總是凄迷。如果可以回去,我想我還是那個風雨中一路泥濘,心懷月光的人。二十年了,如果沒有雨后的爽朗月色,我的詩會蒼白枯味如同殘蠟。
很多人歆羨我現在擁有心儀的工作,貌似美滿的人生,指向清晰的前程。一個治愈文字的人,卻治愈不了自己的破碎。一個在自己制造的汪洋中左奔右突的流亡者,還要頂住浪花的嘲諷和踐踏。一個自我傷害自我療愈的人,一個一邊放棄一邊挽回的人。
一個風雨客,在月光之海打撈滯重的影子。
胡興尚: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詩歌見于《人民文學》《中國作家》《青年文學》《詩收獲》《星星》《草堂》《江南詩》《長江文藝》等多家刊物及各種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