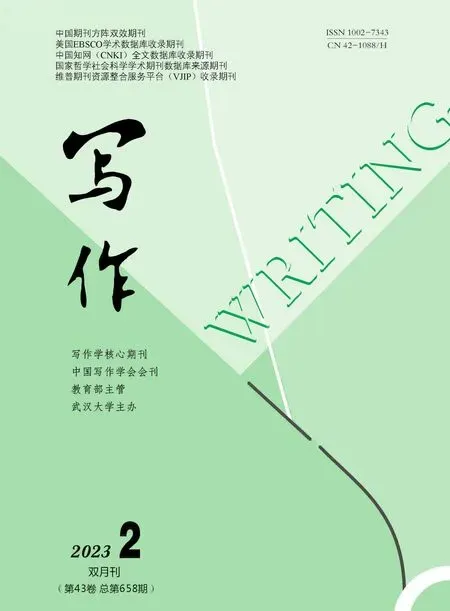欲望倫理學(xué)視域下《庭院中的女人》“情欲救贖”主題書寫
田榮昌
美國(guó)文本主義批評(píng)論的代表性人物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瑞恰茲(I. A. Richards,1883—1981)等認(rèn)為,文學(xué)作品的藝術(shù)價(jià)值是通過作品本身的“自足性”“獨(dú)立性”來實(shí)現(xiàn)的,意即考察文學(xué)作品的藝術(shù)性需要對(duì)作品本身進(jìn)行切實(shí)的文字分析,要做細(xì)讀式批評(píng),而不需要考慮太多外在因素,如作者身份和背景、作品生成的時(shí)代、社會(huì)、宗教、倫理、政治等附庸性因素①孔智光、蔣茂禮:《文藝批評(píng)方法論》,山東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136頁。。這種觀點(diǎn)無疑會(huì)割裂文學(xué)作品與其賴以生成和傳世的歷史的、社會(huì)的、政治的、經(jīng)濟(jì)的等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文學(xué)作品的誕生,離不開特定的社會(huì)背景。特殊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往往賦予文學(xué)作品與眾不同的文學(xué)價(jià)值或文化意義。因此,要對(duì)一部文學(xué)作品做出較為可靠合理的解讀,也許有必要綜合考量以上所述的看似外在的、不重要的或游離于作品之外的隱性要素。這些因素也是一部文學(xué)作品能夠被合理解讀的重要條件。
《庭院中的女人》(Pavilion of Women)是一部寫實(shí)主義與浪漫主義相交織的敘事小說,反映了戰(zhàn)火紛飛、民不聊生的舊中國(guó)歷史背景下江南封建家族吳府的興衰起落,以及在新舊交替的重大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吳府每一位家庭成員個(gè)體命運(yùn)何去何從。小說的作者,被稱為“中西文化之橋”的美國(guó)作家賽珍珠(Pearl S.Buck),是一位出生于美國(guó)卻生長(zhǎng)于中國(guó)的跨國(guó)籍、雙重身份的西方作家。她在用英文創(chuàng)作這部關(guān)于舊中國(guó)舊式封建家庭的小說時(shí)的寫作動(dòng)機(jī)是什么,她要給西方讀者傳達(dá)什么樣的思想和主題,西方讀者的閱讀視域應(yīng)該放在哪里等問題令人深思。這些問題也是深入解讀賽珍珠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關(guān)于舊中國(guó)小說作品的關(guān)鍵點(diǎn)。
一、《庭院中的女人》的視角和主題思想
首先是賽珍珠的雙重身份,賦予了其小說作品獨(dú)特的“視野”和“視角”。賽珍珠于1892年出生于美國(guó)一個(gè)傳教士家庭,出生4個(gè)月便被父母帶到中國(guó)江蘇鎮(zhèn)江生活。在這里,賽珍珠度過了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shí)期,其間,她曾數(shù)次短暫返美。因此,中國(guó)江蘇南京及其他南方各地的長(zhǎng)期工作和生活經(jīng)歷成為賽珍珠前半生最重要的人生體驗(yàn)和創(chuàng)作來源。1934年她徹底離開中國(guó),雖然她曾計(jì)劃重訪中國(guó),但因種種復(fù)雜原因未能成行。40余年豐富直觀的中國(guó)文化背景和親身體驗(yàn)的生活經(jīng)歷成就了賽珍珠獨(dú)特的“他者(The Others)”和“我者(Self-being)”雙重身份。她既是中國(guó)文化的“旁觀者(Beholder)”“看客(Spectator)”,同時(shí)又是中國(guó)文化的親歷者、參與者和敘述者。可以說,賽珍珠身上雖然流著美國(guó)人的血,攜帶者西方文化的原初基因,但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卻潛藏著中國(guó)文化的主體意識(shí)和思想觀念。美式的原初思想和意識(shí),總與潛藏涌流在她內(nèi)心深處的中國(guó)人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價(jià)值取向、情感趨向、文化品味、生活場(chǎng)景,甚至儒家傳統(tǒng)思維交織互滲,既相互碰撞,又彼此融合;既有沖突和抵牾,又有媾和與讓步。這一點(diǎn)從1922年起她所創(chuàng)作的有關(guān)中國(guó)的文學(xué)作品中都可覓其蹤跡,辨其蛛絲。
尤其是1932年為她帶來美國(guó)普利策小說獎(jiǎng)、1938年又為她帶來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反映中國(guó)農(nóng)民生活的長(zhǎng)篇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1931)一書,更能體現(xiàn)出她的這種矛盾雙元的文化心理和雙語文化意識(shí)。她在諾獎(jiǎng)獲獎(jiǎng)感言里說,是中國(guó)小說,而非美國(guó)小說成就了我的小說創(chuàng)作……我的早期關(guān)于故事的所有知識(shí),如何講故事、寫故事都來自中國(guó)……中國(guó)人的生活亦是我的生活……在心靈上,我的第二故鄉(xiāng)(my foster country)是中國(guó)。她也曾多次表示,漢語是她的第一語言,江蘇鎮(zhèn)江是她的中國(guó)故鄉(xiāng)。可以說,賽珍珠是第一位在美國(guó)出生、在中國(guó)成長(zhǎng)的身份極為獨(dú)特的西方作家,可謂“腳踏中西,心念中美”。1973年3月6日,賽珍珠帶著未能在生前重返第二故鄉(xiāng)的遺憾離世。尼克松總統(tǒng)在致賽珍珠的悼詞里稱她是“一座溝通東西方文明的人橋……一位偉大的藝術(shù)家,一位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人”①[美]賽珍珠:《我的中國(guó)世界》,尚營(yíng)林等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譯序第2-3頁。。
其次是她主動(dòng)參與中國(guó)大事件的西方創(chuàng)作者意識(shí)為其作品帶來了與眾不同的主題思想:她試圖通過西方人的寫作方式深度剖析舊中國(guó)民眾,尤其是舊式女性多被忽略的人生觀、生存觀和情欲觀。《庭院中的女人》即是以西方女性寫作觀和“他者”視野來反映舊中國(guó)封建家庭中不同女性身份和命運(yùn)的敘事體小說。該部小說雖然算不上賽珍珠最負(fù)盛名的作品,但其中所流露出的中西合璧的文化價(jià)值觀和認(rèn)同感,對(duì)舊式中國(guó)女性內(nèi)心情欲和主體欲望的探索尤為突出。該部小說于1946年在美國(guó)發(fā)表,中文節(jié)譯本于1948年由上海百新書店發(fā)行,取名《深閨里》,但爭(zhēng)議頗多。1998年,漓江出版社發(fā)行劉源平、王守仁、張子清的全譯本,采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書名《群芳亭》。小說一經(jīng)面世,便引起中西方讀者的廣泛關(guān)注,并多次重印再版,備受好評(píng)。2001年美國(guó)銀夢(mèng)電影公司與北京電影制片廠聯(lián)合將其改編為電影,取名《庭院中的女人》公開上映。本文所依版本為2002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的新銳翻譯家黃昱寧女士翻譯的中譯版②[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之所以選擇該譯本,不僅在于譯者超越固化的女性主義這一單一的文本翻譯技巧和視角,更在于其細(xì)微而縝密地再現(xiàn)了小說文本中女性最不為人知或有意回避的“情欲”欲求的本真和內(nèi)里,在于其設(shè)定的“庭院(物理空間)”與“女人(情感主體)”之間的矛盾關(guān)系。
小說選取1938年中國(guó)江南某小鎮(zhèn)為故事發(fā)生的宏觀社會(huì)背景,此地遠(yuǎn)離正處于日本帝國(guó)主義入侵者鐵騎蹂躪下的中國(guó)北方①[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頁。。在看似平靜了無微瀾的大環(huán)境下,主人公吳太太那感人至深又令人扼腕嘆息的“情欲救贖”之路正緩緩開啟。
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guān)鍵歷史時(shí)刻,偏安江南小鎮(zhèn)的首富吳家,仍按部就班地延續(xù)著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多數(shù)富裕大家族所恪守的生存方式——男主人吳老爺廣置田產(chǎn),重積農(nóng)桑,殷實(shí)家財(cái);吳太太愛蓮恪守婦道,相夫教子,竭盡所能輔助吳老爺打理好吳家上下婚喪嫁娶等諸番事務(wù)。在二十四載婚姻生活中,吳太太覺得這一切都是命運(yùn)使然,她對(duì)此心滿意足,毫無違和感。但在40歲的某個(gè)早晨,從夢(mèng)中醒來的吳太太,突然意識(shí)到自己的人生豈能如此度過。她要沖出吳家這座令人窒息的老宅,沖破久久捆縛自己的封建禮教,與24年來自己并不愛的吳老爺分房而居。
相夫教子多年的吳太太,在時(shí)年40歲的某個(gè)早晨,睡醒之后,突然萌生出這樣從未有過的忤逆?zhèn)鹘y(tǒng)、違背倫常、不合時(shí)宜的念頭,表面看似乎難以理解。但實(shí)際上,深入小說文本,細(xì)讀文字就不難發(fā)現(xiàn),吳太太與其丈夫吳老爺起初的分房而居,只不過是她肉體層面的斷舍和隔離,是她淺層或者說初級(jí)不自覺“情欲救贖”意識(shí)的外化表現(xiàn)和行為反應(yīng),也是吳太太擺脫傳統(tǒng)道德對(duì)女性“理性約束”需要突破的第一步。此時(shí),吳太太并未有非常明確和顯性的“自我”意識(shí),而是出于傳統(tǒng)的認(rèn)知,即女性完成生兒育女的基本使命后便無法帶給丈夫更多的肉體歡愉所做出的讓位。讓位于下一位年輕美貌身體健康的女性——即主動(dòng)替丈夫納妾。但這種意識(shí)仍未跳脫出女性作為男性附庸的傳統(tǒng)認(rèn)知。
依照拉康的欲望倫理學(xué)觀點(diǎn),“無知”的激情和欲望是驅(qū)動(dòng)人性的原初動(dòng)力,類同于弗洛伊德提出的“力比多(Libido)”,它潛藏于人性的最深處,是人獲得情欲幸福感的本初和源泉。但在拉康看來,人的“無知”的欲望有別于動(dòng)物,它本身包含著“合理性”,是理性思維與理性欲求相結(jié)合之后的產(chǎn)物。“理性的統(tǒng)治仍然是貫徹全局的,這就保證了選擇的正確性,由此也就保證了作為選擇結(jié)果的行動(dòng)的正確性。”②盧毅:《欲望、思維與行動(dòng)——從拉康的視角探討精神分析倫理學(xué)與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哲學(xué)動(dòng)態(tài)》2015年第2期。因此,要實(shí)現(xiàn)人性的自由,獲得獨(dú)立的人格,人最終要超越“無知”的激情而做出正確的選擇,要從淺層的滿足上升到“至善”的高級(jí)階段。
而吳太太之后在精神和情感層面上與吳老爺?shù)膹氐讛嚯x,毅然決然地劃清界限,跳出前半生任人擺布缺乏自主的“情欲空間”,則是其“情欲救贖”得以完成的最高象征,遠(yuǎn)遠(yuǎn)超過女性主義意識(shí)覺醒這一淺顯層面。弗洛伊德認(rèn)為“文明制定了道德倫理的律令,對(duì)律令的違背會(huì)給主體帶來負(fù)罪感……文明發(fā)展壓抑了主體本能,兩者產(chǎn)生了對(duì)立和沖突”③趙淳:《拉康的精神分析倫理學(xué):一種批判的姿態(tài)》,《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2021年第5期。。中國(guó)古代的封建倫常對(duì)傳統(tǒng)女性的禁錮非同一般,吳太太概莫能外,因此,她在肉體上與吳老爺?shù)臄嗌犭x,可視為吳太太摒棄負(fù)罪感,使自己的“主體欲望”沖破抑制,開始實(shí)施“欲望救贖”的第一步。跨出第一步最直接最有力的“催化劑”是她為三兒子豐漠請(qǐng)來的洋人家教意大利傳教士安德烈先生,即拉康所謂的主體受到來自“大他者”的外力的驅(qū)使和激發(fā)。
賽珍珠在小說中設(shè)定的安德烈這一傳教士身份,既符合當(dāng)時(shí)西方殖民思想逐漸傳入中國(guó)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也反映出她希望借助于自視為文明的“他者文化”來喚醒和拯救無數(shù)個(gè)像吳太太一樣,被舊中國(guó)傳統(tǒng)禮教褫奪去個(gè)人幸福的舊式女性,激活她們作為女性原本就應(yīng)該得到的情欲和身份——既包括性、性別、女性身份和意識(shí)、女性地位等。沒有安德烈,吳太太也許充其量只能做到與丈夫吳老爺在肉體上的斷舍離,不太可能領(lǐng)悟到自己人生的幸福和愉悅更多地來自尊重吳家大家庭里每個(gè)人的選擇,讓他人獲得充分的自由;放手一切外物和他人的牽絆和羈縻,讓自我游離于自然無為的狀態(tài)之中。沒有安德烈,吳太太更不會(huì)在后半生有“怦然心動(dòng)”的內(nèi)心暖流,不太可能體會(huì)到輾轉(zhuǎn)反側(cè)夜不能寐的“思念一個(gè)人”的感覺,更無法體會(huì)到與一個(gè)洋人在靈魂層面相知相交的滿足感和幸福感——這一切都是她的情欲被后者激活被喚起的復(fù)雜而糾葛的心理折射和行動(dòng)表現(xiàn),也是她“情欲救贖”之路從量變到質(zhì)變,從“無意識(shí)”到“有意識(shí)”的精神衍化過程的外化,也是拉康所說的個(gè)體在追求從肉體到精神的欲望滿足過程完成之后所獲得的“最高境界的愉悅感(jouissance)”。
二、女主人公吳太太的“情欲救贖”心路歷程
該部小說塑造了一系列舊中國(guó)傳統(tǒng)女性形象,但吳太太無疑是體現(xiàn)作者賽珍珠女士對(duì)舊中國(guó)傳統(tǒng)女性命運(yùn)特別關(guān)注的代表性人物,將作者對(duì)舊中國(guó)傳統(tǒng)女性的美好理想和信念集于一身。作者希望舊式中國(guó)女性找回自我,獲得獨(dú)立人格,實(shí)現(xiàn)女性情欲自由,滿足個(gè)體欲望,對(duì)吳太太寄予厚望。因此,吳太太的形象是現(xiàn)實(shí)主義與浪漫主義合二為一的“情欲”鏡像。40 歲之后的吳太太,經(jīng)歷了心靈與肉體、意志與情感、欲望與信仰幾個(gè)層面的糾葛和斗爭(zhēng),從而完成了她“情欲救贖”的心路歷程。
(一)脫離肉體束縛——情欲萌芽
事實(shí)上,吳太太的“情欲救贖”之路之所以得以圓滿,是因?yàn)樗?jīng)歷了“無意識(shí)”到“意識(shí)”的漸進(jìn)過程。拉康的“欲望倫理學(xué)”與瑞士心理學(xué)家榮格對(duì)人類“意識(shí)”與“無意識(shí)”關(guān)系的闡釋似乎有比較相似的指歸:“猶如一個(gè)島的可見部分,在意識(shí)的下面一層,即島的可見部分的下面則是大部分未知的部分,是屬于個(gè)體的個(gè)人無意識(shí),它是一個(gè)神秘的隱藏著的底層,是由一切沖動(dòng)的愿望、模糊的知覺以及無數(shù)的其他經(jīng)驗(yàn)組成的。它們?cè)?jīng)一度是意識(shí)的,但由于被遺忘或受壓抑而在意識(shí)中消失了。由于它們的內(nèi)容大部分是情結(jié),因此來自個(gè)人無意識(shí)的偶然事件也有可能被召回到覺醒的意識(shí)中來。”①程孟輝:《西方美學(xué)文藝學(xué)論稿》,商務(wù)印書館國(guó)際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543-544頁。不難看出,吳太太的“情欲救贖”其實(shí)在40 歲之前是潛藏在內(nèi)心深處的一股暗流,是以“無意識(shí)”方式存在的種種“意識(shí)”,諸種“意識(shí)”一旦沖破壓抑個(gè)人情感的藩籬和拘囿,必將得到徹底的精神和心靈層面的釋放——也意味著吳太太“情欲救贖”歷程的徹底實(shí)現(xiàn)和本我的完全回歸。
像吳太太這樣讀過不少書的聰慧女性,即使受到中國(guó)傳統(tǒng)封建禮教的束縛和禁錮,只要受過一定的教育,一定會(huì)渴望自由而浪漫的愛情。所以,盡管吳太太與丈夫吳老爺徹底分居,但在她的潛意識(shí)里,仍然對(duì)“情欲”充滿著無限的期待和想象。
24年前,新婚燕爾之際,當(dāng)她的公公吳老太爺問吳太太,為何愿意嫁給他兒子時(shí),她的回答“我愛他”三個(gè)字,令吳老太爺瞠目結(jié)舌,因?yàn)樵趨抢咸珷數(shù)男哪恐校约旱膬鹤邮恰耙粋€(gè)成不了事的窩囊廢”。但“情欲救贖”這個(gè)話題,與這24年間的吳太太并無太大關(guān)系,因?yàn)樵诼L(zhǎng)歲月里,她并未從丈夫吳老爺身上享受到愛情的滋潤(rùn),并未得到過任何欲望的滿足,無論肉體還是精神。她“費(fèi)盡了心機(jī),不論大事小情,都讓他順心遂意。……這么多年來,他從來沒有什么愿望是滿足不了的”②[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8-89頁。。這并不意味著吳老爺不愛她,而是他無法理解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愛情”,他要的只是酒足飯飽之后滿足自己肉體上的欲望,而妻子只不過是讓他完成這一行為的物質(zhì)工具。在愛情上,吳老爺與吳太太是兩條永遠(yuǎn)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線。吳太太的愛情世界,一直是一片浩瀚無際的荒漠,她如同一朵依舊美麗的蓮花,渴望著愛情雨露的潤(rùn)澤。而如今,愛情對(duì)于吳太太,或許和她尋找到女性的自我和完成情欲救贖緊密相關(guān),甚至有些混同難辨,就連她自己都有些困惑。
中國(guó)古代用來約束女性身心的封建禮教可謂歷史悠久。“男女授受不親”“夫?yàn)閶D綱”等道德準(zhǔn)則令女性無法獲得與男性等同的地位和尊重,而是淪為男性的附庸物,甚至犧牲品。女性不但被視為玩物,甚至是歷史興亡的肇端。所謂“紅顏禍水”,多少個(gè)王朝的衰變最終無端地推給女人。而男權(quán)社會(huì)未給予女人任何公正的評(píng)價(jià),尤其作為女性婚姻忠貞最高象征的“貞節(jié)牌坊”,其實(shí)是給意圖實(shí)現(xiàn)基本人性的女人扣上一幅決然不可卸下的“緊箍咒”。所以,西方社會(huì)女權(quán)主義者“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主張?jiān)谥袊?guó)封建體制下很難實(shí)現(xiàn),封建婚姻中的女性更無從談及什么“愛情”。因此,吳太太決然與丈夫吳老爺分房而居,這種做法似乎是極其忤逆封建綱常倫理的行為。在吳太太經(jīng)夏修女介紹,給兒子引見家庭教師、來自意大利的傳教士安德烈之后,在她內(nèi)心至深處,所暗藏的“情欲”開始被激活。
“在抗日時(shí)代的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是一個(gè)雖曾受過現(xiàn)代化的洗禮而顯然尚非相當(dāng)開放的時(shí)代”①葉維廉:《葉維廉文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頁。,對(duì)于深受封建傳統(tǒng)禮教熏染的吳太太,這種情感欲求雖然沒有可以讓它顯性外化的社會(huì)土壤,但她像少女一樣對(duì)如安德烈一樣偉岸高大的男子心生愛慕之情也是情理之中。少女懷春,古已有之,即使是三千年前的“詩經(jīng)”時(shí)代,也有女性大膽表達(dá)愛意的不少詩篇,何況已經(jīng)是社會(huì)開化的民國(guó)時(shí)代。所以,讀了不少書的吳太太,內(nèi)心深處的“無知”激情便逐漸轉(zhuǎn)化為“有意識(shí)”的主體情欲追求。
(二)尋求精神依托——情欲升華
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對(duì)人類的愛情有如此看法:“心靈的愛情在腰部以上,肉體的愛情在腰部往下。”②[哥倫比亞]加西亞·馬爾克斯:《霍亂時(shí)期的愛情》,蔣宗曹、姜風(fēng)光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頁。這句話道出了人類情欲的本質(zhì):肉體上,吳太太擺脫了作為吳老爺生兒育女工具的身份,也不再是供丈夫吳老爺酒足飯飽之后泄欲的被動(dòng)角色。“多少年來,她為了盡責(zé),性情倍受壓抑,靈魂苦苦等候,然而那與生俱來的靈性仍舊在慢慢成長(zhǎng),不錯(cuò),就在恪盡職守的同時(shí)成長(zhǎng),在重重束縛中成長(zhǎng),等待著脫離苦海的那一天。”③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102、131-132頁。
徹底擺脫肉體束縛后的吳太太,孑然于外,游離于吳家寬闊的“物理空間(高墻大院)”與孤獨(dú)的“精神空間(封建禮教)”之外。“時(shí)光悄然流逝,她的魂靈兒仿佛出了竅,兀自在天地間神游。”④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102、131-132頁。一有空,她就躲到吳老太爺?shù)臅浚プx那些原本不讓她碰的禁書。這些書大多是關(guān)于男歡女愛,是獨(dú)立精神追求真愛,獨(dú)立意識(shí)反抗封建禁錮的精神食糧。讀得多了,吳太太自然會(huì)渴望兩個(gè)平等靈魂的自由愛戀。“然而,事實(shí)上她真的是太寂寞了,根本沒有人能探知她的靈魂。她的靈魂所能企及的空間,遠(yuǎn)遠(yuǎn)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疆界,早已飛出了這安置著她肉身的四面圍墻。”⑤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102、131-132頁。
“意大利傳教士安德雷(黃煜寧譯安德烈,筆者注)作為兒子的家庭教師適時(shí)來到她身邊,二人思想上的交流、感情上吸引、靈魂上的拯救隨之開始。”⑥梁香偉、姚慧卿:《不一樣的救贖:宗教救贖與人性救贖——賽珍珠的〈群芳亭〉與多麗絲·萊辛的〈野草在歌唱〉比較分析》,《宿州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0年第3期。安德烈初次踏入象征著封建禮教的“吳家大宅”便給吳太太留下了極其獨(dú)特而深刻的印象,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對(duì)她的感官世界帶來的巨大沖擊,叩開了她長(zhǎng)久閉合的“無知”激情的大門。
首先來自聽覺的沖擊——他的充滿磁性的男性聲音:“恰在此時(shí),她聽到院子的圓洞門那邊傳來一個(gè)低沉渾厚的聲音。‘太太!’她一直在等著這聲音響起來,卻沒料到它的力道會(huì)這么足。”①[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137、139頁。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吳太太便被這渾厚有力充滿雄性荷爾蒙的聲音給攝住了,不像吳老爺,在吳太太面前,總是不敢大聲說話,有些唯唯諾諾,缺乏男人氣概。
其次是來自視覺的沖擊——他的有力的“大手”:“她從蘭花叢中仰起臉,看見一個(gè)高個(gè)子、寬肩膀的男人,身穿一襲褐色長(zhǎng)衫,腰間系著一條繩子。這便是那牧師了。他的右手緊握著掛在胸口的十字架。她知道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可她對(duì)此全無興趣。讓她感興趣的是那只握著十字架的手,那么大,那么有力。”②[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137、139頁。這種力量,吳太太從未在丈夫身上感受過,丈夫在她的內(nèi)心總是那么孱弱和無力。然后是“眼神”——他的“眼神”:“他皮膚黑黝黝的,眼窩深陷,一雙大眼睛嵌在里面,顯得清澈而憂傷。……安德烈教士意味深長(zhǎng)地看了她一眼。盡管他的眼神頗有穿透力,卻并不顯得鹵莽,也沒把吳太太嚇著。那目光里沒有什么感情色彩,就好比有人舉起了一盞燈,替別人照亮了一條未知的路。”③[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137、139頁。這種眼神,眼神里的光芒,在她沒有遇見安德烈之前,也從未見過。
再之后是“語言的觸碰”。語言雖然是非物質(zhì)的,但卻可以對(duì)語言的實(shí)施者,即人這一實(shí)體產(chǎn)生具體的行動(dòng)力。安德烈的一句話卻深深地刺入了吳太太的心靈中,“他平靜地說,‘可是我拿不準(zhǔn)你是不是快樂’這話說得波瀾不驚,卻鋒利得如同一把看不見的刀,刺穿了吳太太,可她又說不清究竟扎在哪里。她慌忙矢口否認(rèn),‘沒有的事,我快樂得很。’……她繼續(xù)說,‘我過得快活極了,頂多就是自個(gè)兒覺得還需要多長(zhǎng)點(diǎn)見識(shí)。’‘或許不完全是長(zhǎng)見識(sh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對(duì)你已經(jīng)知曉的東西能有更深的理解’”④[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137、139頁。。安德烈一席話突然觸動(dòng)了吳太太沉睡已久的心,讓她深埋內(nèi)心的“情欲”開始蘇醒。40歲以前,她早已忘記了自己作為女人應(yīng)有的快樂。首先,她把自己完全交給了丈夫,能讓丈夫心滿意足,為丈夫生兒養(yǎng)女,似乎是她24年間唯一的快樂來源。或者說她把自己完全交給了繁雜的家族事務(wù)和龐大復(fù)雜的家眷妯娌而難以抽身,根本沒有意識(shí)到何為自己的“快樂”。安德烈寥寥數(shù)語,如同黑暗中劃過的一道亮光,一下子觸動(dòng)了吳太太沉睡已久的“自我意識(shí)”。
有研究者認(rèn)為,賽珍珠在該部小說中特意安排了夏修女和安德烈兩位宗教人物,其用意是希望以西方基督教思想來救贖吳太太,這種觀點(diǎn)有待商榷⑤延緣:《賽珍珠的宗教觀與文學(xué)表象——以〈東風(fēng)·西風(fēng)〉、〈大地〉、〈群芳亭〉為例》,《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學(xué)報(bào)》2015年第6期;鐘翼:《〈群芳亭〉中賽珍珠的宗教觀》,《鄂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5年第7期;陳超:《中西宗教觀的共融——賽珍珠作品〈群芳亭〉中的宗教觀》,《長(zhǎng)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年第2期;陳超:《寬容與仁愛——從〈群芳亭〉與〈龍子〉透視賽珍珠的宗教觀》,福建師范大學(xué)2011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許硯梅、宋艷芬:《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從小說〈群芳亭〉透視賽珍珠的宗教觀》,《電影評(píng)介》2007年第14期。。實(shí)際上,賽珍珠雖然出生于美國(guó)傳教士家庭,其父親賽兆祥雖然篤信基督教,而且被派往中國(guó)的使命也是傳播基督教信仰,但他對(duì)中國(guó)的儒學(xué)和佛學(xué)思想并不抵觸⑥宋穎:《和而不同,美美與共——評(píng)賽珍珠小說〈東風(fēng)·西風(fēng)〉》,《山花》2015年第20期。。賽珍珠深受其父親博愛、寬容、平等等思想意識(shí)的影響,由此形成了她多元化的宗教思想,并不認(rèn)同單一宗教和基督教的救贖功能。甚至于“耶穌會(huì)期刊《美國(guó)》(America)把賽珍珠稱為‘……失去了對(duì)宗教的忠誠(chéng)與熱愛’”⑦[美]葛蘭·華克:《賽珍珠與美國(guó)的海外傳教》,郭英劍、馮元元譯,《江蘇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7年第3期。。基督教信仰也許僅是賽珍珠意識(shí)形態(tài)之表,其里則是超越宗教功能的人性中的“至善”——寬厚博愛、仁義忠信。“賽珍珠在作品里,卻恰恰體現(xiàn)出要以救拔困苦、樂善好施等實(shí)際行為建立一個(gè)充滿溫情、博愛的人間天堂。事實(shí)上,她信奉的惟一宗教就是愛的宗教。”⑧張春蕾:《寬容仁愛平等——賽珍珠的宗教理念》,《中國(guó)宗教》2004年第12期。
在賽珍珠看來,基督教信仰并不能救贖吳太太。由此,夏修女這一身份,即成為與安德烈教士構(gòu)成鮮明對(duì)比的特定人物設(shè)計(jì)。夏修女喋喋不休地給吳太太傳輸基督信仰的行為,以及為了宗教信仰而放棄婚姻和愛情的做法,在吳太太眼里顯得迂腐而可笑。真正激發(fā)和觸動(dòng)吳太太的是潛意識(shí)之下的人類共通的“情欲”原初力。安德烈雖有傳教士身份,但他來中國(guó)的目的并非是宣揚(yáng)“上帝”的旨意。安德烈代表他自己,帶著胸懷天下解救他人疾苦的壯志來到了中國(guó)。在吳太太眼里,安德烈不像夏修女那般愚鈍冥頑地陷入宗教說教之中。他是一位謙謙君子,不做作,不沉淪,不虛偽;肉體上,他清心寡欲,不食人間煙火;道德上,他正直無私,以救濟(jì)蒼生為終身使命;情感上,他純粹而博愛,以慈愛寬宥世俗之惡。“一時(shí)間,她心里涌起一種奇異的感覺,恍若身處兩個(gè)世界之間。……她站在那里側(cè)耳細(xì)聽,似乎在等著他呼喚。”①[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7、147-148、166、150、150-151頁。這些美好的字眼她從來沒有從自己別無愛好的丈夫吳老爺?shù)纳砩峡吹竭^。
安德烈第二次來吳府給豐漠上英文課前為吳太太母子二人背了一首詩:
“當(dāng)黎明來臨,曙光初綻,
光線不只從東窗照進(jìn)來。
前方,太陽緩緩升起,何其緩慢!
且慢,向西看,大地一片絢爛!”②[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7、147-148、166、150、150-151頁。
“吳太太和豐漠凝神聆聽,字字如純水,沁人心田。……房間的四面墻似乎在漸漸消失;而她在其中過了大半輩子的院墻也在向后退。有那么一會(huì)兒工夫,她的視野無比清晰。……她很想呆著不走,聽安德烈教士講下一課。”③[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7、147-148、166、150、150-151頁。這首詩有非常明顯的隱喻性,“西方”正是帶給吳太太光明,開啟她的“情欲”的地理源點(diǎn),但她并不清楚“西方”到底是哪里。安德烈來的地方,就是“西方”,就是吳太太暗黑情欲世界里的啟明燈。雖然安德烈因?yàn)樨S漠與琳儀新婚而好久未到吳府來教課,但他在吳太太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因好久未見而被她淡忘,反而愈發(fā)強(qiáng)烈,“她其實(shí)抱著這樣的信念,那些一味耽于肉身享樂的人,會(huì)隨著肉身的消亡而消亡。在她的想象中,安德烈教士即便沒了肉身也能活下去。”④[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7、147-148、166、150、150-151頁。
當(dāng)然,吳太太絕不可能做出任何違背婚姻或忤逆?zhèn)惓?缭饺怏w的出格之舉,她此時(shí)對(duì)安德烈的情感(也許此時(shí)尚不能稱為“情愛”),僅發(fā)于心,止乎禮,禁于行,她是不會(huì)讓任何人察覺到自己內(nèi)心的“波瀾涌動(dòng)”。雖然愛情的火苗僅瞬間迸發(fā),但對(duì)于封建禮教禁錮下的中國(guó)舊式女性卻是破天荒的大事。吳太太從未對(duì)丈夫有過絲毫這種心動(dòng)的感覺,這一點(diǎn)在其閨蜜康太太直挖心底的盤問中暴露無遺,“愛蓮,也許你福氣好(指吳太太不用承受四十歲后懷孕的尷尬和痛苦,筆者注),因?yàn)槟悴幌矚g你的男人⑤[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7、147-148、166、150、150-151頁。。”“誰能想到,此時(shí)此刻,吳太太那一顆心兒,竟會(huì)被一種難言的痛楚扭結(jié)成一團(tuán)?……她仿佛站在山尖上,四周全是冰,冷冷的,煢煢孑立,茫然若失。她想哭出聲來,喉嚨卻發(fā)不出聲音來。暮色替她掩飾了慌張。康太太看不出她的臉已是一片刷白,雖然康太太全神貫注,還是沒能發(fā)現(xiàn)吳太太的身子在一陣緊似一陣的恐懼中僵硬起來。……在這莫名的恐懼中,吳太太看見了安德烈教士。牧師龐大挺拔的身軀恰巧出現(xiàn)在她孤獨(dú)的時(shí)刻,因?yàn)橐f話,孤獨(dú)感散了開去。”⑥[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7、147-148、166、150、150-151頁。就在吳老太太去世后不久,吳家不再像昔日那般寧靜:先是秋明告訴吳太太她懷上了吳老爺?shù)暮⒆樱瑓翘嬷獏抢蠣斶@一重大消息時(shí),“兩個(gè)人的笑聲融會(huì)在一起,過去,他們生活在一起的時(shí)候,這樣的笑聲有過多少次啊,如今,他們又憑借這笑的橋梁重逢了。就在這笑聲中,她突然覺察到了真相。她不愛他,從來就不愛他”①[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79、219、185-186、191、193頁。。這一事件標(biāo)志著吳太太與吳老爺從肉體關(guān)系到情感紐帶的徹底斷裂。在她心里,肉體和靈魂組合就像建房子,身體是地基,精神靈魂是屋頂、裝飾,為房子錦上添花,沒有了地基,其它都是徒勞。所以,吳太太從肉體上與吳老爺?shù)膹氐赘顢啵匀徽劜簧暇窈挽`魂上的默契了。
再是豐漠與琳儀婚后爭(zhēng)執(zhí)不斷,萌萌、若蘭、琳儀妯娌之間互生齟齬,令吳太太心煩意亂,她認(rèn)為是吳老太太的靈魂在吳宅里游蕩而不得安生,因此想超度吳老太太的靈魂以求得家庭平靜。解決這一難題的出路,吳太太首先想到的不是中國(guó)的和尚,而是安德烈教士。這一點(diǎn)完全不同于昔日的吳太太,放在過去,她一定想到的是和尚,至少也是道士。同樣,在處理兒子、兒媳們之間的矛盾,祈盼他們能和睦相處這個(gè)問題上,吳太太想到的仍然是安德烈教士。“她想起了安德烈教士。他的智慧遠(yuǎn)遠(yuǎn)逾越了這四面高墻。她得把豐漠叫來,建議他重拾學(xué)業(yè)。這樣一來,等安德烈教士來了,就讓他分擔(dān)這些小輩給她出的難題了。”②[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79、219、185-186、191、193頁。
此時(shí)此刻,吳太太對(duì)安德烈從產(chǎn)生好感逐漸過渡到情感依賴,這是前所未有的。放在以前,吳太太可能會(huì)和自己的丈夫吳老爺一起商量請(qǐng)和尚還是道士,或者怎樣處理這些家庭矛盾,但自從安德烈出現(xiàn)在她的生活里,她在情感上終于找到了替換吳老爺?shù)淖罴讶诉x。“她真是恨不得夜幕早早降臨,家里息事寧人,到時(shí)候她就可以在安德烈教士的引導(dǎo)下,拋開肉體,讓沒有了牽絆的靈魂進(jìn)入大千世界。”③[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79、219、185-186、191、193頁。
(三)找到靈魂所寄——情欲至臻
安德烈當(dāng)然無法真正解決吳府的家庭糾紛,但他通過自己的言行默默地喚醒了吳太太心底沉睡已久的女性情欲和自我意識(shí)。豐漠復(fù)課后,安德烈再次來到吳府。吳太太每晚都要待在安德烈上課的院子里,即使秋意漸涼,她也要再捱一兩個(gè)晚上。她對(duì)安德烈的好奇心越來越重,跟他交談中一連串看似無心的問題卻暴露了她情感深處的一種情愫:“‘可你是那么個(gè)孤零零的人啊……難道你我的血是一樣的嗎?……那為什么你偏偏就是一個(gè)牧師呢?……’她覺得很不好意思,居然對(duì)他的事情那么好奇,可她就是忍不住。……‘你好生孤單啊……,瞧你,白天干活的時(shí)候身邊圍著的是窮人,晚上身邊圍著的是星星。……你就從來沒想過成個(gè)家娶一房太太生一群孩子嗎?’”④[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79、219、185-186、191、193頁。
安德烈的回答令吳太太幡然醒悟,那就是“為了靈魂的自由”:“她知道,這樣的自由會(huì)成為心靈渴望的美酒,抵擋這樣的佳釀就像讓酒鬼不喝酒一樣艱難。……她又生起安德烈教士的氣來,怪他誘導(dǎo)著自己接近那樣的自由,她也很害怕自己,因?yàn)樗睦锔械侥菢拥淖杂梢呀?jīng)讓她臣服。她一醒來,負(fù)疚感就重重壓在她身上,重得就好像她偷了漢子失了身。”⑤[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79、219、185-186、191、193頁。
實(shí)際上,自從安德烈教士來到吳府之后,吳太太種種魂不守舍的表現(xiàn)都進(jìn)入了吳老爺作為男人的直覺中,“有那么一會(huì)兒工夫,他心里掠過一個(gè)古怪的念頭,或許,出于某種奇怪的扭曲的本能,她跟那個(gè)洋牧師是靈犀相通的。可他不好意思把這個(gè)念頭當(dāng)著她的面說出來。”⑥[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79、219、185-186、191、193頁。
看起來情欲的種子已經(jīng)在吳太太的心靈深處悄然萌芽,她之前以為所有男人都和她的丈夫一樣,像一只雄雞或公牛,除了男女之事以外,便再無其它。就像她讀過的希臘故事里的有夫之婦,曾經(jīng)覺得所有的男人都像自己的丈夫一樣臭烘烘,直到有一天她愛上了一個(gè)連呼吸都甜膩無比的男人。吳太太終于明白,男人并非千人一面,也并非像自己的丈夫吳老爺一樣,整日除了酒足飯飽和男歡女愛這兩件事之外,再無其他。比如自己的三兒子豐漠和安德烈教士就遠(yuǎn)非其他男人可比,他們的追求和境界遠(yuǎn)超生理層面的滿足,但在未見到安德烈之前,她并不明白這一點(diǎn)。
吳太太對(duì)洋人傳教士有所心動(dòng)的說法可能會(huì)令有些人產(chǎn)生懷疑,那么,以上文字,雖寥寥幾筆,卻有力地證明了吳太太靈魂深處的隱秘動(dòng)情。即使她自己認(rèn)為男女“首先在身體上水乳交融,其他方面才能琴瑟和鳴”①[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210、210-211、213、224-225、225頁。,但也不能否認(rèn)有一種對(duì)安德烈柏拉圖式的純粹精神愛戀已經(jīng)在吳太太的情感世界里萌生,因?yàn)樗靼祝翈熓遣豢赡苡心信碌模信檎l能知道?這種與中國(guó)傳統(tǒng)舊式女性身份相悖的意識(shí)是吳太太情欲外化的顯性表現(xiàn)。
吳太太原初的性和愛欲是被長(zhǎng)久壓抑的,根本原因在于她的不自知和無意識(shí)。女性身份和意識(shí)的進(jìn)一步表現(xiàn),則是對(duì)既往性壓抑的大膽突破,突破了原本限制女性大膽表達(dá)欲望的倫理道德,即傳統(tǒng)男權(quán)社會(huì)對(duì)女性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桎梏。她不僅開始認(rèn)識(shí)到性和愛欲的區(qū)別,也更加清楚地意識(shí)到自己不再是丈夫的附庸,而是具有獨(dú)立人格的女性,知道自己后半生的幸福之所在。
因此,在放走了想闖蕩天下的三兒子豐漠后,吳太太依然希望安德烈教士能來吳府教豐漠的媳婦琳儀英文,這也許只是一個(gè)可以繼續(xù)見到安德烈的合理借口。每當(dāng)安德烈教授琳儀西洋學(xué)問時(shí),吳太太便在一旁督習(xí),一怕琳儀懶惰怠學(xué),二怕孤男寡女相處一室,惹人閑話(而實(shí)際是想天天見到安德烈)。但趁此機(jī)會(huì),吳太太自己不僅學(xué)會(huì)了生死愛恨、花鳥魚蟲等簡(jiǎn)單的英文名字,“毫無二致的詞兒居然能用迥然相異的語言說出來,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②[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210、210-211、213、224-225、225頁。她也明白了日月星辰與人類地球的運(yùn)轉(zhuǎn)道理,更懂得了人在世間生死輪回的要義,參悟了來自靈魂深處的自我拷問。安德烈此際已成為吳太太走出人生霧谷迷途的一盞指路明燈,“在她看來,安德烈教士是口井,井里有的是學(xué)問和見識(shí),又大又深。……他頗有古時(shí)候的道家遺風(fēng),善于以寥寥數(shù)語直入肯綮。”③[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210、210-211、213、224-225、225頁。
吳太太深深地向往著高墻(物理的高墻和精神的高墻)之外的世界,并破天荒地要求安德烈收她為徒,在每天晚上教完琳儀后再單獨(dú)給她講課一個(gè)時(shí)辰。這種行為,不僅僅出于吳太太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驅(qū)使,更是出于精神層面一步步向安德烈靠近的“有意識(shí)”和情欲層面尋找深層慰藉和愉悅感的驅(qū)動(dòng)。漸漸地,吳太太的情感世界不再是一片荒蕪,而是充滿了溫暖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精神的高墻)。她的世界曾是一片荒蕪,自從他來后,這里變成了一片綠洲。
如今的她,就連審視吳家大院(物理的高墻)的角度都非同昔日,“院墻里的這片土地,充塞著人間的諸般煩憂,但她覺得她能面對(duì),甚至能化解,因?yàn)樗约阂巡辉偈瞧渲械囊环葑印W詮乃c吳老爺斷了肌膚之親后,等于把捆綁在身上的所有繩索統(tǒng)統(tǒng)扯斷了。關(guān)于這肉體之間堅(jiān)不可摧卻又神秘莫測(cè)的結(jié)合,她曾左思右想過。原來,一旦把這種結(jié)合打破,解放的不僅是肉身,更有靈魂啊。在這片土地上,如今處處都辟開了條條大道,她的靈魂便沿著這些路向前去。”④[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210、210-211、213、224-225、225頁。
為了解決二兒子、三兒子與各自媳婦不斷發(fā)生矛盾的僵局,吳太太將兩個(gè)兒子逐一打發(fā)離開吳府。當(dāng)她把這些事告訴安德烈時(shí),“‘有必要解釋嗎?’安德烈教士微微一笑。他這樣的微笑常常讓她看得入神。那微笑始于濃濃的眉毛和胡子之間,就像一道閃電在樹林中劃亮。他的碩大的腦袋、他的整個(gè)壯實(shí)健碩、毛發(fā)叢生的身軀,曾經(jīng)把她嚇得目瞪口呆。如今,對(duì)這一切,她都習(xí)慣了。”⑤[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210、210-211、213、224-225、225頁。其實(shí),安德烈也一定對(duì)吳太太有所心動(dòng),“深夜,當(dāng)他一個(gè)人躺在竹榻上時(shí),曾想過,幸虧上帝沒有讓他遇見少女時(shí)代的吳太太。‘啊,上帝,真要那樣的話,我就沒法向自己的靈魂交代啦!’”⑥[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210、210-211、213、224-225、225頁。兩個(gè)自由的靈魂,在靈犀相交中,逐漸靠得更近了,“待在那個(gè)長(zhǎng)長(zhǎng)的安靜的房間里,吳太太忘了自己的屋子。她坐著,呆呆地注視著安德烈教士那粗獷的紫銅色臉龐。他被她看得有些神思恍惚。他教導(dǎo)著眼前的這個(gè)人,專注得就好像這是他頭一遭給別人上課。……他怎么會(huì)情不自禁地向她完全敞開心扉呢?”①[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321、223、298、392、339頁。“只有當(dāng)她跟安德烈在一起的時(shí)候,才能暢所欲言,探討人之本性”②[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321、223、298、392、339頁。,但他們也許無法越過封建世俗和禮教這道堅(jiān)固而無形的“隔墻”。
而對(duì)于心泉封閉了24年的吳太太,她從未離開過吳家大院(物理的高墻),也從未離開過這座人老幾輩生存過的城市,也從未想象過吳老爺以外的男人(精神的高墻),但后來,她向往著更寬、更廣、更遠(yuǎn)的世界——她要朝著愛的路上愈行愈遠(yuǎn),如同她告訴二兒媳若蘭的話,“要等你重新做得了自己的主,也就得到了自由……你在這座院墻里得到了自由,就像得到了全天下的自由一樣……這愛情呀,只有在自由中才活得下去”③[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321、223、298、392、339頁。。這可能是吳太太完成自己愛情的救贖后最透徹的領(lǐng)悟和最有力的證明。
但令吳太太意想不到的是,安德烈因熱心幫助他人而被欺行霸市的街頭黑幫失手打死。聽聞噩耗后,吳太太悲從心生,痛楚不堪,但她抑制住淚水,不但體面地安葬了安德烈,之后還正式接管并安頓好安德烈生前收養(yǎng)撫育的二十幾個(gè)孤兒,差人負(fù)責(zé)照料他們的日常生活,直到長(zhǎng)大成人。
雖然安德烈肉體不在,但他的靈魂卻永存于吳太太的心靈深處。每個(gè)夜晚,她都想告訴在天國(guó)里繼續(xù)做著善事的安德烈,“我們用不著執(zhí)手相看,就能融為一體。縱然肉身湮滅,此情依然能綿延不絕。我們并不是靠肉身才結(jié)合在一起的。”④[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321、223、298、392、339頁。天亦有情,安德烈一定是知道的。
黃昱寧在譯后記里說:“以我們現(xiàn)在的眼光看,是很難理解如此不食人間煙火的愛情的。”⑤[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321、223、298、392、339頁。事實(shí)上,愛情不一定需要男女肉身合為一體,不一定需要有腰部以下的行為,雖然這也是人類自然的本性和行為之一。但精神戀愛往往在男女之間表現(xiàn)得更為持久和強(qiáng)烈,也是人類所有情感中最為美好的珍貴的部分,這也正是吳太太“情欲救贖”真諦之所在,心路歷程的意義之所在。試想一下,吳太太剛剛擺脫了與吳老爺?shù)娜怏w糾葛,又陷入與安德烈的肉體關(guān)系之中,那第一層次的肉體救贖豈不顯得滑稽可笑,小說也會(huì)落入傳統(tǒng)寫作的窠臼之中。另一方面,以葉維廉先生的觀點(diǎn)作一解釋:“中國(guó)人感情的流露與外國(guó)人大不相同,中國(guó)人是蘊(yùn)藏的,外國(guó)人大多趨向爆炸性。……中國(guó)人則盡量抑制住欲沖出的激動(dòng)的行為或說話。”⑥葉維廉:《葉維廉文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頁。
只有保持各自肉體的獨(dú)立和純潔,彼此將熾熱的情感深藏心底,才能突顯出吳太太完成自我“情欲救贖”的獨(dú)特意義,也是該部作品最值得讀者品讀和悅賞之處,更是賽珍珠向中國(guó)讀者積極傳達(dá)的一種普世價(jià)值觀的目的所在,即“人類一切知識(shí)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愛,實(shí)現(xiàn)愛,回歸愛”⑦[意]波納文圖拉:《中世紀(jì)的心靈之旅:波納文圖拉神學(xué)著作選》,溥林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頁。。只有安德烈,才讓吳太太領(lǐng)悟到了人與人之間平等的愛情真諦:“愛宛若陽光雨露,灑下來誰都有份,哪管什么君子小人、富人貧者、白丁鴻儒。”⑧[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321、223、298、392、339頁。
吳太太的“情欲救贖”得以實(shí)現(xiàn)的靈魂人物——來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教士。他的出場(chǎng)無疑是賽珍珠為吳太太的“情欲救贖”心路歷程特意安排的“近乎”宗教教義上的解釋和證據(jù)。如果缺少了安德烈這一宗教人物的“特定身份”,像吳太太這樣在濃厚的封建家族制度和森嚴(yán)的禮教氛圍下誕生并成長(zhǎng)的人物,很難擺脫固有的成長(zhǎng)模式,很難真正實(shí)現(xiàn)她個(gè)人的“情欲救贖”。所以安德烈的“宗教身份”是賽珍珠在特殊的歷史時(shí)代和獨(dú)特的舊中國(guó)文化背景下精心醞釀的創(chuàng)作技巧的體現(xiàn)。他的出場(chǎng)是偶然中的必然,也是賽珍珠為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對(duì)被封建禮教長(zhǎng)期禁錮的女性,能夠完成“情欲救贖”的一種個(gè)案設(shè)定,是一種完美甚至理想主義的訴求①[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383、334,265頁。。
安德烈不但使吳太太獲得了肉體的自由,完成了道德的升華,更重要的是,從情感上有了精神愛戀的對(duì)象,她時(shí)刻記得“當(dāng)初她是如何打開門,讓他進(jìn)來的呢?她記不得了。有人把他領(lǐng)進(jìn)來見她,于是她打開了自己的門,他就進(jìn)來了,為她帶來了永生。是啊,現(xiàn)在她信了,有朝一日,即便肉身死去,靈魂仍將永存。她不崇拜上帝,也全無信仰可言,可她有愛,綿延不絕的愛。是愛喚醒了她沉睡的靈魂,讓它生生不息”②[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383、334,265頁。。這種狀態(tài)也是拉康“欲望倫理學(xué)”的核心觀點(diǎn),即“至善”是激活人類“無知”激情的最高境界,是實(shí)現(xiàn)個(gè)體價(jià)值的終極表現(xiàn)。
專事美國(guó)文學(xué)研究的學(xué)者郭英劍教授的觀點(diǎn)可以為吳太太如此渴望愛情的根本原因提供一種比較合理的解讀:“人們之所以渴望愛情決不僅僅是為了滿足與生俱來的‘愛’的本能,更多是為了尋找心靈的溝通、情感的慰藉,在夫妻關(guān)系中,有一條重要的、無形的紐帶——心靈的默契。而這是在與安修士認(rèn)識(shí)后,吳太太才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的。”③郭英劍、于艷平:《尋求女性個(gè)體生命的意義——論賽珍珠的〈群芳亭〉》,《鎮(zhèn)江師專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0年第2期。肉體已獲得自由的吳太太,迫切需要的正是心靈的溝通與情感的慰藉,她的“情欲救贖”即是這種精神追求的明證。“她這一輩子,拜上天之賜,能有幸了解——甚至愛上了一個(gè)盡善盡美的人。……這種愛,平靜而不失強(qiáng)烈,宛如午時(shí)的陽光,給了她溫暖,給了她力量,也給了她自信。”④[美]賽珍珠:《庭院中的女人》,黃昱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383、334,265頁。
三、以安德列形象反觀“情欲救贖”的書寫動(dòng)機(jī)
基督教用“原罪說”和“贖罪說”告訴人們,既然耶穌是為人類贖罪而獻(xiàn)身的,那么人就不再應(yīng)該為自己而活著了,而應(yīng)當(dāng)為神而活著;人生活的目的、人的最大幸福以及人的最高美德也只能在信仰上帝的過程中獲得。因此,在基督教倫理思想中,信仰神既是最高的美德,也是達(dá)到最高道德境界的唯一途徑⑤蔣堅(jiān)松、寧一中:《英美文學(xué)研究》,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頁。。有研究者據(jù)此認(rèn)為,出生于傳教士家庭的賽珍珠顯然是以宗教救贖為目標(biāo)來刻畫吳太太,所以特意安排安德烈教士出場(chǎng)去不斷地感化教化吳太太,但這種夸大宗教力量的解讀并不符合賽珍珠創(chuàng)作該小說的初衷。
實(shí)際上,賽珍珠筆下的安德烈是一位被自己的祖國(guó)意大利放逐的異教徒,他對(duì)宗教并不篤信,甚至有些離經(jīng)叛道。他之所以能夠感動(dòng)舊中國(guó)封建體制下的吳太太去做善事,承繼他的未竟之業(yè),并非單純?cè)从谧诮绦叛龅牧α浚莵碜砸粋€(gè)有高度社會(huì)責(zé)任感,一個(gè)寬懷大度,能容天下之苦難,心懷善念的偉岸男性形象的力量,也是吳太太從少女時(shí)代就一直渴望的那種與吳老爺全然不同的男性的呵護(hù)和慰藉——即情欲的力量。拉康的欲望倫理學(xué)認(rèn)為,“至善”是理性道德觀的最高參照,這一點(diǎn)不同于弗洛伊德對(duì)“至善”的否認(rèn)。“善”的欲望也是人類的本能欲望和自然欲望,是實(shí)現(xiàn)人類幸福感的高級(jí)層面的倫理追求,遠(yuǎn)遠(yuǎn)大于肉體滿足所獲得的淺層或初級(jí)的快樂感⑥[法]納塔莉·沙鷗:《欲望倫理:拉康思想引論》,鄭天喆等譯,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7-12頁。。
由此看來,賽珍珠以浪漫主義手法所刻畫的安德烈教士,也是她本人理想主義的話語者和承載者。通過安德烈這一象征著“至善”和“博愛”的“男性”形象,賽珍珠試圖喚醒無數(shù)個(gè)舊中國(guó)女性,擺脫精神桎梏,去大膽追求自我命運(yùn)的主宰權(quán),實(shí)現(xiàn)女性的身份自由,獲得生命和存在的終極幸福感。安德烈教士是吳太太得到情欲啟悟的最直接源泉,是她交付情感托付心靈的唯一人選,是她精神世界里永遠(yuǎn)的導(dǎo)師①徐燕:《對(duì)“給賽珍珠翻案”的回應(yīng)——兼論〈群芳亭〉中的異質(zhì)文化交流》,《寧波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科學(xué)版)》2000年第5期。。正如黑格爾說:“愛情里確實(shí)有一種高尚的品質(zhì),因?yàn)樗恢煌A粼谛杂希秋@出一種本身豐富的高尚優(yōu)美的心靈,要求以生動(dòng)活潑、勇敢和犧牲的精神和另一個(gè)人達(dá)到統(tǒng)一。”②[德]黑格爾:《美學(xué)》第2卷,朱光潛譯,商務(wù)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頁。
文學(xué)作品特質(zhì)之一在于共情性,創(chuàng)作之初是與創(chuàng)作者產(chǎn)生共情,問世之后又與讀者產(chǎn)生共情,讓“人們往往能夠通過文學(xué)作品找到某些超越文化異質(zhì)、超過語言限制的美感力量”③[美]葉維廉:《葉維廉文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序,第8頁。。
吳太太“情欲救贖”所經(jīng)歷的心路歷程正是賽珍珠本人愛情觀核心主張的一種表現(xiàn):“愛情不能強(qiáng)迫。對(duì)于一位感情細(xì)膩聰穎過人而又富于幻想的女性來說,肉體與心靈和情感是三位一體,密不可分。”④[美]賽珍珠:《我的中國(guó)世界》,尚營(yíng)林等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頁。賽珍珠在摹畫吳太太時(shí),即是在極力呈現(xiàn)這種女性欲望的“美感力量”和“美學(xué)藝術(shù)”。她不僅對(duì)吳太太深懷憐惜之情,不惜以大量筆墨反復(fù)褒贊她完成情欲救贖的奮爭(zhēng)過程——二十多年的青春,卻從未嘗試過“愛”的滋味;但又對(duì)“愛”滿含希望——余生至少應(yīng)該去大膽追求真愛,哪怕僅僅停留于精神層面也算生有意義,哪怕活著的時(shí)候只有一次“心動(dòng)”也算不枉此生。就好比海子的詩歌所吟唱的:“你來人間一趟/你要看看太陽//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了解她/也要了解太陽……當(dāng)年基督入世/也在這太陽下長(zhǎng)大//”⑤西川編:《海子詩全編》,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62-63頁。在封建禮教余燼尚存的民國(guó)時(shí)代,吳太太不太可能與心儀的意大利傳教士一起公開地大膽地走在街上,但至少有權(quán)利可以在精神的世界里,乘著陽光,一起徜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