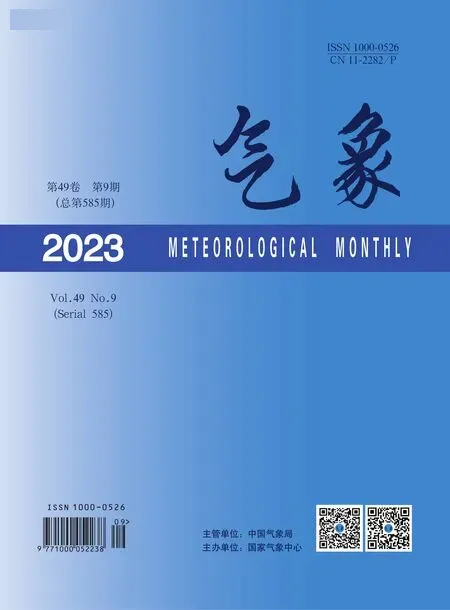2022年盛夏重慶不同階段高溫特征及成因對比*
羅 娟 鄧承之 朱 巖 夏 蘩 龐 玥 朱浩楠
1 中國氣象局氣候資源經濟轉化重點開放實驗室,重慶 401147 2 重慶市氣象臺,重慶 401147 3 重慶市氣候中心,重慶 401147
提 要: 2022年盛夏,重慶地區出現了兩段高溫天氣,兩段高溫均為先大陸高壓、后副熱帶高壓控制下形成的。利用地面觀測資料和ERA5再分析資料,對比分析了重慶大陸高壓階段和副熱帶高壓階段的高溫特征差異。結果表明:大陸高壓持續時間短,為高溫發展階段,高溫強度弱、相對濕度大、氣溫日較差大;副熱帶高壓持續時間長,為高溫強盛階段,高溫極端性強,干熱特征顯著、夜間升溫明顯。熱力學方程診斷表明,大陸高壓階段,增溫為非絕熱加熱和垂直運動項共同作用;副熱帶高壓階段,白天增溫主要源于非絕熱加熱,其次為溫度平流項,垂直運動項作用弱,夜間低空干絕熱或超絕熱層減弱消失,翻越云貴高原的下沉氣流帶來的增溫效應顯著增強。地表熱力差異表明,副熱帶高壓階段較大陸高壓階段地表潛熱通量下降,感熱通量顯著上升,地表感熱直接加熱大氣,對地面增溫作用明顯。
引 言
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和城市化進展加快,夏季極端高溫事件呈現出明顯增多的趨勢,高溫熱浪嚴重影響人體健康,加劇能源消耗,威脅生態環境,已經成為主要的氣象災害之一(楊宏青等,2013;許霜等,2014;謝志清等,2015;高璇等,2023)。目前,高溫成因研究方面已取得不少成果,大氣中的高壓環流系統是影響高溫熱浪的直接因素。對于我國夏季南方地區高溫而言,最主要的高壓環流系統包括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以下簡稱副熱帶高壓)(林建等,2005;尹東屏等,2006;賈子康等,2020)、大陸副熱帶高壓(以下簡稱大陸高壓)(彭京備等,2007;陳麗華等,2010;袁媛等,2018)、以及對流層中高層的南亞高壓(張瓊和吳國雄,2001;錢永甫等,2002)。大陸副熱帶高壓是由謝義炳(1997)提出,有別于海洋上空的副熱帶高壓,大陸高壓環流位于陸地上。2006年夏季,大陸高壓與西伸的副熱帶高壓打通,控制川渝地區,導致該地區出現歷史罕見的高溫天氣(彭京備等,2007;陳麗華等,2010)。副熱帶高壓和南亞高壓異常偏強也是出現高溫的重要原因,例如2003年夏季,我國江南出現大范圍異常高溫天氣就是由于副熱帶高壓的異常偏強和偏西,同時南亞高壓異常偏強和偏東造成的(彭海燕等,2005;林建等,2005;楊輝和李崇銀,2005)。2013年中國大范圍的強高溫事件也與副熱帶高壓和南亞高壓的活動密切相關,高壓中空氣的下沉絕熱增溫是形成高溫天氣的主要物理機制(唐恬等,2014;楊涵洧和封國林,2016;彭京備等,2016)。
此外,還有一些氣象學者從熱力學方程出發,從熱力成因方面對高溫天氣做了很多研究(周后福,2005;張迎新和張守保,2010)。尹東屏等(2006)的研究表明,在副熱帶高壓控制下,非絕熱加熱是2003年7—8月江蘇高溫出現的關鍵,而溫度平流和絕熱加熱對高溫的貢獻非常小。方宇凌和簡茂球(2011)發現,在2003年夏季的三段持續性高溫期間,大氣升溫主要是由非絕熱加熱造成,而溫度平流對升溫起負貢獻。鄒海波等(2015)研究了2013年盛夏中國中東部地區異常高溫天氣的成因,也得出類似的結論,非絕熱加熱(主要是長波凈輻射)是夏季中國中東部地區升溫最為主要的因子,而異常的溫度平流(冷平流)則起著負貢獻。
2022年夏季,中國南方地區再次出現持續性異常高溫天氣,具有影響范圍廣、持續時間長、極端性強的特點,高溫天氣綜合強度為1961年有完整氣象觀測記錄以來最強,中央氣象臺連續多日發布高溫紅色預警。針對2022年極端高溫事件,林紓等(2022)對高溫干旱特征和環流形勢進行了分析,表明2022年夏季對流層高層南亞高壓異常偏東,與中層的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相向而行,高壓系統疊加呈穩定正壓結構,高壓中心位于川渝上空,致使川渝地區成為高溫日數和極端高溫事件次數的高值中心。郝立生等(2022)認為2022年長江流域夏季異常高溫干旱氣候事件的發生是高緯、中低緯、低緯熱帶地區環流異常協同作用影響的結果。可見,現有研究從大氣環流異常的角度,表明異常偏強的高壓環流系統是2022年長江流域持續性高溫天氣的主要原因,但對不同高壓系統下高溫天氣學特征的認識仍然不足。
重慶素有“火爐”之稱,副熱帶高壓和大陸高壓是高溫天氣最為直接和重要的影響系統,那么2022年盛夏(7—8月)不同高壓控制下的重慶高溫究竟有何不同?為了回答這一科學問題,本文利用地面觀測資料和ERA5再分析資料,首先從環流形勢、高溫強度、相對濕度和氣溫日較差等方面進行對比,再從熱力學方程出發進行診斷,探討和總結不同高壓控制下重慶高溫特征差異和可能成因,以期為高溫預警服務提供科學依據。
1 資料和方法
1.1 資 料
本文使用的最高氣溫和相對濕度資料來自重慶國家地面站。環流分析和熱力學方程診斷所用資料要素包括高度場、風場、溫度場和垂直速度等,4.2小節中的地表熱力差異特征分析采用的地表接收到的太陽輻射、地表感熱通量和潛熱通量數據,均來源于ERA5再分析數據集,資料時間分辨率為1 h,水平分辨率為0.25°×0.25°。地表感熱和潛熱通量在ERA5中規定向下為正通量,向上為負通量,為了符合使用習慣,本文在垂直通量前乘以-1。另外,本文所使用的站點為沙坪壩和北碚站。
1.2 方 法
為了診斷分析造成2022年盛夏重慶不同階段高溫天氣的主要因子,有必要定量計算影響溫度局地變化的各項因子,由熱力學第一定律可得溫度隨時間的變化方程,即:
(1)
引起溫度局地變化的因子主要有三項,分別為溫度平流項-V·T,垂直運動項-w(γd-γ)和非絕熱加熱項其中T為溫度,V為水平風矢量,w為垂直速度,γd為干絕熱垂直遞減率,γ為環境溫度垂直遞減率,cp為定壓比熱容,Q為外源加熱量。由于Q的計算非常復雜,因此本文4.1小節進行熱力學方程診斷時先計算出溫度隨時間變化、溫度平流項和垂直運動項,再由式(1)推算出非絕熱加熱項。另外,本文給出了大陸高壓階段和副熱帶高壓階段各項因子的合成結果,是先根據式(1)使用ERA5資料進行逐日逐時計算,再將不同階段的計算結果合成。
2 高溫天氣概況
2022年盛夏,重慶出現大范圍持續性晴熱高溫天氣,高溫呈現出持續時間長、影響范圍廣和極端性強的特點。圖1給出了≥35℃和≥40℃高溫日數歷年變化,由圖可知,全市35℃以上高溫日數達49.7 d,超過2006年(49.4 d)(圖1a);40℃以上高溫日數達15.8 d,刷新了2006年歷史極值(10.2 d),高溫日數為1961年有完整氣象觀測記錄以來同期最多(圖1b)。圖2a為各區縣≥40℃高溫日數分布,由圖可見,高溫天氣范圍廣且持續時間長,全市有31個區(縣)(占比為91%)出現40℃以上的高溫天氣,有25個區(縣)(占比為74%)40℃以上高溫日數超過了10 d,15個區(縣)(占比為44%)超過20 d(圖2a)。圖2b顯示了日最高氣溫刷新歷史紀錄的區(縣),高溫極端性突出,日最高氣溫連創新高,15個區(縣)(占比為44%)日最高氣溫刷新當地有氣象記錄以來歷史極值,其中北碚站連續兩天日最高氣溫達45℃,超過2006年重慶綦江站(44.5℃),這也是除新疆吐魯番以外目前國家站觀測到的最高值。

圖1 1961—2022年重慶(a)≥35℃和(b)≥40℃高溫日數年變化Fig.1 Annual variation of days with maximum temperatures (a) ≥35℃ and (b) ≥40℃ in Chongqing from 1961 to 2022

注:五角星代表北碚站和沙坪壩站位置。圖2 2022年盛夏重慶各區(縣)(a)≥40℃的高溫日數和(b)日最高氣溫刷新歷史紀錄的區(縣)分布情況Fig.2 (a) Days of maximum temperature ≥40℃ and (b) counties with record-breaking maximum temperature in Chongqing in midsummer of 2022
3 高溫演變及不同階段高溫特征對比
圖3顯示了2022年盛夏重慶高溫站數逐日演變。2022年盛夏重慶高溫主要有兩段:第一段在7月4—17日,第二段在7月24日至8月29日。從逐日天氣圖演變來看(圖略),兩段高溫均表現為先大陸高壓控制,后轉為副熱帶高壓控制。第一階段期間:7月4—8日為大陸高壓控制,7月9—17日轉為副熱帶高壓控制;第二階段期間:7月24—31日為大陸高壓控制,而8月1—29日再次轉為副熱帶高壓控制。大陸高壓和副熱帶高壓控制的重慶高溫特征究竟有何不同?

圖3 2022年盛夏重慶逐日高溫站數演變Fig.3 Time series of the stations with daily high temperature in Chongqing in midsummer of 2022
圖4給出了不同高壓階段合成環流形勢。由圖可見,大陸高壓階段200 hPa(圖4a)南亞高壓位于伊朗高原至青藏高原上空,位勢高度場有強的正距平,對流層中部500 hPa(圖4b)強的正距平位于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重慶受到大陸高壓脊前側的偏北氣流控制。副熱帶高壓階段南亞高壓明顯東擴,異常強盛的南亞高壓盤踞在長江流域上空(圖4c);500 hPa副熱帶高壓顯著西伸北抬,且呈現出異常偏西的特征,長時間穩定控制重慶地區(圖4d)。因此,大陸高壓和強盛的副熱帶高壓是2022年盛夏重慶高溫的關鍵環流系統。

圖4 2022年(a,b)7月4—8日和24—31日大陸高壓階段以及(c,d)7月9—17日和8月1—29日副熱帶高壓階段平均位勢高度(等值線,單位:dagpm)、位勢高度距平(填色)和風場(風羽)分布(a,c)200 hPa,(b,d)500 hPaFig.4 Synoptic patterns of mean geopotential height (contour, unit: dagpm), geopotential height anomaly (colored) and wind (barb) under (a, b) the domination of continental high in 4-8 and 24-31 July 2022 and (c, d) the domination of subtropical high in 9-17 July and 1-29 August 2022(a, c) 200 hPa, (b, d) 500 hPa
圖3還顯示了高溫的持續時間和強度,大陸高壓持續時間短,而副熱帶高壓持續時間長。大陸高壓階段主要為兩段高溫的初期發展階段,以35℃和37℃的高溫天氣為主,個別站點超過40℃;而副熱帶高壓階段則為兩段高溫的強盛階段,40℃以上的高溫范圍明顯擴大,特別是8月8—25日,持續有70%左右的國家站出現40℃以上的高溫天氣,此階段也為2022年盛夏重慶高溫的最強時段。
先大陸高壓后副熱帶高壓控制是否為重慶持續性高溫天氣的普遍特征?圖5給出了2006年盛夏川渝異常高溫天氣500 hPa環流對比。由圖可見,2006年盛夏重慶高溫也具有類似環流演變特征,以7月下旬階段性高溫為例,7月22—27日(圖5a)重慶受大陸高壓控制,高溫處于發展階段,隨后副熱帶高壓西伸(圖5b),7月31日后(圖5c),強烈西伸的副熱帶高壓與大陸高壓打通,高溫進入強盛階段。可見,先大陸高壓、后副熱帶高壓控制是盛夏重慶持續性高溫的典型發展形勢。

圖5 2006年7月(a)22日08時,(b)28日08時,(c)31日08時500hPa位勢高度(等值線,單位:dagpm)、位勢高度距平(填色)和風場(風羽)分布Fig.5 Geopotential height (contour, unit: dagpm), geopotential height anomaly (colored), and wind (barb) at 500 hPa at (a) 08:00 BT 22, (b) 08:00 BT 28 and (c) 08:00 BT 31 July 2006
為了對比不同高壓控制下高溫的干熱和濕熱特征,圖6a給出了北碚站7—8月逐日相對濕度、最高氣溫和氣溫日較差的演變。由圖可知,大陸高壓階段以濕熱為主,相對濕度為60%~80%,而副熱帶高壓階段則以干熱為主,特別是8月8日以后干熱特征更為顯著,隨著溫度攀升,相對濕度明顯下降,僅為30%~40%。這是因為大陸高壓階段持續時間短且出現在降雨過程后,相對濕度較高;而副熱帶高壓階段持續時間長,地表水分逐漸蒸發,且高溫強度強于大陸高壓階段,使得空氣飽和水汽壓增加,從而導致相對濕度降低。

圖6 2022年(a)盛夏北碚站逐日最高氣溫、氣溫日較差和平均相對濕度,(b)8月20日沙坪壩站逐時氣溫演變Fig.6 (a) Daily maximum temperature, diurnal temperature range and mean relative humidity at Beibei Station from July to August of 2022, and (b) hourly temperature series at Shapingba Station on 20 August 2022
圖6a還顯示了大陸高壓階段氣溫日較差較大,約為15℃左右,副熱帶高壓階段氣溫日較差明顯減小,約為10℃左右。這是因為副熱帶高壓階段除了最高氣溫在攀升之外,日最低氣溫升幅尤為顯著,特別是8月8日以后,重慶多個國家站夜間最低氣溫在34℃以上(圖略)。以8月20日沙坪壩站氣溫為例(圖6b),可以看出,沙坪壩站有23 h氣溫在35℃以上,18 h氣溫在37℃以上(09時至次日02時),10 h 氣溫在40℃以上(12—21時)。
4 不同高壓控制下高溫成因對比
4.1 溫度局地變化
為了尋找造成2022年盛夏重慶不同階段高溫天氣的主要因子,從熱力學方程出發進行診斷分析。圖7和圖8 分別給出大陸高壓和副熱帶高壓階段850 hPa溫度局地變化、溫度平流項、垂直運動和非絕熱加熱項分布。由圖7可知,大陸高壓控制期間,重慶大部地區溫度局地變化為正值,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升溫明顯(圖7a)。大陸高壓階段增溫主要源于垂直運動項和非絕熱加熱,兩者貢獻相當(圖7c,7d)。而溫度平流項作用較小,且在武陵山脈和云貴高原北側還有弱的冷平流(圖7b),這可能與重慶處于大陸高壓脊前側,武陵山脈和云貴高原北側存在偏北氣流攜帶冷空氣在山前堆積有關。由圖8可知,副熱帶高壓階段,增溫較大陸高壓階段更為強盛(圖8a),各項因子對增溫的貢獻也有明顯不同,副熱帶高壓階段白天最重要的增溫源于非絕熱加熱項(圖8d),即太陽短波輻射、地面長波輻射、感熱及尺度較小的湍流等作用,其次為溫度平流項(圖8b),偏南風攜帶暖空氣北上,在武陵山脈和云貴高原北側有一定的正貢獻。另外,副熱帶高壓階段白天增溫垂直運動項貢獻小(圖8c),較大陸高壓階段明顯減弱。

圖8 2022年7月9—17日和8月1—29日14時副熱帶高壓階段平均的850 hPa(a)溫度局地變化,(b)溫度平流項,(c)垂直運動項及(d)非絕熱加熱項的分布Fig.8 Distribution of mean (a) local temperature variation, (b) temperature advection, (c) vertical motion and (d) diabatic heating at 850 hPa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subtropical high at 14:00 BT in 9-17 July and 1-29 August 2022
圖9給出了北碚站熱力學方程各項因子時間-高度演變。由圖可知,副熱帶高壓階段白天低空850 hPa以下增溫仍然主要源于非絕熱加熱作用(圖9d),其次為溫度平流項(圖9b),垂直運動項作用弱,但對于對流層中上部700~300 hPa的增溫則主要源于垂直運動作用(圖9c),即下沉運動導致的絕熱增溫現象。另外,夜間與白天的情況也有明顯不同,夜間在近地面有非絕熱冷卻(圖9d),溫度平流也以負貢獻為主(圖9b),但垂直運動項的作用明顯加大(圖9c),可見偏南風翻越云貴高原產生的下沉氣流在夜間形成了一定的增溫效應,這也是副熱帶高壓階段重慶夜間升溫的原因之一。

圖9 2022年7月9—17日及8月1—29日副熱帶高壓階段北碚站平均(a)溫度局地變化,(b)溫度平流項,(c)垂直運動項及(d)非絕熱加熱項的時間-高度演變Fig.9 Time-height diagram of mean (a) local temperature variation, (b) temperature advection, (c) vertical motion and (d) diabatic heating at Beibei Station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subtropical high in 9-17 July and 1-29 August 2022
垂直運動項造成的增溫效應在高溫不同階段、白天和夜間均有明顯不同,其原因與垂直速度和低空氣溫直減率有關。由垂直運動項-w(γd-γ)可知,該項取決于w和γ。圖10為重慶北碚站分別在副熱帶高壓階段和大陸高壓階段氣溫直減率及垂直速度的時間-高度演變。由圖10a可知,白天副熱帶高壓階段在非絕熱加熱作用下低空快速增溫,800 hPa 以下形成了氣溫直減率在-10~-9℃·km-1的干絕熱甚至超絕熱層結,環境大氣的氣溫直減率和氣塊干絕熱直減率相當,γd-γ較小,因此帶來的增溫效應非常弱。圖10b顯示大陸高壓階段這種干絕熱層結較弱,γd-γ增大,因此由垂直運動項產生的增溫效應增強。圖10a還顯示出,副熱帶高壓階段低空氣溫直減率的日變化顯著,夜間低空干絕熱或超絕熱層消失,且下沉氣流有所增強,因而垂直運動項在夜間會產生更顯著的增溫效應。

圖10 2022年(a)7月9—17日及8月1—29日副熱帶高壓階段,(b)7月4—8日及24—31日大陸高壓階段平均的北碚站氣溫直減率(填色)及垂直速度(等值線,單位Pa·s-1)的時間-高度演變Fig.10 Time-height diagram of mean temperature lapse rate (colored) and vertical velocity (contour, unit: Pa·s-1) at Beibei Station under (a) the domination of subtropical high in 9-17 July and 1-29 August, and (b) continental high in 4-8 and 24-31 July 2022
綜上所述,2022年盛夏重慶副熱帶高壓階段增溫明顯強于大陸高壓階段。大陸高壓階段的增溫主要為非絕熱加熱和垂直運動項共同作用。副熱帶高壓階段的白天增溫主要源于非絕熱加熱項,其次為溫度平流項,垂直運動項作用弱,但夜間隨著低空干絕熱或超絕熱層減弱消失,翻越云貴高原的下沉氣流帶來的增溫效應顯著增強。
4.2 地表熱力差異
上述分析表明,非絕熱加熱是重慶增溫最為主要的因子。大氣的熱量主要來自地球表面,近地面非絕熱加熱包括地表長波輻射通量加熱、地表感熱通量加熱以及潛熱通量加熱。地球表面吸收太陽短波輻射后,同時放射出長波輻射加熱大氣;地表感熱通量是通過空氣湍流影響地球表面和大氣之間熱量傳遞的物理量,感熱通量的大小取決于地表和覆蓋大氣之間的溫差、風速差、地表粗糙度和土壤相對濕度等;地表潛熱通量是通過相變影響地球表面和大氣之間潛熱傳遞的物理量,地球表面的蒸發表示有熱量從地表轉移到大氣中。圖11為大陸高壓階段和副熱帶高壓階段地表熱力差異,由圖可知,兩個階段地表接收到的太陽輻射量接近,大陸高壓階段平均太陽輻射通量約700 W·m-2(圖11a),副熱帶高壓階段略有增加,為750 W·m-2(圖11d)。地表感熱通量在大陸高壓階段較小,僅為100 W·m-2(圖11b),副熱帶高壓階段明顯增大,達到300~350 W·m-2(圖11e)。潛熱通量則相反,大陸高壓階段較大,為500 W·m-2(圖11c),副熱帶高壓階段明顯減小,不足200 W·m-2(圖11f)。

圖11 2022年(a~c)7月4—8日和24—31日大陸高壓階段和(d~f)7月9—17日和8月1—29日副熱帶高壓階段的(a,d)太陽輻射通量,(b,e)地表感熱通量,(c,f)地表潛熱通量Fig.11 (a, d) Solar radiation flux, (b, e) surface sensible heat flux and (c, f) latent heat flux under (a-c) the domination of continental high in 4-8 and 24-31 July and (d-f) the domination of subtropical high in 9-17 July and 1-29 August 2022
副熱帶高壓階段較大陸高壓階段太陽輻射變化不大,但地表感熱通量顯著上升,可能與持續晴熱天氣導致土壤濕度減小有關。易翔等(2016)利用WRF模式就土壤濕度擾動對高溫天氣影響進行模擬,結果表明土壤濕度減小會引起地面向上的感熱通量增加。地表感熱可以直接加熱大氣,對地面增溫作用更為明顯,而潛熱不直接加熱大氣,需要通過凝結釋放而對氣溫產生影響,對高溫作用相對較小,因此副熱帶高壓階段高溫強于大陸高壓階段。
5 結論與討論
2022年盛夏重慶經歷了罕見的晴熱高溫天氣,高溫強度強、范圍廣、持續時間長。大陸高壓和副熱帶高壓是此次重慶高溫天氣的關鍵環流系統,本文對比分析了不同高壓控制下高溫特征差異及可能成因,得到以下結論:
(1)先大陸高壓、后副熱帶高壓控制是盛夏重慶持續性高溫典型發展形勢,不同高壓控制下高溫特征表現不同。大陸高壓為持續性高溫發展階段,高溫強度較小,以35℃和37℃的高溫為主,副熱帶高壓進入高溫強盛階段,出現大范圍40℃以上的極端高溫天氣。大陸高壓階段相對濕度較高,副熱帶高壓階段由于溫度高、飽和水汽壓增大,干熱特征更為顯著。另外,大陸高壓階段氣溫日較差大,約為15℃左右,副熱帶高壓階段氣溫日較差減小,約為10℃左右。
(2)溫度局地變化分析表明,副熱帶高壓階段增溫明顯強于大陸高壓階段。大陸高壓階段增溫主要為非絕熱加熱和垂直運動項共同作用;副熱帶高壓階段增溫主要源于非絕熱加熱,其次為溫度平流項,垂直運動項白天低空增溫作用弱,但夜間隨著干絕熱或超絕熱層減弱消失,翻越山脈的下坡風在云貴高原北側帶來顯著的下沉增溫效應。
(3)地表熱力差異表明,副熱帶高壓階段較大陸高壓階段太陽輻射變化不大,地表潛熱通量下降,感熱通量顯著上升,地表感熱可以直接加熱大氣,對地面增溫作用更為明顯,因此副熱帶高壓階段高溫強于大陸高壓階段。
重慶極端高溫成因復雜,除與大氣環流形勢有關外,還與本地特殊地形密不可分。極端高溫位于重慶境內平壩、河谷及嶺谷地帶,特殊地形使得熱量難以散發。加之近年來城市化進展加快,“熱島效應”也是重慶城市極端高溫的重要因子(白瑩瑩等,2015),因此,今后還需結合本地特殊地形及城市“熱島效應”等對高溫成因做更全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