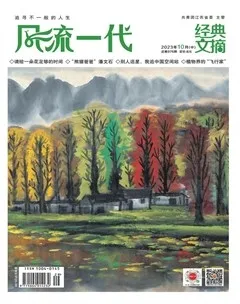遠行的木耳
艾苓
林場的四周都是大山,到了冬天,整個林場被一場又一場大雪覆蓋。那天幼兒園放寒假,我穿戴整齊,跟著爸爸去百米開外的姥姥家。才走出幾步,爸爸回頭問:“冷不冷?”
我說:“冷。”
爸爸說:“好好學習吧,你一定要走出大山,可不能像我一樣留在這兒,記住了嗎?”
我說:“記住了。”
爸爸一定是怕我忘了,從小到大,這句話他說了好多次。
菌房失火
我上小學二年級那年,林場小學停辦了,我們不得不外出上學。離林場最近的小鎮,坐客車得兩個小時,一天一趟。鎮里的小學沒有宿舍,林場來的孩子住到當地人家,男生住大屋,女生住小屋。只有我生病了,媽媽才來陪兩天,跟我一起睡在炕上。那時候林場沒活干,我上學的費用占了爸媽工資的一半。
爸爸不服氣。以前伐木,全林場誰都比不了他和叔叔那一組。跑山誰都跑不過他,他們在山里采靈芝、采蘑菇。
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家里開始做木耳菌。我們林場地多,不適合耕種,最適合栽木耳和養蜂,爸爸把渾身的力氣都用在做木耳菌上。他用賺來的錢租房子、修房子、買設備。我家有了專門的菌鍋、菌房。擺放菌袋的木頭架子,是爸爸用山里撿的零碎木頭一錘子一錘子釘起來的。那個大菌鍋一次可以為2000袋木耳菌滅菌,一切都是新的,位置還好,很多人在我家做木耳菌。
2010年大年初一清早,爸爸到菌房點火,只要開始做菌,菌鍋就24小時不能停火。那年先做我家的菌,一共兩萬多袋。菌房里熱氣騰騰,霧氣繚繞,爸爸打量著那些等著裝鍋的菌袋跟我說:“等這兩萬多袋木耳菌栽到地里,那就是兩萬多個錢串子!”
大年初二,舅媽請我們一家去吃飯。媽媽忙到下午6點半才過來吃飯,她端起飯碗沒吃幾口,外面有人跑進來喊:“不好了!老李家的菌房著火了!”
媽媽放下飯碗往菌房跑,我到處跑著喊人:“我家菌房著火了!求求你們快去幫我家救火吧!”
人是喊來了,去了也是看著,菌房是剛翻新的彩鋼瓦房,誰也不敢上前去。爸爸想上去,被媽媽死死拉住。他扶墻站住,背著我們渾身顫抖,一定是哭了。
林場的消防車壞了,開不出來,有人從別的林場調來消防車,但已經晚了。火從叔叔家的菌房開始著,除了我家菌房,還燒了一戶人家、兩戶空菌房,那場大火一直著到凌晨2點。
我們都去奶奶家商量事情,商定的結果是,我家的5萬多元損失自己負責,鄰居的損失由叔叔賠償。回家以后,一家三口一夜無眠。
天剛亮,爸爸起身出去,媽媽囑咐我:“你一天都跟著他,去哪兒都跟著,明白嗎?”我當然明白,媽媽怕爸爸出事,我也怕。
爸爸在院子里搖著鐵把手正在給三輪車打火,他滿臉是淚,看見我出來趕緊轉過臉去。我跟爸爸去了菌房,滿眼望去一片漆黑,能燒的都燒了,留下幾堆廢鐵。爸爸嘆了口氣說:“好好的東西都成廢物了!”他揀了幾件可能有用的東西,裝到三輪車上。
2011年,爸爸準備東山再起,他重新找房子,重新做起來。那時候我已經上高中,家里在鎮上租了房子,媽媽時不時過來陪讀。5月份正是家里最忙的時候,媽媽回家干活了。
有一天晚上,媽媽匆匆回到住的地方,拿了幾件衣服就走了,我正在寫作業沒在意。三四天后,鄰居阿姨問:“你爸爸怎么樣了?轉院沒有?”我嚇壞了,大聲問:“我爸爸怎么了?”“他在這兒住院你不知道嗎?聽說粉塵爆炸,把你爸爸炸傷了。”
我放下書本拼命往小鎮醫院跑,出了這么大的事,我竟然一無所知。我滿頭大汗地沖進病房,我親愛的爸爸身上纏滿紗布,僅僅露出兩只眼睛!我顫聲問:“爸爸,你沒事吧?”爸爸無法說話,但他使勁點點頭,眼淚不斷。
每天中午放學,我都去醫院看爸爸。爸爸燒傷嚴重,應該在無菌環境下治療,但轉院治療需要一大筆費用,只能就近住院。爸爸住院一個多月,基本痊愈,但身上和手上留下很多疤痕。
出院以后,爸爸繼續做木耳菌,但他再沒參加過林場人家的婚禮。大一那年,爸爸來學校看我。我特意帶他看了九思湖、圖書館,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戴著手套。
學著長大
外人說林場是“山里”,我們說林場是“溝里”,山里人睜開眼睛到處是活,特別是夏天。
就說做木耳菌吧,先得備齊各種配料,按比例配好,兩斤一個裝到塑料袋里,再將壓口封好。經過菌鍋滅菌后,擺到菌房架子上,發酵3個月,溫度和濕度都有要求。發酵好了,用麻袋背到地里,一袋袋擺好,剩下的就是等著木耳菌破袋而出后摘木耳。這是做春耳。不等忙完春耳,4月前又該忙秋耳了。
受益于天時地利,林場的木耳格外飽滿。長大以后,我每年夏天都跟著摘木耳,但如果連續干,我受不了,頂多連干三天,歇一天我才能接著干。
野外摘木耳要全副武裝,長褲、長袖上衣、運動鞋、遮陽帽、膠皮手套。山里蚊子大,隔著褲子照樣叮你。我們在太陽底下,坐在小凳子上一袋一袋、一朵一朵地摘木耳。一個菌袋兩斤多重,我一天要拎起再放下幾百個菌袋,汗都來不及擦。那時候很絕望,我什么時候能擺脫大山、擺脫這么累的活兒呢?
著名的雪鄉離我家不遠。大二寒假,我去餐廳打工,餐廳25張桌子,每天接待旅行社游客80到100桌,端菜、撤菜、刷碗,忙得腳打后腦勺。這活比摘木耳還累,第一天晚上拖地,我根本拖不動。姑姑一邊幫我拖地,一邊批評我缺乏鍛煉。從這以后,我不再厭煩摘木耳,還學會了做飯,爸爸媽媽都說我長大了。
走出大山
考研失敗后,我加入找工作的人潮,過程挺波折,也挺糾結。人家看了簡歷都問:“綏化學院在哪兒?是本科院校嗎?”這讓我的自信心備受打擊。
后來,我去哈爾濱師范大學參加招聘會,參加了海南某開發區小學的筆試,中午吃掉包里的梨權當午餐,下午參加了面試。校長還是問:“綏化學院在哪兒?是本科院校嗎?”這回我有備而來,說:“綏化在哈爾濱北面,坐火車只要一個多小時。綏化學院是省屬普通本科院校。”
校長問:“和哈師大的學生比,你的優勢在哪里?”有根弦繃了很久,我突然繃不住了,瞬間滿眼淚花。我說:“在對專業的深入程度上,和他們相比,我的確有差距。因為知道差距,才更加努力,小時候我學過單簧管和朗誦,大學期間專門學了書法和畫畫。”校長讓我朗誦,我朗誦了岳飛的《滿江紅》。說課環節說了一半,被他叫停說可以了,他還說:“同學,你要自信一點。”
從面試場地到主校門的路特別長,天已經黑下來,我一邊走一邊哭,在這個陌生的校園里,誰會在意一個陌生女孩的眼淚呢?
到下半夜手機響了一聲,校方短信通知我:“恭喜你被我校錄用了!天亮以后請過來簽三方協議。”
去海南,我內心挺掙扎的。我完成了爸爸的夙愿,真的走出了大山,卻跟他們天南地北。
從自然環境說,我更喜歡夏天家鄉的林場。那里四面環山,空氣清新,整體改造后的房子像迷宮一樣,家家戶戶都是紅色鋼瓦房,紅色大門,藍色障子,兩家一組房子連脊,巷道四通八達,一側種櫻桃樹,一側種黑加侖。林場人還有一個習慣,家家戶戶都不鎖門。出去的時候,我們把鎖頭掛在門上,用這種方式告訴來人:主人不在家,有空再來吧。
只身在外,我常常看到自己身上的山里人印記——真誠、直率、肯吃苦、不服輸,那也是爸爸身上的印記。我是爸爸親手培植的一朵木耳,怎么可能不像他呢?
(摘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我教過的苦孩子》,西米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