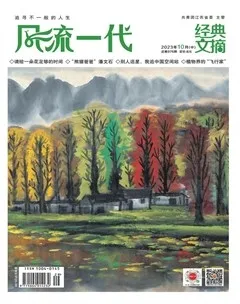別人追星,我追中國空間站
劉博洋

“吹出去的牛,要自己圓回來”
2020年,我在西澳大學讀博士。由于疫情,我不得不在澳大利亞滯留半年,每天封在家里,我就開始研究如何用軟件去控制望遠鏡,從而跟蹤拍攝空間站。
我一直在找相關工具,一開始試著用國外作者的一些軟件來操作,但能用的很少,各有各的bug,過了很久也沒什么進展。我終于實在受不了等待別的軟件作者更新,下定決心要自己做一個。
在網上發布視頻,包括跟一些媒體在聊的時候,我都說了這件事。牛吹出去了,要是不兌現,結果會很尷尬。所以我格外認真地做這件事,大概用了半個月時間,我一口氣把程序做了出來。其實那時候國內至少有三個團隊在寫相關程序,只不過我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拍空間站有很復雜的流程,光有軟件遠遠不夠。首先,我要知道空間站什么時候過境,掌握它的規律很重要。根據公開資料以及請教航天專家,我搞清楚了每一次發射前后它有哪些構型變化。在此基礎上,我再去請教航空專家,我再去確定觀測日期和地點,只有這樣,才能捕捉到它的全部構型的影像。
硬件同樣需要花費不少功夫。要有一個大口徑、長焦的望遠鏡,高像素密度的相機,并配上相應的赤道儀來保證追蹤精度。我當時什么都沒有,跑到朋友那里去借,相機靠租,每天120多元,電腦用的是二手的,配的搖桿也是大學同學送的。之前有人誤會我是“富二代”才能有錢搞這事,完全錯誤。我算了算,租兩周相機的費用是我那時所有的開銷。
籌備的過程中,有兩個好朋友對我至關重要,他們是龜龜和王卓驍。龜龜是文科生,負責拍視頻,并時不時提供“情緒價值”,常鼓勵我們。王卓驍是隔壁清華的天體物理學博士,我們是2014年在天文社團圈認識的。
2022年4月4日,我們和往常一樣,到了這個停車場。那天,我們一直在等,直到國際空間站出現在畫面中。它的過境時間在5分鐘左右,我們拍到了近3分鐘。這足以觀察它過境期間相對姿態的變化了。而且因為在之前大部分人都只能拍到少數幾幀的畫面,而我們一次觀測可以收集上萬幀圖像,可以疊出更清晰的畫面。
那一刻,我們全部歡呼了起來。
打開新世界的望遠鏡
我是比較幸運的人。我從小喜歡天文,這個愛好被保護得很好,后來的求學時期還受到了專業教育,這才能有今天。
4歲時,我從電視里看到一條新聞——彗星會在當晚撞擊木星。我一聽,覺得特別有意思,我想象著,天上出現放禮花的壯觀景象。實際上什么也看不到,因為撞擊點在木星背面,哪怕在它轉過來之后,地球上的我們也要用很大的望遠鏡才瞧得見。
當時我不懂,拉著媽媽一起去夜觀天象,結果可想而知。但即使觀測失敗了,我現在仍記得,我在得知這件事時的那種興奮與期待。我對天空的好奇,從那時候開始了。后來,我爸媽帶我去了北京天文館,更是打開了我的世界。
我還記得天文館里有個展廊,上面掛了很多介紹星座和行星的宣傳海報。我大為震撼,回家后不久,我求爸媽給我買個望遠鏡,我想往天上看看。我父母很開明,托朋友辦了這件事,花了700元,兩人當時的月工資才200多元。
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高中加入的天文社。在那之前,我雖然有望遠鏡,但絕稱不上是天文愛好者。因為我沒有太多常識,進了社團,我才算正式入門。我發現,在月亮之外,有很多東西可看,比如木星、土星光環、彗星、深空天體。
那時,我還很愛看科幻,劉慈欣的所有作品都是在高中看完的。再加上當時讀了些科普書,又在學校論壇上結識了上北大的學長,我就立志要去北大物理學院。高考那年,我正趕上北大天文學系第一年恢復單獨招生,在填志愿時,我自然而然地就報名了。
在大學里,我開始參與拍攝銥星閃光之類的人造天體觀測活動,也知道一些資深愛好者可以拍到空間站凌日、凌月——通俗解釋,就是看到空間站在太陽或月球表面快速掠過,那時我也沒想過自己后來會去拍中國空間站。
為中國空間站而“跑”的人
在中國空間站的建設過程中,它前后經歷了13種構型,其中有2種是相同的。而我們的拍攝次數遠遠多于十二三次,所以出現的這些變化,都在我和小伙伴的記錄之中。當然,有些特殊的場景,像航天員出艙這種,我們還沒有拍到。
2022年,我們的日常是全國各地到處跑。說到跑,有幾段經歷能充分體現這種狀態。其中的一次,是我們先從上海飛到南昌,之后從南昌開車4小時到贛州。我們在當地好不容易找了個云縫,剛架起望遠鏡,云從四面八方涌過來。看到云過來,我們又趕緊往南跑,跑到下一個觀測環境好些的地方,剛放下心,結果云又追來了。中國空間站過境的5分鐘,云把天全遮住了,我們什么也沒拍到。
還有一次是在11月初。“夢天”發射后的一段日子,中國空間站的構型變化非常頻繁,我們要在10天之內拍攝完。最開始,我們在海南拍“夢天”發射,然后一路向北,到浙江、江蘇、北京。
尤其是從江蘇跑到北京那天,我們坐貨拉拉跑了17個小時才到地方。王卓驍在高速路口接的我們,又換了輛車,直奔懷柔。那天有大霧,連望遠鏡上都是水,我用紙一直擦,擦完左邊右邊起霧,擦完右邊左邊起霧,一直擦到中國空間站過境前,實在不能擦了為止。最后我們還是拍到了,盡管效果不太好。
整體來看,我在知乎上得到的反饋還是挺多的,其中不乏一些專業的建議和指導。話里話外,他們很為我驕傲,倒不是說咱們國家專業領域沒有高精尖的設備和相應的能力,只是說我和朋友們用低成本、消費者級別的設備完成了“拍空間站”這件事。
有人問過我什么時候最艱難。我實在想不出,困難肯定是有,想辦法克服就好了,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古人云,“為之,則難者亦易矣”,這是我所信奉的。
(舒暢摘自《新周刊》2023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