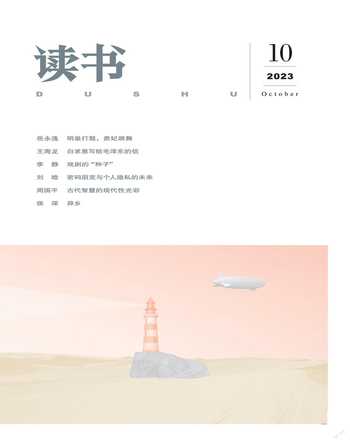回不去的孟加拉之夜
范晶晶
一
伊利亞德是宗教研究領域的巨擘,閱讀他的《神圣與世俗》《神圣的存在》《永恒回歸的神話》等著作,往往會震撼于其淵博的學識與詩性的想象力。他同時是一位作家,留學印度時與導師的女兒彌勒薏(Maitreyi,意為“慈愛”)有過刻骨銘心的情緣,并將這段往事寫成了半自傳體小說。小說女主角的原型彌勒薏是《家庭中的泰戈爾》一書的作者梅特麗娜·黛維夫人(梅特麗娜與彌勒薏是同一人名的不同音譯)。她是印度現當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熱心公益事業,促進婦女解放,多次赴海外講學,著作包括四卷孟加拉語詩集、八部關于泰戈爾的論著、四部關于旅行與社會改革的論述,還編選了三種泰戈爾、甘地與孟加拉世俗作家的文集。一次講座上,晏可佳教授生動地介紹了季羨林先生翻譯《家庭中的泰戈爾》時的幾番波折,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雖然大學本科時就讀過這本書,還抄錄了不少段落,但那時只停留在“好讀書,不求甚解”的階段,遑論知人論世。晏教授的講座似是一根細線,將之前遺落各處的珠子串聯起來。于是,一個個清冷的冬日,在完成日常的學術工作之后,我一頭扎進了二十世紀的孟加拉。
一九二八年,在一位印度土邦王公的資助下,伊利亞德來到加爾各答學習梵語與印度哲學,導師是達斯古普塔(Surendranath?Dasgupta),劍橋大學出版社五卷本《印度哲學史》的主編、蜚聲海內外的印度哲學史家。達斯古普塔對伊利亞德極為賞識,安排他住進了自己家里,與長女彌勒薏一起學習梵語、編訂圖書目錄。一個是來自歐洲的前途無量的弟子,一個是自己精心培養的少女詩人—十六歲時發表第一部孟加拉語詩集,由泰戈爾作序,二人成了達斯古普塔的驕傲。盡管旁人有些非議,但達斯古普塔毫不介意這對少男少女的密切交往,甚至主動提出由彌勒薏教伊利亞德孟加拉語、伊利亞德教彌勒薏法語。雖然彌勒薏一直都清醒地認識到傳統種姓制度的強大與二人之間深刻的鴻溝,伊利亞德卻堅信導師定會同意將女兒嫁給自己。當達斯古普塔終于發現兩人的情愫,立刻毫不留情地將伊利亞德趕出家門,并讓他承諾不再與彌勒薏有任何瓜葛。
事情至此,本來只是世上無數愛情悲劇中的一樁。然而,伊利亞德畢竟是天才的作家與學者。在喜馬拉雅山上苦修一段時間、療愈心傷后,他將這段經歷寫成小說《彌勒薏》。起初,小說是用羅馬尼亞語寫就,出版于一九三三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間陸續被翻譯成意大利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等,影響力最大的法語版將小說題名改為《孟加拉之夜》(La Nuit Bengali )。若僅是這樣,可能也只算是學界文壇的一件風流韻事。傳奇的是,當彌勒薏輾轉聽到這部小說的內容,驚怒交加,毅然決定去芝加哥與伊利亞德面談,二人達成和解并商定:在兩人的有生之年,不能出版小說的英譯版。之后,彌勒薏又提筆寫出了自己的故事版本,即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孟加拉語版《永不消逝》(Na Hanyate )。這部小說于一九七六年獲得印度文學院獎。同年,彌勒薏推出英文版(I t Does Not Die )。兩人分別于一九八六年、一九九0年離世后,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于一九九三年出版英譯《孟加拉之夜》(Bengal Night s ),并于一九九四年推出英文雙子版的《孟加拉之夜》與《永不消逝》。至此,延綿半個多世紀的一段情緣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這是一場旗鼓相當的愛情,經由文字獲得了不朽。在文學史上,書寫愛情的往往是男性,女性是沉默的、被消聲的。《鶯鶯傳》如是,《洛麗塔》亦如是。正如《閣樓上的瘋女人》的兩位作者所言,筆是陰莖的隱喻。在傳統社會中,膽敢握筆的女性是膽大妄為、無可救藥的冒犯者。不少評論者都觀察到:伊利亞德與彌勒薏之間不僅是男女關系,還疊加著歐洲與印度、西方與東方、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等各種關系的陰影。由此,彌勒薏的書寫就顯得尤為重要。她不滿于成為伊利亞德筆下異域的奇情女子、欲望的符號,勇敢地寫出自己的故事,既控訴了父權(夫權)、種姓制對女性的壓迫,也反抗了歐洲對印度的刻板想象。求真、尋美是貫穿小說始終的主旨所在,背后是彌勒薏的兩位精神導師泰戈爾與甘地的影子。
二
與伊利亞德的小說原題“彌勒薏”相比,法譯書名“孟加拉之夜”承載了太多的東方想象,無怪乎最為暢銷。當然,這一改名并非無據可依。小說的高潮部分正是女主角彌勒薏夜間溜進男主角阿蘭(作者本人在小說中的化名)的房間,實現靈與肉的結合。由于我閱讀的英譯版也沿用了法譯書名,下文就以《孟加拉之夜》指稱這部小說。
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基于對印度宗教的深刻體認,伊利亞德才建構起自己獨特的宗教研究體系,在論述中也經常援引印度的宗教現象為例,并給予了充分的理解與同情。但在《孟加拉之夜》里,或是羞于承認赴印度是為了拜師學藝,或是迎合當時歐洲對印度的想象,他將阿蘭的身份設定成鐵路工程師,承擔著為印度送去先進文明的使命。這樣一個關鍵的角色變化,給小說帶來了一系列邏輯無法自洽的問題,導致人物扁平化、行為方式莫名其妙。小說中,彌勒薏的父親對阿蘭青眼有加,目的竟然是收養他,以便在他回國時能一起移民歐洲。發現阿蘭與女兒的私情之后,父親勃然大怒,譴責他們破壞了自己的計劃,堅決棒打鴛鴦,甚至逼瘋了女兒。這就讓人很費解。阿蘭此時已有二十三歲,作為養子顯然年齡太大。成為女婿,反而能更好地實現移民的目的。由于人物行為不合常理,彌勒薏的父親就成了徹頭徹尾的暴君,一手促成了家庭悲劇—家族名聲掃地,一個女兒自殺,一個女兒發瘋。
在彌勒薏的小說中,女主角阿姆麗達(作者本人在小說中的化名,Amrita,意為“不朽、甘露”)得知男主角米爾恰以二人經歷為原型寫作的小說內容后,大為驚駭,認為不僅不真實、耽于幻想,而且過于色情,描寫的是欲望(lus t)而不是愛(love),因此致力于寫出一個還原真相的版本。孟加拉語版小說的標題Na Hanyate 來源于梵語,取自《薄伽梵歌》:
它無生,恒常,永久,原始;
當肉體被消滅時,它永不消逝。
米爾恰曾向阿姆麗達訴說過傾慕她的靈魂,二人最后見面時米爾恰吟誦的也正是《薄伽梵歌》中的這首頌詩。在獻辭頁,彌勒薏將小說作為祭品敬獻給大時神廟。這大概也是對自己終身景仰的導師泰戈爾的一種致敬:泰戈爾的《吉檀迦利》,標題意為獻給神的頌歌。《永不消逝》的敘事也被嵌入大時神的神力運作之下。大時神即Mahākāla,印度教三相神中主司毀滅之神濕婆的別號,在佛教文獻中被譯為大黑天(kāla兼具“時間”與“黑色”之義)。阿姆麗達少女時代曾寫過一首詩:
留在身后的時間忽而向前
…………
每一剎那,從空無的海洋中都有物成形,
落向無岸之岸。
逝去的可能回歸,陳舊的或能更新,過去與現在的界限崩塌了。阿姆麗達的身體被禁錮于現實,意識卻進入了無限的時間。正是在這樣一種流動的時間里,她以意識流式的敘事穿梭于現在與過往之間。在過去與現在的重影中,阿姆麗達看到米爾恰正坐在餐椅上,將咖啡杯放在桌子上:
熱騰騰的咖啡上升起蒸汽,
潤濕了你眼鏡的黑邊;
那個清晨,還在無垠之藍的某處等待。
二人共讀《沙恭達羅》是兩部小說都描述過的一個浪漫場景,在小說中的地位類似于《紅樓夢》中寶黛二人共讀《西廂記》。伊利亞德采取了其中愛欲與贖罪的主題來建構小說敘事。這也是當時歐洲的東方學家對《沙恭達羅》的普遍評價,并影響到印度本土知識分子對這部經典梵劇的理解。當兩人坐在墊子上聽高度近視的老師評點《沙恭達羅》時,阿蘭一個字也沒聽進去,而是悄悄地撫摩彌勒薏的手、親吻她的頭發。彌勒薏向阿蘭講解迦梨陀娑每一句詩頌里的情愛細節,以對應二人秘密的愛戀。在那些幽會的夜里,也是彌勒薏占據主導地位。她猶如愛欲的化身,引導阿蘭享受魚水之歡。與此同時,彌勒薏又常常發問:他們這樣是否在犯罪?在這樣一種愛與罪的糾纏中,阿蘭懷疑彌勒薏是否有意勾引自己,二人之間并非愛情,而是魅惑。他還疑心彌勒薏行為不檢、可能有別的情人,甚至到了蕩婦羞辱的程度。小說末尾果然給彌勒薏安排了這樣一種結局:她將自己隨便委身于一個水果小販,生下私生子;原本是想以此自甘墮落、辱沒門楣的方式讓父親放棄自己,從而能與阿蘭廝守,但并未如愿。這段無疾而終的愛戀最終因阿蘭被趕出家門后的自虐、在喜馬拉雅山上的苦修才得以升華。對應的是梵劇中沙恭達羅通過凈修林里的數年苦行,滌盡身上愛欲的罪愆,加上子嗣的加持,才能與丈夫團圓。彌勒薏與阿蘭的故事卻以無可避免的分離收場。
難怪彌勒薏聽到小說情節后勃然大怒,決心寫出真實的過往。她在記憶里搜尋真相,往事一幕幕浮現。事隔四十余年,當阿姆麗達接到米爾恰學生的電話,她夜不成寐,想起《沙恭達羅》中的一段話:
看到美麗的東西,聽到甜蜜的樂聲,
連幸福愉快的人也會渴望又激動。
他心里現在回想到以前沒有想到的
前生的堅貞不渝的愛情。
她回憶起的都是情竇初開的少女怦然心動的時刻。從和平鄉返回加爾各答的火車上,二人曾四目相對,阿姆麗達立刻體會到泰戈爾詩中所吟詠的分離中的合一、相會時的渴望與惆悵,甚至能夠聞到想象中的米爾恰項上花環的香氣—在古代印度的選婿大典上,少女會為心儀的愛人戴上花環,表達傾慕。她每天無數次地去查看門口的信箱,只為路過米爾恰的房間,期待他能看到自己的身影,或許還能說上一兩句話。這種陷入愛河時的小兒女情態,在《孟加拉之夜》中是看不到的。《孟加拉之夜》中的阿蘭也有不少糾結的心緒,但令他左右搖擺的主要是作為白人該不該愛上一個印度女子,患得患失,表現得萬分擰巴。
阿姆麗達對感情的體認深受梵語詩人迦梨陀娑的影響。她在小說中自陳:像她家那樣的中產階級家庭,對愛情與性事是避而不談的。在母親片言只語的教導下,她或許能夠識別那些想猥褻她的親友,但少女情懷萌動的時刻,是迦梨陀娑充當了愛情導師的角色。在為米爾恰盛裝打扮時,她想到的是《云使》中的詩句:
那里的女郎手握秋蓮,發間斜插冬茉莉,
面容與春季的羅陀花相襯,更添嬌艷,
發上有鮮花古羅波,耳旁有夜合花逞美麗,
你所催開的迦曇波花正在發上中分線。
還要女伴為自己找來蓮花,才算是完成了裝扮。夜晚枯坐于樓上的閨房,想著住在樓下的米爾恰,她常常感到痛苦的思慕。一想到二人可能會天各一方,更是陷入難以想象的無盡黑暗。這時她以念誦《云使》排遣愁緒,與那位藥叉一樣,在“離思”(viraha)中夢想重逢的天堂。
三
伊利亞德與彌勒薏的情緣始于一九三0年,兩人分別是二十三歲與十六歲,都正值少艾慕色的美好年華。被迫分開后,他們都度過了重建身心的艱難時期。不到三年,伊利亞德寫作《彌勒薏》,將這段歲月封存于文字,開始自己的新生活。《彌勒薏》獲得的巨大成功,與其說僅歸功于小說本身,不如說是借力于印度異域題材在歐洲的流行。早在一九二四年,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就已風靡整個歐洲。伊利亞德的寫作也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了這類小說的一些套路。例如將主人公設定為赴印度的鐵路工程師,阿蘭在日記里寫道:“這里蔓草叢生,人們殘忍又無知。我想發掘這些人的美學與倫理生活,每天都收集趣聞、拍攝相片、繪制系譜圖。”多么典型的東方主義敘事!得知在孟加拉精英圈小有名氣的少女詩人彌勒薏要做一場關于“美的本質”的演講,阿蘭發出感慨:“我絕想不到這孩子能解析這么嚴肅的問題。”即便是對傾心仰慕的女子,殖民者的傲慢依然無處不在。在《永不消逝》中,最后一次見面時,彌勒薏對米爾恰提出抗議:“看看你在書中描述的我的樣子,我看不出一點我的影子。這不是我。”米爾恰解釋道:“幻想,幻想。我想把你塑造成一個神秘的存在,一位女神,比如說迦利女神。”米爾恰的回答對應了《孟加拉之夜》中阿蘭對彌勒薏的評價:“我多么熱愛這些印度人,甚至想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他們所有人都在自身存在的暗處培養了一種完全無法洞穿的歷史與神話。對我來說,他們是多么深不可測、復雜難懂。”神秘的印度、輕佻多情而不可捉摸的異域女子,伊利亞德牢牢把握住了暢銷書的密碼。《永不消逝》里米爾恰的弟子塞巴斯蒂安曾坦承:他正是通過《彌勒薏》這部小說來了解印度的。
相較而言,彌勒薏的小說《永不消逝》出版于四十余年之后。經過歲月的沉淀,情感愈加醇厚,視野也更為開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加爾各答,群英薈萃。常來彌勒薏家中做客的既有本土精英如甘地,也有后來享譽西方的印度學家如圖齊。在小圈子之外,民族獨立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孟加拉之夜》對這些并無著墨,集中于描寫二人的情愛。《永不消逝》卻看似閑筆式地交代了社會大環境,阿姆麗達不無反諷地評論:精英階層根本不相信,或者說不愿意看到,英國人被趕出印度。走過人生的悲歡離合,彌勒薏能更深刻地反思當年二人悲劇的根由。種姓制度的偏見、父權與夫權的專制,讓她無路可逃。小說中,當妹妹無意間說出阿姆麗達與米爾恰的秘密戀情,母親在了解阿姆麗達的心意之后,有意成全二人。父親卻堅決要將女兒嫁給相同種姓的印度人,母親只好違背對女兒的承諾,屈從于丈夫的意志。盡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安貝卡的領導下,成千的印度民眾已見證了焚燒《摩奴法論》的歷史事件,但《摩奴法論》所規定的“愛的律法”,依然禁錮著無數人的人生。正如阿蘭達蒂在《微物之神》中所言,它規定了“誰應該被愛,如何被愛,以及得到多少愛”。
《永不消逝》不僅描述了阿姆麗達與米爾恰的悲劇戀情,還交代了之后阿姆麗達父母的婚姻失敗,從而在更廣闊的范圍內討論印度的父權與夫權。米爾恰住在阿姆麗達家的那段日子,仿佛伊甸園般的時光。彼時母親三十二歲,是美麗能干的家庭主婦,熱情接待丈夫的同事、弟子、親友,將家事打理得井井有條。阿姆麗達將母親比作羅陀(Rādhā ),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侍奉她唯一的神——丈夫,時刻滿足他的需求,取悅于他。米爾恰被趕出家門以后,這個家開始分崩離析,不再高朋滿座,寄居的親戚也紛紛散去。不久之后,父親嫌棄身為傳統女性的妻子沒有文化,有了外遇,與一位女博士走到了一起。一九四一年,父親拋下虔誠的妻子與六個孩子,離家出走。阿姆麗達感慨:“我們漂浮于詩歌與哲學桂冠上的美好家庭,在現實世界凹凸不平的巖石上撞得粉碎。”小說交代了一個細節:當阿姆麗達在火車上痛哭流涕時,父親沒有絲毫反應。阿姆麗達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這些事情上,父親就是一個什么也不會的孩子。他被照顧得太好,事事有人代勞,甚至從未親自倒過一杯水。這樣一位父親,當然沒有無私愛人的能力,更無法共情家人的痛苦。只有他的愿望才需要被滿足,其他人都不值一提。在這個正統的印度教家庭,妻子縱容了專制的丈夫,間接傷害了無辜的女兒,卻也難逃被遺棄的命運。
米爾恰離開之后的第四年,家里將阿姆麗達嫁給未曾謀面、年長十四歲的丈夫。在制造了一對悲情戀人、一對怨偶夫妻之后,或許是不忍心摧毀所有的美好,造物主好心地給阿姆麗達安排了一位模范丈夫。雖是盲婚啞嫁,二人之間并無多少共同語言——與世間大多數夫妻類似,一天的交談不超過七八句話——但丈夫性格溫和、隨遇而安、富有同情心,給了阿姆麗達最大程度的尊重與信任。新婚不久,阿姆麗達拜訪泰戈爾,詩人開導她:“我希望無論你的命運如何,你都會變得比它更強大。……如果你能筑起一個美好的愛巢——家中人人安樂——我答應你,我會去你的樂園做客。”當阿姆麗達隨夫遷居到大吉嶺附近的茶葉種植園,那個曾在米爾恰面前意氣風發地自詡為“哲人”、立志欣賞并書寫世間美好的少女詩人不見了。她感覺自己成了被流放的深閨怨婦,時時忍受孤獨的吞噬,于是給泰戈爾寫信。詩人也果然履行了諾言,在逝世前的三年間,不顧路途險阻,四次造訪阿姆麗達,并在她家小住。泰戈爾告訴她工作是最好的伙伴,鼓勵她與種植園里的五六千苦力、工人交朋友,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由此,阿姆麗達“找到了尋求解脫的新方法”。她認為這三年才是充實的三年,而在林間居住的其他十九年不過是單調的重復罷了。這三年的經歷,彌勒薏寫進了《家庭中的泰戈爾》。對阿姆麗達來說,詩人的離世,意味著青年時代的結束。
當一對戀人于一九三0年被迫分離時,泰戈爾正在歐洲旅行。他返回印度后,阿姆麗達寄去了一封傾訴痛苦的信件。詩人回信安慰:
生活的圓滿不在于忘記痛苦,而是日復一日將悲傷轉化為理解,將殘酷轉化為溫柔,將酸楚轉化為甜蜜。我認為對你來說這不無可能,因為你有想象力,想象力就是創造力。不要將自己棄置于命運之手。你將會創造自己的命運。
可以說,這段話完美地詮釋了《永不消逝》這部小說的精神內涵。書中數次提到:博學與知識不一定能讓人變得完善。拋妻棄子的專制父親就經常被泰戈爾戲稱為“博學的山羊”,阿姆麗達也曾疑心米爾恰是為了追求哲學才遁入山林、與自己完全斷絕聯系。想象力則是詩人的特權。彌勒薏也曾是天才煥發的少年詩人,后來歷經生活的磨煉,又有數年親侍泰戈爾身旁。她于暮年寫成的《永不消逝》,比起伊利亞德的年少之作《孟加拉之夜》,褪去了青澀,多了溫柔與堅定。
最后在芝加哥重逢時,曾經的少年男女都已白發蒼蒼。一個是功成名就的宗教史家,一個是熱心公益事業的作家,但往事依舊無法釋懷。阿姆麗達質問米爾恰為何多年間從不回復自己的信件。這時,米爾恰已不再是當年那個偶爾多疑、嫉妒、魯莽的小伙子,盡管還保留著一些調皮的赤子心性,但終究是熬過了歲月的大學者,他沉吟答道:
我將你安置于時空之外……
有那么多美麗的事物——須彌山、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你能得到它們嗎?我們知道它們屬于我們,但你能占有它們嗎?然而那并不是遺忘。它們依然像是一個人隱秘宇宙最深處捕捉到的最美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