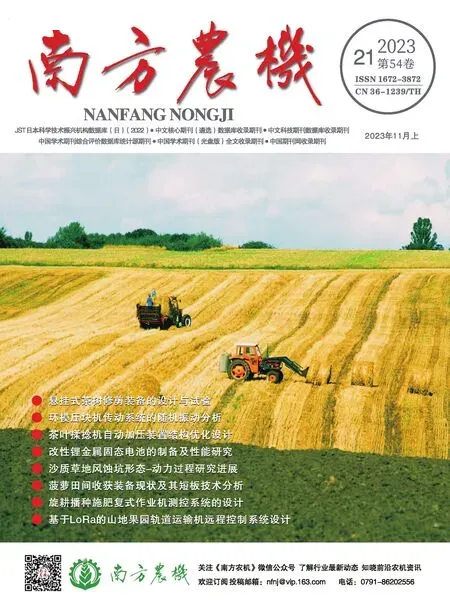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
——基于全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王作功 ,陳正星
(1.貴州財經大學綠色發展戰略研究院,貴州 貴陽 550000;2.貴州財經大學大數據應用與經濟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0)
0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均得到顯著、持續提升,并于2020年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但在肯定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經濟社會發展仍然面臨不少問題和困難,其中就包括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差距仍然較大等,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不平衡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因素。改善城鄉收入差距已成為我國“三農”工作的重點和“十四五”時期的宏觀政策基本導向。
中國是農業大國,用全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近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使14 億人端牢了飯碗,成就舉世矚目,但在農業生產中使用農藥、化肥、農膜等產生的大量溫室氣體也給我國的生態環境帶來了沉重的打擊。2022 年,我國提出了“雙碳”目標,即在2030 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而在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中,農業溫室氣體排放約占總量的17%,因此,提升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是實現農業綠色發展,實現“碳中和”目標的必由之路,同時,對保持耕地生態健康亦具有積極意義。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與推動農業綠色發展都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偉大征程上的重要內容,那么兩者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政策目標的表現又是否具有趨同性?本文嘗試分析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以期為農業綠色發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
1 文獻綜述
鄭殿元等[1]認為,中國當前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同時,面臨著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和空氣質量惡化加劇等問題,不僅阻礙了城鄉一體化建設,而且嚴重制約了我國從經濟增長向經濟高質量發展轉變的步伐。持續的城鄉收入差距會導致農村勞動力的重新分配,使得更年輕、更健康、接受過更高教育的人口流出農村。而當收入差距較大時,由于農業投資回報較低,農民寧愿將生產要素投向非農業生產,也不愿投資于農業活動。并且,長時間以來,我國的可用耕地數量一直呈溫和下降趨勢,糧食播種面積亦是如此,但中國能實現如此長時間的農業生產力增長,除了對糧食品種的改良,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化肥的使用。Zhang(2020)等[2]研究發現,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將會顯著提高化肥的使用強度,而化肥使用強度與農村人均收入間表現出“倒U”型關系,但其峰值點遠高于我國各省農村人均實際收入,即在達到峰值之前,化肥的使用強度將進一步增加。而王寶義(2016)[3]的研究發現,農業化學制品對農業碳排放量的貢獻巨大,其中,化肥源排放的占比高達60%,減少、控制以化肥為主的農業化學制品對降低農業碳排放意義巨大。但高晶晶等(2021)[4]的研究發現,當前農業化學制品對農業產出增長的動力已經開始減弱,農膜的產出貢獻也不再顯著,因此,未來不能再依靠農業化學制品的投入來實現增長。Zhang等(2022)[5]實證研究了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與空氣質量之間的關系,發現城鄉收入差距雖然不會影響空氣質量的“倒U”形狀,但會延遲經濟增長與環境脫鉤的時間。并且,城鄉收入差距與空氣質量間呈現“U”型關系,其閾值為泰爾指數計算的0.03,當低于該值時,城鄉收入差距是空氣污染的“絆腳石”,超過則成為“墊腳石”,意味著當前階段,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會增強民眾為環境治理付費的意愿。另一方面,Gao 等(2014)[6]以1978—2010 年省級面板數據實證研究了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增長的不利影響,研究發現城鄉收入差距與農業產出呈負相關關系,會對農業增長產生不利影響,進而不利于經濟增長。由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導致的年輕人口流失,加上人口老齡化的影響,農村勞動力的數量、質量以及技術經驗的積累、更新等生產要素的投入將受到影響。蔣健等(2023)[7]研究發現,現階段,我國人口老齡化將不利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即農業的產出將受到不利影響。在對環境質量的態度上,不同收入人群對其要求存在差異,通常情況下,收入水平更高的群體對環境質量有著更高的要求,而由于城鄉收入差距的存在,一方面,環境規制與居民環保意識的不同,可能導致大氣污染向農村地區轉移;另一方面,農村地區較低的收入,可能使得農村居民對收入問題的關注程度高于環境問題,將出于提高收入或解決就業的目的,引入環境門檻較低的企業或產業,進一步惡化農村地區的環境質量。井波等(2021)[8]的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認為城鄉收入差距與環境污染間表現出正相關關系,即收入差距的擴大會顯著降低環境質量,并且這一現象在西部地區比中東部地區更為明顯。
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增加農業化學制品的使用,導致年輕勞動力的流出,農民生產要素投向的轉變,進而增加農業的碳排放量,造成大氣污染,同時降低農業產出,不利于農村居民收入的可持續增長,將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形成惡性循環。那在促進農業綠色發展的背景下,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將產生怎樣的影響?收入差距的擴大是否不利于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兩者之間的關系在不同省份間是否表現出差異性?這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也是本文擬回答的關鍵問題。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擬探究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選取我國30 個省份2011—2019 年的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西藏自治區因數據缺失嚴重而剔除,其中,主要數據來源為各年份《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部分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
2.2 變量說明
2.2.1 解釋變量
本文以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Prop)作為城鄉收入差距的測度指標,即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該值越接近1,則城鄉收入差距越小。為確保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計算了相應年份的泰爾指數(Theil),以便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計算過程如下:
其中,j=1,2 表示城鎮或者農村地區;yi,t,j表示i省在t年的城鎮或農村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yi,t表示i省在t年的總收入;pi,t,j表示i省在t年的城鎮或農村地區人口數,pi,t表示i省在t年的總人口數。
2.2.2 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參考沈滿洪等[9]的研究采用SBM-GML 模型計算得出,構建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表1 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指標
2.2.3 控制變量
分別選取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Pgdp)、城鎮化率(Ur)、政府干預程度(Int)、對外開放水平(Op)、區域創新能力(Inv)以及產業結構水平(Is)等為控制變量。其中,城鎮化率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值;政府干預程度為政府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該值越大表示政府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干預程度越大;對外開放水平以進出口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表示;區域創新能力為每萬人的專利申請受理量;產業結構水平以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表示,該值越大表示產業結構水平越高級。
2.3 模型構建
通過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探究城鄉收入差距是否能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本文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GTFPi,t表示省份i在第t年的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Propi,t表示省份i在第t年的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Controli,t表示系列控制變量;λi和ηt表示控制了省份與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系數α2為本文關注的回歸結果,若該系數顯著為正,則表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將促進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反之則抑制。
2.4 描述性統計
由如表2 所示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可知,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比(Prop)的最大值為0.542,最小值為0.272,說明收入差距小的省份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約是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4%,收入差距大的省份農民可支配收入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到30%。可以看出各省份間均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并且這種差距在不同省份間的表現也存在較大的差距。從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來看,最大值為1,最小值為0.123,標準差為0.153,表明各省份間的農業綠色發展存在較大的差距。

表2 描述性統計結果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基準回歸
基于前文模型構建,本文主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列(1)為控制省份和年份固定效應但不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列(2)為同時控制省份和年份固定效應并引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這樣就得到了一組有對比性的結果數據。

表3 城鄉收入差距對各省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由表3 可以看出,在控制年份和省份固定效應并引入控制變量的過程中,核心解釋變量Prop 的系數符號分別在1%、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擬合優度從0.243 提升到0.424。變量Prop 表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該值越接近1 則城鄉收入差距越小。以列(2)為例進行解讀,其回歸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兩者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能顯著提高各省的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水平。
3.2 異質性分析
中國幅員遼闊,各省份在地貌類型、氣候生態、自然資源稟賦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整體上呈現西高東低的局面,由于地形地貌、土地肥力、適種糧食種類等存在差異,可將各省份區分為糧食主產區和非糧食主產區(黑龍江、河南、山東、四川、江蘇、河北、吉林、安徽、湖南、湖北、內蒙古、江西、遼寧13個省份為糧食主產區,其余省份為非糧食主產區)。而兩種區域在農業技術條件、農業政策支持力度、惠農政策的貫徹落實等方面會存在一定的差異。據此,本文參考金紹榮等[10]的研究區分糧食主產區與非糧食主產區,探究兩者關系表現的異質性,具體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區域異質性
表4 中的第(1)、(3)列為未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第(2)、(4)列為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其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符號始終在1%、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意味著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對糧食主產地區和非糧食主產地區的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均能起到促進作用。但對糧食主產地區的系數(2.667)要大于非糧食主產地區(2.355)。表明就促進作用的強度而言,對糧食主產地區的促進作用比非糧食主產地區更強,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糧食主產區第一產業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占比更大,政府對各項農業財政補貼的支持和傾斜力度也更大。若能通過其他渠道使得農民收入增加,農民增加農業化學制品投入以提高收入的意愿將會降低,農業碳排放將會減少,進而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更大。
3.3 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計算了相應年份的泰爾指數,該指標越小則收入差距越小,將其作為解釋變量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 所示。從回歸結果看,在加入控制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Theil 的系數符號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意味著泰爾指數與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即泰爾指數增大,將會抑制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反之,泰爾指數減小(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會促進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與本文之前得出的結論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5 穩健性檢驗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對2011—2019 年30 個省份的城鄉收入差距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測度,而后通過固定效應模型實證研究了兩者之間的關系,并對糧食主產地區和非糧食主產地區進行了異質性檢驗,最后為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計算了相應年份的泰爾指數,替換城鄉收入比值重新進行回歸,得出以下結論:
1)城鄉收入差距與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將抑制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與推進農業綠色生產在政策目標上具有趨同性質;
2)無論對糧食主產地還是非糧食主產地而言,兩者之間的關系不變,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對糧食主產地區的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促進作用更強。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堅定不移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補齊農業農村發展存在的短板弱項,不斷優化對“三農”的政策供給,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持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推動城鄉協調發展。同時,要重視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降低的負面影響,健全耕地休耕制度,推廣病蟲害綠色防控產品和方法,加強可降解農業化學制品的研發推廣,推動農業綠色發展。最后,加強農業宣講,增強農民對生態農業的認知,鼓勵使用農業綠色生產技術,完善農業補貼制度中生態綠色導向的制度建設,讓農民嘗到綠色農業的甜頭,使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與農業綠色發展和弦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