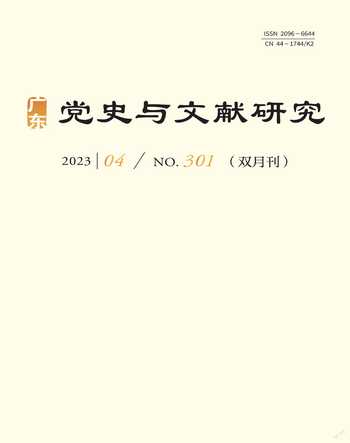四三會議前東西蒙聯絡史事之探析
【摘 要】1945年底,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派出以秘書長劉春為團長的東蒙工作團,隨后由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信使”包玉昆陪同,從張家口出發,經由承德、赤峰,前往王爺廟了解情況,協商邀請東蒙自治運動領導人,與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主席烏蘭夫進一步談判內蒙古自治運動問題。中經諸多曲折,1946年4月3日,東西蒙領導人終在承德召開會議,商談并協定自治運動實行形式上的統一領導。歷史上長期分割的東西蒙就此逐步走上聯合之途,統一的內蒙古自治區域就此發端。
【關鍵詞】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四三會議;劉春;烏蘭夫
【中圖分類號】K26;D2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6644(2023)04-0031-11
抗日戰爭勝利前后,在蘇聯紅軍的迅猛打擊下,偽蒙疆和偽滿政權土崩瓦解。乘此時機,內蒙古東部、西部地區的蒙古族迅速掀起民族自治浪潮,形成兩個運動中心。在東部的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市),東蒙繼舊式王公貴族衰落而新興起的一批接受近代教育的蒙古族精英,恢復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組建東蒙本部,1946年1月中旬成立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并得到中共中央東北局、西滿分局及其地方黨政軍組織的贊助;在西部的張家口,1945年11月底,在中共中央晉察冀局支持下,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蒙古族干部烏蘭夫(當時名云澤)領導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這時,無論是東部還是西部的蒙古族,受到近代民族主義潮流的影響,都迫切渴望實現統一自治。1945年10月初,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派出代表包玉昆等人,前往西蒙聯絡,在途中路經張家口時,包玉昆聽說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剛剛成立,便與之取得聯系。1945年12月底,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組成以劉春為團長的東蒙工作團,前往王爺廟了解情況,協商邀請對方領導人到赤峰或承德,與烏蘭夫進一步談判內蒙古自治運動問題。中經諸多曲折,1946年3月底,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席博彥滿都等高層領導人,到承德與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主席烏蘭夫等人舉行會談,并就內蒙古自治運動的諸多問題達成原則性協議。內蒙古東、西部自治運動實現形式上的統一,歷史上長期分隔的東西蒙以及互相割裂的各盟旗逐步走向聯合之路。
到目前為止,對于上述東、西蒙聯絡的過程,既有研究成果或限于體例,或缺乏材料,大都語焉不詳。2016年,包玉昆之子包文漢整理注釋出版《包玉昆日記》,逐日記錄東、西蒙聯絡的行程,為考察這一段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本文擬根據該日記,結合重要當事人劉春、烏力吉那仁、克力更等人的回憶、文集,以及中共西滿軍區派駐王爺廟代表胡昭衡的日記、《晉察冀日報》的相關報道等,仔細厘清東、西蒙聯絡的大略過程。
一、東蒙自治運動領導人尋求聯絡西蒙
內蒙古地區東西狹長,從王爺廟到張家口,直線距離也有850公里。抗日戰爭結束之際,兩地雖經赤峰、圍場、庫倫,有公路連通,但經日軍破壞,行軍困難;從王爺廟出發的鐵路交通,呈大大的反轉“L”形,要一直向南,再向西,繞道洮南、鄭家屯、通遼、錦州、北京,長達1300余公里。更要者,戰亂時期,地方秩序混亂,火車基本不通。其他的通信方式,如電話、電報等同樣受到波及,也無法及時互通消息。當時,王爺廟周圍地區正在鬧“百斯篤”(即鼠疫),進出均需消毒,極不便利。因此,王爺廟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東蒙本部與張家口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很難迅速了解對方的真實情況。直到1946年2月初,哈豐阿等人僅僅得到云澤活動的只言片語,還不知道烏蘭夫早已改名云澤,到張家口領導自治運動。錫林郭勒盟的“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在1945年10月被烏蘭夫改組三個月后,王爺廟仍然沒有得到任何消息。
同樣,對王爺廟東蒙自治運動的詳細情況,遠在張家口的烏蘭夫也不甚了了。1946年2月2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烏蘭夫以答“新華社晉察冀總分社”采訪的形式,發表談話,稱對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沒有得到關于這問題任何消息”。烏蘭夫此時擔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委員和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常務委員會主席。他的上述說法雖有托詞之嫌,可也并非全是虛言。在發表上述談話的第二天,烏蘭夫給中共西滿分局和冀熱遼分局發去一封電報,其中對“東蒙問題”的介紹同樣簡略而模糊:“據悉,蘇(聯)解放東北時,主要蒙奸被俘,次要者(官僚政客)自行組織一政府,要求高度自治,負責者為包寶臣(即包音滿)(應指博彥滿都。博漢名包云蔚,字豹忱——引者注)。另有一內蒙人民革命黨,系哈豐額(即哈豐阿——引者注)負責。哈曾與日(本)關系甚密,此輩與外蒙關系不詳。白云梯之弟白云航,亦負責該黨,已被王爺廟派赴赤峰活動。”這封電報系中共不同地區黨組織之間互通消息之用,烏蘭夫不可能在這里再隱瞞任何訊息。這進一步證實烏蘭夫的確不了解東蒙自治運動的具體情況。
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東蒙本部成立后,希望與蒙古國聯絡,可苦于沒有直接通道。為此,1945年10月5日,他們以特木爾巴根、薩嘎拉扎布、哈豐阿、烏云達賚的名義,給烏力吉敖其爾(又名寶彥陶格陶乎、烏獻文)、都楞倉(白海風)、阿拉坦道爾吉(佛鼎)、敖其爾等人寫信,派包玉昆與富理清桂(后者在途中因病很快返回王爺廟)親自去送。該信說明東蒙的情況和意圖,詢問西蒙對自治運動的意見,并要他們代為與蒙古國溝通。
另有說法稱,特木爾巴根曾給佛鼎和云潤寫信,派包玉昆帶著去西蒙聯系,時間在1945年12月1日。從包玉昆于12月19日之前(一說11月底,一說12月初)已經抵達張家口來看,按照當時的交通、治安狀況,即便快馬加鞭,要在半個多月內從王爺廟趕到張家口,也是幾乎不可能的。據音樂家馬可的日記,1946年中,他們一行人從張家口到突泉縣(此地距王爺廟僅100余公里),乘坐汽車,行程3000里,歷時長達3個星期。因此,特木爾巴根在1945年12月1日寫信,請包玉昆帶去西蒙聯系佛鼎、云潤的說法,可能不正確。
1945年10月5日這封信的署名之所以以特木爾巴根為首,并非其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地位最高,而是因為:第一,其他如薩嘎拉扎布、哈豐阿、烏云達賚等人一直在東蒙生活和工作,與西蒙缺少聯系;第二,特木爾巴根與佛鼎、烏力吉敖其爾等人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系北平蒙藏學校中學部的同窗,后又一起到蘇聯學習。1929年6月末,受共產國際派遣,佛鼎帶領烏蘭夫、特木爾巴根、烏力吉敖其爾等一批蒙古族干部從莫斯科出發,回內蒙古分三路從事地下工作。其中,佛鼎、烏蘭夫、奎璧等人到歸綏(今呼和浩特)、包頭一帶,為西路;德勒格爾回克什克騰旗和察哈爾,為中路;特木爾巴根、朋斯克、烏力吉敖其爾回哲里木盟(今通遼)和熱河一帶,為東路。烏力吉敖其爾后打入偽蒙古軍第九師,到西蒙活動。特木爾巴根在寫這封信時,不知道烏力吉敖其爾在蘇蒙軍占領錫林郭勒盟時已率部起義,隨即被調往蒙古國集訓,也不知道佛鼎早已離華去蘇。
從王爺廟經熱河、察哈爾去往西蒙,張家口是必經之地。1945年11月底或12月初,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剛剛成立。包玉昆聽說這個組織后,即到聯合會聯系。在王爺廟,包玉昆不屬于最高層領導人,啟程時自治運動又剛剛展開,掌握的信息自然有限。可是,在當時交通、通信基本斷絕的情況下,他畢竟給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帶來了東蒙自治運動的大致情況。
二、東蒙工作團從張家口抵赤峰
約略聽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在東蒙的活動后,烏蘭夫扛著內蒙古“聯合”自治運動的大旗,立刻敏銳地意識到,與東蒙取得聯絡勢在必行。1945年12月29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組成東蒙工作團,從張家口出發。該工作團由劉春、克力更、孔飛、烏蘭、包彥、田戶、烏力吉那仁、賽西雅勒圖、慶格勒圖、高德明、桑培勒、白音倉等十余人組成,劉春任團長,包玉昆陪同帶路。劉春,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長期從事民族研究工作,抗戰結束后來到張家口,協助烏蘭夫領導內蒙古工作,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立時任秘書長。其任務是代表烏蘭夫赴王爺廟,了解對方情況和態度,就內蒙古自治問題“進行初步協商”,再邀請東蒙主要負責人到赤峰或承德,與烏蘭夫進一步會談。同時,中途留下一部分干部,在東蒙開展工作。
東蒙工作團從張家口乘火車出發,于次日凌晨抵達懷來縣兵站。自此改為步行,經延慶縣(1945年12月31日,此為路經或抵達的時間,下同),懷柔區琉璃廟鎮、湯河口鎮、長哨營鄉(1946年1月3日),灤平縣虎什哈鎮(1月5日)、張百灣鎮(今小白旗鄉)小白旗村、灤平縣城(1月6日),灤平縣張百灣鎮張百灣村、藍旗村(1月8日),于1月9日到達承德。承德時為中共冀熱遼中央分局、熱河省委駐地。
停留8天后,1月17日,除田戶、慶格勒圖、高德明、桑培勒等四人留下組建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承德辦事處外,東蒙工作團其余人員乘汽車離開承德,準備沿承(德)赤(峰)公路,經隆化、圍場、(西)老府前往赤峰,并在當天到達圍場縣城。按照該天的行進速度,再用一天就能到赤峰(承德距離圍場縣城約138公里,距離赤峰267公里)。可次日,一行人離圍場60余公里時,在“敖包屯”(應為今赤峰市老府鎮東敖包村)遭遇土匪襲擊,無法通過。無奈之下,他們只好退到“大榆樹底下”(當為大榆樹底鄉駐地大榆樹底村,現為赤峰市松山區老府鎮二道河子水庫庫區),再于1月19日返回圍場縣城。劉春先派克力更、烏蘭夫婦二人回承德,再于20日留下包玉昆、烏力吉那仁、白音倉三人在原地待命尋機,其他人員同返承德。包、烏、白三人在等待一天后,于22日從圍場出發,沿另一線路,先向南再向東,經圍場縣碑亭子村、銀窩溝鄉、克勒溝鎮(23日)、三叉口(今赤峰市松山區穆家營子鎮)(25日),于26日上午抵赤峰。
劉春回憶說,從承德到圍場,東蒙工作團由熱河省軍區司令員段蘇權帶領一支小部隊護送。此說部分存疑。從在“敖包屯”遭遇土匪發生戰斗并斃匪2名、繳獲乘馬2匹的情況來看,有部隊護送應屬可信。可晉察冀中央局機關報《晉察冀日報》的一則消息稱,1月17日,即劉春一行離開承德那天早晨,段蘇權正陪同軍調部赤峰執行小組乘飛機前往赤峰。
那么,劉春等人是何時離開承德到達赤峰的呢?據劉春回憶,他們“在承德等了幾天,正好國共兩黨宣布停戰,要在赤峰設立一個軍事調處執行小組,段蘇權同志是赤峰軍調小組我方組長,美國派了兩架運輸機送段蘇權同志和其他一些設備器材到赤峰去。我和包彥同志就作為段司令員的隨從工作人員,一同乘飛機到了赤峰”。劉春第一次乘飛機,還坐在飛機運送的中型吉普車里面,印象肯定非常深刻,其上述回憶中的事實應當比較準確。只是年代久遠,具體日期已然模糊。由此判斷,段蘇權作為軍事調處執行部赤峰執行小組中共代表,乘兩架美國運輸機赴赤峰的時間,無疑就是劉春到達赤峰的日期。
第一,據段蘇權回憶,他作為軍調部赤峰執行小組中共代表,乘飛機于1946年1月16日經承德,19日抵赤峰。實際上,1月16日確有軍調部赤峰執行小組美方代表托爾·提羅德上校、中共代表楊建中、國民政府代表谷漢禮三人,乘美國飛機到達承德,任務“系接我方人員(指中共方面——引者注)同去赤峰”,“(當天)下午四時,執行小組三代表與我熱河軍區代表舒參謀長(指熱河省軍區參謀長舒行——引者注)偕同另一代表段司令員,已于17日晨乘汽車前往機場,暨翻譯人員同機飛往赤峰”。顯然,這時段蘇權的身份僅僅是送行、陪伴的熱河省軍區代表之一,軍調部赤峰執行小組的中共代表應為楊建中。再結合《包玉昆日記》1月17日的記載,劉春乘接送段蘇權的飛機一同往赤峰,應不是這趟飛機和這個時間。
第二,據上海《申報》轉載的“合眾社熱河赤峰飛機場二十八日電”:“美海軍飛行人員,本日下午攜帶軍事調處執行總部命令及供應物,與在赤峰勾留已歷十日之三人監導團發生接觸。彼等駕駛之美國運輸機兩架,載有共軍司令段蘇源(譯音)(應是段蘇權——引者注)自熱河共軍大本營承德,飛抵此間飛機場。”《晉察冀日報》也報道,1月31日,軍調部赤峰執行小組中共代表已經易為段蘇權。綜合以上兩則報道,可得出判斷:一是段蘇權于1月28日再次經承德飛往赤峰,并隨后被任命為軍調部赤峰執行小組中共代表;二是1月16日抵達承德的美國飛機應只有一架,任務是接中共人員同去赤峰。1月28日則有“美國運輸機兩架”,“攜帶軍事調處執行總部命令及供應物”,經承德飛赤峰。因此,劉春與包彥“蹭坐”的美國飛機,應是1月28日這兩架運輸機中的一架。
第三,包玉昆于1月26日上午到達赤峰后,曾托中共熱河省熱中專署(駐地在赤峰)專員王新華給承德發電報,代與劉春聯絡。同月30日早晨7時,包玉昆即離開赤峰,前往林東,解決熱河北部中共軍隊與巴林左旗和子章部隊之間的沖突。這說明劉春應在1月27日至29日之間抵達赤峰。否則,包玉昆以“信使”的身份,不可能擅自去調解熱北沖突。
綜合以上三點,劉春、包彥由承德到達赤峰的時間,應是1月28日下午。2月2日,克力更、孔飛、烏蘭、白音倉等人也趕到赤峰。
三、東蒙工作團三請王爺廟
始料不及的是,劉春剛到赤峰,突發重病,不能繼續前進。他只得改變預定計劃,派出烏力吉那仁、包玉昆,先行去王爺廟,或者商請東蒙負責人轉來赤峰,或者待自己病愈后繼續去王爺廟會談。
1946年1月30日,烏力吉那仁、包玉昆二人離開赤峰,向北經“道德營子”(30日)、翁牛特旗烏丹鎮(31日)、胡日哈廟(2月1日)、察罕諾爾(2日),于2月4日抵巴林左旗林東鎮。
抗日戰爭時期,包玉昆曾在熱河北部工作過一段時間,當與巴林左旗知名人士和子章相識。此時作為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信使,包玉昆奉劉春之命,暫時留在林東,設法調解中共熱北武裝與和子章部的矛盾。烏力吉那仁則獨自繼續北行,在2月中旬(15日之前兩三天)抵達王爺廟。包玉昆在2月8日至12日間折返赤峰市。2月13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代表白云航、和子章代表老松不來與中共熱河省委書記胡錫奎會談,包玉昆參加,商定解決熱北沖突的四條辦法。
劉春在赤峰養病數日,未見根本好轉。考慮到不大可能立即親去王爺廟,只好于2月6日再派克力更、包彥,作為自己的代表前往王爺廟,正式邀請東蒙負責人,改為來赤峰商談。克、包二人沿另一條線路,經開魯、通遼、鄭家屯(今吉林省雙遼市),當在2月下旬初到達王爺廟。
之所以說烏力吉那仁和克力更、包彥三人沿著不同路線,先后在2月中旬和下旬初來到王爺廟,是基于以下推斷:一是據烏力吉那仁回憶,2月4日,他與包玉昆在林東鎮分手后獨自前行,一路向北偏東方向,“過了八、九天,我們到了烏蘭浩特”,“在我到烏蘭浩特二、三天后,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召開成立大會(2月15日——引者注),還把我請去當來賓”。這說明烏力吉那仁到王爺廟的時間當在2月中旬,15日之前。另從包玉昆后來由赤峰到王爺廟用時14天來看,烏回憶抵達王爺廟的日期大致不錯。二是據《胡昭衡日記》記載,胡昭衡作為西滿軍區的代表,赴王爺廟的任務之一,就是與西蒙云澤的代表劉春接頭。他于2月17日至王爺廟的第一天,就發現“在這里,劉春的黨的面目非常公開……他帶的人中有幾個中共黨員,等等。這大約是西部(指在張家口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引者注)來的人泄漏的”。當天,烏力吉那仁還親自到胡昭衡的住處談話。這說明,至遲到2月17日,克力更、包彥二人應還沒有到王爺廟。否則,同屬東蒙工作團的成員,克力更又是中共黨員(一說為東蒙工作團副團長)、劉春的正式代表,烏力吉那仁應與克、包同去拜訪胡昭衡。三是據克力更回憶,從鄭家屯到王爺廟,他與包彥曾乘坐中共西滿分局書記李富春派出的汽車,行進速度當快得多。從2月6日離開赤峰,經通遼到鄭家屯,以包玉昆的行進速度推斷,克、包約用時11天;再從鄭家屯乘汽車到王爺廟,從胡昭衡1946年3月同樣的行程來判斷,克、包用時約5天。由此,克力更等抵王爺廟的時間應在2月下旬初。烏力吉那仁的另一則回憶同樣可作佐證。
包玉昆于2月中旬返回赤峰時,距其與烏力吉那仁上次離赤峰已近半月,理論上東蒙方面應有反饋消息。遲遲不見東蒙的回音,2月17日,劉春再派包玉昆帶著自己給東蒙負責人的一封信,繼續往王爺廟相請。包玉昆經翁牛特旗烏丹鎮(18日)、阿貴廟(位于巴林右旗查干諾爾鎮)(20日)、巴林左旗林東鎮(21日)、阿魯科爾沁旗坤都鎮(24日)、突泉縣水泉鎮(28日),于3月2日返抵王爺廟。
據劉春回憶,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派到赤峰開展工作的白云航等人,同樣贊成統一內蒙古自治運動,認為“應盡速進行”。他們曾于2月13日托劉春等代為致電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又派專人乘快馬,再去王爺廟催請。
四、東蒙自治政府領導人終決赴會赤峰
1946年2月中旬,劉春派出的東蒙工作團成員烏力吉那仁到達王爺廟,“只是先通個氣,并不是談判代表”。是劉春前來王爺廟,還是邀請東蒙派人去赤峰,尚屬兩可。相反,克力更既是中共黨員,又是劉春的代表,自然有權與東蒙方面初步會商下一步的行動。
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方面,無論是年齡稍長的領導人,還是青年人,“他們有極高的政治熱情,都是為了振興民族,不畏艱險”。對于東西蒙聯合自治,對于與中共合作,他們持積極的態度。同時,處在復雜的國內外局勢中,2月11日,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派出“東蒙古人民代表團”,準備經北平到南京“請愿”,爭取國民黨承認和支持。克力更來邀請時,“請愿”尚無結果,東蒙就沒有及時響應劉春的邀約。
進入2月下旬,國內主要報紙開始陸續刊登東蒙自治的消息,稱東蒙成立“共和國”,行近獨立。同時,因為蘇聯紅軍遲遲不從東北撤軍、國民政府接收東北受阻,在輿論和國民黨的鼓動下,重慶等全國各大中城市的學生紛紛涌上街頭,示威游行。其中,東蒙自治即是他們抗議的目標之一。在這股日益高漲的反對聲中,2月25日,“東蒙古人民代表團”請愿前途十分渺茫的消息公開見諸報端。這篇報道含沙射影地披露:“蒙代表抵(北)平后……據消息靈通者稱,當局對彼等能于蘇軍駐防區內,召開意志自由之人民大會,且于治安混亂中得以從容自蒙到達長春,表示懷疑。……至于東蒙代表所提自治要求,目前實無法答復與解決,因迄今此等地區蘇軍尚未撤去許我接收也。東蒙代表團原擬至重慶,但能否成行,尚須視北平商談情形而定。”至此,東蒙方面得到國民黨承認的想法基本走入死胡同,與中共進一步合作成為較為現實可行的出路。
再經過與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派出的東蒙工作團成員幾經商談,2月底,東蒙與克力更等人達成初步協議。雙方表示盡早互派代表,舉行談判。3月2日,包玉昆返回王爺廟,還帶來東蒙工作團團長劉春的親筆信。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派人邀請的消息再度得到證實。3月4日,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派出政府主席博彥滿都、秘書長哈豐阿、經濟部長特木爾巴根等人,組成最高規格的代表團,由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東蒙工作團成員克力更、烏力吉那仁、包彥等人陪同,赴赤峰與中共領導下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會商。東蒙代表團乘火車,經白城子(今吉林省白城市),于3月9日到達中共西滿分局駐地鄭家屯,在與西滿分局會談后,3月11日乘汽車離開,經通遼、巴林左旗林東鎮(14日)、巴林右旗林西鎮(15日)、翁牛特旗烏丹鎮(17日),于18日抵達赤峰。
五、東西蒙會談內容、目標與地點的調整
在初進東北、西滿時,無論中共中央東北局、西滿分局領導人,還是各級地方干部,都切實感受到國共爭奪日益激烈,自己在實力上并不占優勢,迫切希望能聯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這支強大的力量。在地緣政治上,整個東蒙地域,恰好位于中共期待建立的東北根據地的西側,與西滿根據地還有許多交錯重合區域。因此,他們基本上按照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的相關論斷,來認識和處理內蒙古民族問題,傾向于贊助和扶持東蒙古自治運動。
與西滿分局的做法不同,冀熱遼分局與東蒙多發生矛盾和沖突。冀熱遼區域位于東北、華北兩大根據地的連接地帶,在山海關失守后,成為中共進出東北的唯一交通要道,勢在必爭。晉察冀中央局及冀熱遼分局早在抗戰勝利后,即迅速搶占張家口、承德、赤峰等地區,實力相對較強。從1945年10月開始,在熱河北部巴林左、右旗與和子章,在赤峰市與白云航等人,都發生意見分歧乃至軍事沖突。延至1946年3月初,麻煩仍然未能得到徹底解決。
到1946年2月下旬,國統區反對東蒙自治的聲調日盛。中共中央在初步獲悉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主張與行動后,感到“在今天整個國內國際形勢下,成立這種自治共和國式的政府仍然是過左的,對蒙古民族、中國人民與蘇聯和外蒙的外交都是不利的,徒然供給反動派一個反蘇反共的借口,造成中國人民中狹隘民族主義者的一種恐懼”。2月24日,中共中央轉而認為,東蒙應當依據政治協商會議剛剛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實行地方自治。即“在遼北省與熱河省省政府下成立自治區,至多要求成立一單獨的省,作為普通地方政府出現”。中央還要求相關地方黨組織,如東北局、西滿分局、冀熱遼分局“以此方針耐心說服他們,改變作法”。換言之,中共這時既要說服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改行國民黨能夠接受的辦法,實行地方自治,以平息國內輿論,又要避免操之過急,把對方推到國民黨陣營;既須處理好雙方在地盤、利益上的棘手問題,又要把對方拉到自己一邊。這就要求中共在處理東蒙問題時必須小心翼翼,拿捏好分寸。
在接到中共中央的上述電報后,第二天晚上,西滿分局就輾轉給剛到王爺廟工作一周的胡昭衡打電話,催促胡趕快回鄭家屯,商量對策。等胡昭衡于3月5日返回鄭家屯后,西滿分局連夜聽取匯報,直至晚上11時多。分局書記李富春這時才發現,東蒙上層政治態度十分復雜,也日漸明朗。其中,部分人親近中共,另一部分人相對游離,但都希冀與中共平等合作;部分人希望靠近國民黨,另一部分人則反感甚至反對國民黨,但都謀求向當政的國民黨找一條出路。考慮到這些狀況,擔心東蒙有可能被國民黨分化利用,倒向國民黨一邊,李富春立即決定派西滿分局常委張平化與胡昭衡一道,速回王爺廟“進一步了解情況與相機談判中央指示的方針”。同時,對于晉察冀中央局、冀熱遼分局、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關于東蒙的“工作方針與進行情況”,西滿分局并不詳細了解,只是隱約覺得雙方政策有所不同。加上缺少熟悉蒙古民族事務的干部,感到一時無從下手,實在不知道與即將到來的東蒙代表團怎樣談、談什么。最好的辦法是派汽車把東蒙代表團博彥滿都等人送去赤峰,讓他們直接與冀熱遼分局、烏蘭夫等人談判,解決東蒙自治的原則性問題,自己不再另行先與東蒙會商。
冀熱遼分局與西滿分局對東蒙的政策出現分歧,肯定不利于東蒙問題的解決。中共中央覺察后,立即建議冀熱遼分局和西滿分局應各派一人到赤峰與烏蘭夫商談,或請烏蘭夫到鄭家屯協調兩方的東蒙政策。東北局則主張折中辦理,一方面告訴西滿分局可以等東蒙與烏蘭夫談判回來時,再與東蒙商量具體問題;另一方面提議西滿分局最好選派了解東蒙情況的干部,與東蒙代表團同往赤峰,征求烏蘭夫的意見。
3月10日,東蒙代表團博彥滿都等人路過鄭家屯。西滿分局在與對方接觸后,發現雙方政治主張、具體需求差距太大,不好談攏,最終決定堅持原議,不派任何代表同去赤峰,先讓東蒙與烏蘭夫直接談判。等“大政方針”確定下來,東蒙代表團返回經過鄭家屯時,自己再與之商量具體措施。顯然,面對2月下旬以來國內局勢的急劇變動,西滿、熱河的中共干部猝不及防,難以應對。他們過去長期習慣于軍事斗爭、階級斗爭,對民族問題普遍缺乏實踐經驗;即便是過去掌握的民族主張,至少當時也不再適用。更重要的是,東蒙問題既涉及民族理論,又關乎現實謀劃,牽一發而動全身,非通盤考慮不可。相較于西滿,冀熱遼分局面臨著更棘手、更急待解決的麻煩,因而在1946年3月初就向上級乃至中央反映,堅決要求請烏蘭夫親臨熱河,以便確定統一的東蒙政策,協調、理順與東蒙的關系。現在,西滿分局選擇“退出”,冀熱遼分局必須與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主席烏蘭夫一道,首先解決東蒙自治的限界,再協調東西蒙古自治運動問題。
至于會談地點緣何選在承德,而非赤峰,除上述會談對象、內容、任務和目標調整等因素外,應當還與劉春的建議有關。劉春止步在赤峰,實因生病,迫不得已暫時滯留。到3月初,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代表團已經啟程,東蒙工作團的任務便告完成。下一步,就是在赤峰還是在承德舉行烏蘭夫與東蒙的會談。劉春考慮到在冀熱遼分局駐地承德開會,既可以表明中共對這次會談非常重視,又易于冀熱遼分局直接領導,免得電訊往返,便在3月6日首向熱河省委和冀熱遼分局建議,把會談地點改在承德。東蒙代表團在3月18日抵達赤峰后,劉春再度向冀熱遼分局和烏蘭夫提議,自己帶東蒙工作團其余成員,與東蒙代表團一起轉去承德,烏蘭夫也到那里,舉行談判。劉春之所以堅持要改去承德會談,可能另有一層不便明言的道理。即在清代,承德屬于北京之外的另一個政治中心,主要擔負清廷與蒙古、西藏等邊疆地區親密互動的功能,又不似赤峰那樣地處蒙區。最終,晉察冀中央局同意把會談地點定為承德。
3月21日,東蒙代表團與劉春等人踏上去往承德的路途。他們基本上沿著今(北)京漠(河)公路,經老府(今赤峰市松山區老府鎮)、海蘇灣子(今圍場縣楊家灣鄉海蘇灣村)(22日)、圍場縣(23日)、圍場縣唐三營鎮(24日)、隆化縣(25日),于26日到達承德。3月29日,烏蘭夫率領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代表團來到承德。第二天,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代表七人(烏蘭夫、劉春、克力更、包彥、田戶、烏力吉那仁、慶格勒圖)與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代表七人(博彥滿都、哈豐阿、特木爾巴根、包玉昆、白云航、義達嘎蘇隆、哈薩巴特爾)立即開始個別會談。至4月3日,經過五次準備會議,兩方圍繞現階段內蒙古自治運動的方向、路線、政策等各項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并在當天正式舉行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是為“四三會議”。根據會議通過的九項原則性議案,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準備解散,改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東蒙總分會。
六、結語
蒙古分東、西蒙,是歷史上蒙古部落內部互相爭斗的產物。民國以降,外蒙古在俄國指使下“獨立”,東蒙古遂縮小為內札薩克蒙古東部區域,概指清代漠南蒙古的哲里木盟、昭烏達盟、卓索圖盟。西蒙則包括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以及后來“擴編”進來的察哈爾部等。1928年國民黨統一全國后,東蒙大體分屬于東北三省和熱河省,而西蒙則劃為察哈爾省和綏遠省。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先后侵占該地區,其建立的偽政權,也是分為東、西兩部分,即東部屬于偽“滿洲國”的興安省或興安總省,西部的部分地區轄于偽蒙疆自治政府。抗日戰爭勝利后內蒙古地區的民族自治運動,東、西蒙同樣獨自展開,互不通氣。恰恰是東蒙古自治運動領導人試與西蒙溝通,派去的“信使”包玉昆途經張家口,偶遇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又恰恰是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派出以劉春為首的東蒙工作團,千里迢迢到王爺廟與東蒙聯絡,雙方才在承德四三會議上,在民族自治運動的旗幟下,初步實現形式上的聯合和統一。東西長達2000余公里的內蒙古自治區域的建立,終于達成“而今邁步從頭越”。
[李國芳,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