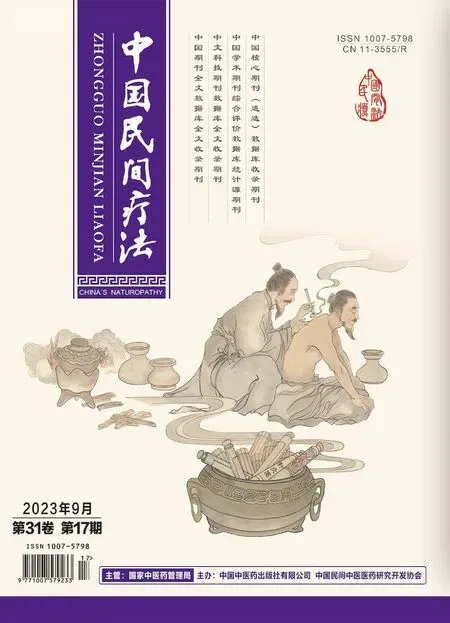董少龍從氣血論治不寐合并月經病經驗※
呂 璽,劉小瑤,董少龍,竇維華
(1.廣西中醫藥大學,廣西 南寧 530023;2.廣西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廣西 南寧 530023)
不寐的主要特征是不能獲得正常睡眠,一般認為生理性睡眠每晚少于5~6 h,每周至少發生3次,并持續1個月以上的稱為不寐[1]。有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成年人失眠率已達到38.2%[2]。不寐又稱“失眠”“目不瞑”,其名源自《難經》。失眠并非單獨發生,常伴隨焦慮、抑郁、精神萎靡等癥狀,易與女子月經病同發,給患者的工作和生活帶來煩惱。
董少龍,首批桂派中醫大師,第4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廣西中醫藥大學教授。董教授臨證40余年,教學嚴格,臨床嚴謹,對于內科疾病的診治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尤以氣血論治失眠合并月經病方面獨有心得。筆者跟隨董教授出診,總結董教授治療不寐合并月經病心得。本文介紹董教授治療不寐合并月經病的臨證體會,闡述本病病機、治療遣方原則、用藥特色等,以供臨床參考。
1 從氣血論述不寐和月經病的關系
董教授在臨床中發現,女子失眠患者較男子多,且問診時多與月經病同時發生,以女子絕經期前后較為多見,亦可見崩漏、痛經等情況。董教授認為不寐的總病機為“陽不入陰,心神失養”,陰陽以氣血形式反映于人體,故臨床上多合并女子月經問題。徐云霞主任認為,月經周期紊亂是由人體氣血陰陽失衡、陰陽不相順接所導致[3]。不寐與氣血的關系最早見于《難經》,《難經·四十六難》曰:“老人臥而不寐……何也……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榮衛之道澀,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4]《黃帝內經》中以“陽不入陰”為不寐的總病機,后世醫家亦多有發揮。董教授認為,《黃帝內經》所言之陰陽,指的是營陰與衛陽,對于人體而言,則是指衛氣和營血;結合《難經》所述,溯本求源,回歸經典,提出不寐的總病機為“陽不入陰,心神失養”,氣血失常是引起不寐的重要原因。婦人以血為本,經、帶、胎、產均易耗損氣血,氣血與女子的關系見于《靈樞》,《靈樞·五音五味》曰:“婦人之生,有余于氣,不足于血。”故氣血失常可同時引起不寐和月經病,治療以氣血理論為綱領,在調理氣血的同時加入安神藥物,對于兩者合病的臨床治療具有重要意義。本病臨床多見虛證、實證、虛實夾雜3種證型,氣虛血瘀證較為常見。
2 辨證論治
2.1 虛證——氣血兩虛、心神失養證 董教授認為,體虛之人易患不寐病證,尤以氣血虛弱為主,臨床常見女子因氣血兩虛導致停經與不寐并見,常有經量減少、周身乏力、心神不安等癥。明·吳崑云:“人之身,氣血而已。氣者百骸之父,血者百骸之母。”[5]氣血虛則不能濡養心神,致使心神失養,發為不寐。中醫認為,心為君主之官,主神明,神安則夜寐自安,心神不安則不得眠。如《景岳全書》所言:“蓋寐本乎陰,神其主也,神安則寐,神不安則不寐。”[6]故心神之安,不離營血之滋養與心氣之溫煦,以補益氣血、寧心安神為治療原則,臨床多選用八珍湯加減治療。八珍湯出自《瑞竹堂經驗方》,由健脾益氣之四君子湯和養血活血之四物湯組成,為益氣養血之代表方。董教授臨證時常易熟地黃為生地黃,易人參為太子參,其認為:廣西多濕熱,熟地黃用之易滋膩,會阻礙脾胃;生地黃偏涼,補血而清熱;太子參微苦,補氣而不生熱。在不影響治療方向的同時,要因地用藥,考慮氣候差異,治療方能顯效。組方時常加用酸棗仁和首烏藤,兩者皆有養血安神之效,可寧心定神。
2.2 實證——肝郁氣滯、膽郁痰擾證 董教授認為,氣機不暢,痰濕阻滯,常發生不寐,且兩者亦因亦果。女子絕經期前常見躁郁、煩熱等癥,常因氣郁痰阻生熱所致。《壽世保元·卷五·不寐》言:“有痰在膽經……亦令不寐。”肝氣郁而不暢,心情抑郁,情緒低落,氣郁則痰濕聚集于膽,膽郁痰擾,心神不寧,故見失眠。氣滯則濕生,致身體困重,納差惡心;痰濕為寒邪,使膽腑寒涼,又因肝火熱盛,痰濕夾熱,多見心煩口苦。董教授臨床中多用溫膽湯治療該證,溫膽湯出自《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具有和胃利膽、理氣化痰之功,主治心膽虛怯或夢寐不祥,其在《諸病源候論》《中藏經》中亦有記載,為祛痰理氣之名方。《外臺秘要》論溫膽湯以半夏為君藥,燥濕化痰;竹茹、枳實為臣藥,清熱行氣消痰;陳皮理氣燥濕,為佐藥;生姜、甘草調和諸藥,兼和脾胃,為使藥。臨證見患者煩熱嚴重時,董教授常用黃連溫膽湯,在理氣的同時可清利肝膽濕熱,黃連亦可清心火,或加梔子豉湯清心泄熱,臨床效果頗佳;加用行氣解郁之郁金、合歡皮,在疏肝理氣的同時有安眠之效。韓麗華常用龍膽瀉肝湯治療失眠肝郁化火證患者,此類患者常伴有急躁易怒癥狀[7]。
2.3 虛實夾雜證——氣虛血瘀、心脾兩虛證 虛實夾雜證臨床較為多見,標為血瘀之象,卻以氣血虛弱為本。現代人思慮多,易耗傷心脾之氣血,心血耗傷則見神志不安、眠差易驚。氣能攝血,脾能統血,脾氣耗傷則血逸脈外,發為瘀血,易引發崩漏或月經先后不定期等月經病。董教授臨床多用自擬活血安神方為主方:桃仁15 g,紅花15 g,生地黃10 g,白芍12 g,川芎20 g,太子參10 g,當歸尾20 g,炙甘草6 g,茯神20 g,遠志20 g,酸棗仁20 g,木香15 g,首烏藤15 g。此方由桃紅四物湯合歸脾湯加減而成。清·蒲輔周認為“崩血、漏血過多,有瘀滯者,宜四物湯加香附、桃仁、紅花行之”。《醫宗金鑒·婦科心法要訣》中對四物湯加用桃仁、紅花亦有詳細記載,使其成為后世治療婦人病的常用方。《類證治裁·不寐》曰:“蓋不寐多由思慮勞神……宜歸脾湯。”[8]歸脾湯首載于《濟生方》,治“思慮過度,勞傷心脾”之證。方中當歸、川芎用量達到20 g,以增強其行氣活血的功效;再加養血安神之酸棗仁和首烏藤,組成益氣活血、健脾養心的活血安神方。董教授臨床多用此方治療不寐兼有崩漏患者,效如桴鼓。
3 用藥特色
3.1 注重藥對 藥對是介于單味藥和方劑之間的特殊中藥配伍形式,具有同類相須、合用增效的特點,尤其在治療不寐時,與辨證相合的藥對往往起到很好的效果。董教授常用藥對如下:①靈芝-首烏藤。靈芝味甘、性平,歸肺、心、脾經,能補氣安神;首烏藤味甘、性平,可養血安神,多用于無明顯寒熱、氣血俱虛之婦人,亦用于月經病之收尾階段。②磁石-龍骨。龍骨味甘澀,可鎮心安神;磁石味辛咸,可安神定驚。兩者合用重鎮安神,用于治療心悸易驚、惕惕不安之不寐,患者常有情志問題,故常合用郁金、合歡皮。③黃連-肉桂。既為藥對,亦為成方。黃連苦寒,可瀉上焦心火;肉桂溫補下焦,使腎水得陽氣可化氣升揚,兩者組合寓“交泰”之意,補陽育陰,心腎得交,故曰交泰丸[9]。患者常見夜間煩熱,舌脈卻呈虛象,故上熱下寒證多用此藥對。
3.2 擅用首烏藤 董教授治療失眠的常用藥為首烏藤,認為其對于女性失眠兼有月經問題有良好的效果,且藥性溫和,平人亦可用。首烏藤始載于《圖經本草》,根部名為何首烏,具有益血黑發、補精填髓的作用;其藤莖為首烏藤,又名夜交藤,性味甘平,善益血安神,治療失眠多夢屬陰血虛者[10]。因女子月經病多與氣血受損有關,合并失眠日久者亦多耗傷陰血,在用首烏藤養陰養血的同時,發揮安神之效。董教授認為,首烏藤與靈芝或酸棗仁合用時,養心安眠的效果倍增,臨床應用多有成效。
4 驗案舉隅
患者,女,44歲,因“失眠伴月經淋漓不盡5個月,加重1個月”于2021年11月16日就診。現病史:患者自訴5個月前因兒子高考出現情緒焦慮、心悸易驚、入睡困難、月經淋漓不盡等癥狀。曾于外院就診,查下腹部B超顯示:子宮內膜息肉。診斷:失眠;焦慮抑郁狀態;子宮內膜息肉。服用阿普唑侖片2個月,服藥時睡眠改善。近1個月失眠加重,恐對西藥產生依賴,遂來我院就診,尋求中醫治療。刻下癥:不易入睡,每晚入睡約3.5 h,夢多,偶有煩熱,伴情志緊張,易躁易怒,動則乏力,納欠佳,月經淋漓不盡,色暗有血塊,大便溏,小便可,舌暗,邊有齒痕,苔薄白,脈細澀。西醫診斷:失眠;焦慮抑郁狀態;子宮內膜息肉。中醫診斷:不寐合并崩漏,氣虛血瘀證。方劑:歸脾湯合桃紅四物湯加減。用藥:首烏藤15 g,黨參片25 g,桃仁12 g,熟地黃12 g,炙甘草5 g,當歸12 g,茯神15 g,磁石20 g(先煎),酸棗仁12 g,紅花10 g,黃芪15 g,遠志10 g,白芍15 g,川芎10 g,木香12 g,7劑,每日1劑,水煎服。
二診:患者訴月經已停,睡眠稍有改善,但乏力同前,夜間多煩熱,舌紅,苔薄黃,脈細稍數。中醫診斷:不寐病,血虛生熱證。治以益氣養血、養心清熱。方劑:八珍湯合黃連阿膠湯加減。用藥:首烏藤15 g,白術15 g,黨參片25 g,熟地黃12 g,炙甘草5 g,茯苓15 g,酸棗仁12 g,黃連片3 g,黃芩片6 g,阿膠9 g(烊化),白芍15 g,川芎10 g,15劑,煎服法同前。
三診:患者睡眠基本好轉,每晚入睡6 h,但偶有郁悶不樂,情緒急躁,舌淡紅,脈弦細。診斷為郁證-肝氣郁滯證。方劑:四逆散合八珍湯加減。用藥:柴胡15 g,茯苓15 g,白芍15 g,川芎10 g,枳實20 g,首烏藤15 g,白術15 g,黨參片25 g,熟地黃12 g,炙甘草5 g,15劑,煎服法同前。1個月后隨訪,患者睡眠情況較好,每晚入睡約6.5 h,經期持續6 d,量、質均正常,平素情緒煩躁癥狀消失。
按語:患者因其子高考,思慮過度,耗傷心脾,心氣耗則夜寐不安;脾傷則運化無力,耗血傷營,最終發為不寐和崩漏,同時肝氣郁滯,氣行不暢,兼有情緒抑郁或煩躁等表現。初診時患者血瘀之象明顯,失眠嚴重,伴有心神不安之象,故以攻為主,以化瘀活血、養血安神為治則,先用桃紅四物湯重活血、輕養血,防治破血太過,使瘀血得化,離經之血得消。二診時,患者瘀血雖消,但新血未生,出現血虛發熱、熱擾心神之證,董教授用八珍湯益氣血治其本、黃連阿膠湯除煩熱治其標,患者病證亦消大半。三診時,董教授審視用方,益氣有余但理氣不足,患者出現氣郁之象,故用四逆散之柴胡、枳實理氣疏肝,續用八珍湯益氣養血,最終患者之不寐、崩漏、郁證均有較大改善。此病案治療過程中出現3次變化,分別為氣虛血瘀、血虛發熱、肝郁氣滯,董教授臨證用方思路清晰,以氣血為主線,先攻后補,寓補于攻,加入首烏藤、酸棗仁等養血安神藥,則氣血得復,病愈癥消。遺憾之處在于,隨訪時患者未復查B超,不知其子宮內膜息肉是否有變化。
5 小結
董教授認為不寐的總病機為“陽不入陰,心神失養”,治療以虛實為本,虛則補益氣血、健脾養心,多用八珍湯和歸脾湯,實則行氣化瘀,多用逍遙散與桃紅四物湯。新病多發作為實證,且廣西地區地處嶺南,氣候濕熱,氣郁多夾痰濕,伴有情志不暢,故常用疏肝化痰之法。久病多虛多瘀,在補益氣血的同時加強理氣活血,加用不同的安神藥對,使氣血虧虛之病機得到改善。綜上所述,董教授治療不寐合并月經病注重兼癥,對整體病機進行分析,辨證準確,以調整氣血、養心安神為總治則,病證相應,方藥精確,療效彰顯。